胡展奋:“咖啡阿三”
繁体上海当年有条“咖啡弄”。
始于南京西路的江宁路一路向北,遇到长寿路一个熊抱便造就了个繁华的十字路口,“五福里”三十余排石库门正好位于江宁路与长寿路以及昌化路的转弯角子,当年被叫作“咖啡弄”。 作为石库门,它算是较新的,都是“双亭子间”,客堂的后面, 一左一右还有两个采光拔风的小天井。老辈爷叔讲,因为“德胜咖啡行”(上海咖啡厂的前身)的老板张宝存曾住过这里,长期地免费送邻居咖啡,久而久之,尽管他后来搬走了,喝咖啡(上海人叫 “吃咖啡”)的风气却弥漫了开来,大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沪西一带的教师、牧师、小公务员、银行职员、账房、跑街、医生、律师都入住了“五福里”,这些人小资情调足,和原住民好咖啡的风气一拍即合,“咖啡弄”便在沪西出了名。
弄堂里的早餐“四大金刚”不太热乎,居民晨起大都一杯咖啡,佐以切片面包,条件好点的吃蛋糕、华夫,为此,西边弄口还开了一家专售西点的“甜香公司”,生意极好。
尽管这样,如果没有“咖啡阿三”,咖啡弄的咖啡就没这么香了。
他住我家隔壁,小时候我常跟着他,从老虎天窗爬出去,坐在屋顶的大瓦片上,望野眼。首先就是左邻右舍的“万国旗”,晒台与弄堂,凡能拉线的都拉了,凡能撑杆的都撑了,然后晾满了五颜六色的尿布、毛衣、衬衫、内衣……从衣物的质地可以直接判断邻居的经济状态。再就是年货,鳗鲞、风鸡、酱油肉。咖啡阿三的真名就不说了。那个“十年”之前,他还是个无业的“社会青年”,黑圆眼镜,长条脸,成天捧着一杯咖啡——听大人说,他家是虹口搬来的,爷爷就是开咖啡店的,后来关忒了,就搬来了咖啡弄,用“条子”顶下了客堂与前楼。阿三的中学同学多,三天两头上门,都挟着一叠叠黑黑的胶木唱片而来。

我边浪看看,咖啡阿三招待同学,其实是看人头的。对付“草根”的同学,他就用上咖的“鹅牌”方块咖啡招待,“给他们好咖啡,是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他常对我冷冷地撇撇嘴;“克勒”一点的朋友,他会动用3.25元1听的铁罐咖啡(这种咖啡吃完后罐子是不扔的,要放在玻璃橱里炫耀),小壶一煮,纱布滤一滤后悠悠地细品,品它的酸度,品它的香型;只有最好的而且也懂咖啡的同学,他才会提前一天取出密封的生咖啡豆,亲自烘烤,老辈人都知道,这是一门很高级的手艺,一般买来业经烘烤的咖啡豆,自己研磨,已经够“克勒”,但只有真正的老克勒才敢买来生咖啡豆,自己烘烤。牙买加的蓝山咖啡只能“中度”烘烤,出“轻油”,而墨西哥咖啡则必须深度烘烤,出“重油”,才能尽显风味。他的烘烤箱也传自爷爷,很老式的那种,用撑脚固定后温度可达200多度,因此常常要小孩走开。他用一个手柄来操纵机器内部的两个垂直金属片,它们可以在烘烤时旋转咖啡豆,那过程不但发出满屋的奇香而且高温将导致咖啡豆“出油”,出“轻油”还是出“重油”都靠手控的。再比如烘烤十多分钟后,咖啡豆就爆裂,爆米花一样“乒乒乓乓”地欢蹦,这时咖啡阿三就紧张地观察咖啡豆的颜色,针对不同的咖啡,他必须适时地取出咖啡豆,放到窗外竹匾里,摊摊开冷却。
整个过程,无以名状的咖啡香弥漫全弄堂,香得你饥肠辘辘,香得你抓耳挠腮,坐立不安。与板烟斗丝一样,闻香的,才是真正的享受。
等同学来了,他就招呼同学一起研磨,粗磨、中磨、细磨,刚烘烤的咖啡豆并不适合马上研磨饮用,一般来说,咖啡的最佳享用期为隔天烘烤,当场研磨,此时的咖啡最“鲜滑”。然而咖啡的调制方法又惊艳无穷,阿三最最惊为天人的绝招是:邻居的围观下蒙住他的双眼,给他一根筷子,点尝一下,就能分清哪一杯是意式浓缩、法式欧蕾、美式黑咖,哪一杯是港式鸳鸯、爱尔兰咖啡酒、希腊法拉沛……
那是咖啡弄特有的乐趣。不过这一切都突然中断了。1966年的那场巨变突然来临,弄堂里的牧师、旧公务员、旧职员、账房、跑街、旧律师,大都落魄了,每个月只拿12元生活费。咖啡阿三的家也不例外,烘烤箱与研磨机突然被收缴,而且“定息”取消,只拿生活费, 一下子沦为弄堂贫民。
弄堂里的咖啡香于是突然消失。
要知道那时的普通收入是“月工资36元”,“阿三”他们的收入一下子跌进了“月入12元”,7分一包的鹅牌方块咖啡也吃不起了。
不服,可以算一算:7分一天, 一个月2元,设若每个家庭3人喝咖啡,还加糖,一个家庭一个月就是10元以上,当然吃勿消。
鹅牌方块咖啡,听说是上海咖啡厂的下脚料制作的,以前咖啡弄的人不碰,现在当宝了。7分钱毕竟可以买一副大饼油条,酱油虾皮汤泡泡,就是一顿主食,谁敢不当回事。
问题是,咖啡不饶人。它的成瘾性众所周知。
自从喝不起咖啡,咖啡弄很多人就无精打采,饭后都焦躁不安。
因为是“咖啡世家”,邻居都把希望押在阿三身上,盼望他像“糖精”“代盐”一样研发出一种“代咖”聊补无咖之炊。
一天,阿三把我叫去前楼,品尝他发明的“代咖”。先不说穿,让我把一大杯褐色的饮料喝下。还真有点像,甚至非常像。他得意地说,这叫决明子,中药里挑出来的,再放了一点板蓝根粉,怎么样?还别说,经他精心煽炒浓缩以后,那味道苦隐隐有点像清咖。另一次他要我喝另一杯褐色的液体,那是他加入决明子混炒的大麦茶,熬得非常浓稠。加点炼乳,差一点像奶咖。
这一切他像贼一样偷着试。几位邻居尝了以后,都说 “像”,最想咖啡的时候,猛呷几口是可以忽悠的,但多喝了不行,毕竟是大麦茶、决明子,都不提神,不过瘾。而“咖啡”不提神,等于打牌没王炸。“代咖”研发失败了。
他有个同学的父亲是上海咖啡厂管仓库的,以前不太在阿三的眼里,现在阿三开始动他的脑筋了。
没几天,他带回来一口袋咖啡豆,左眼圈却黑得像熊猫,说是不小心撞的。要我们几个孩子跟他上楼分拣一下,可这都是什么垃圾货呀,很多咖啡豆是畸形的、变色的、变酸的、过度发酵的,大量的泥沙、草屑、叶梗与豆豆混在一起,先用粗筛,继而细筛,再人工剔除各种原因混入的咖啡外皮、果肉、内果皮、银皮……
整整四五个小时,累得我等差点脱水。分拣后用锅炒,毕竟是咖啡店小开,从小耳濡目染,阿三以极其娴熟的手法,手持木铲飞快地翻炒。
但最难的是研磨了。研磨机早没了。阿三苦想了多天,忽然打起了我们家那只每年磨“水磨粉”的小石磨主意,试着干磨了一下,虽然效果不太好,再也分不清什么粗磨、中磨、细磨,但毕竟磨碎了,磨细了。磨,也是硬道理。
尽管豆豆是“畸形的、变色的、变酸的、过度发酵”的,但尝过的人都说,比鹅牌方块咖啡不知要好多少。
那个特殊的年代,咖啡居然复活了!一时间,邻居间都悄悄来蹭咖啡,偷偷地,倒一杯就走,阿三家本来被斗得抬不起头,那几天忽然被笑脸包围了,咖啡弄又有咖啡香了。
只有我对阿三的“熊猫眼”心存疑虑。这咖啡豆虽然脏乱不堪,但毕竟还是咖啡豆,哪来的呢?
天气渐渐热了,阿三的“熊猫眼”渐渐褪色,但白天常常不见踪影。
那天我去西康路外婆家, 一时心血来潮,去西康路码头张张,陡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眼帘——阿三!干什么?扛大包吗?
我叫了他一声。发现是我,他也有点慌张,赶紧解释。原来,正是咖啡厂管仓库的同学他爹,告诉了他一个秘密,咖啡厂的原料都是在西康路码头装卸的,那时的生咖啡豆主要是云南咖啡豆,也有进口的,装在黄麻或波罗麻织成的粗纤维袋子里,驳运与装卸的作风则是一贯地野蛮粗糙,码头上到处是洒落的咖啡豆,如何“揩油”就看造化啦。
阿三闻讯混进了西康路码头,开头几次借“扫垃圾”收罗咖啡豆时每每被码头工人痛扁,不过说他“偷”也勉强了一点,那豆沙相混的严重程度,不是垃圾还能是什么呢?所以当阿三坚持再去时,师傅们对其更多的已是怜悯,阿三也很“识相”,抽空也帮忙扛几个大包,收工时的“垃圾”也就都归他了。
三层阁里,类似的“垃圾”已经五六袋了,看他的意思似乎不能排除继续囤积。“就是对不起你们了!”他的长条脸一直红到脖子,拍拍我,满面的羞惭与无奈。作为咖啡弄曾经的“课代表”,喝咖啡,在他的口气里一直是一种“克勒”的腔调与“爷叔”的修养,谁会想到是如此瘪三般的沦落与不堪呢……
我们后来搬离了五福里,和阿三渐渐失去了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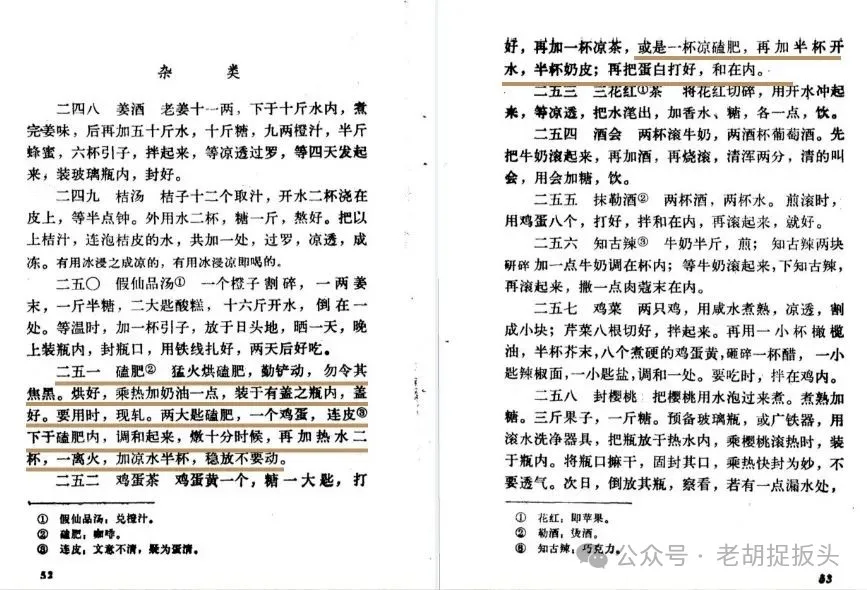
咖啡弄也于20世纪90年代被拆迁。但它在人心里的印记却难以磨灭。五十年多前的上海,只有它才菌类般地遇冬不死,并稍有阳光就绽出了绿意。
来源:老胡捉板头
本文初摘录于:2024-07-07,最后校对或编辑于:2024-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