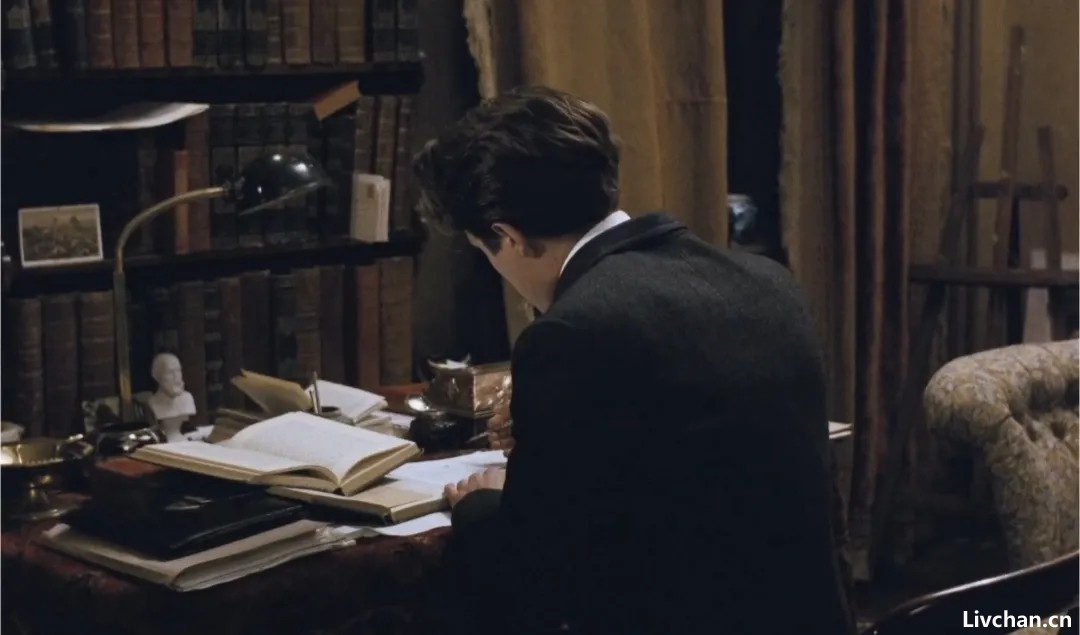细说诗词里的音乐性:节奏
繁体中国古人的诗词,是不用分行书写的,其作品集也绝无分行排印。因为有固定的格律:一是诗句字数有规定——四言诗四字,五言诗五字,七言诗七字,词曲则按牌谱填字;二是对句押韵,声音上行间分明。
这样的诗,不仅不用分行,甚至可以不用标点符号断句。而新诗抛弃格律自由化之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分行书写、分行印刷,才能有效地表现出诗句的存在与作用。
为什么要表现诗句呢?这就说到了诗与散文两种文体的根本区别:散文只求以字达意,诗词则还要以声音表现感情。
声音表现感情的重要方面,就是诗的强烈节奏性。而要实现这种节奏,必有两个条件:
第一,关于诗句(或诗行)长短的限度。
首先,诗句不能少于两个节拍,而每个节拍不少于两个音节,或虽不足两个音节,也必须用空拍补足。这在韵律学上被概括为对偶(或二分)原则,即节拍(音步)必由两个音(重轻、长短或同音分立)对比构成;而每个诗句至少必有两个节拍(音步)。之所以这样,道理很简单:单音不成乐,一个音或一个音的无论多长的延续,都不构成节奏,节奏只有至少两个声音元素的对比或重复,才能产生。
此一由自然形成的对偶原则,我们古人早就明白。刘勰在《文心雕龙·俪辞第三十五》中就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中国传统诗词曲赋的创作实践,也证明对偶或叫对称重复,是构造节奏的主要手段。比如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诗歌,绝大部分都是对称的四言句,即每句两拍,每拍两个音节(字)。音节若不够时,宁可以虚字填足。
当然,现存零星资料似表明,上古也曾有过单字成句,或两字成句的个别诗例,似乎不符合节拍(音步)中音节成双、诗句中节拍成双的要求。但一是此类诗例很少;二是按语言学家猜测,很可能远古华夏语言曾是多音节语言,其单个字读为两个音节,仍符合音节对偶的节拍要求。
事实上,中国诗体发展到词曲后,又出现了单字句,但只占很小比例,且在吟诵节奏上,在单字后必须加空拍,使其在节奏上满足音节成双、节拍成双的要求。
另一方面,诗句也不能太长。
所谓节奏,必须有“节”,“节”就包括节制之意。因为“节”的长度恰当,才能让听者对节奏产生明显感知并记住。从中国传统诗词曲赋作品实际看,最长的诗句没有超过十二字的。
第二,关于诗句的规律性。
节奏来自对比重复,包括诗句内部音节组(节拍)的重复,以及诗句之间节拍组合的重复、句间韵的对比与重复。
第一和第二是相关的。诗句如果过长,重复就很难实现,或即使实现,在声音上也不易记忆,丧失节奏的可感受性。
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我是文学家》里,郭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解释诗与赋的区别:诗每行几个字都是几个字,赋则是上一行四万五千字,下一行两个字!
相声虽是夸张,却准确描述了诗与散文——所谓赋就是韵体散文——体裁的本质区别,既说明了字数限制的区别,也说明了句间重复与否的区别。
中国传统诗词的诗句字数以五七字(言)居多,但随着音乐入诗和戏曲口语化,一方面诗句的长度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节奏类型由原来的简单重复为主,增加了对比变化。我们逐一举例如下:
一言句:
缁衣之宜兮,
敝,(1)
予又改为兮。
——《诗 · 郑风· 缁衣》
山,(1)
快马加鞭未下鞍。
——毛泽东《十六字令 · 山》
前面已说过,组成节拍必须满足至少两个音节,即韵律学上的对偶或二分原则,所以将只有一个音节的音步称为“残音步”。同时,韵律学也要求一个诗句最少必须由两拍构成,即诗句(行)也必须满足二分原则。于是,在吟诵时,为保证拍节完整,人们总是在一言后停顿半拍,即增加一个音节的时值,尔后再空一拍,让一言诗行也能不仅成拍,而且足句。
比如《十六字令》中的“山”字,要按下面节奏吟诵:
山0—0 0
∨ ∨
即在占半拍时值的“山”字后边加半个空拍,让山构成一拍时值;然后再空一拍(两个半拍),让整个诗句满足必须至少两拍才能成句的要求。
二言句:
予美亡此。
谁与?( 2)
独处!( 2)
——《诗 · 唐风 · 葛生》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2)
——(宋)苏轼《定风波 · 莫听穿林打叶声》
注意,只能凑足一拍的两个音节(二言),在节奏上不能足句,即不能成为一个完整诗行,所以在吟诵时,也要求在其后增加一个空拍:
谁怕? 0 0
∨ ∨
三言句:
江有汜,(3)
之子归,(3)
不我以!(3)
——《诗 · 召南 · 江有汜》
莫忘故人憔悴,
老江边。(3)
——(宋)苏轼《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
三言句中前两个字构成一拍,余下第三个字后面必须补半个空拍,才能构成一拍,并与前一拍成句。其节奏即:
江有/汜 0 ( 2—2)
∨ ∨
四言句:
关关/雎鸠,(2—2)
在河/之洲。(2—2)
——《诗·周南·关雎》
蓦然/回首,(2—2)
那人/却在,(2—2)
灯火阑珊处。
——(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五言句:
五言句有三种节奏型。
一是2—3 节奏,即二言拍在前,三言拍在后,这是五言古诗和五言律诗的诗句主要节奏型,如:
溯游从之,
宛在/水中央。(2—3)
——《诗 · 秦风·蒹葭》
明月/出天山 ( 2—3)
苍茫/云海间( 2—3)
——(唐)李白《关山月》
其中句未的三言拍在吟诵时又有两种节奏,一种是大多数情况,即为满足句尾稳定的节拍需要,常将三言拍分解为一个二言拍加一个单言拍,而单言为成一拍,则在单言后加半个空拍:
床前/明月/光 0 (2—2—2)
∨ ∨ ∨
但也有时为了加快节奏,尤其是在四句的五绝或七绝中的第三句上,句尾的三言往往连读成一拍,而不切割为两拍,如:
床前/明月/光 0 ( 2—2—2)
∨ ∨ ∨
疑是/地上/霜 0 (2—2—2)
∨ ∨ ∨
举头/望明月 (2—3)
∨ ∨
低头/思故/乡0 (2—2—2)
∨ ∨ ∨
其中第三句是所谓“起、承、转、合”的“转折句”,类似音乐中的高潮乐句,因此要求快速向最后的“合题句”(音乐中叫“主题再现”或“解决”)推进,需要声音上的不稳定,所以常会将“望明月”三字快速连续吟出,三个字要平分一拍的时值,当然不可能对称、平衡、稳定了。
五言句第二种节奏型,是三言拍在前,二言拍在后的 3—2句式:
一之日/觱发,(3—2)
二之日/栗烈。(3—2)
——《诗·豳风·七月》
左壁厢/唱的,(3—2)
右壁厢/舞的。(3—2)
——(元)张养浩《胡十八·客可人》
第三种,句首的三言拍,是可以按照语义分割为1—2结构的,使整句成为1—2—2节奏,比如:
或/息偃/在床,(1—2—2)
或/不已/于行。(1—2—2)
——《诗·小雅·北山》
这在词曲中尤多:
念/累累/枯冢,(1—2—2)
茫茫梦境。
——(宋)陆游《沁园春 · 孤鹤归飞》
其中句首的单言,在吟诵节奏上,也必须或拖长为一拍时值,或附加半拍空拍时值。
六言句:
2-2-2式:
谓尔/迁于/王都,(2—2—2)
曰予/未有/室家。(2—2—2)
——《诗·小雅·雨无正》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2—2—2)
——(宋)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还有3—3式:
草间路/六七里,(3—3)
溪上梅/三四花。(3—3)
——(宋)吴浚《六言》
我到此/闲登眺(3—3)
日远天高。
——(元)张弘范《中吕 · 满庭芳》
注意,3—3式中两个连续三言拍,都应三音节连读成一拍,因两拍已成对称,可以足句了。
七言句:
第一种,2—2—3式,七古、七绝、七律等七言诗均为此式。尽人皆知,不必举例。句尾三言拍的吟诵节奏同五言句。由于句首比五言句多了一个二言拍,使七言与五言节奏有很大差别,且以苏轼两个内容相同的五言和七言诗句比较:
明月/入华/池 0
∨ ∨ ∨
明月/谁分/上下/池 0
∨ ∨ ∨ ∨
一目了然,五言诗吟诵节奏每句是三拍,而七言诗句多了一拍,成了四拍。所以,从全句节奏上说,五言三拍,属于非对称的节奏型,全句稳定性不强;而七言诗每句四拍,是对称节奏型,诗句的稳定感更强,向下推进的力度就弱了,节奏感没有五言快速激进。这才是诗论者一致认为五言“气促”的真正原因。
七言句第二种节奏型是3—2—2式:
知我者/谓我/心忧(3—2—2)
——《诗·王风· 黍离》
更能消/几番/风雨,(3—2—2)
匆匆春又归去。
——(宋)辛弃疾《摸鱼儿 · 更能消几番风雨》
第三种是1—2—2—2式:
念/柳外/青骢/别后,(1—2—2—2)
水边红袂分时,
怆然暗惊。
——(宋)秦观《八六子·倚危亭》
在元曲中还有一种2—3—2式,接近口语:
是个/不识字/渔父。(2—3—2)
——(金)白贲《鹦鹉曲·侬家鹦鹉洲边住》
八言句:
有当代学者研究认为,七言是汉语韵律构句的最佳上限,因此,中国传统狭义概念的诗,极少有超过七言者。个别诗中超七言者,如李白《梦游天姆吟留别》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句竟达九言,只能看作借鉴先人辞赋句式,或激情下的口语入诗。至于楚辞中多有七言以上句,那是迥别于诗的另一种体式,古人并不将其视为诗。但在后起的诗体词曲中,八言还是较多的。
2—2—2—2式,实为四言诗扩倍: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2—2—2—2)
——《诗·王风·黍离》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2—2—2—2)
——《诗 · 小雅· 十月之交》
祥瑞/不在/凤凰/麒麟,(2—2—2—2)
太平/须得/边将/忠臣。(2—2—2—2)
——卢群《吴少诚席上作》
有时/三点/两点/雨霁,(2—2—2—2)
朱门柳细风斜。
——(宋)欧阳修《越溪春·三月十三寒食日》
2—3—3式:
纵被/无情弃/不能差。(2—3—3)
——(五代)韦庄《思帝乡·春日游》
更折/竹声中/吹细香。(2—3—3)
——(元)张雨《柳梢青·面目冰霜》
3—3—2式:
眼见得/吹翻了/这家。(3—3—2)
——(明)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韩信功/兀的般/证果,(3—3—2)
蒯通言/那里是/风魔?(3—3—2)
——(元)马致远《蟾宫曲·叹世二首》
1-2-2-3式:
见/千门/万户/乐升平。(1—2—2—3)
——(宋)晏殊《拂霓裳·喜秋成》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1—2—2—3)
——(宋)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在词和元曲中,更多的八言句实为七言句加了一个口语衬字。如:
3-2-3式:
可怜许/沦落/在风尘。(3—2—3)
——(唐)王衍《甘州曲·画罗裙》
漫觑著/秋千/腰褪裙
——(宋)万俟咏《武陵春·燕子飞来春在否》
这一般/气味/胜从前。(3—2—3)
——(宋)苏轼《翻香令·金炉犹暖麝煤残》
对人前/乔做/娇模样。(3—2—3)
——(元)真氏《解三酲·奴本是》
再不见/烟村/四五家。(3—2—3)
——(元)关汉卿《大德歌·雪粉华》
其中句首三言拍中的“许”、“著”、“这”、“对”、“再”几字均为衬字。
九言句:
2-2-2-3式: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2—2—2—3)
——(唐)李白《梦游天姆吟留别》
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2—2—2—3)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2—2—2—3)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2—2—2—3)
——(唐)李白《蜀道难》
唯有/阮朗/春尽/不归家。(2—2—2—3)
——(唐)温庭筠《思帝乡·花花》
正值/花明/柳媚/大寒食。(2—2—2—3)
——(元)张养浩《胡十八·从退闲》
3-2-2-2式:
轩楹雨/轻压/暑气/低沈,
逞妖艳/昵欢/邀宠/难禁。
——(宋)柳永《夏云峰·宴堂深》
十言句:
向尊前/又忆/漉酒/插花人。(3—2—2—3)
——(宋)姚云文《紫萸香慢·近重阳》
十一言句: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2-2-2-3-2)
——(唐)李白《蜀道难》
恰便似/图画/中间/裹着/老夫。(3-2-2-2-2)
——(元)张养浩《胡十八·自隐居》
十二言句:
只宜/辅枕簟/向凉亭/披襟/散发。(2—3—3—2—2)
——(元)白朴《得胜乐·夏》
诗句字数再多就成口语了,比如元杂剧中那些曲词:
你去那/受刑法/尸骸上/烈些/纸钱。
再也/不要/啼啼/哭哭/烦烦/恼恼/怨气/冲天。
这都是/我做/窦娥的/没时/没运/不明/不暗/负屈/衔冤。
——(元)关汉卿《窦娥冤》第三折
以上我们例举了中国传统诗词曲的诗句中字数与节奏式,从中有几点规律:
一是诗句中的节拍,以二言拍和三言拍为主体,一言拍为辅;
二是诗句节奏,早期以四言两拍为主,后来以五言三拍、七言四拍为主。
三是诗句尾拍节奏,四言诗为对称二言拍结句;五七言诗以非对称的三言拍结句;发展到词曲,则二言拍和三言拍都可结句。
四是单言拍可在句首或句尾出现,但一般不会出现在句中。
五是诗句长度,最少四言二拍(不足时要补足空拍);最长不宜超过八言四拍,否则即近口语。
自由体新诗以口语入诗,打破了格律,甚至诗句长度超过散文句,完全放弃了诗句节奏。比如,写出《雨巷》那优美节奏和意象而闻名的诗人,也写了不少这样的诗句:
我不懂/别人/为什么/给那些/星辰/取一些/它们/不需要的/名称(3—2—3—3—2—3—2—4—2)
——戴望舒《赠木克》
整句长达24个字,不要说比口语长,即使当代白话书面语,也很少有这么长的句子。全句语词构成9个节拍,由于太多,根本不能形成韵律节奏。这显然不能算作诗了!
至于一般作者,这样的创作已成泛滥之势:
身边/经常有/关于/大师的/高谈/阔论
有人/长于/此道/熟稔的/话题
时而使用昵称
我常会/在这时/不安,/偶尔/感到/滑稽
——《诗人》(摘自网上)
记住/那些/面容/是记住/岁月
人生/旷野,/百感/交集的/际遇
蝶形/纷繁的花/是你/说出的/话语
——《紫藤花开》(摘自网上)
比这长的还有,根本不是诗,就不举例了。
我们还须认识到,虽然新诗打破了传统诗词的格律,却不应丢弃汉语语音特有的构诗元素,以及由这些构诗元素形成的韵律。
其实,现代语言韵律学认为,语音韵律——包括高低、轻重、长短等节奏变化,不仅是语音外壳的物理属性,也是语义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段,甚至规约了词汇生长与语法演变。
新诗使用的仍是汉语。现代汉语与古汉语虽有区别,但在韵律上并无本质变化。比如,基本韵律词或节拍单位,仍是二字(二音节)和三字词;单音词和三字以上的多音词,只起辅助性,不能构成节奏主体。
同时,诗句字数不可过长,应以全句三至四拍,最多不超过五拍;总字数以五至九字为宜,最多不超过十二字。才能有效形成可称为诗的节奏。
虽然我们的白话口语没有格律,但语音仍具有一定韵律,只是并不刻意对形成韵律的元素进行选择、组织、安排。而诗歌创作则相反,要刻意地运用这些语音构诗元素,使之形成更鲜明、更适合表达诗歌内容感情的韵律节奏。否则,写出的东西就只能是散文而已。
来源:醉是侠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