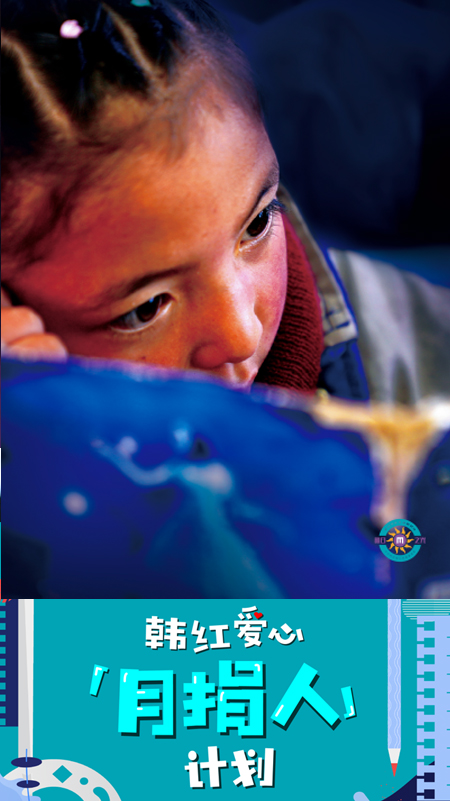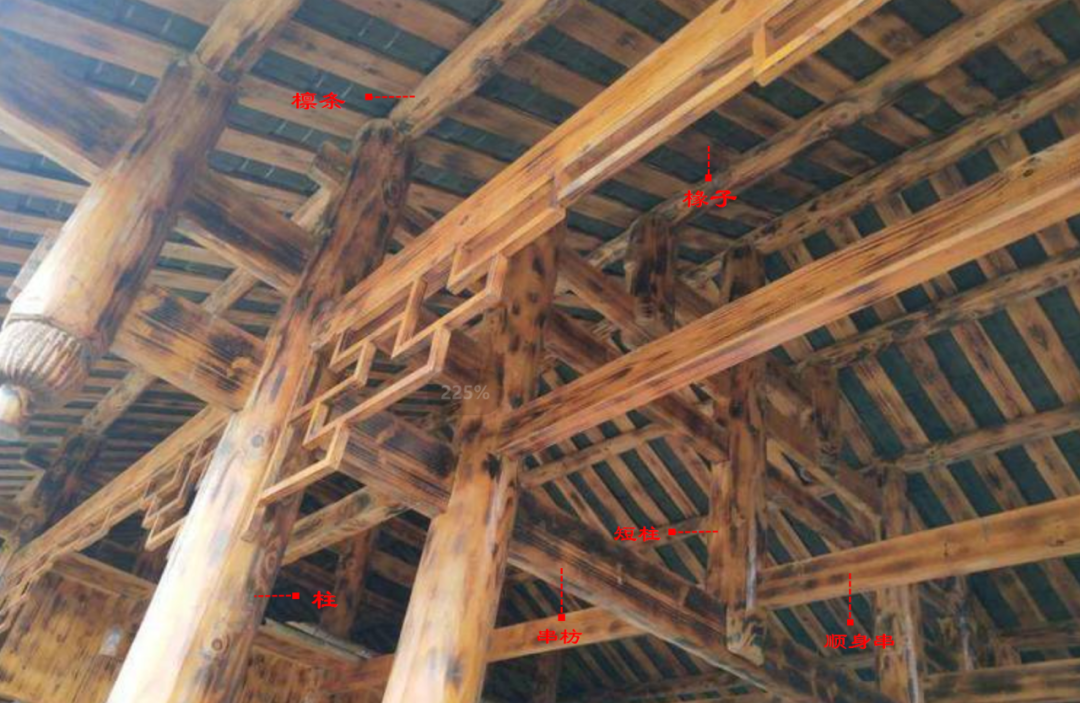将遗产留给初恋、网友、野生动物园……30多万份遗嘱里,封存着最真实的牵挂
繁体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平时不会讲出口的话,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时或是因为沟通机会少,或是碍于面子,没能得到当面表达的机会。
新京报记者 彭冲 左琳 编辑 杨海 校对 李立军
人们对遗产的分配方式各不相同。有人留给伴侣和子女,有人留给孙子,有人留给素未谋面的网友,甚至是一群陌生的孩子。
借一份薄薄的遗嘱,人们表达了对亲人最深的惦念,或者留下最彻底的隔阂。
据中华遗嘱库统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已提供遗嘱咨询478850人次,登记保管311868份遗嘱。
绝大部分遗嘱来自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但不可忽视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提前作出规划。一场突发的疾病,身边人的一次意外,继承父母遗产过程中遇到的麻烦,都可能成为促使他们订立遗嘱的契机。
写进遗嘱的,除了那些常见的财富成果——房子、车子和存款,还有支付宝账号、书籍和有百万粉丝的社交媒体账号。人们把自己在这个世界留下的零散痕迹一一列明,理好去向,作为一种嘱托,希望自己的“牵挂”能更好地生活下去。

▲中华遗嘱库。受访者供图
━━━━━
财产留给朋友、网友或者动物
39岁的董英想把遗产留给自己的猫。
那是一只捡回来的流浪猫,黑色,有点发灰,毛发不算好看,来到家已经有8年。2022年,母亲患癌去世后,这只猫和陪了自己20年的那只乌龟算是董英唯一的牵挂。
她未婚未育,在北京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薪资不错。成长过程中,她吃了不少苦,父亲有过家暴史,对她照顾也少。小时候,董英身体不好,每次生病,都是母亲带她去医院。3岁的时候,她发高烧进了ICU,父亲在外读书,没回家。董英馋橘子水,母亲只能把她自己扔在医院。买完饮料回来,被医生一通批评,“但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别人(来照顾我)。”董英说。
董英5岁前,父亲一直在读大学,俩人很少见面,“我和父亲说过的话可能还没有我这几年和公司保洁阿姨说的多。”
10岁那年,父母分开,董英跟着母亲生活,和父亲多年没联系,直到母亲被确诊癌症。董英慌张地向父亲求助,但对方也没帮忙。最无助的时间都是一位好朋友陪她度过的,包括后来母亲火化,董英抱着骨灰盒准备回老家,也是那位朋友送她上了车。
母亲的离世给她带来了不小的打击。由于在医疗行业工作,常看写满了病例生存率的医学报告,所以之前很长一段时间,生死对董英来说就是一个数字。母亲的离世,让死亡成了一个具体的画面,“不管你多么伟大或者渺小,不管你怎么挣扎,这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结局。”
“死亡来到我身上的时候,我的财产怎么办?我的猫怎么办?”董英意识到,自己的财产继承是个问题。她不想把自己的钱留给家里的亲戚,他们和自己都比较疏远,她只想把自己在世界上的唯一的牵挂安置好。

▲市民来中华遗嘱库咨询。受访者供图
过程波澜不惊。董英选了一个平常的工作日,没有特意装扮,来到中华遗嘱库,把自己的房子、股票和存款一一列明,安排好去处:50万元存款给那位陪伴自己度过晦暗时期的朋友,拜托她帮忙照顾自己的猫和乌龟;30万元留给了父亲。剩下的,她决定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教育是把人拖出泥潭的唯一路径。”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庭,董英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她想让更多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受教育,在未来有能力独立养育自己。
越来越多像董英一样的年轻人开始立遗嘱。根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近十一年,立遗嘱人群平均年龄从77.43岁下降至67.82岁,中青年人群的遗嘱保管数量近七年间增长了六十余倍,未婚不婚者的遗嘱保管数量2017年至2022年间增长了13倍。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崔文姬也注意到了明显的变化。六七年前,她刚入行时,来咨询的几乎全是老人,“年轻人很少,一年可能超不过10个。”如今,90后甚至00后都开始立遗嘱。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有2461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还有一家三口一起来的。聊起来的时候,也不像以前一样完全不了解(怎么立遗嘱),很多人都在网上查过。”
年轻人立遗嘱的契机五花八门。有时是体检报告里一个异常的指标,有时是恰逢另一半生日、想要送上一份特殊的礼物,还有可能是继承父母遗产时发现没有遗嘱导致程序复杂,甚至只是想体验一下和世界说再见的感觉。新京报曾就“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立遗嘱”在微博上发起投票,有超过半数的人选择“怕意外发生时,来不及跟世界体面告别”。
他们的财产也五花八门。2023年初,一位有百万粉丝的90后B站博主来到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决定去世后将自己名下价值300万元的虚拟资产留给父母,并将自己的B站账号留给好友运营。
家人已不是年轻人遗产的全部去处,有人留给初恋,有人留给未婚妻。一位22岁的男性室内设计师把存款和老家保存的几千本书都留给了一位网友,“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位朋友给过我极大的鼓励。”青海西宁一位35岁的未婚女子把部分财产捐给了当地的野生动物园,她本身就喜欢动物,“我觉得西宁野生动物园救助高原动物很有意义,我也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

▲中华遗嘱库登记场景。受访者供图
今年30岁的崔文姬也给自己立了遗嘱。那是6年前,她第一次在地铁上低血糖,浑身冒冷汗,眩晕,呼吸也困难,总觉得自己和身边的人都飘在半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她喝了水、吃了糖,慢慢缓过来。当时,崔文姬的作息也不规律,“猝死”也是新闻报道里常出现的词,她心里有些害怕,决定提前做好安排,“既然自己也是做这个工作的,就当体验了。”
那次,同事坐在她此前的位置,她坐在了之前市民坐的位置上。因为对整套流程很熟悉,崔文姬毫不紧张,“感觉像在演戏一样。”
直到需要简述遗嘱内容的环节,她一个字一个字把遗嘱读出来,再拿到一张薄薄的遗嘱证,才有了真实感。
━━━━━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
或许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死亡都不算迫近。但老年人不一样。
每次接待完老人,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刘千都会祝对方活到百岁,老人很感激,但几乎都摇摇头:明天怎样我还不知道呢。
死亡的确会随时来临。63岁的陈闻本和丈夫约好,在2024年5月27日下午前往公证处,把房子公证给女儿。但当天早上,丈夫突发心脏病去世。
陈闻有些后悔,“我觉得(立遗嘱的想法)还是和他提晚了。”其实,她很早就有立遗嘱的计划,“女儿结婚了,我们也老了,想方便女儿继承财产。”在和朋友聊天的过程中,陈闻发现很多比自己年纪小的人都准备好了遗嘱。她和丈夫商量,但遭到了反对,“他觉得人还活着,不想搞这些。”
后来,丈夫确诊肺癌,身体越来越差。一开始,陈闻还是不敢提,怕对方“有想法”。等到终于开了口,丈夫也点了头,意外却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崔文姬见过太多这种情况。2019年以前,中华遗嘱库只在北京西交民巷开设了一处登记中心,老人们在这里排起长队,常常是预约的时候身体还不错,等过了近一年、真正开始登记办理的时候,老人已经不在了。“大家还是对遗嘱这个事情有一点忌讳,让他身体好的时候做,他觉得不吉利,就等身体查出毛病了再做,但那个时候听说读写能力就比较差了,健康情况的变化是很快的,得赶紧办。”崔文姬说。
不少老人在立遗嘱时显得有些紧张。为了确保老人订立遗嘱时认知状态良好,中华遗嘱库设置了精神评估环节,包括算数和记忆力相关题目,“很多人紧张,说‘没上过几年学,还要考试’。”立遗嘱全程都要录像,不能暂停、剪辑、拼接,“有的老人(念遗嘱的时候)一紧张就卡壳,要重复录好几遍。签字的时候,突然一紧张就说‘年纪大了老是糊里糊涂的’,这也会造成歧义,要重新录。”

▲市民登记场景模拟。受访者供图
薄薄的一张遗嘱凝结着老人这一辈子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据统计,多数老人选择将遗产留给配偶和子女。“很多老人满眼都是孩子,根本不会想自己的吃穿问题,都是想着未来要少给子女添麻烦。”刘千常和老人聊聊他们年轻时的生活、和家人的关系,老人常常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
也有老人在这里袒露了绝望和决绝。曾有一位衣兜里揣着房产证的老人告诉工作人员,“我来立遗嘱是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他的儿子常年失业在家,动不动向他要钱,不高兴时还殴打老人。
后来,儿子将老人赶出家门,在家里到处找老人的房产证,想变卖家产。无奈之下,老人决定立下遗嘱,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后手段。还有北京郊区的一位老人,选择把存款和房产都留给大儿媳,其他子女一份不给——她的老伴因病去世,大儿子也早逝,在老人确诊癌症住院做手术期间,大儿媳悉心照料,其他子女却不闻不问。
张柳和老伴把房产、存款留给了16岁孙子——孙子患有自闭症,两人想尽力给他的未来增加一点保障。
孙子3岁时被诊断为自闭症后,孩子父亲辞去了工作,专心带他看病。三年过后,积蓄耗光,差点房子也要卖掉,仍看不见治愈的希望。人的心力也被耗没了,夫妻俩离了婚,孩子判给了母亲。
张柳放心不下。孙子刚出生几天,她就开始照顾。她决定,帮前儿媳一起继续照料孙子,但这遭到了儿子的强烈反对,“他觉得我们身体也不好,孩子也判给了他前妻,我们干吗还要掺和。”有了隔阂,儿子和两位老人也渐渐少了联系。
这几年,孩子周一到周五都跟着母亲,每天去培训机构上课,学习穿衣服、洗澡、和人沟通。到了周末,张柳就把孙子接回自己家,陪他出去逛公园、博物馆。
孙子虽不善于沟通和长篇大论,但很擅长表达爱意,常搂着张柳说:“奶奶我很喜欢你。”如今他身高已有一米八,有时候张柳抱怨他在前面走得太快,自己跟不上,男孩会转头回来,拉起奶奶的手。
张柳总希望能多看到孙子的一些进步和成长,但她和老伴都已经75岁,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如果两人去世,孩子的母亲也老了,独自生活的孩子就只能进托管机构,需要生活费,“我尽量留点钱给他,希望他将来去托管机构不要受太多罪。”
立遗嘱时,在最后的幸福留言环节,张柳表达了自己的期望:希望孙子健康长大,听母亲的话,多学些东西,也希望自己能再多陪他几年。
━━━━━肉麻的、酸楚的,平日讲不出口的话
幸福留言、情感录像等是中华遗嘱库推出的情感服务。遗嘱负责用“法言法语”明确财产归属,这些文字和影像负责用真情实感的表达,来传递遗嘱人对家人的关爱。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为市民介绍幸福留言服务。受访者供图
根据数据分析,近90%的幸福留言和子女有关,超过3%与孙辈有关,超过6%与配偶有关,与挚友、同学、同事有关的占1.07%。此外,超过80%的幸福留言内容是对后人寄予期望与祝福。
崔文姬发现,女性遗嘱人往往更感性,也更愿意表达感情,甚至说着说着开始流泪。而男性长辈则相对含蓄。有的老人会给家人唱一首歌,甚至唱一曲家人最爱听的戏。还有的老人会为了立遗嘱特意精心打扮一番,做个美甲,戴上耳钉和珍珠项链,在镜头前留下庄重的影像。
崔文姬对一对做中医事业的老夫妻印象很深。两人打拼一生,财产不少,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很顺利,老两口决定把财产互相留给对方,不给孩子,两人都去世后,就把财产回馈社会。那位女性长辈在情感录像里叮嘱子女,“没有什么财产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只有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财富。我们只希望将财产回馈社会,为国家的中医事业做一些贡献。”
85岁的金丽留下了类似的留言。她曾做过中小学和大学老师,如今还在写东西、做讲座,唯一的儿子已经定居国外,子孙的生活都不错。
对金丽来说,财产的继承没有太多需要考虑的问题,“我只有一个儿子,过得也很好。我不是有多少财产要给儿子、孙子,我是想把我的精神、对人生的看法和感悟、我的努力传给他们,想用一种书面或语音的方式把家风传下去。”平日里,子孙工作都很忙,能坐下来好好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金丽想给他们一个了解自己的机会,“他们看到留言,知道曾有这么一位长辈,为了目标和理想放弃一切、勇往直前,就可以了。”
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太多平时不会讲出口的话,肉麻的、酸楚的、直白的,平时或是因为沟通机会少,或是碍于面子,没能得到当面表达的机会。

▲中华遗嘱库工作人员协助市民填写资料。受访者供图
崔文姬记得,有一位老人在留言卡上写了大几百字,又拿了几张A4纸,满篇地写。她在字句里回忆了自己和爱人的生平: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当年知青下乡,为了儿子的生活考虑,他们把儿子留在城市里的姥姥家,把女儿带在了身边。因为常年在两地生活,父母和儿子的情感联络比较少,儿子不知道两人的良苦用心,一直觉得父母偏心,慢慢地从不亲近转为敌对。父亲去世的时候,儿子都没有参加葬礼。“这位阿姨非常伤心,她和孩子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去说,就决定在留言卡中写下来,让儿子知道之前的经历。”
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这样平日难以启齿的秘密,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把它封存在这里。近几年,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都在增长。据《中华遗嘱库白皮书(2023年度)》,2013年,我国订立遗嘱的人数仅为6804人,但2016年到2023年,每年订立遗嘱的人数平均在4万人左右,2023年,这个数字突破了6万。
如今,崔文姬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位咨询者。有人来咨询时会有些不好意思,说“我没什么财产”,但在崔文姬看来,无论钱多钱少,只要想给家人保障、不希望以后生出无关的纠纷,最好就提前作出安排。这也是用来对抗无常和不确定性的一份底气,“每次哪个地方不太平,或者身体上有点不舒服了,会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份遗嘱,就觉得也没什么了,因为都安排好了。”
有些老人立完遗嘱后仍然有些担忧,“如果孩子对我不好了,我能不能改?”崔文姬总是宽慰对方:“遗嘱的修改很正常。”她自己立遗嘱的时候,还没有谈恋爱,财产理所应当地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父母和妹妹。但等今后结婚或者有了孩子,重心可能要偏向自己的家庭,给孩子保留。再过几十年,和爱人关系稳定后,可能也会给爱人做出保留,“一份遗嘱只是在当下的人生阶段做一个预先安排,它会随着你的成长、家庭结构的变化而修改。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安排。”

▲遗嘱宣读。受访者供图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9亿人,占总人口的21.1%。预计到2033年,这部分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订立遗嘱、防范纠纷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未来,遗嘱也会像保险一样更加普及,成为人生必须要做的几件大事中的一件。”崔文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