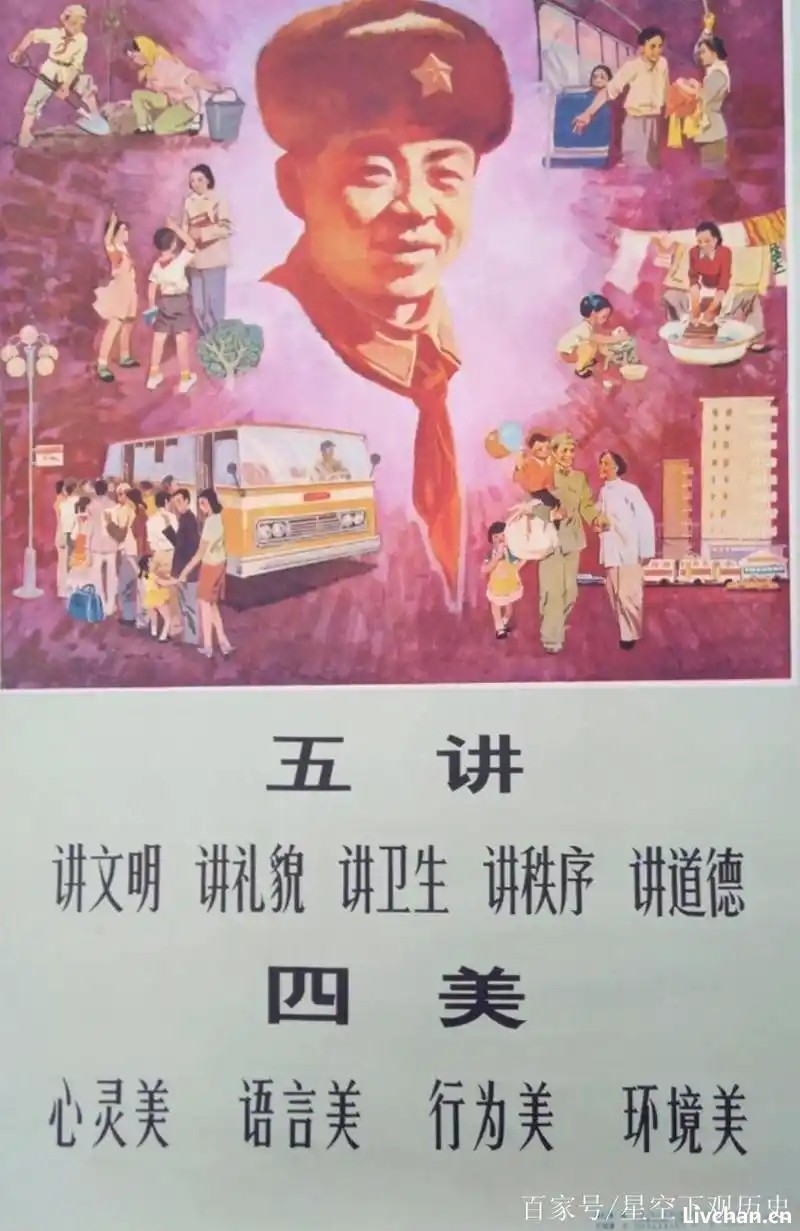从儒佛融通看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
繁体佛教初传中国,如何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文化和礼俗相适应、相结合是一种挑战。早期文献《牟子理惑论》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为背五经而向异道。”(《弘明集》)对此,佛教徒不得不作自我辩护,自《牟子理惑论》始,《弘明集》中充斥着护教文字。如孙绰《喻道论》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外内名之耳。……佛者梵语,晋训觉也。觉之为义,悟物之谓,犹孟轲以圣人为先觉,其旨一也。应世轨物,盖亦随时,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弘明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由汉地佛教徒创作的“疑伪经”,宣扬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如《提谓波利经》讲五戒与五常、五行相通,《梵网经》提出“孝名为戒”,都是典型事例。概略而言,这一时期的佛教徒以儒释二家相比附,不外乎是为了给佛教谋求在汉地生存的空间,辩护的成分更重。随着时间的推移,佛教与儒家思想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自然的融合,主要体现为佛教心识观与儒家心性说的结合、佛教佛性观与儒家性善论的结合、佛教二利观与儒家修齐治平说的结合。
心识观与心性说的结合
儒家强调心的作用,体现于对道德自觉的重视。古文《尚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以之为尧舜以来所传的圣人心法。自子思、孟子以来,倡言慎独。《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性”秉承自天,人人具有,将之发扬光大就是“道”,依照“道”历练就是“教”。
人的内心世界深微而不可测,只有自己才能察觉,故而君子不能因为别人不知晓就放纵自己。《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又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佛教同样重视心意识的作用,在佛陀和部派佛教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以“识”为业报轮回的主体,为“十二因缘”核心的思想。到大乘佛教阶段,又明确提出了“心生万法”“三界唯心”的主张。大乘瑜伽行派继承发展了部派的心识说、种子说,提出“唯识无境”说。自禅宗起,佛教徒自觉地将儒释两家的心性与心识说相结合,提出“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以心传心”“明心见性”等著名的主张。如《坛经》云:“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这些主张又对宋明儒产生了影响,尽管它们是以被批判的方式得到的继承和发展。
佛性观与性善论的结合
尽管佛性说以《涅槃经》等大乘经典为理据,但道生之所以能“孤明先发”,在大本《涅槃经》传入前就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主张,固然有其对大乘佛教慈悲平等精神的领会,但也不能说没有受到儒家性善论的影响。《孟子·告子上》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明确指出了“性”的普遍性和内在性。上文提到《中庸》主张人人生而具有秉自天命之性,《孟子》则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性,人人生而具有,并不神秘,“亦为之而已矣”,只要去践行就可以实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按照尧舜的方式言行,就是尧舜;按照桀纣的方式言行,就是桀纣。这些都为众生皆内具佛性的思想奠定了文化土壤。故而在汉传佛教的传统中,一乘佛性说始终是主流,源自印度的“五性各别说”则难以获得接纳。
二利观与修齐治平说的结合
汉传佛教尤为强调出世与入世不二、自利与利他不二的思想,这也受到了儒家重视人伦日用、倡导修齐治平的影响。道生《注维摩诘经疏》说:“夫大乘之悟,本不近舍生死,远更求之也。斯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实,为悟矣。苟在其事,而变其实为悟始者,岂非佛之萌芽,起于生死事哉?”这是将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与大乘佛教“生死即涅槃”的思想予以了结合。又儒家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慧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强调利乐有情、觉悟人生。又儒家提倡忠恕之道,所谓“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澄观《华严经随疏演义钞》说“六度等行,以为自利;四摄等行,以为利他。……自他诸行,皆同一体,互相助成”,强调自利与利他相辅相成。上述思想经太虚法师予以提炼总结,提出“人间佛教”的思想,即“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佛教徒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
近代以来,佛教徒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更表现出高度认同,对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有了高度自觉。
一方面,他们宣扬儒佛同为东方文化之根本,以此抵御西方文化的侵蚀。如唐大圆说:“东亚文化之根本二:一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诸圣人之酝酿,而有生民未有之孔子出,以集其大成;一经婆罗门教胜论、数论等,奇伟超轶之思想,互相陶炼,彼此取舍,而有出类拔粹之释迦起,以成其正觉。两派并兴,辉映同时,一华一印,岂其偶然。”(《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另一方面,他们将中国文化突出的亲亲尊尊、重视家庭和亲情的精神视为儒释二家共同的传统。
如太虚说:“笃于内行,发为伦常之德。世界人类,近而家庭,远而社会、国家,应当为如此即如此,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尽其道。立身处世,先须保存德行,扩充理性,各安其分,各适其宜,人到恰好地位,使人类有人类之道德,异于禽兽,方有人生之真价值。故曰:孔子之道,为人生在世最正当之办法。”(《佛法与孔子之道》)如果说太虚法师被公认为近代佛教“改革派”领袖的话,那么印光法师则在更普遍意义上被视为“保守派”的代表。他在其著名的“净土廿四字箴言”中同样推崇“敦伦尽分”,其言曰“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其中“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完全概括提炼自儒家,特别是《中庸》的思想。《尔雅·释诂》云:“敦,勉也。”《疏》云:“敦者,厚相勉也。”“伦”自然指五伦,“分”指本分。《中庸》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周易·乾·文言》曰:“闲存其诚。”孔颖达疏云:“闲邪存其诚者,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儒家重视“诚”,《尚书·太甲》云:“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对此,宋代的净源法师就有言,“夫儒典之述诚明,犹释教之谈寂照焉。彼以圣人自诚而明,类妙觉即寂而照矣;贤者自明而诚,比等觉即照而寂欤。斯皆为教不同,而同归乎善者也”。印光与净源可谓一脉相承。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语出《增一阿含经》,更因白居易和鸟窠禅师的对话而广为人知。按照印顺法师的考证,“此偈颂于诸戒本有说,是作为一切佛的教诫,所以称为‘七佛所说通戒偈’。依佛法的意趣来说,这些偈颂——一偈、三偈,或者多偈,是被传说为七佛所说的(佛佛道同)波罗提木叉”。(《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可见就狭义而言,这八个字可以理解为对佛教戒律精神的概括;而“敦伦尽分,闲邪存诚”如上所言是儒家对个人操守和社会规范的总结。由此可见,印光自觉地将儒释二家的思想予以会通,以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贯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结合儒释二家历史上展现出的这种高度融合的实例,我们或许能对五大特性的论断有更深的认识和领会。“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华文明并未因佛教的传入而发生断裂,正相反,她不但保持了连续性,还展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极大的创新性,在合理地吸收以佛教为载体的外来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同时,以其统一性使后者不断发生演变,最终成为了其自身传统的一部分。同时,佛教作为和平使者,远传日、韩和东南亚如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各国人民的和平、友好交流,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项目“人间佛教的海外传播研究”(23VRC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