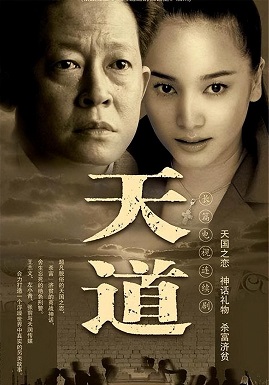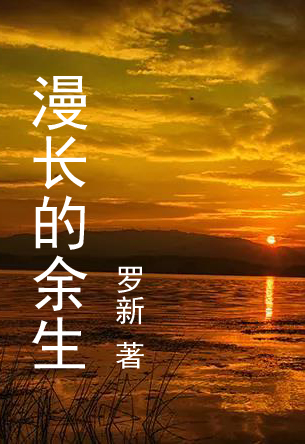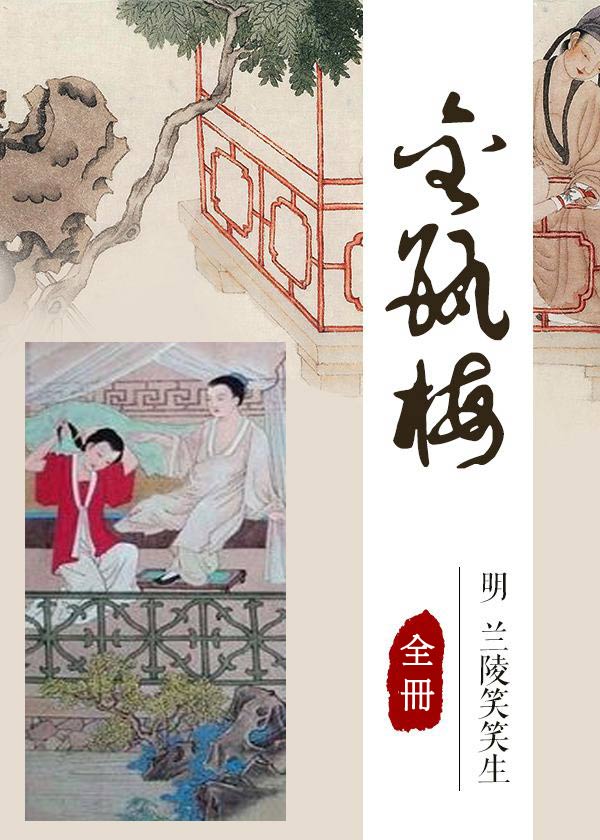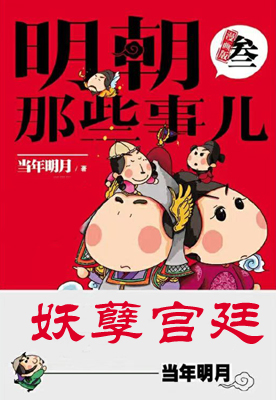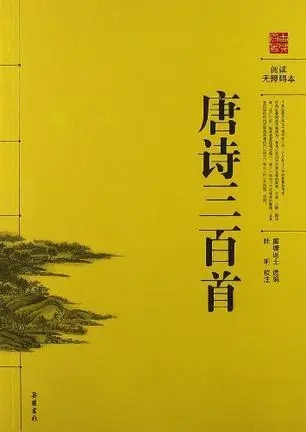拈花微笑是禅门第一公案,提起禅宗,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拈花微笑。读这则公案会让人感到轻松和惬意,甚至内心会生起阵阵快感,但为什么会这样,却说不清楚。
按佛经记载,如来在每次说法时,都会示现种种异象,或舒金色长臂,或现眉间毫光,总之是宝相庄严,无比尊贵,但在拈花微笑时,却有点漫不经心,甚至是有点不正经,一场无上法会的庄严肃穆就在这一拈一笑中被消解得无影无踪。不要说这是在神圣的法会上,就是在今天的某些重要场合,有人胆敢在主席台上搞小动作,台下还有听众嬉笑迎合,也会被视为大不敬。但佛祖却偏偏将此大不敬视为正法眼藏,微妙法门,法会是如来的法会,如来自己这么捣乱,分明是自己对自己大不敬,是自己砸自己的场子,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这么一想的话,对这则公案的理解是不是就有点意思了?
后来的许多公案也都在体现这种自己对自己的大不敬和自己对自己的过不去,也都是在自己砸自己的场子,可以说和拈花微笑是一脉相承,只不过,后世的禅师们没有佛祖和迦叶那么优雅,而是表现得更为激烈和简单粗暴,也更容易让人看明白。看懂了这些公案,也更有助于对拈花微笑这则公案的了解和体悟。
先看德山焚疏的公案。
话说德山原本是蜀地一位著名的经师,尤其擅讲金刚经,后来听说禅宗有人讲即心即佛,与佛经中历百千万劫方得成佛的教义不同,便把自己所有的讲义都收集起来,自己挑着上路,想找禅师们论个高低,
“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心。婆指担曰:‘这个是什么文字?’师曰:‘青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那个心?’师无语,遂往龙潭。”
一个经纶满腹的佛门高僧,竟然在一个卖点心的婆子身上半点手段也施展不出,德山的沮丧可想而知,后来,他投至沩山门下,受尽百般历练,终得开悟,一日,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烛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开悟后的德山禅师以棒喝驰名天下。
即便能把佛经教义讲得微妙玄通,但在生活中却派不上一点用场,这样的佛法又有何用呢?德山在这里烧掉的是佛法的文字相。
再看丹霞烧佛的公案。
“唐元和中,丹霞天然至洛京龙门香山,与伏牛和尚为友。后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烧火向。院主呵曰:‘何得烧我木佛?’师以杖子拨灰曰:‘吾烧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师曰:‘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 ”
这简直就是大不敬之至了。但木佛确实不是佛,对于开悟的禅师来说,只是一块木头而已。丹霞天然此时烧掉的应该是佛法的言说相。
还有赵州禅师的“佛之一字,我不喜闻”和云门文偃禅师的“干屎橛”(僧问云门文偃:“如何是佛?”,文偃答:“干屎橛”)之说,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所谓自己明明是和尚,却偏偏喜欢骂秃驴,明明成佛成祖是每个修行人的终极梦想,却偏偏又要避之唯恐不及,一旦沾上了就臭不可闻。这应该是在扫除人们心中的佛相圣相,也就是所谓的心缘相。
说完这几个公案,再回过头来看拈花微笑,是不是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佛祖的拈花,迦叶的微笑,其实是在消解灵山法会的庄严相和神秘相。
佛法原本是为了消除烦恼,让生命得到自由和解脱,然而一旦成为死板的教义,反而会让人平添更多的枷锁。禅宗的出现就是要把人们从佛法的束缚中重新解放出来,消解或者说化解掉人们强加在佛法身上的种种虚妄的价值和意义,让佛法从神坛上走下来,重归生命和生活,让生命更自由,让生活更自在。禅师们对佛法所谓的种种大不敬,其实也不是在否定佛法,而是在破除人们对佛法的种种迷思和迷信,重新发现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意义,这也许就是禅师们念兹在兹的所谓“向上一路”。
拈花微笑最后指向的当然也是生活。灵山法会对弘扬佛法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果人人都沉耽于法会之中,生活反而会因此荒废不堪。拈花是生活,微笑是生活,而弘扬佛法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那么好吧,佛祖就用这一拈一笑在轻描淡写中让人们从法的世界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由此看来,佛祖可真称得上是法力无边。
佛祖的法力来自敢于对自己大不敬,敢于自己否定自己,敢于自己造自己的反,自己砸自己的场子。这种精神和勇气,不仅出家人修行需要,于今天的社会而言,也不乏可以借鉴的积极意义。
对于拈花微笑这则公案,佛学界一直是存有争议的,很多人认为这则公案在佛经中并无记载,只是出于后人的杜撰。虽然也有书中说,王安石曾经在皇家收藏的佛教典籍中看到过,但也是查无实据。但在我看来,即便是后人的杜撰,也是一个天才的创造,这则公案看似轻巧,实则具有千钧之力,只在一拈一笑间,就将对佛法的宏大构建和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化解于无形,让佛法重新回归人间,实在是功莫大焉。这样的天才,对于一个一直喜欢贴标语喊口号的社会来说,更显得尤为重要。
至于大多数普通人,即便是出于无奈,在焦虑苦闷之余,也不妨拈拈花,也许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还真的会有人在冲你微笑呢。
文章写完后,心里总觉得不踏实,有点惴惴不安,便发给我的大学同学柯杨看。在我认识的喜欢禅宗的人当中,柯杨是个一禅到底的人,和他说话,总感到天空中有大棒飞舞,不知什么时候头顶上就会挨一下,他是敢于把禅家精神运用到生活中的人,不像我,虽然平时也喜欢谈点禅论点道,但一遇到生活中的小波浪,那点禅意就早飞到了九霄云外。我知道这样的文章是难入柯杨法眼的,但若能引来他的一棒一喝,也不失为一件妙事。
很快,柯杨回话了,也许正赶上这老兄心情不错,所以话说得也比较客气:“你这还属于落在明白里,是教内不是教外。禅家的不知道里面,有一种精神,有一种气势,一旦说破,就成死的了。”是啊,拈花微笑经我这么一说,确实已没有了任何风情和味道,成为一碗白开水了。见我许久不着声,他接着又发来三个字,“吃茶去”。哈哈,这老兄确实是禅门高人,几句话,就能让人心里七荤八素的。“吃茶去”也是一则公案,在这里引述一下:
师问新到:“曾到此间么?”曰:“曾到。”师曰:“吃茶去。”又问僧,僧曰:“不曾到。”师曰:“吃茶去。”后院主问曰:“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师召院主,主应诺,师曰:“吃茶去。”
这世界上的事情,你知道也不好,不知道也好,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知道就好一点,不知道就差一点,那我们除了喝茶,还能做什么呢?
吃茶去!
来源:北冥那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