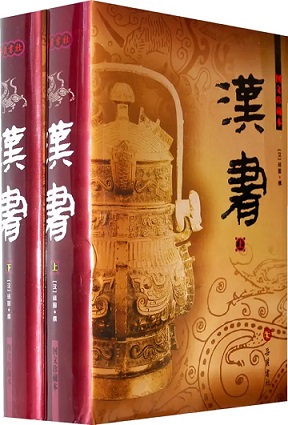阿列克谢站就像是展览馆站的盗版,只不过盗得很差劲。这里也学着种蘑菇,养猪,只可惜蘑菇和猪全都半死不活,只能勉强自给自足,根本没有剩余的量拿来卖。但当地人的性子跟自己养的猪也差不多,混吃等死,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故事,无论开端还是结局都平淡乏味,而且早已提前剧透。这里的墙壁早先是白色大理石的,但现在已经看不出是什么样的了。但凡能抠下来的,早就被抠下来卖掉了,只剩下混凝土和为数不多的几十条人命。混凝土抠不下来,而且也没人愿要,因此这里最主要的贸易,就是“卖命”。假如市场有竞争,价格自然会高些,但除了展览馆站并没有其他买家。故而,阿列克谢站存在的最主要意义就是:保卫展览馆站。
所以,通往阿列克谢站的南边隧道,对展览馆站而言是基本安全的。其他隧道也许要花上一周时间才能通过,而这条南边隧道,阿尔乔姆和荷马因准备充分,小心谨慎,大概只用了半小时。二人在站台某处停留了几分钟,在展览馆站的相同位置挂着一块钟表,而阿列克谢站的钟表早在十年前就不翼而飞,从那以后,这里的每个人全凭自己的直觉来判断时间。谁想要黑夜,谁就有黑夜。毕竟,在地铁里,黑夜是没有尽头的,反倒是谁想要白昼,就得自个儿去想象。
通道守卫漫不经心地看了来人一眼,他们的瞳孔跟针眼一般大小,哨所上空飘着一团混浊的白色烟雾,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包脚布味。显然,守卫们抽大麻了。守卫长叹口气,打起精神问:“去哪儿?”
阿尔乔姆用低不可闻的声音答道:“和平大道站,去赶集。”
“那边过不去。”
阿尔乔姆对他热络地一笑:“这个不用您操心,大叔。”
守卫长似乎被阿尔乔姆的亲切感染了,没头没脑地背了个似是而非的数学定理:“正切乘正切等于余切。”说罢就放二人通行了。
“我们怎么走?”荷马问阿尔乔姆。
“从和平大道站往下吗?如果汉萨放我们入境,那我们就沿环线走。反正怎么都好过走我们橙线——不愉快的回忆,你懂的。去汉萨更稳妥。我有签证,还是梅尔尼克签发的呢。你有签证吗?”
“那边不是隔离了吗?”
“隔离不叫事,想想办法总能进去。麻烦在于大剧院站,从哪个方向进去都难。你可是给自己的无线电员挑了个好地方,大爷,雷区正当间儿。”
“怎么是我给他挑的呢……”
“开个玩笑。”
老者的目光低垂下去,仿佛在凝视自己的内心,那里应该贴着一张地铁线路图。而阿尔乔姆的地图永远挂在眼睛正前方,像全息投影一样,这是他在梅尔尼克手底下服役一年学到的本事。
“我倒是觉得,走帕维列茨站更好些,路虽然远,但更快。从那儿再沿着绿线向上,顺利的话,一天就到了。”
二人沿着隧道一路前行。
手电筒尽忠职守,但射出的光线顶多只能照亮十步开外,再远就会被黑暗吞噬。棚顶在滴水,墙壁发出湿漉漉的反光,远处有什么东西在咕噜作响,某种液体从顶棚滴到脑袋上,刺激着头皮,与之说它是水,更像是胃液。
两侧墙壁不时会出现一些门或者通道口,但大部分都用钢筋焊上了。
乘客们平日所见的那张光鲜的地铁示意图上所标注的,实际上还不及真正地铁的三分之一。想想也对,何必让乘客们觉得难堪呢?他们从一个大理石站台,到另一个大理石站台,煲个电话粥,把时间往前调上个把小时,好了,到达目的地了。没有人会去想,自己在地底多深的地方转了一圈,也不会有人去关心,站台墙壁后面是什么,那些被格栅围起来的隧道支线通往何处。不想也好,看看手机,想想自己的人生大事,不该想的就别想。
两人迈着走隧道专用的步伐,每一步都是四分之三米,以便刚好能踩在每一根枕木上。需要走很多的隧道,才能习惯这种步距,那些窝在站台的人是不行的,总会踩空。
“大爷,你,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生活。”
光线全部射向前方,看不清老人脸上是何表情,也许,只有胡子和皱纹。
又跨过了大概五十根枕木,装着电台的背包开始往下坠,不断提醒阿尔乔姆自己的存在。阿尔乔姆两鬓全湿,汗流浃背。
“我以前有过妻子,在塞瓦斯托波尔站。”
“你住在塞瓦斯托波尔站?”
“早先。”
“她离开你了?”阿尔乔姆莫名觉得,这是最有可能的情形。
“是我离开了,为了写书。当时我觉得,书更重要,我想在自己死后留下点什么。妻子嘛,反正也跑不了。你懂吗?”
“为了写书离开妻子?”阿尔乔姆难以置信,“还有这种事儿?那她呢……她就放你走了?”
“是我偷着跑出来的。等再回去,她已经不在了。”
“离开了?”
“死了。”
阿尔乔姆将装有防化服的旅行箱从右手倒到左手,说:“我不确定。”
“不确定什么?”
“我不确定自己懂不懂。”
“你懂的。”老者疲惫但坚定地说。
阿尔乔姆突然感到害怕,怕自己也做出无法挽回的事。
接下来的枕木是在心里默数的,只听到咕噜咕噜的回响和遥远的呻吟,那是地铁在消化远方某个不幸的人。
****
他们没有顾虑背后的危险,只顾盯着眼前的隧道,凝视着这口装满墨水的深井,凝视着井面随时可能出现的微弱涟漪,防备前所未见的可怕东西猝然钻出。至于背后,他们根本没去管。
这真是失算。
吱吱嘎嘎……吱吱嘎嘎。
这声音就这样悄悄地、渐渐地钻进耳朵。
等他们察觉时,已经来不及端起枪管了。
“哎呜!”
如果有人给他们背后来颗“黑枣”,那他们是绝对躲不过的。地铁第一法则:在隧道里绝不能分神,会丢掉性命的。就是记不住,阿尔乔姆。
“站住!谁?!”阿尔乔姆大喊。
“哎呜!自己人!”
是刚才那个守卫长——“正切余切”。他胆子还不小,一个人开着轨道车就来了,而且还擅离职守——肯定是大麻嗑多了。
他来干什么?
“伙计们,我想了想,也许我可以送你们过去,到下一个车站。”说罢,他向二人递上一个谄媚的微笑,露出参差不齐的牙齿,挤出满脸皱纹。
身体当然更希望坐车,而不是一步一步挪。阿尔乔姆打量了一下这个热心人:棉袄,秃顶,大眼袋,但瞳孔里放出光,就像锁孔一样。
“多少钱?”
“提什么钱啊!你不是苏霍伊站长的儿子嘛。我是为了……为了世界和平。”
阿尔乔姆精神一振。把背包往上一送,让它更舒服地骑在了背上。
“谢谢。”阿尔乔姆接受了提议。
“这就对了嘛!”“正切余切”兴奋地挥舞双手,像要驱散积攒多年的烟雾,“你已经是大小伙子了,应该理解数学的精妙!没有游标卡尺根本不行。”
一直到里加站他都没闭嘴。
****
“带大便了吗?”
在巡逻兵之前,第一个迎接他们的一个短头发、高颧骨、兜风耳的小伙子。眼睛有点斗鸡眼,颜色是天空那种水泥色。身上的皮衣不大合身,衬衣敞着怀,胸口露出一个大大的耶稣文身,正从十字架上平静而自信地向外凝视。小伙子两腿间夹着一个铁皮桶,肩上搭一个褡裢,被他轻轻一拍,立刻发出诱人的叮当声。
“我出最好的价!”
早先,这个地铁站的上面是里加市场,以物美价廉的玫瑰闻名全城。当年,防空警报响起之后,人们只有七分钟时间来做出全部反应:确信这并非演习,掏出证件,跑进最近的地铁站。机灵的卖花小贩离地铁入口最近,他们用胳膊肘拨开惊慌失措的人群,头一个钻入地下。
当在地底下如何谋生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打开气密门,挪开堵在门口的尸体,返回自己的花市,取回了玫瑰和郁金香。鲜花已经枯萎了,但用来作干花装饰绰绰有余。就这样,里加站人做了很长时间的干花生意。这些干花虽然带有霉菌和辐射,但人们照买不误,毕竟,这是全地铁能找到的最美好的东西了。要知道,人们还要继续爱,继续哀悼,没有花怎么能行呢?
凭借干花,凭借对恍如昨日却一去不返的幸福的追忆,里加站展开了腾飞的翅膀。但在地底下没法种植新花,花朵不是蘑菇,不是人类,它们离不开阳光。而地面上看似取之不尽的花,也终于枯竭了。
危机出现了。
过惯了好日子的里加站人,终于也不得不缩减口粮,甚至要沦落到吃老鼠的地步了——就像其他毫无出路的车站那样。但精明的商业头脑又一次拯救了他们。
他们权衡了各种机会,盘算了自己地理位置的优势,向北边的邻居展览馆站提出了交易:由他们购买多余的猪粪,然后转手卖给其他种植蘑菇的车站,充当肥料。展览馆站接受了这个提议——大粪他们有的是。
就这样,即将被贫穷熄灭的里加站再次焕发生机。新商品味道固然不好,却更实在、更可靠。况且,在眼下这个艰难时代,里加站人也没办法挑三拣四。
“伙计们,咋着,你们没货?”短发小伙儿对来客初步嗅过之后,失望地问道。
这时,其他同样带着铁桶的人也飞跑过来,争先恐后地高喊:
“收大粪!”
“大粪有没有?高价!”
“一公斤一颗子弹!”
这里的结算货币跟全地铁一样,也是AK自动步枪子弹,这是如今唯一的硬通货。卢布早在最初就失去了效力——在信用一文不值、国家不复存在的地下世界,拿什么来保证它的价值?而子弹,就另当别论了。
纸币早就被卷成烟卷抽掉了,大面值的比小面值的更受欢迎,因为它们更干净,更好烧,冒烟也少。硬币则成了那些玩不上子弹壳的穷孩子们的玩具。如今,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就是子弹。
一公斤大粪在里加站只能换一颗子弹,而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站就能换三颗。自然,这门生意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干,但没关系,干的人越少,竞争就越小。
“喂,廖哈,滚一边去!我头一个来的!”一个皮肤黝黑的大胡子将耶稣文身的小伙儿一把推开,小伙儿敢怒不敢言地退到一旁。
“你往哪儿钻,啊?你以为你先在隧道碰上他们,大粪就全归你了?”另一个紫脸膛的秃头也跳过来。
“瞧瞧,刚入行没规矩!”又有人跟着起哄。
“行啦,各位大哥,你们干吗……反正他们也是空车!”小伙儿辩解道。
“让我看看!”
那个叫廖哈的小伙儿闻得果然没错,“正切余切”车上一坨大粪也没有。
待阿尔乔姆和荷马下车,“正切余切”无辜地一摊手:“我的货卸完啦!”说罢,吹着难听的口哨,掉头向黑暗驶去。
巡逻兵例行公事地检查了来客,将其放行,聚拢而来的大粪贩子们纷纷散去,只剩下头一个——廖哈。看得出来,他是最需要生意的。
“要不要来个观光,伙计们?我们这儿可有的看哪。你们最后一次见列车是什么时候?我们这儿有列车宾馆,豪华间!带电!在廊道里!我能搞到优惠!”
“我对这里了如指掌。”阿尔乔姆诚恳地说罢,向前走去,荷马踢里趿拉地跟在后面。
里加站原先被涂成了两种喜庆的颜色——红色和黄色,但想要发现这一点,得先用指甲把覆盖在全站台所有瓷砖上的那层油脂括去。一条隧道被一列死去的地铁列车堵住,车厢被改造成了宾馆。第二条隧道是站台全部生活的供给线。
“那您知道我们的酒吧吗?新开业的。家酿啤酒,上等货。至于原料嘛,也是用——”
“停!”阿尔乔姆赶紧把他的嘴堵住。
“那……伙计们,你们总得找点什么乐子吧?和平大道站被封了,检疫。轨道被横着拦住了,机枪手带狗执勤。你们不知道?”
阿尔乔姆耸耸肩:“那又怎样,就没办法通融吗?”
廖哈冷哼了一声:“你自己通融去吧。汉萨那帮人正搞运动呢,反腐。你呀,正好撞枪口上。那些受贿的,回头就放出来了,毕竟是自己人,但是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为什么封闭了?”
“说是有什么蘑菇病,霉菌什么的。不知道是空气传播的,还是外人带过去的。所以一切事务都暂停了。”
“就是冲我来的,”阿尔乔姆嘟囔了一声,“不想让我进去。”
“啥?”廖哈皱着眉头问道。
“我倒腾过这些蘑菇。”阿尔乔姆说。
“我明白,”廖哈似有同感,“倒腾蘑菇最没意思了。”
这时,几个小贩从身边飞奔而过,铁皮桶咣当作响,廖哈刚想追上去,又站住了。他似乎觉得,跟这两个倔脾气的游客在一起更有趣些。
“您这买卖可有意思。”荷马揶揄道。
“你还别说,大爷,”廖哈拧着眉毛道,“经纪人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得有才能。”
“经纪人?”
“对啊,就像我这样的,还有那边的,都是经纪人。不然你以为呢?”
荷马没法搭腔——他正努力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但嘴角还是忍不住往上翘了。
就在这时,阿尔乔姆发现荷马神情突变。他的脸色变得冰冷、惊恐,形同死人,他的视线越过经纪人,盯住旁边什么地方。
“你还别不信,”廖哈对着充耳不闻的荷马继续说,“大粪哪,我告诉你,那可是经济的血脉。蘑菇靠什么生长?塞瓦斯托波尔站的番茄靠什么施肥?所以说,你可别瞧不起大粪……”
廖哈每停顿一次,荷马便机械地点一下头,与此同时,侧着身子,慢慢地从廖哈身边走开,走过阿尔乔姆。阿尔乔姆用视线画出了他的轨迹,但仍感莫名其妙:离他们几步开外,站着一个浅色头发的清瘦姑娘,正跟一个大胖子经纪人亲吻,后者一边亲,一边悄悄地用脚将自己的粪桶踢向一旁,以免大煞风景。荷马那迟疑的步子正是迈向这对情侣的。
“你说,我们赚的能算多吗?”丢失了老者这位听众后,廖哈立刻转向了阿尔乔姆。
荷马走到情侣身边,尴尬地挑选着合适的角度,以便看清亲热者的脸。他认出谁了吗?但老人终究没敢把两张贴在一起的嘴分开。
“你干吗?”胖子用后脖子上的肉觉察到了老人,怒叱道,“你有病啊,老头?”
停止亲吻的姑娘脸上汗渍渍,皱巴巴的,活像刚从胳膊上拽下来的水蛭的吸盘。这不是老人要找的那张脸,阿尔乔姆一下就看出来了。
“对不起。”老人说。
“走开!”水蛭女说。
神色黯然,难以平复的荷马走回阿尔乔姆和廖哈身边。“认错人了。”他解释道。
但阿尔乔姆决定什么都不问:贸然拧开老人感慨的阀门,搞不好会让螺钉的滑丝坏掉。
荷马自言自语:“她当然不会……绝不可能跟这种人……老傻瓜……”
阿尔乔姆没理会荷马,反问廖哈:“怎么,难不成你们还赔钱了?”
“赔不赔的吧……汉萨每批货都要扣一半税,现如今更是……搞那些个检疫。”
所谓“汉萨”[历史上的“汉萨”指的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为保护其贸易利益而结成的商业同盟,13世纪逐渐形成,14世纪达到鼎盛,加盟城市超过160个。15世纪转衰,1669年解体],是环线车站联盟的自称。从地铁各个方向来的任何商品都要经过汉萨的市场和海关。很多倒爷,较之于冒着生命危险跨越整个地铁,更倾向于将货物运抵环线与辐射线交叉处的最近的集市,卖给当地商人。收到的货款通常也就地存到汉萨的某家银行,以免在漆黑的隧道里被眼红的强人给抹了脖子。那些犯倔非要自己运送商品的人,到头来也免不了要缴纳高额税款。因此,不管其他车站再怎么贫苦,汉萨始终富得流油。全地铁没有任何势力能对汉萨发号施令,这令汉萨公民趾高气扬,也令其他所有站台徒唤奈何。
从站台中央可以看到,载货轨道车排成的长龙向区间延伸而去,这些轨道车是不得进入里加站的。经纪人的全部生意,就是从北部隧道抢购货物,然后卖到南部隧道。接下来,货就是别人的了。
“整个商业都停滞了。”廖哈抱怨道,“他们在扼杀企业家,这帮混蛋,该死的垄断者。人们想勤勤恳恳地做事,可是不行!谁给他们的权力靠我们发财?凭什么我们腰都累折了,他们却腆个大肚子?这是压迫,该死的!要是让我们自由发展贸易,整个地铁早就共同繁荣了!”
阿尔乔姆突然对小伙子心生好感,甚至忽略了气味。他想继续这个话题。
“汉萨的小日子过得不错。”他回忆道,“有一回,我在环线上的帕维列茨站做强制劳动,清理厕所。原本判我干一年,结果干了一个星期我就跑了。”
廖哈点头道:“你这也算是经过洗礼啦。”
阿尔乔姆接着说:“这些粪便都被他们扔到污水坑或者竖井里了,根本不打算拿出去卖。”
廖哈不悦地冷笑了一下:“他们倒是富裕。”
廖哈掏出烟盒,里面是裁剪好的卷烟纸和一小包烟叶。他请两人抽烟,荷马拒绝了,阿尔乔姆接了过来。他凑到悬在顶棚的灯泡下方,在卷烟之前仔细辨认纸上的字母。那是一页发黄的书页,上面是工整的印刷体字母。但纸页是手撕的,撕纸的人是按照卷烟纸的规格操作的,而并非是为了叫人阅读的。只见上面没头没尾地写着:
还有年轻的重力:
开启了少数人的权力。
……
准备好在这样的时代生活:
那里没有豺狼和恶魔。
……
天空孕育着未来,
大地生长着小麦。
……
不像今天的胜利者,
绕过古远的墓地,
折断了蜻蜓的羽翼……
文字恰巧在“羽翼”处折断了。阿尔乔姆在这毫无意义的文字上放上烟叶,仔细地卷成筒状,用唾液将其黏合,向廖哈借火。廖哈划着了一个用子弹壳改造的酒精打火机。纸张烧起来很好闻,但烟叶太差。
“怎么,你们非得去和平大道站?”廖哈被烟熏得眯缝着眼,低声问道。
“去汉萨。是的,必须去。”
“签证有吗?”
“有。”
两人又各自深吸了一口烟,荷马被呛得咳嗽起来,阿尔乔姆满不在意。
“你准备出多少钱?”
“你开个价。”
“开价也不是我开,大哥,那边的人定,我只能帮你引荐。”
“那你就引荐。”
廖哈提议临行前喝上一杯,就在那个挂着“最后一次”招牌的闹哄哄的本地酒吧。但阿尔乔姆拒绝了,他知道那酒是用什么东西酿的。
价钱谈好了:十颗子弹,送到地方并引荐。这个价钱很公道。
****
防疫线刚好布在和平大道站入口前的区间。形式上,汉萨只管辖环线车站,而辐射线车站原则上是各自为政的。但这仅仅是形式上和原则上,一旦有需要,汉萨会立马隔断这些线路。
汉萨的边防部队身着灰色迷彩,用手电筒刺眼的白光在人们脸上乱晃,对他们大吼大叫,叫他们掉头,原路返回。一幅写着“检疫!”字样、配着霉变蘑菇图片的宣传画,像稻草人一样插在竹竿上。卫兵非但不跟倒爷们说话,甚至用帽檐遮住眼睛,看都不看他们一眼。除非发动强攻,否则这道防线根本无法突破。
经纪人廖哈转来转去,在一片帽檐底下寻找熟人。终于,他钻到其中一个下面,跟大盖帽低语了几句,扭过脸朝阿尔乔姆挤了个眼,下巴一扬,示意他们过去。
“他们被捕了!”大盖帽一边向沸腾的人群解释这三个人何以能通行,一边高声呵斥,“后退!小心感染!”
三人被押送着,穿过戒严的和平大道站。站台两侧的店铺被封了,顾客们围着警备队追问,披头散发的女售货员们劈腿坐在冰凉的花岗岩地板上,叨唠着生活、死亡和命运。到处黑灯瞎火,既然市场没有运行,电力就需要节省。倘若换作平日,此时此地正是人声鼎沸。和平大道站是中心站点,各种商品货物从四面八方云集至此。各种品味的衣服,阿尔乔姆每次见了就迈不开腿的书摊,一堆堆烧焦的智能手机,从中偶尔能淘到一个能用的,里面保存着照片,彩色的,承载着某人的回忆……买下来吗?但那里面全是别人的回忆,至于打电话,只能打给虚无。此外当然也少不了武器,各式各样的武器。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以子弹计算。人们卖掉用不着的,入手必需的,然后继续赶路。
押送队对阿尔乔姆和荷马严密防范,谨防逃跑。他们用枪顶住二人的后背,一直押送到辐射线与环线的交会处,然后让二人连同廖哈在白石墙壁上的一扇铁门旁等候。
过了十分钟,里面有人叫他们进去。
门很矮,一共有三道,他们不得不先后三次猫下腰去,好像这办公室是给侏儒人盖的似的。地铁里出生的那一代人,身材普遍矮小,应该刚好合适。
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坐着两个矮人。其中一个长着一张大胖脸,戴着眼镜,头发稀少,除一颗大头以外,身体其余部分全部藏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看上去仿佛只有一个完全自动化控制的脑袋。另一个矮人毫无特别之处。
“这位是环线和平大道站副站长,罗任·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不起眼的矮人毕恭毕敬地介绍大胖脸。
“什么事?”大胖脸用威严而低沉的嗓音问道。
“是这样的,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这两位需要去汉萨。他们有签证。”廖哈恭敬回道。
大胖脸费劲儿地把自己的大鼻子转向廖哈,大声地吸了口空气,面孔立刻变得扭曲。显然,这间办公室很少放“经纪人”进入。
“通往汉萨的入口在得到进一步指示之前不得进入就这样!”大胖脸说起话来不加标点。
气氛变得尴尬。
“怎么,没有通融的余地吗?”阿尔乔姆蹙眉问道,廖哈连忙示意他闭嘴。
“什么通融行贿公职人员是头等大罪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提起明白了没有!”大胖脸义正词严地说,“作为地铁公民你没有任何权利搞特殊!检疫之所以设立就是为了……形势不会失控你们明不明白!既然派我们在这里维持秩序我们就会维持秩序直到最后一个人牺牲因为这关系到你们自己知道是什么!植物检疫控制措施!而且是干腐病!谈话结束!”
大胖脸一闭上嘴,房间立刻陷入死寂。似乎这番说辞是提前录在磁带上的,等录音播放结束,咔嗒一声,后面就再没有任何音乐了。
大胖脸透过自己厚厚的眼镜片,用目光灼烧着阿尔乔姆和廖哈。寂静在积聚、积聚,仿佛在等待他们做出什么反应。
突然飞出一只粪蝇,轰鸣盘旋,宛如一架重型轰炸机。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不成是廖哈放在口袋里带进来的?
“既然如此,我从上面走。”阿尔乔姆双手一摊,转向廖哈,“你这个糊涂蛋,廖哈。”
“那我的十颗子弹……”廖哈忙问。
“何必从上面走呢?”不起眼的矮人终于开口道,“那样不安全。”
有别于大胖脸,不起眼的矮人在整个会面期间,一次也没有皱眉头或者打响鼻。看得出来,他平时也不怎么皱眉,他的脸很光滑,五官很恬淡,声音很轻柔:“刚才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陈述的是官方立场。要知道,他正在执行公务,请理解他。而且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也准确地指出了问题所在:我们的任务是阻止干腐病的蔓延,以免这种危险的传染病毒危及蘑菇。如果你们有成熟的折中方案,请与我商量。形势严峻,三个人一百颗子弹。”
“我不跟他们去。”廖哈忙道。
“两个人一百颗子弹。”
阿尔乔姆偷眼观察大胖脸的反应,下属的这种忤逆之举应该令他大发痉挛才对。但根本没有,副站长面不改色,似乎不起眼的矮人刚才发出的是次声波,他的耳朵根本接收不到。
一百颗子弹。
阿尔乔姆总共只带了六个弹匣,一百颗子弹就是三个弹匣还多。仅仅是为了进入汉萨,而这只不过是行程的开始。但即便如此……
任何其他路线,包括走地面,都可能开出更高的价码——比如说,脑袋。
一张地图在阿尔乔姆眼前浮现:向下进入汉萨,乘坐汉萨方便快捷的定线公交车直抵帕维列茨站,然后再直接地、畅通无阻地抵达大剧院站。而且还不用穿越红线边境,也能避开帝国……
“成交。”阿尔乔姆道,“现在交钱?”
“当然。”不起眼的矮人谄媚答道。
阿尔乔姆卸下背包,打开旅行箱,摸出藏在衣物中的弹盘,把暗淡的尖顶子弹放到桌上。
“一十。”他把第一批子弹推到大胖脸面前。
“你这人好不懂事!”不起眼的矮人一边埋怨,一边从座位站起身来,把子弹搂到自己这边,“副站长正执行公务呢!你是怎么回事?你当我是干什么的?”
幸亏,副站长没看见。
他傲慢地蹙着眉头,清清嗓子,开始整理桌面的文件,把它们从一小摞放到另外一小摞,似乎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其他所有人的存在都无法使其感觉器官产生任何反应。
“八十,九十,一百。”
“没错。”不起眼的矮人说道,“谢谢,会有人送你们过去。”
廖哈大功告成般地轻轻拍了拍胸口的耶稣。
“下不为例!”副站长终于开口道,“原则就是原则!特别是在当前这种严峻时刻更需要精诚团结!干腐病!刻不容缓!再见!”
荷马被眼前所见惊得目瞪口呆,心悦诚服地向大胖脸鞠了一躬,由衷地赞道:“漂亮!”
“再见!”大胖脸严正地重复道。
阿尔乔姆一把将背包扛到背上,由于动作过猛,一块绿色铁皮从背包上角露了出来。
副站长眼前一亮,将短胖的身躯从桌子后边挪了出来:“你包里背的可是无线电台么?这很像军用电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允许带入汉萨境内的。”
阿尔乔姆斜眼瞟了一下不起眼的矮人,可是,在副站长醒过来之后,这个不起眼的矮人只顾把那一百颗子弹收到桌子底下,然后就对眼前的事情完全失去了兴趣,开始漫不经心地剔指甲里的泥垢。
“谢谢!”阿尔乔姆回了一句,拎起旅行箱,把荷马拽向出口。
“我的十颗子弹!”经纪人紧跟在后面提醒。
门在身后关上,阿尔乔姆听到一阵低语。
等出到站台,已经有人在等候他们了。不是把他们押到这儿来的那些穿迷彩服的警卫队,而是一些穿便服的人,手里拿着展开的证件,但光线太暗,根本看不清楚。
“安全部门,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维诺卢普少校。”一个高个子彬彬有礼地表明身份,“请交出你们的武器和通信设备。你们被捕了,涉嫌间谍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