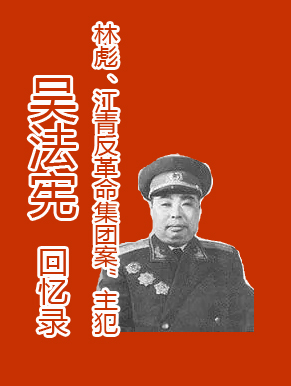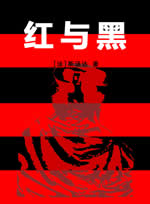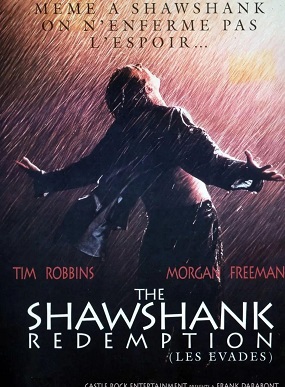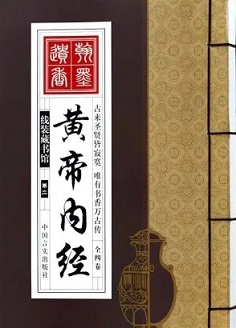唐代大诗人兼画家王维有一幅名画“雪中芭蕉图”,是《袁安卧雪图》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仍见于著录,后佚。此画在历代久负盛名,评论这幅画的著名学者颇不乏人。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中有一段比较完整的评论:
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摘其间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如彦远画评,言王维画物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余家所藏摩诘画《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难可与俗人论也。
沈括的意思就是,在大自然中,雪与芭蕉不能同时并存,而王维偏偏画在一起,却又“造理入神,迥得天意”,令人觉不出矛盾。
沈括的说法影响深远,它被后人用来阐释“神似”胜过“形似”的理论。具体例子颇多,请参阅陈允吉《王维“雪中芭蕉”寓意蠡测》,见《唐音佛教辨思录》,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页1—11。这里不再引用。
到了当代,陈允吉教授对王维的诗画受佛教影响的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他广征博引,不但引用了释典和中国学人的著作,而且还引用了王维自己的著作。他引征了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四“诗忌”一条:
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
他认为,惠洪的思路是正确的,王维这一幅画确实是“妙观逸想之所寓”。但“寓”的是什么呢?惠洪没有明说,只暗示其中有佛教影响。陈允吉教授在这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利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能发古人之覆的深入的洞察力,经过详细的论证,引经据典,最后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综上所述,王维“雪中芭蕉”这幅作品,寄托着“人身空虚”的佛教神学思想。这种神学寓意的实质,不论从认识论或者人生观来说,都是体现出一种阴冷消沉的宗教观念,它的思想倾向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一定的艺术形式,总是为一定的思想内容服务的。如果说“雪中芭蕉”确实在艺术上具有“不拘形似”的特点,那末,它同样也是服膺于表现其神学寓意而出现的。(上引书,页10—11)
这结论是能令人信服的。这比沈括以及他的追随者的意见恢廓深入得多了。
写到这里,我一时心血来潮,忽然联想到《歌德谈话录》里谈到的一件事情。1827年4月18日,歌德叫人取出登载荷兰大画师们的作品复制件的画册,特别把其中的一幅吕邦斯的风景画指给爱克曼(谈话的记录者)看。这一幅画画的是太阳正要落山的黄昏时分的农村景色:有村庄,有市镇,有羊群,有装满干草的大车,有吃草的马,还有骡子和骡驹等等。这些都画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光线和阴影却出了问题:光是从对面的方向照射过来的,被照射对象的阴影投到画这边来。这也是符合自然现象的,没有注意和研究的必要。但是画中的一丛树却把阴影投到和看画者对立的那边去。结果是画中的人、兽、树丛等等,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受到光照。这是完全违反自然现象的。然而爱克曼在最初却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个矛盾。等到歌德指了出来,他才恍然大悟。在这个节骨眼上,歌德说了一段很长的话:
关键正在这里啊!吕邦斯正是用这个办法来证明他伟大,显示出他本着自由精神站得比自然要高一层,按照他的更高的目的来处理自然。光从相反的两个方向射来,这当然是牵强歪曲,你可以说,这是违反自然。不过尽管这是违反自然,我还是要说它高于自然,要说这是大画师的大胆手笔,他用这种天才的方式向世人显示:艺术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
歌德接着说:
艺术家在个别细节上当然要忠实于自然,要恭顺地摹仿自然,他画一个动物,当然不能任意改变骨骼构造和筋络的部位。如果任意改变,就会破坏那种动物的特性。这就无异于消灭自然。但是,在艺术创造的较高境界里,一幅画要真正是一幅画,艺术家就可以挥洒自如,可以求助于虚构(Fiktion),吕邦斯在这幅风景画里用了从相反两个方向来的光,就是如此。
艺术家对于自然有着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是自然的奴隶,因为他必须用人世间的材料来进行工作,才能使人理解;同时他又是自然的主宰,因为他使这种人世间的材料服从他的较高的意旨,并且为这较高的意旨服务。
下面还有不少十分精彩的议论,我不再抄录了,请读者参阅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页136—137。
为了细致深入地说明问题,我抄录得已经似乎太多了,但是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抄录歌德的原话,比我自己来阐释要好得多。
看了上面的故事,我想,谁也会立刻就发现,中国唐代王维的“雪中芭蕉”和德国19世纪歌德议论的荷兰大画家吕邦斯的风景画,虽然相距千余年,相去万余里,却有完完全全相似之处:都是违反自然的,都是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然而却又都是让人觉得很自然的。
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中国的评论家和西方的歌德采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评论家所采用的观点是——我想在这里借用陈允吉教授使用的一个现成的词儿——“咏物言志”,而歌德所采用的观点则是“高于自然”。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不想也没有能力去深究。我只是认为,从这一件小事上也可以反映出东西方评论重点的分歧:中国着重个人的“志”,也就是个人的思想感情,而西方的着眼点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分歧是再明显不过的。这是不是也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分歧有关呢?我认为是的。
我对于文艺理论只能算是一个业余的爱好者,决不敢冒充内行。堂奥未窥,妄论先发,其不贻笑大方者几希矣。但是一个外行或者半外行的看法有时候会为真正的内行所忽略,他们往往能看到内行视而不见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一个事实。真正的内行是“司空见惯浑无事”了,外行人却觉得新鲜。质诸方家,以为何如?
---1991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