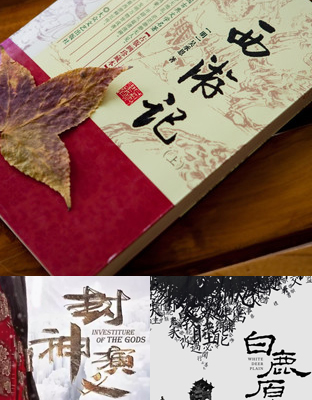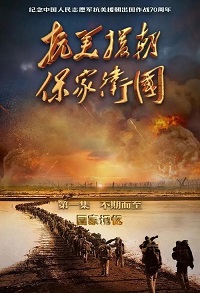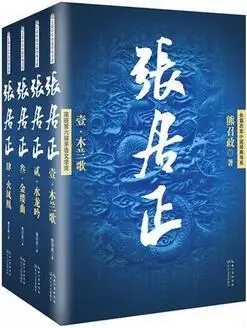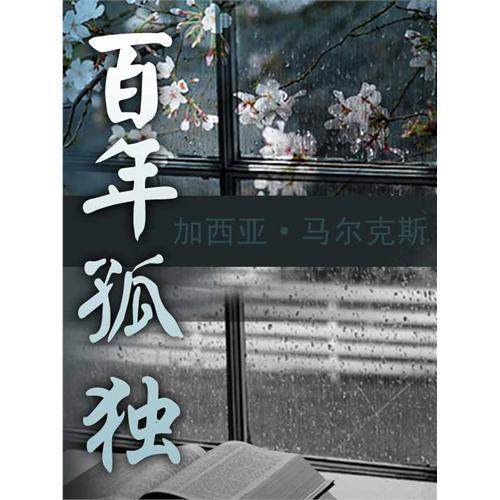守余有余,开疆不足
——略说沙陀枭雄李克用
“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
这是东汉末年名士裴潜对刘备的评论。事实也证明,刘备确实不具备曹操那样控制全局的能力,但乘间守险,遂成蜀汉偏霸。说来很巧合,朱温和曹操的人生轨迹非常相似,而唐末五代也有一个“刘备”,甚至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原,但得天时地利,乘间守险,也成一方伟业,他就是李克用。
李克用的名气,在历史上远不如他那个过山车般走完传奇人生的儿子李存勖。李存勖灭梁后,过足了“唐光武”的瘾。但李存勖的江山并不是他打下来的,如果没有父亲李克用在乱世中占据河东,以李存勖善攻而不善守的性格,他是很难赤手空拳打下江山的。当然,李克用的江山也是从他的老爹李国昌那里传来的。所不同的是,李国昌传给李克用的只是一间临街手工作坊,而李存勖却从父亲接过一家国际化大公司。在五代政治史上,其实是分为两个不同角度的政治层面:一个是单打独斗,最后被唐晋汉周否定的梁朝;另一个就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大王朝。而四大王朝的真正开创者,正是李克用。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对李克用多持正面评价,代后周而立的北宋对李克用也极尽恭维,称赞李克用是辅佐唐王朝从黄巢魔爪下重生的当代齐桓、晋文。
李克用其实不是汉人,而是西突厥的分支——沙陀人,后来改姓朱邪。姓李,是因为李克用率河东黑鸦军剿灭黄巢有功,唐王朝赐姓李,所以李克用一脉打着李唐宗室的旗号在江湖上“招摇撞骗”,其实他们的政权和唐朝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黄巢当初撤出长安后,在长安城中放火抢金银财宝的,就是李克用的沙陀兵,刘秀可从来没烧过长安城。不但如此,李克用甚至遭到了唐王朝的大兵镇压,原因是李克用虐杀朝廷委任的云州防御使段文楚。
五代十国宋初的创业帝王多为武将,比如李存勖、李嗣源、李从珂、石敬瑭、杨行密、郭威、柴荣、赵匡胤。而其中最负盛名者,当属人称“李横冲”的李嗣源,大名满河朔,但实际上要论武力指数,李克用当为第一!
因为生长在马踏胡月的边陲地区,李克用从小就学弓马劲射,十三岁时就射得一手好弓箭。有一次,天上飞来两只大雁,十三岁的李克用纵马出箭,“射之连中,众皆臣伏”。晚唐有一位著名的“落雕侍御”高骈,一箭能落双雕,李克用同样不让高骈。有人指天上双雕问李克用:“你能不能射下双雕?”李克用大笑,“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而这时的李克用,就已经“渺一目”,所以江湖人称“独眼龙”。一只眼就能射落双雕,可见李克用的功夫是何等了得。
有了一身好武艺,李克用十五岁时跟着父亲李国昌闯荡血雨腥风的江湖,就大杀四方,当时人称李克用是“飞虎子”,江湖新锐地位可见一二。人都是有野心的,得到第一块大饼后,总想再得到一块更大的饼。李克用在跟随父亲打败了朝廷方面的昭义军节度使李钧后,极具政治眼光地盯上了早成笼中困兽的黄巢。只要能拿下黄巢,李克用在政治上就可以摆脱累次被朝廷打压的负面政治形象。
一切都非常顺利,善于骑兵作战的四万河东黑鸦军将黄巢军打得风流云散,而李克用因为赶跑黄巢出长安立下头等功,唐王朝也知道是时候给李克用转正了,正式封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其实朝廷也知道,即使不封李克用,以李克用的实力,他早晚会霸占河东,不如做了顺水人情。
河东是天下第一大镇,监近大漠,拥有数量庞大的优质作战马匹,李克用的发迹不知道让多少人眼红。如果说唐王朝给李克用的是一块新做出来的美味蛋糕,那么给朱温的,不过是一块过了夜的硬馒头。正因为朱温觉得朝廷对自己赏赐不公,再加之眼红李克用吃到了肥肉,为绝后患,朱温在上源驿策划了一场骇人的大火。
朱温的计算非常精准,几乎对上源驿围得水泄不通,但朱三千算万算,唯独没有算到会突降大雨,浇灭了大火,让几乎无路可逃的李克用逃出生天。而朱温在上源驿火烧李克用,却被大雨浇灭,这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著名桥段“火烧上方谷”的原型。
有人常说汉人心眼比少数民族要多,或者说少数民族比起油滑的汉人相对比较朴实。如果从某种角度上看,也并非没有道理,至少李克用是拿朱温当兄弟的,李克用甚至都没想过将来要与朱温争天下。但朱温这场阴损的大火彻底烧醒了李克用,也把李克用待人的真诚彻底烧没了,所以李克用对朱温充满难以压制的怒火。
而更让李克用郁闷的是,明明自己吃亏在先,明明自己拥有天下最精锐的河东沙陀兵,可偏偏就拿无耻的朱三没有丝毫办法。要论二人事业的起点,李克用远高于朱温,但河东与汴州的发展轨迹却完全不同。朱温由弱到强,败秦宗权据淮西、杀朱瑄兄弟据兖郓,杀时溥据徐州,逐安师儒据郑滑,让魏博罗弘信俯首称臣,收降李罕之、张全义收河洛,平卢王师范举家骑驴归降。虽然清河一战被杨行密水淹七军,大将庞师古战死,朱温的触角被阻止在淮河以北,但朱温依然是天下头号强藩。而李克用虽然勇武过人,淮南王杨行密久慕河东独眼龙的大名,派人去河东画了李克用的画像观瞻,但李克用在对外开疆拓土方面却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死守河东一地。
河东,北有契丹阿保机,东有大燕刘守光、义武王处直、成德王镕、魏博罗绍威(罗弘信之子),南有朱温,西有夏银(西夏前身)李思恭、岐凤李茂贞,战略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虽然李克用恨透了朱温,但他的创业能力,根本无法给朱温制造大的生存威胁,只能对朱温零敲碎打,也没占多少上风,甚至还把一个儿子李落落给搭了进去。
这件事情发生在唐乾宁三年(896年)正月,李克用亲率沙陀兵来取魏博,而他所面对的正是仇人朱温。势力早已坐大的朱温根本没把李克用放在眼里,大将葛从周出马,生擒李落落,甚至还差点活捉李克用本人。李落落的下场是被朱温当场斩首,差点没把李克用心疼得晕过去。但客观来说,李落落的死,其实还是因为李克用的实力不足以让朱温产生敬畏,否则朱温也不敢杀李落落,反而会和李克用讨价还价。这和做人质是一个道理,输出人质的一方实力越强,控制人质方越不敢轻举妄动。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朱温觉得自己的实力足够吃掉李克用的,那又何必再和李克用称兄道弟?今天杀了你的儿子,明天人头落地的就是你这个独眼龙。
唐光化四年(901年)三月,这是李克用平淡人生中遭受到的第二次大劫难。第一次是朱温在上源驿差点烧死李克用;而第二次的苦主还是朱温。已经晋封梁王的朱温觉得是时候搞死李克用了,几乎是倾巢而出,数路强兵围剿李克用,粗略估计,计有:
氏叔琮出太行;
晋州刺史侯言出阴地关(今山西汾西东北);
洺州刺史张归厚出马岭关(今山西太谷东南);
葛从周出土门(即大名鼎鼎的井陉口);
义武节度使王处直出飞狐(今河北涞源);
魏博罗弘信的部将张文恭出新口(今河北磁县附近)。
六路大军集合,声势浩荡地直扑李克用的老巢太原府。
在当时的诸侯争霸格局中,朱温相当于“二战”后的美国,而李克用的河东最多也就相当于“二战”后的法国,是根本无法和美国相抗衡的。六路大军杀进河东,迫使很多河东大将投降朱温,梁军几乎扫掉了太原城所有的外围城镇,随后就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形势对李克用来说非常危急,他几乎发动全城老小死守城池,而朱温开始盘算哪一天能欣赏到李克用血淋淋的人头。
如果从唯心主义的天意论来看,老天对李克用是极为厚爱的,几次帮助李克用死里逃生。上源驿大火,突降一场大雨,而这次梁军围攻太原,虽然也下了一场大雨,客观上影响了李克用守城,他每天都泡在水里指挥守城。但这场大雨同样给汴军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汴军人马泡在大雨中,很快就暴发不可控的疟疾,大量士兵病倒。再加上后方粮草运输也出了麻烦,朱温权衡再三,只好灰头土脸地撤军,李克用侥幸逃过一劫。以后朱温虽然也数次敲打李克用,但朱温的精力主要用在与淮南杨行密的纠葛,以及在政治上控制唐王朝的内政上,对李克用实际上处在半放任的状态,李克用才终于可以缓过气来。
从军事能力上看,李克用不如朱温,就如同刘备不如曹操一样。这一点李克用也知道,单纯比大腿粗,李克用是玩不过朱温的,那就另辟蹊径,在政治上捞取对抗朱温的资本。
刘备之所以最后能三分天下,政治上的“投机”占了很大因素,刘备扛着“大汉皇族”的旗号,在政治上处处针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李克用同样如此,虽然李克用根本不是李唐血脉,但在政治上,李克用及其幕僚团队把李克用打扮成了忠于李唐王朝,誓死与逆臣朱温抗衡的一代忠臣。因为在政治上高举兴唐反梁的大旗,李克用与南方的反梁势力如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达到了某种程度的默契。晋、蜀、吴三国联合起来,在与梁朝的战略空间博弈上互相声援,有效地牵制了朱温的兵力,反而在客观上扩大了河东的生存空间。为日后李存勖的经典大逆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同陈武帝陈霸先为几近灭亡的江东汉文明留下了一丝微弱的火种,苦苦撑到了汉人杨坚建立大隋朝,汉文明才绵延不绝。
李克用在政治上成熟的体现还在于他坚决不称帝,为自己争取到了极高的政治声望。朱温代唐称帝后,西川王建立刻跟着称帝,并写信劝李克用也称帝。王建这么做,实际上是想让李克用与他一起分担称帝后的政治压力,天下人要骂王建,他得拉着李克用陪绑。李克用拒绝了王建所谓先称帝,等将来唐朝复兴,再把帝位还给李唐的荒唐建议。
李克用回复王建的这封信非常感人,应该是河东统治集团精心谋划过的。李克用在信中说自己深蒙唐朝三代厚恩,位至将相,名列宗籍,怎么能背唐自立?实际上,王建虽然称了帝,但淮南杨行密那一派却没有称帝,而杨吴一直打着复兴唐朝的旗号,甚至年号都一直沿用唐朝的天祐旧号。刘备称帝,是因为孙权并没有打着复兴汉朝的旗号,所以刘备可以亮出这杆破旗。但如果杨吴高举兴唐旗帜,而李克用称帝,即使李克用还用唐朝名号,那么天下正统依然在杨吴,而不在李克用。从这一点考虑,李克用拒绝称帝是非常明智的,而只要李克用不称帝,无论杨吴在政治上出什么幺蛾子,凭借李克用的“宗室”身份,他能获得的政治资本都要远大于杨吴。
李克用不称帝的心态和闽国开国大王王审知差不多。有人劝王审知称帝,王审知笑答:做个关门天子,不如做个开门节度使。为了过上帝王瘾,而牺牲自己手上并不多的战略政治资源,是非常愚蠢的,比如东汉末的袁术。
李克用不是不想称帝,而是现在称帝,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好处。人无利不往,李克用把自己打扮成前唐孤臣,不过是在演戏而已,和刘备自诩汉朝忠臣一样,当不得真。
玩政治的个个都是好演员,没点演技还怎么在江湖上混?但李克用在遍地枭雄的时代能所险守一方,那也是有真本事的。
李存勖教会我们在羽翼未丰之时如何以退为进
在纷繁杂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李存勖是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人物,他个人的生死荣辱,都极深刻地影响了公元10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如果不是李存勖作死,把自己打下来的五代第一疆域大国后唐生生地给折腾散架,就不可能有千古大帝后周世宗的横空出世,一扫残唐积秽;更不会有赵匡胤凭空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而骄傲地站在历史的最高点,接受万众膜拜的千古一帝,就是这个小名李亚子的沙陀人。
唐光启二年(886年)十月二十二日,一个幼弱的生命从李克用妻子曹夫人的肚子里爬出来的时候,李克用就觉得这个头胎儿子有些非同寻常,他似乎感觉到了这应该是老天在向他暗示着什么。
李克用虽然有十几个干儿子,但在有自己子嗣的情况下,不可能把江山传给外人。所以李克用非常重视对李存勖的培养,经史子集无所不教,诗词歌赋无所不传,李存勖在尚未成年时已是文武全才。
李存勖从小就含着金钥匙出生,更让人羡慕的是,他还是五代十国第二代中唯一一个见过唐昭宗李晔,并得到昭宗极高肯定的人。年仅十一岁的李存勖站在昭宗面前,但也许是李存勖有胡人血统,还没成年的李存勖就身材挺拔,面目俊美,从这个少年眼中流露出一股时人少见的英气。所以昭宗“一见骇之”,震惊看上去邋里邋遢的李克用怎么会有这么个英俊儿子。因为当时李克用已被唐朝正式列入李氏宗籍,而昭宗也知道自己是无力再兴复唐朝了,他认定眼前这个英俊少年将来必能成大器。昭宗送给了李存勖很多珍珠宝贝,但最让李存勖或者是说是李克用受用的,是昭宗摸着李存勖后背时说的一句评语:这个孩子长大后必能成为一代栋梁,希望他以后能忠孝唐室。
这句话对李克用来非常重要,这几乎就是在向天下人,特别是向朱温宣告: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勖才是大唐帝国的正统传人,这在政治上给予李克用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这句话对李存勖来说更加重要,因为昭宗的这句话也几乎定下了将来河东江山必须由李存勖继承的基调。后来李克用选定李存勖为储君,一则是因为李存勖文武全才;二则他是李家嫡长子;三则是昭宗的这句评语。在李存勖的综合条件都强于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如果李克用不选择李存勖,且不说会置河东于巨大的政治军事隐患之下,也等于在政治上简单地否定了昭宗皇帝。政治成熟的李克用是不可能做出这样自毁前程的蠢事的。但因为干儿子们势力太大,李克用不敢过早宣布立李存勖为嗣,否则那些带兵的干儿子铁定会闹事,甚至不排除有人引梁入室。再加上李克用还有个弟弟——总制河东禁军的内外蕃汉都知兵马使李克宁对那个位子也有点想法。所以直到907年,李克用行将咽气,才当众宣布由长子李存勖继承王位。
李存勖初出江湖,并没有多少威望。虽然李克用吹捧长子“此子志气远大,必能成吾事”,但无论是近亲宗室,还是养子名将,都不服李存勖。
河东天下在法理上是传给了李存勖,但面对身边一群虎狼,李存勖能不能守得住还是一个问题,历史上少主被废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李克用死的也不是时候,梁兵北攻河东的南线门户潞州,河东人情上下汹汹,一旦统治高层内部不稳,极易造成军情动荡,河东一夜崩溃也并非没有可能。而这一年,李存勖只有二十三岁。
李存勖并非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其实他最担心的暂时还不是在外领兵的所谓兄长们,而是近在肘腋的叔父李克宁。李克宁控制着太原近卫部队,“军中之中,无大小皆决克宁”。一旦李克宁有异心,不用李嗣源、李存信们在外起兵,李克宁一句话,李存勖就有可能人头落地。所以李存勖及其幕僚团队的对策,是先稳住李克宁,夺过近卫部队的指挥权,首先要确保自己在太原城的安全。
李存勖灭梁后,在政治上几乎就变成了一个傻子,但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还不算糊涂。李存勖首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弱势的君主,主动向李克宁示弱,绝不挑战李克宁现有的地位,以退为进。
李存勖装得可怜楚楚地站在李克宁面前,说自己年少德薄,情愿把晋王的位置让给叔父。“儿年幼稚,未通庶政,虽承遗命,恐未能弹压。季父勋德俱高,众情推伏。”
以当时李克宁“久总兵柄,有次立之势”的势力,他只要点头答应,至少在太原城中是没有人敢说什么闲话的。
离最高权力这么近,李克宁没有动心,出于权力制衡的考虑,李克宁没有答应李存勖所谓的让贤。李克宁的主要顾虑,还是那伙在外“各挽强兵”的干侄子们,这些人仗着军功,不但瞧不起寸功未立的李存勖,像李克宁这样靠哥哥李克用吃饭的,他们也照样瞧不上。这些强藩随便哪一个跳出来捣乱,都够李克宁喝一壶的。现在内外情势极为不稳,李克宁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出头接这个烫手山芋。
另外,李克宁和兄长李克用感情深厚,李克用死前希望李克宁能像照看自己的儿子一样看管好李存勖,再加上李存勖突然像待宰的羔羊一样可怜兮兮地求他,李克宁心一软,放过了李存勖。李克宁以叔父之尊给侄子李存勖行了君臣大礼,正式确定了李存勖的河东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渡过了这一劫难后,李存勖在太原城中的统治瞬间变得明朗起来。即使李克宁随后被自己的老婆孟氏说动,后悔自己的让位,和干侄子李存颢四处联系,图谋推翻李存勖,但在名分上,李克宁明显吃了亏。自己装蒜在前,又吃翔在后,很容易给人造成首鼠两端政治不可靠的观感,是很难收拢人心的。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克宁为了达到目的,竟然暗中向大梁朱温通款,准备通过向梁称臣割地,以换取朱温的有力支持。具体办法是等李存勖到李克宁府上饮酒时一刀杀之,举河东九州之地甘做朱温附庸。李克宁这么做,在政治上等于自杀!至少他背叛了李氏列祖列宗百战才血拼下来的河东社稷,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头号反贼。
李克宁亏大义在前,李存勖在政治上就有了极大的转圜空间,此时拿下李克宁,于情于理李存勖都是无可指责的。但李存勖不愧是梨园老祖师,演技极为精湛,他并没有着急拿下李克宁,而是把朝中所有反李克宁的势力召集起来,说什么自己年少德薄,既然叔父这么热衷王位,为了李家江山千秋万代,我情愿让位。张承业、李存璋等人向来与李克宁不和,怎么可能答应李存勖,自然群情激愤,“众咸愤怒”。李存勖成功地挑起了反李克宁势力铲除李克宁的强烈愿望,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李存勖摆了一场酒会,邀请李克宁等人赴宴,李克宁等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阴谋已经外泄,坦然赴约,结果被侄子命武士当场拿下。李存勖虽然年轻,但他在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他始终站在道义高地上,对李克宁的指责也合情合理。李克宁自知理亏,干脆认罪,只求速死。
“是日,杀克宁及存颢。”
由于李克宁的罪名是通款逆臣朱温,这在当时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之首,所以即使有人同情李克宁,也对李存勖无可指责。李存勖在政治上翻转腾挪,却始终有理有据,不让人抓住自己的丝毫把柄,所以李存勖能在杀李克宁之后迅速地稳定太原局势。
太原城中发生的这场宫廷政变,在外诸藩都在密切关注。太原是河东政治中枢,一动一静,都将极大地影响着周边藩镇的政治抉择。一旦太原陷入动荡,这些强藩要么会率兵杀回太原夺位,要么举城降附梁朝。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发生,李存勖脖子上的吃饭家伙都很难保全。而李存勖稳定了太原局势,断绝了外藩们打着各种政治旗号浑水摸鱼的可能,在太原稳定的情况下还要起兵,那道义就会始终站在李存勖一边。
这种情况很像南北朝萧梁末年,侯景兵围金陵城一年有余,虽然城内几陷险境,但始终没有沦陷,所以萧梁外围还算稳定。而等金陵城陷,梁武帝萧衍绝粮而死后,与西魏、北齐接壤的萧梁外围彻底崩溃,导致南朝弱势,最终为北朝吞并。如果萧衍能灭掉侯景,金陵在,则大梁在,西魏、北齐又怎么会有机会凭空捡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