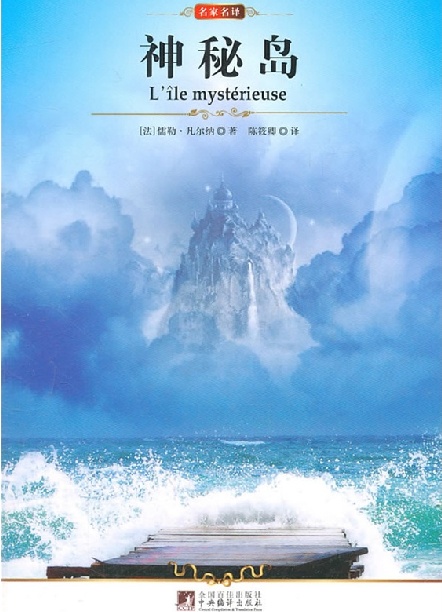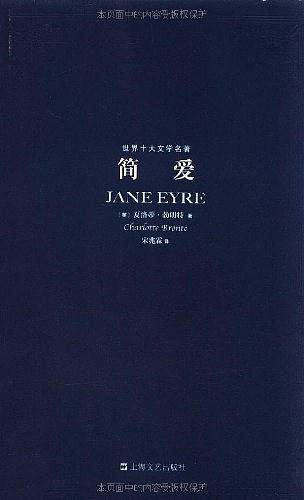窗外众汉子大声呼喝,鳌拜举起手铐铁链,往铁窗上猛击。韦小宝心想:“他如回过身来打我,老子可得要归天!”急急之下,不及细想,提起匕首,猛力向鳌拜后心戳去。
鳌拜服药后神知已失,浑不知背后有人来袭,韦小宝匕首戳去,他竟不知闪避,波的一声,匕首直刺入背。鳌拜张口狂呼,双手连着手铐乱舞。韦小宝顺势往下一拖,那匕首削铁如泥,直切了下去,鳌拜的背脊一剖为二,立即摔到。窗外一众青衣人霎时之间都怔住了,似乎见到了世上最稀奇古怪之事。三四人同时叫了出来:“这小孩子杀了鳌拜!这小孩杀了鳌拜!”
那长须人道:“撬开铁窗,进去瞧个明白,是否真的鳌拜!”当下便有二人拾起钢鞭,用力扳撬窗上铁条。两名王府卫士冲进室来,长须人挥动弯刀,一一砍死。一名青衣汉子提起短枪,隔窗向韦小宝不住虚刺,令他无法走进窗格伤人。
过不多进,铁条的空隙扩大,一个青衣瘦子说道:“待我进去!”从铁条空隙间跳进囚室。韦小宝举匕首向他刺去。那瘦子举刀一挡,嗤的一声响,单刀断为两截。那瘦子一惊,手中断刀向韦小宝掷出。韦小宝低头闪避,双手手腕已被那瘦子抓住,顺势反到背后。另一个青衣汉子举刀架在他颈中,喝道:“不许动!”窗上的铁条又撬开了两根,长须人和一名身穿青衣的秃子钻进囚室,抓住鳌拜的辫子,提起头来一看,齐声道:“果是鳌拜!”长须人想将尸首推出窗外,但铐镣上的铁链牢牢钉在石墙之中,一进无法弄断。那瘦子拿起韦小宝的匕首,嗤嗤四声响,将连在鳌拜尸身上的铁链割断了。长须人赞道:“好刀!”将尸身从窗格中推出,外边的肯衣汉子拉了出去。那瘦子将韦小宝推出,余下三人也都钻出囚室。长须人发令:“带了这孩子走!大伙儿退兵!”众人齐声答应,向外冲出。一名青衣大汉将韦小宝挟在肋下,冲出石屋。只得飕飕声响,箭如飞蝗般射来。王府中二十余名卫士不住放箭,康亲王提刀亲自督战。
众青衣人为箭所阻,冲不出去。抱着鳌拜尸首的是个道士,叫道:“跟我来!”举起尸身挡在身前。康亲王见到鳌拜,不知他已死,又见韦小宝被刺客拿住,大叫:“停箭!别伤了桂公公!”韦小宝心想:“康亲王倒有良心,老子会记得你的!”王府弓箭手登时停箭。那些青衣汉子高声呐喊,冲出石屋。那长须人手一挥,四名汉子疾向康亲王冲去。众卫士大惊,顾不得追敌,都赤保护王爷,岂知这是那长须人声东击西之计,余人乘隙跃上围墙,逃出王府。攻击康亲王的四名汉子轻功甚佳,并不与众卫士交手,东一窜,西一纵,似乎伺机要取康亲王性命,待得同伴尽数出了王府,四人几声呼啸,跃上围墙,连连挥手,十余件暗器份向康亲王射去。众卫士又是连声惊呼,挥兵刃砸暗器,但还是有一枝钢镖打中了康亲王左臂。这么一阵乱,四名青衣汉子又都出了王府。
韦小宝被一条大汉挟在肋下飞奔,但听得街道上蹄声如雷,有人大叫:“康亲王府中有刺客!”正是大队官军到来增援。一众青衣汉子奔入王府旁的一间民房,闩上了大门,又从后门奔出,显然这些人干事之前,早就把地形察看明白,预备了退路。在小巷在奔行一程,又进了一间民房,仍是从后门奔出,转了几个弯,奔入一座大宅之中。
各人立刻除下身上青衣,迅速换上各式衣衫,顷刻间都扮成了乡家模样,挑柴的挑柴,挑菜的挑菜。一名汉子将韦小宝用麻绳牢牢绑住。两名汉子推过一辆木车,车上有两只大木桶,将鳌拜的尸体和韦小宝分别装入桶中。韦小宝心中只骂得一句:“他妈的!”头上便有无数枣子倒下来,将他盖没,桶盖盖上,什么也瞧不见了。跟着身子晃动,料想木车推出大门。枣子之间虽有空隙,不致窒息,却也呼吸困难。韦小宝惊魂略定,心想:“这些鳌拜的家将部属把老子拿了去,势必要挖出老子的心肝来祭鳌拜。最好是途中遇上官兵,老子用力一滚,木桶翻倒,那便露出了马脚。”可是四肢被紧紧绑住,哪里动得分毫?木桶外隐隐传来辚辚车声,身子颠簸不已,行了良久,又哪里遇到官兵了?韦小宝咒骂一阵,害怕一阵,忽然张口咬了一枚枣子来吃,倒也肥大香甜,吃得几枚,惊惧之余,极其疲倦,过不多时,竟尔沉沉睡去。一觉醒来,车子仍是在动,只觉全身酸痛,想要转动一下身子,仍半分动弹不得,心想:“老子这次定然逃不过难关了,待会只好大骂一场,出一口心中的恶气,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大汉。”又想:“幸亏我已将鳌拜杀了,否则这厮被这批狗贼救了出去,老子又被他们拿住,一样的难以活命,死得可不够本。鳌拜是朝廷大官,韦小宝只不过是丽春院的一个小鬼,一命拚一命,老子便宜之极,哈哈,大大便宜!”既然无法逃命,只好自己如此宽解,虽说便宜之级,心中却也没半点高兴。过了一会,便又睡着了,这一觉睡得甚久,醒来时发觉车子所行的地面甚为平滑,行得一会,车子停住,却没有人放他出来,让他留在枣子桶中。过了大半天,韦小宝气闷之极,又要朦胧睡去,忽听得豁啦一响,桶盖打开,有人在捧出他头顶的枣子。韦小宝深深吸了口气,大感舒畅,睁开眼来,只见黑沉沉地,头顶略有微光。有人双手入桶,将他提了起来,横抱在手臂之中,旁边有人提着一盏灯笼,原来已是夜晚。韦小宝抱着他的是个老者,神色肃穆,处身所在一是一个极大的院子。
那老者抱着韦小宝走向后堂,提着灯笼的汉子推开长窗。韦小宝暗叫一声:“苦也!”不知高低,但见一座极大的大厅之中,黑压压的站满了人,少说也有二百多人。这些人一色青衣,头缠白布,腰系白带,都是戴了丧,脸含悲愤哀痛之色。大厅正中设着灵堂,桌上点燃着八根极粗的蓝色蜡烛。灵堂旁挂着几条白布挽联,竖着招魂幡子。韦小宝在扬州之时,每逢大户人家有丧事,总是去凑热闹,讨赏钱,乘人忙乱不觉,就顺手牵羊,拿些器皿藏入怀中,到市上卖了,便去赌钱,因此,灵堂的陈设看得惯了,一见便知。他在枣桶中时,早料到会被剖心开膛,去祭鳌拜,此刻事到临头,还是吓得全身皆酥,牙齿打战,格格作响。那老者将他放下,左手抓住他肩头,右手割断绑住他手足的麻绳。韦小宝双足酸软,无法站定。那老者伸手到他右肋之下扶住。韦小宝见厅上这些人显然都有武功,自己只怕一个也打不过,要逃走那是千难万难,但左右是个死,好在绑缚已解,总得试试,最不济逃不了,给抓了回来,一样的开心剖膛,难道还能多开一次,多剖一回?眼前切要之事,第一要那老头子的手不在自己肋下托住,以免身子一动便给他抓住;第二要设法弄熄灯笼烛火,黑暗一团,便有脱身之机。
他偷眼瞧厅上众人,只见各人身上都挂插刀剑兵刃。一名中年汉子走到灵座之侧,说道:“今日大......大仇得报,大......大可你可以眼闭......眼闭了。”一句话没说完,已泣不成声。他一翻身,扑倒在灵前,放声大哭。厅上众人跟着都号啕大哭。韦小宝心道:“辣块妈妈,老子来骂几句。”但立即转念:“我开口一骂,这些乌龟王八蛋向老子动手,可逃不了啦。”斜眼见托着自己的老者正自伸衣袖拭泪,便想转身就逃,但身后站满了人,只须逃出一步,立时便给人抓住,心想时机未到,不可卤莽。
人丛中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上祭!”一名上身赤裸,头缠白布的雄壮大汉大踏步走上前来,手托木盘,高举过顶,盘中铺着一块细布,细布上赫然放着一个血肉模糊的人头。韦小宝险些儿晕去,心想:“辣块妈妈,这些王八蛋要来割老子的头了。”又想:“这是谁的头?是康亲王吗?还是索额图的?不会是小皇帝的罢?”木盘高举得甚高,看不见首级面容。那大汉将木盘放在供桌上,扑地拜倒。大厅上哭声又振,众人纷纷跪拜。韦小宝心道:“他妈的,此时不走,便待何时?”转身正欲奔跑,那老者拉拉他家袖,腿上没半点力气,给他一推之下,立即跪倒,见众人都在磕头,只好跟着磕头,心中大骂:“贼鳌拜,乌龟鳌拜。老子一刀戳死了你,到得阴间,老子又再来戳你几刀!”
有些汉子拜毕站起身来,有些兀自伏地大哭。韦小宝心想:“男子汉大丈夫,这般大哭也不怕羞,鳌拜这王八蛋有什么好,死了又有什么可惜?又用得着你们这般大流马尿?”众人哭了一阵,一个高高瘦瘦的老者走到灵座之侧,朗声说道:“各位兄弟,咱们尹香主的大仇已报,鳌拜这厮终于杀头,实是咱们天地会青木堂的天大喜事......”
韦小宝听到“鳌拜这厮终于杀头”八个字,耳中嗡的一声,又惊又喜,一个念头闪电似的钻入脑中:“他们不是鳌拜的部属,反是鳌拜的仇人?”那高瘦老者下面的十几句话,韦小宝全然听而不闻,过了好一会,定下神来,才慢慢将他说话听入心中,但中间已然漏了一大段,只听他说道:“......今日咱们大闹康亲王府,杀了鳌拜,全师而归,鞑子势必丧胆,于本会反清复明的大业,实有大大好处。本会各堂的兄弟们知道了,一定佩服咱们青木堂有智有勇,敢作敢为。”众汉子纷纷说道:“正是,正是!”“咱们青木堂这次可大大的露了脸。”“莲花堂、赤火堂他们老是自吹自擂,可哪有青木堂这次干得惊逃诏地!”“这件事传遍天下,只怕到处茶馆中都要编成了故事来唱。将来把鞑子逐出关外,天地会青木堂名垂不朽!”“什么把鞑子逐出关外?要将众鞑子斩尽杀绝,个个死无葬身之地。”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精神大振,适才的悲戚之情,顷刻间一扫而空。
韦小宝听到这里,更无怀疑,知道这批人是反对朝廷的志士。他在遇到茅十八之前,在扬州街坊市井之间,便已常听人说起天地会反清的种种侠义事迹。当年清兵攻入扬州,大肆屠杀,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谓:“扬州一日,嘉定三屠”,实是惨不堪言。扬州城中几乎每一家人家,都有人在这场大屠杀中遭难。因之对于反清义士的钦佩,扬州人比之别地人氏,无形中又多了几分。其时离“扬州十日”的惨事不过二十几年,韦小宝从小便听人不断说起清军的恶行,又听人说史阁部如何抗敌殉难,某人又如何和敌兵同归于尽。这次茅十八和众盐枭在丽春院中打架,便是为了强行替天地会出头而起,一路上听他说了不少天地会的英雄事迹,又有什么“为人不见陈近南,就称英雄也枉然”等等言语,心中早已万分向往仰慕,这时亲眼见到这一大群以杀鞑子为已任的英雄豪杰,不由得大为兴奋,一时意忘了自己是鞑子朝廷中“小太监”身份。那高瘦老者待人稍静,续道:“咱青木堂这两年中,时时刻刻记着尹香主尹大哥的大仇,人人在万云龙大哥的灵前沥血为誓,定要杀了鳌拜这厮为尹大哥报仇。尹香主当时慷慨就义,江湖上人人钦仰,今日他在天之灵,见到了鳌拜这个狗头,一定会仰天大笑。”众人都道:“正是,正是!”
人丛中一个雄壮的声音道:“两年前大伙儿立誓,倘若杀不得鳌拜,我青木堂人人都是狗熊灰孙子,再也没脸面在江湖上行走。今日终于雪了这场奇耻大辱。我姓樊的这两年饭也吃不饱,觉也睡不好,日思夜想,就是打算给尹香主报仇,为青木堂雪耻,大伙儿终于心愿得偿,哈哈,哈哈!”许多人跟着他都狂笑起来。
那高瘦老者说道:“好,我青木堂重振雄风,大伙扬眉吐气,重新抬起头来做人。这两年来,青木堂兄弟们个个都似无主孤魂一般,在天地会中聚会,别堂的兄弟只消瞧我一眼,冷笑一声,我就惭愧得无地自容,对会中的大事小右,不敢插嘴说一句话。虽然总舵主几次传了话来,开导咱们,说道为尹香主报仇,是天是会全体兄弟们的事,决不是青木堂一堂的事。可是别堂兄弟们冷言冷语,却不这么想啊。自今而后,那可是大不相同了。”另一人道:“对,对,李大哥说得对,咱们乘此机会,一鼓作气,轰轰烈烈的再干他几件大事出来。鳌拜这恶贼号称‘满洲第一勇士’,今日死在咱们手下,那些满洲第二勇士,第三勇士,第四勇士,那是个个怕得要死了!”
众人一听,又都轰然大笑起来。韦小宝心想:“你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倒像小孩儿一般。”
人丛中忽然有个冷冷的声音说:“是我们青木堂杀了鳌拜么?”
众人一听此言,立时静了下来,大厅中聚着二百来人,片刻之间鸦雀无声。
过了良久,一人说道:“杀死鳌拜的,虽是另有其人,但那也是咱们青木堂攻入康亲王府之后,那人乘着混乱,才将鳌拜杀死。”
先前那人又冷冷的道:“原来如此。”
那声音粗壮之人大声道:“祁老三,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祁老三仍是冷言冷语:“我又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一点也没有意思!只不过别堂中兄弟如果说道:‘这番青木堂可当真威风啦!但不知杀死鳌拜的,却是贵堂中哪一位兄弟?’这一句话问了出来,只怕有些儿难以对答。大家不妨想想,这句话人家会不会问?只怕一千个人中,倒有九百九十九个要问罢!大伙儿自吹自擂,尽往自己脸上贴金,未免......未免有点......嘿嘿,大伙儿肚里明白!”众人尽皆默然,都觉他说话刺耳,听来极不受用,但这番话却确是实情,难以辩驳。
过了好一会,那高瘦老者道:“这个清宫中的小太监阴错阳差,杀了鳌拜,那自是尹香主在天之灵暗中佑护,假手于一个小孩子,除此大奸。大家都是铁铮铮的男子汉,也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众人面面相虐觑,有的不禁摇头,本来兴高采烈,但想到杀死鳌拜的并非青木堂的兄弟,登时都感大为扫兴。那高瘦老者道:“这两年来,本堂无主,大伙儿推兄弟暂代执掌香主的职司,。现下尹香主的大仇已报,兄弟将令牌交在尹香主灵前,请众兄弟另选贤能。”说着在灵座前跪倒,双手拿着一块木牌,拜了几拜,站起身来,将令牌放在灵位之前。一人说道:“李大哥,这两年之中,你将会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我香主之位,除了你之处,又有谁能配当?你也不用客气啦,乘早将令牌收起来罢!”众人默然半晌。另一人道:“这香主之位,可并不是凭着咱们自己的意思,要谁来当就由谁当。那是总舵主委派下来的。”
先一人道:“规矩虽是如此,但历来惯例,每一堂商定之后报了上去,上头从来没驳回过,所谓委派,也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
另一人道:“据兄弟所知,各堂的新香主,向来都由旧堂主推荐。旧香主或者年老,或者有病,又或是临终之时留下遗言,从本堂兄弟之中挑出一人接替,可就从来没有自行推选的规矩。”
先一人道:“尹香主不幸为鳌拜所害,哪有什么遗言留下?贾老六,这件事你又不是不知,又干么在这时挑眼了?我明白你的用意,你反对李大哥当本堂香主,乃是心怀不轨,另有图谋。”韦小宝听到“贾老六”三字,心下一凛,记得扬州众盐枭所要找的就是此人,转头向他瞧去,果见他头顶头秃秃地,一根小辫子上没剩下几根头发,脸上有个大刀疤。
那贾老六怒道:“我又心怀什么不轨,另有什么图谋?崔瞎子,你话说得清楚些,可别含血喷人。”
那姓崔之人少了一只左目,大声道:“哼,打开天窗说亮话,青木堂中,又有谁不知道你想捧你姊夫关夫子做香主。关夫子做了香主,你便是国舅老爷,那还不是大权在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吗?”贾老六大声道:“关夫子是不是我姊无,那是另一回 事。这次攻入康王府,是关夫子率领的,终于大功告成,奏凯而归,凭着我姊无的才干,他不能当香主吗?李大哥资格老,人缘好,我并不是反对他。不过讲到本事,毕竟还是关夫子行得多。”
崔瞎子突然纵声大笑,笑声中充满了轻蔑之意。贾老六怒道:“你笑什么?难道我的话说错了?”崔瞎子笑道:“没有错,咱们贾六哥的话怎么会错?我只是觉得关无子的本事太也厉害了些。五关是过了,六将却没有斩。事到临头,却将一个大仇人鳌拜,让人家小孩儿一刀杀了。”突然人丛中走出一人,满脸怒容在灵座前一站,韦小宝认得他便是率领众人攻入康亲王府的那个长须人。见他一部长须飘在胸前,模样甚是威严。原来此人姓关,名叫安基,因胡子生得神气,又是姓关,大家便都叫他关夫子。他双目瞪着崔瞎子,粗声说道:“崔兄弟,你跟贾老六斗口,说什么都可以,我姓关的可没的罪你。大家好兄弟,在万云龙大哥灵前赌过咒,发过誓来,说什么同生共死,我这般损我,是什么意思?”
崔瞎子心下有些害怕,退了一步,说道:“我......我可没敢损你。”顿了一顿,又道:“关二哥,你......你如赞成推举李大哥作本堂香主,那么......那么做兄弟的给你磕头赔罪,算是我说错了话。”关安基铁青着脸,说道:“磕头赔罪,那怎么敢当?本堂香主由谁来当,姓生的可不配说这一句话。崔兄弟,你也还没当上天地会的总舵主,青木堂的香主是谁,还轮不到你来说话。”
崔瞎子又退了一步,大声道:“关二哥,你这话也不明摆着损人吗?我崔瞎子是什么脚色,便是再投十八次胎,也挨不上当天地会的部舵主。我只是说,李力世李大哥德高望重,本堂之中,再也没哪一位像李大哥那样,教人打从心窝里佩服出来。本堂的香主倘若不是请李大哥当,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都会不服。”人丛中有一人道:“崔瞎子,你又不是本堂十之八九的兄弟,怎知道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不服?我看啊,李大哥人是挺好的,大伙儿跟他老人家喝喝酒,晒晒太阳,那是再好不过的。可是说到做本堂香主,只怕十之八九的兄弟们心中大大的不以为然。”
又一人道:“我说呢,张兄弟的话对得不能再对。德高望重又怎么样?咱们天地会是反清复明,又不是学孔夫子,讲什么仁义道德。德高望重,就能将鞑子吓跑吗?要找德高望重之人,私塾中整天‘诗云子曰’的老秀才可多得很。”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