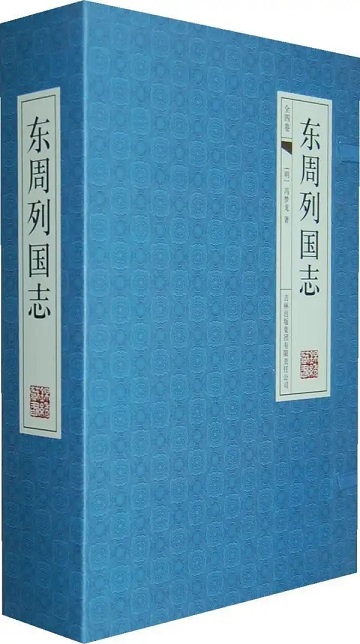韦小宝出宫去和李力世、关安基、玄贞道人、钱老本等人相见。天地会群雄尽皆欢然。李力世道:“属下刚得到讯息,总舵主已到天津,日内就上京来。韦香主也正回京,那真太好了。”韦小宝道:“是,是。那真太好了!”想到再见师父,心下不免惴惴。群雄当即打酒杀鸡,为他接风。傍晚时分,韦小宝将马彦超拉在一旁,说道:“马大哥,请你给我预备一的把斧头,还要一柄铁锤,一把凿子。”马彦超答应了,去取来他。韦小宝命他带到停放在那口棺木的园中土屋,说道:“我要打开棺材,放些东西进去。”马彦超应道:“是!”甚觉奇怪,但香主不说,也不便多问。韦小宝道:“前天夜里,这个死了的朋友托梦,说要这件东西。瞧在朋友一场,非给他不可。”马彦超更奇怪了,唯唯称是。韦小宝道:“你给我守在门外,谁也不许进来。”当下推门而入,关上了门,上了门闩。见那口棺木上灰尘厚积,显是无人动过,用凿子斧头逐一撬开棺材钉,推开棺盖,取出包着那五部经书的油布包,正要推上棺盖,忽听得马彦超在门外呼喝:“什么人?”接着有人问道:“陈近南在哪里?”韦小宝吃了一惊:“谁问我师父?”听口音依稀有些熟悉。
马彦超道:“你是谁?”又有一人冷冷的道:“不论他躲到哪里,总能揪他出来。”这人的声音韦小宝入耳即知,即是郑克爽。他更加惊奇:“怎么这臭小子到了这里?”随即想到,先前说话之人乃是“一剑无血”冯锡范。只听得铮的一声,兵刃相交,跟着马彦超闷哼一声,砰的一声倒地。韦小宝一惊更甚,当下不及细想,纵身入棺材,只听得郑克爽道:“这叛贼定是躲在里面。”韦小宝惊惶之下,托起棺盖便即盖上,紧跟着喀喇一声,土屋的木门已被踢破,郑克爽和冯锡范走了进来。韦小宝从棺材内望出去,见到一线亮光,知道慌忙之中,棺材盖并未密合,暗暗叫苦:“糟糕,糟糕!他们要找我师父,却找到了他徒弟。”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公子要找我吗?不知有什么事?”正是师父陈近南的声音。韦小宝大喜:“师父来了。”
突然之间,陈近南“啊”的一声大叫,似乎受了伤。跟着铮铮两声,兵刃相交。陈近南怒喝:“冯锡范,你忽施暗算?干什么了?”冯锡范冷冷的道:“我奉命拿你!”只听郑克爽道:“陈永华,你还把我放在眼里么?”语气中充满怒意。陈近南道:“二公子何出此言?属下前天才得知二公子临北京,连夜从天津赶来。不料二公子先到了。属下未克迎迓,还请恕罪。”韦小宝听师父说道恭谨,暗骂:“狗屁二公子,神气什么?”
只听郑克爽道:“父王命我到中原公干,你总知道罢?”陈近南道:“是。”郑克爽道:“你既得知,怎地不早来随侍保护?”陈近南道:“属下有几件紧急大事要办,未能分身,请二公子原谅。属下又知冯大哥随侍在侧,冯大哥神功无敌,群小慑伏,自能卫护二公子平安周全。”郑克爽哼了一声,怒道:“怎么我来到天地会中,你手下为些虾兵蟹将,狐群狗党,对我又如此无礼?”陈近南道:“想是他们不识二公子。在这京师之地,咱们天地会干的又是反叛鞑子之事,大家特别小心谨慎,以致失了礼数。属下这里谢过。”韦小宝越听越怒,心道:“师父对这臭小子何必这样客气?”
郑克爽道:“你推得一干二净,那么反倒是我错了?”陈近南道:“不敢!”随怒听到纸张翻动之声,郑克爽道:“这是父王的谕示,你读来听听。”陈近南道:“是。王爷谕示说:‘大明延平郡王令曰:派郑克爽前赴中原公干,凡事利于国家者,一要便宜行事。’”郑克爽道:“什么叫做‘便宜行事’?”韦小宝心想:“便宜就是不吃亏,那有什么难解的?你老子叫你有便宜就占,不必客气。”哪知陈近南却道:“王爷吩咐二公子,只要是不利于国家之事,可以不必回禀王爷,自行处断。”郑克爽道:“你奉不奉父王谕示?”陈近南道:“王爷谕示,属下自当遵从。”郑克爽道:“好,你把自己的右臂砍了去罢。”
陈近南惊道:“却是为何?”郑克爽冷冷的道:“你目无主上,不敬重我,就是不敬重父王。我瞧你所作所为,不有不臣之心,哼,你在中原拚命培植自己势力,扩充天地会,哪里还把台湾郑家放在心上。你想自立为王,是不是?”陈近声颤声道:“属下决无此意。”郑克爽道:“哼!决不此意?这次河间府大会,他们推我为福建省盟主,你知道么?”陈近南道:“是。这是普天下英雄共敬王爷忠心为国之意。”郑克爽道:“你们天地会却得了几省盟主?”陈近南默然。韦小宝心道:“他妈的,你这小子大发脾气,原来是喝天地会的醋。”又想:“我老婆的奸夫是我师父的上司,本来这件事很有点麻烦。现下他二人大起冲突,那是妙之极矣。只不过师父中了暗算,身上受伤,可别给他们害死才好。”
只听郑克爽大声道:“你天地会得了三省盟主,我却只有福建一省。跟你天地会相比,我郑家算老几?我只不过是小小福建省的盟主,你却是‘锄奸盟’总军师,你这可不是爬到我头上去了啦?你心里还有父王没有?”陈近南道:“二公子明鉴:天地会是属下秉承先国姓爷将令所创,旨在驱除鞑子。天地会和王爷本是一体,不分彼此。天地会的一切大事,属下都禀明王爷而行。”郑克爽冷笑道:“你天地会只知有陈近南,哪里还知道台湾郑家?就算天地会当真成了大事,驱逐了鞑子,这天下之主也是你陈近南,不是我们姓家的。”陈近南道:“二公子这话不对了。驱除鞑子之后,咱们同奉大明皇室后裔姓朱的为主。”郑克爽道:“你话倒说得漂亮。此刻你已不把姓郑的放在眼里,将来又怎会将姓朱的放在眼里?我要你自断一臂,你就不奉号令。这一次我从河间府回来,路上遇到不少危难,却不见有你天地会的一兵一卒来保护我,若不是冯师父奋力相救,我这时候,也不知是不是还留得性命。你巴不得我命丧小人之手,如此用心,便已死有余辜。哼,你就只会拍我哥哥的马屁,平时全没将我瞧在眼里。”陈近南道:“大公子、二公子是亲兄弟,属下一般的侍奉,岂敢有所偏颇。”郑克爽道:“我哥哥日后是要做王爷的,在你眼中,我兄弟俩怎会相同?”韦小宝听到这里,已明白一大半,心想:“这小子想跟他哥哥争位,怪我师父拥他哥哥,受了冯锡范的挑拔,便想乘机除了我师父。”只听郑克爽又道:“反正你在中原势大,不如就杀了我罢。”
陈近南道:“二公如此相逼,属下难以分说,这就回去台湾,面见王爷,听由王爷吩咐便是。王爷若要杀我,岂敢违命。”郑克爽哼了一声,似乎感到难以回答,又似怕在父亲面前跟他对质。
冯锡范冷冷的道:“只怕陈先生一离此间,不是去投降鞑子,出卖了二公子,便独树一帜,自立为王,再也不回台湾台湾去的了。”陈近南怒道:“你适才偷袭伤我,是奉了王爷之命吗?王爷的谕示在哪里?”冯锡范道:“王爷将令,二公子在中原便宜行事。不奉二公子号令,便是反叛,人人得而诛之。”陈近南道:“二公子好端端地,都是你从中挑拔离间。国姓爷创业维艰,这大好基业,只怕要败坏在你这等奸诈小人手里。你姓冯的就算武功天下无敌,我又何惧于你?”冯锡范厉声道:“如此说来,你是公然反叛延平王府了?”陈近南郎声道:“我陈永华对王爷赤胆忠心,‘反叛’二字,再也诬加不到我头上。”郑克爽喝道:“陈永华作反,给我拿下。”冯锡范道:“是。”只听得铮铮声响,兵刃相撞,三人交起手来。陈近南叫道:“二公子,请你让在一旁,属下不能跟你动手。”郑克爽道:“你不跟我动手?你不跟我动手?”连问了两句,兵刃响了两下,似是他问一声,向陈近南砍一刀。
韦小宝大急,轻轻将棺材盖推高寸许,望眼出去,只见郑克爽和冯锡范分自左右夹攻陈近南。陈近南左手执剑,右臂下垂,鲜血不断下滴,自是给冯锡范偷袭所伤。冯锡范剑招极快,陈近南奋力抵御。郑克爽一刀刀横砍直劈,陈近南不敢招架,只得闪避,变成了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加之右手使剑不便,右臂受伤又显然不轻。韦小宝心下焦急:“风际中、关夫子、钱老本他们怎么一个也不进来帮忙?这样打下去,师父非给他们杀了不可。”但外面静悄悄地,土屋中乒乒乓乓的恶斗似充耳不闻。只见冯锡范挺剑疾刺,势道极劲,陈近南举剑挡格,双剑立时相粘。郑克爽挥刀斜砍,陈近南侧身避开。郑克爽单刀横拖,嗤的一声轻响,在陈近南的左腿上划了一道口子。陈近南“啊”的一声,长剑一弹而起,冯锡范就势挺剑,正中他右肩。陈近南浴血奋战,难以支持,一步步向门口移动,竟欲夺门而出。冯锡范知他心意,抢到门口堵住,冷笑道:“反贼,今日还想脱身么?”
韦小宝只盼冯锡范走到棺材之旁,就可从棺材中挺匕首刺出,便以客店中杀喇嘛的手法杀了他。这一招“隔板刺人”原是他的生平绝招,远胜拳术高手的“隔山打牛”。可是冯锡范越斗越远,却如何刺得着他?郑克爽道:“反贼,还不弃剑就缚?”韦小宝眼见情势危急,心想今日舍了性命也要相救师父,逼紧了吩咐喉咙,突然吱吱的叫了两声。冯锡范等三人一听,都吃了一惊。郑克爽问道:“什么?”冯锡范摇了摇头,手上丝毫不缓。韦小宝又吱吱的叫了三下。郑克爽怕鬼,吓得打了个寒战。突见棺材盖一开,一团白色粉末飞了出来,三人登时眼睛刺痛,呛个不住。原来尸体入殓,棺材中必入大量石灰,当日马彦超曾购置了装入,此刻韦小宝抓起一大把,撒了出来。
冯锡范情知决非鬼魅,急跃而前,闭住了眼睛,俯身向棺材中挺剑刺落。突的一声,剑尖刺入棺材盖,正待拔剑再刺,突觉右边胸口一痛,知是中了暗算,急忙纵身跃起,后心重重撞在墙上。他武功了得,左手按住胸前伤口,右手将一柄使得风雨不透,护住身前。韦小宝在棺材中“隔板刺人”,一刺得手,握着匕首跳了出来,只见冯锡范、郑克爽和陈近南三人都紧闭双目,将刀剑乱挥乱舞,见冯锡范虽然胸口中剑,却非致命之伤,要待欺近前去再加上一剑,但冯郑二人刀剑舞得甚紧,实不敢贸然上前。此刻时机紧近,待得他二人抹去眼中石灰,睁眼见物,那就糟了,一时无策,只得左手抓起石灰,一见冯锡范或郑克爽伸手去抹眼睛,便一把石灰撒将过去。撒石灰原是他另一项拿手绝招。只掷得几下,冯锡范觉到掷石灰的方位,一招“渴马奔泉”,挺剑直刺过来。韦小宝大骇,急忙坐倒,噗的一声,那剑插入了棺材之中。韦小宝连爬带滚,逃出门外。冯锡范提剑在棺中连劈连刺,还道敌人仍然在内。以他武功修为,韦小宝狼狈万状的逃出,本可立时察觉,只是徒然间眼不见物,胸口受伤,一时心神大乱,又知陈近南武功卓绝,不在自己之下,强敌在侧,实是凶险无比,惶急间全没想到陈近南也已眼不见物,只盼杀了暗算之人,立即逃出。他在棺材中刺得数下,都刺了个空,随即一个“千岩竞秀”,剑花点点,护住身周,听得左边并无兵刃劈风之声,当下向左跃去,肩头在墙上一撞,靠墙而立。
这么一阵全力施为,胸前伤口中更是鲜血迸流。他微一睁眼,石灰粉末立时入眼,剧痛难当,生怕眼睛就此瞎了,不敢再睁,背靠墙壁,一步步移动,心想只须挨墙移步,便能打到门户所在,一出门外,地势空旷,就易于脱险了。韦小宝站在门口,见他移到身子,已猜知他心意,只待他摸到门口时刺他一剑,但想此人武功太高,就算刺中,他临时回手一剑,自己小命不免危危乎哉,于是将匕首轻轻插入门框约莫两寸,见冯锡范离门已不过两尺,突然尖声叫道:“我在这......”一个“里”字还没出口,冯锡范出招快极,一剑斩落,当的一声响,长剑碰到匕首,断为两截,半截断剑跳将上来,在他额头上一斩,这才跌落。韦小宝早已躲到了土屋之侧,心中怦怦乱跳。只听得冯锡范大声吼叫,疾冲而出。
韦小宝回到门口,但见陈近南和郑克爽仍在挥舞刀剑。强敌既去,他对这郑家二公子可丝毫不放在心上,叫道:“师父,那‘一剑无血’,已给我斩得全身是血,逃之夭夭了。你请出来罢。”陈近南一怔,问道:“谁?”韦小宝道:“是弟子小宝。”陈近南大喜,横剑当胸,不再舞动。韦小宝叫道:“张大哥、李大哥、王二哥,你们都来了,很好,很好。这姓郑的臭小子还不放下兵器投降,你们一齐上去把他乱刀分尸罢!”
郑克爽大吃一惊,哪知他是虚张声势,叫道:“师父,师父!”不听冯锡范回答,微一迟疑,便即抛下了手中单刀。韦小宝喝道:“跪下!”郑克爽双膝一曲,跪倒在地。韦小宝哈哈大笑,拾起单刀,将刀尖轻轻抵住郑克爽咽喉,喝道:“站起来,向右,上前三步,爬上去,钻进去!”韦小宝叫一句,郑克爽便战战兢兢的遵命而行,爬入了棺材。韦小宝哈哈大笑,抢上前去,推上了棺材盖,拿起那包经书负在背上,说道:“师父,咱们快洗眼去。”拉着陈近南的手,走出上屋。
走得七八步,只见马彦超倒是花坛之旁,韦小宝吃了一惊,上前相扶。马彦超道:“救总舵要紧,属下只是给封了穴道,没甚干系。”陈近南俯下身来,在他背心和腰里推拿了几下,穴道登时解了。马彦超道:“总舵主眼睛怎样?”陈近南皱眉道:“石灰。”马彦超道:“得用菜油来洗去,不能用水。挽住他手臂快步而行。韦小宝道:“我马上就来。”回进土屋,提起斧头,将七八枚棺材钉都钉入棺材盖中,说道:“郑公子,你躺着休息几天。算你运气,欠我的一万两银子,一笔勾销,也就不用还了。”大笑一阵,走回大厅。只见马彦超已用菜油替陈近南洗去眼中石灰,又缚好了他身上伤口。厅上风中际、钱老本、玄贞道人等躺满了一地,陈近南正在给各人解穴。
原来冯锡范陡然来袭,他武功既高,又攻了众人个措手不及。风中际等并非聚在一起,闻声出来应战,给他逐一点倒。众人都是恼怒已极,只是在总舵主面前,不便破口大骂。马彦超说了韦小宝使诡计重创冯锡范的情形,众人登时兴高采烈,都说这厮如此奸恶,只盼石灰便此弄瞎了他双眼。陈近南以目红肿,泪水仍不断渗出,脸色郑重,说道:“钱兄弟、马兄弟,你们去洗了郑二公子眼中石灰,请他到这里来。”钱马二人答应了。韦小宝突然“啊”的一声,假装晕倒,又目紧闭。陈近南左手一伸,拉住了他手臂,问道:“怎样?”韦小宝道:“我......我刚才......吓......吓得厉害,生怕他们害死了师父......这会儿......这会儿手脚都没了力气......”陈近南抱着他放在椅上,道:“你休息一会。”
原来韦小宝自知用石灰撒人眼睛,实是下三滥的行径,当年茅十八曾为此打了他一顿,虽然群雄大赞他机智,但想他们是我属下,自然要拍马屁,师父是大英雄、大豪杰,比之茅十八又高出十倍,定要重责,索性晕在前头,叫他下不了手,当真要打,落手也好轻些。钱马二人匆匆奔回大厅,说道:“总舵主,没见到郑二公子,想是他已经走了。”陈近南皱眉道:“走了?不在棺材里么?”钱马二人面面相觑,土屋中棺材倒是有一口,但郑公子怎么会在其中?陈近南道:“咱们去瞧瞧。”领着众人走向土屋。韦小宝大急,只得跟在后面,双手揉擦屁股,心道:“屁股啊屁股,师父听到我将那臭小子赶入棺材,你老兄难免要多挨几板了,真正对不住之至。”
来到土屋之中,只见满地都是石灰和鲜血,果然不见郑克爽的人影。陈近南明明听得韦小宝逼着郑克爽爬入棺材,这时棺材盖却钉上了,疑心大起,问道:“小宝,你将二公子钉入了棺材里么?”韦小宝见师父面色不善,赖道:“我没有。说不定他怕师父杀他,自己钉上了。”陈近南喝道:“胡说!!快打开来,别闷死了他。快,快!”钱老本和马彦超拿起斧头凿子,忙将棺材钉子起下,掀开棺材盖,里面果真躺着一人。陈近南叫道:“二公子!”将那人扶着坐起。
众人一见,都是“啊”的一声惊呼。陈近南手一松,退了两步,那人又倒入棺材。众人齐声叫道:“是关夫子!”在这一刹那间,众人已看清棺材中那人乃是关安基。陈近南抢上又再扶起,只见关安基双目圆睁,已然毙命,但身子尚自温暖,却是死去未久。众人又惊又悲,风际中、玄贞道人等跃出墙外察看,已找不到敌人踪迹。陈近南解开关安基衣衫,只见他胸口上印着一个血红手印,失声叫道:“冯锡范!”
玄贞道人怒道:“确是冯锡范!这红砂掌是他昆仑派的独门武功。这恶贼重伤之余,片刻间便去而复回,当真......他妈的,他要救郑二公子那也罢了,怎地却害死了关二哥?”众人纷纷怒骂。关安基的舅子贾老六更是呼天抢地的大哭。陈近南黯然不语。众人回到大厅。钱老本道:“总舵主,二公子与大公子争位,那是众所周知的。咱们天地会向来秉公办事,大公子居长,自然拥大公子。二公子早就把你当作了眼中钉,这次更受了冯锡范的挑拔,想乘机除了你。今日大伙儿更得罪了二公子,这么一来,只怕王爷也要信他们的谗言了。总舵主此后不能再回台湾国。”陈近南叹了口气,说道:“国姓爷侍我恩义深重,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王爷向来英明,又对我礼敬有加,王爷决不是戕害忠良之人。”玄贞道人道:“常言道:疏不间亲。二公子咬定我们天地会不服台湾号令,在中原已是如此,到得台湾,更有什么分辩的余地?他郑家共有八位公子,大家争权夺位,咱们天地会用不着牵涉在内。总舵主,咱们秦桧固然不做,却也不做岳飞。”钱老本道:“总舵主忠心耿耿,一生为郑家效力,却险些儿给二公子害死,这口气无论如何咽不下。”陈近南又叹了口气,说道:“大丈夫行事无愧于天地,旁人要说短长,也只好由他。只是万万料想不到,竟会有此变故。刚才若不是小宝机智,大伙儿都已死于非命了......唉,可惜关二哥......”韦小宝听师父不追究撒石灰、钉棺材之事,登时宽心,生怕他只是一时想不起,须得立即岔开话头,说道:“咱们这么一闹,只握左邻右舍都知道了,要是报知官府,只怕......只怕......须得赶快搬家。”陈近南道:“正是。我心神不定,竟没想此节。”当下众人匆匆在花园中掘地埋葬了关安基的尸身,洒泪跪拜,携了随身物件,便即分批离去。天地会群雄在京时时搬迁,换一个住所乃是家常便饭。韦小宝生怕师父考问武功,乘机辞别,回去皇宫。
他来到自己住处,闩上房门,将六部经书逐一拆开,果见每部经书封皮的夹缝中,都有许多羊皮碎片。他取出碎片,将书函缝起还原,缝不到半部,便觉厌烦,心想:“双儿如在这里就好了,她此刻多半还在少林寺外等我。我给九难师父捉了去,这好丫头一定担心得要命,得派人去叫她来。”又缝了几针,眼睛已不大睁得开,藏好经书便睡。次日一早去上书房侍候听旨。康熙说道:“明日便有朝旨,派你送建宁公主去云南,赐婚给那姓吴的小王八蛋。”韦小宝道:“是。中可惜没服侍皇上几天,又要远离。”康熙低声道:“太后跟我说一件大事,这次你去云南,就可乘机办一办。”韦小宝应了。康熙道:“太后说道,那恶婢假冒太后,原来有个重大阴谋,她想查知我们满洲龙脉的所在,要设法破了。”
韦小宝冲口而出:“这老婊子罪大恶极!”急忙伸手按住嘴巴,自知皇帝面前骂这等粗话,未免太过不敬。岂知康熙丝毫不以为意,跟着道:“对!这老婊子当真不是东西。太后忍辱忍苦,宁死不说,才令老婊子奸计不逞。上天保佑,太后以得保平安至今,却也全仗了不肯吐露这个大秘密。”韦小宝早已知道,却道:“皇上,这个天大的秘密,你最好别跟我说。多一人知道,多一分泄露的危险。”康熙赞道:“你越来越长进啦,懂得诸事须当谨慎。不过你跟我办事以来,从来没泄露过什么。倘若连你也信不过,我是没人可以信得过了的。”韦小宝周身数百根骨头,每根骨头登时都轻了几两几钱,跪下磕头,说道:“皇上如此信得过,奴才就是把自己舌头割了,也不敢泄露半句皇上交代的话。”康熙点点头,说道:“我大清龙脉的秘密,原来藏在八部四十二章经之中。”韦小宝假作惊异,连声道:“咦,奇怪,有这等事?这可万万想不到!”
康熙续道:“当年摄政王爷进关之后,将八部经书分赐八旗旗主。八旗之中,正黄、正白、镶黄上三旗的兵马是天子自将,但田地财物,仍分属三旗旗主管领。正黄旗的经书,父皇一直放在身边,带了去五台山,后来命你拿回来赐给我。镶白旗旗主因事获罪,镶白旗的经书没入宫中,父皇赐了给端敬皇后。”韦小宝心道:“老皇爷宠爱端敬皇后,最好的东西自然要赐给她。要是换作我,八部经书一古脑儿没入宫中,全都赐了给他。”康熙续道:“老婊子害死了端敬皇后,自然也就占了她的经书。鳌拜是镶黄旗旗主。那日派你去抄鳌拜的家,老婊子要你打两部经书,一部便是镶黄旗的,另一部是正白旗的。”韦小宝道:“是。早知老婊子这样坏,奴才便回老婊子说找不到,将经书悄悄献给皇上。”康熙笑道:“那时咱们既不知老婊子是假太后,又不知这四十二章经中有这等重大干系,你如这样胡闹,我非......打你屁股不可。”韦小宝道:“是,是。”心道:“打打屁股就算了吗?那你也甭客气啦!”问道:“另外那部正白旗的,不知鳌拜是哪里来的?”康熙道:“他害死了正白旗旗主苏克萨哈,将家产、财物,连经书一起占去。哼,这逆贼死有余辜。”韦小宝道:“是。这样一来,老婊子手里有了三部经书啦。”
康熙道:“岂止三部?她又派御前侍卫副总管瑞栋,去跟镶红旗旗主和察博为难。当时我不知什么缘故,和察博这家伙一向跟鳌拜勾结,我也不去理会。现下想来,自然是去取他的赐经。瑞栋又莫名其妙的失了踪,定是给老婊子杀了灭口。”韦小宝忙道:“是,是。皇上料事如神。”心道:“你认定瑞栋是给老婊子杀的,我又赞过你料事如神,那就已敲钉转脚。日后你就算知道瑞栋是我杀的,也已不能转口,再来向我查问了。否则的话,你就承认自己不是料事如神。身为皇上,岂可料事不如神而如鬼?”
康熙道:“如果我所料不错......”韦小宝忙道:“决计不错。”康熙道:“......老婊子手中已有了四部经书。可是有一件事奇怪得很,父皇赐我的那部正黄旗经书,我一直放在上书房桌上,却忽然不见了。你想又有谁这么大胆,竟敢到上书房来偷盗物事?”韦小宝道:“能出入上书房,又能胆敢擅自拿书的,只有......只有......”康熙道:“建宁公主!”韦小宝不敢接口,心道:“这次你是真的料事如神。”康熙道:“老婊子派女儿来偷了我这部经书,这一来,她手里已有五部了。”
韦小宝道:“咱们快去慈宁宫搜查。老婊子光着身子逃出宫去,什么也没带。”心中怦怦而跳:“此刻皇上如到我屋中一查,小桂子便有一百个脑袋,也都砍了。”康熙摇头道:“我早细细搜过了,什么也查不到。只查到一套僧袍,老婊子那个相好,原来是个和尚。哈哈,哈哈!”韦小宝跟着大笑,笑得两声,觉得甚为无礼,忙忍住了笑。康熙仍放声大笑,说道:“不过那矮冬瓜抱着老婊子逃走之时,我瞧到他留着一头长发,这倒奇了。多半他也是假扮宫女,头发是假的。这家伙又矮又胖,老婊子什么汉子不好偷,却去找这样个矮冬瓜。”韦小宝笑道:“这矮冬瓜武功很高。相貌英俊的,未必有本事偷进宫来。上次那个假宫女,也就丑得很。”康熙笑道:“那也说得是。”顿了一顿,续道:“另外三部经书,公别在正经旗、正蓝旗、镶蓝旗三旗手中。正红旗的旗主目下是康亲王,我已命他将经书献上来。”
韦小宝心想:“康亲王那部经书,那天晚上已给人偷了去,此刻在我手中。康亲王怎么还献得出?这一下老康可要大糟而特糟了。”康熙又道:“正蓝旗旗主富登年岁尚轻,我刚才问过他。他说上一任的旗主嘉坤在攻打云南时阵亡,一切后事都是吴三桂给料理的。吴三桂交到他手里的,只是一颗印信,几面军旗,还有几万两银子,此外什么都没有了。”韦小宝道:“这部经书定是吴三桂吞没了。”康熙道:“是啊。因此你到了吴三桂府中,仔细打听这件事,想法子把经书取了出来,吴三桂这厮老奸巨滑,千万不能让他得知内情。”韦小宝道:“是,奴才随机应变,设法骗他出来。”
康熙皱起眉头,在书房中踱来踱去,说道:“镶蓝旗旗主鄂硕克哈是个大糊涂蛋,我要他呈缴经书,他竟说好几年前就不见了。我派侍卫到他家搜查,一无踪迹,我已将他下在天牢,叫人好好拷问,到底是当真给人盗去了,还是他隐匿不肯上缴。”韦小宝道:“就怕也是老婊子派人去弄了来,也不知是明抢还是暗偷。”心想:“这可不是冤枉老婊子,明抢暗偷之人,多半便是那矮冬瓜。”又道:“倘若也是老婊子得了去,这六部经书又到了何处?”随即微感懊悔:“我这问话可说错了,自己太也吃亏。我说老婊子得了六部经书,得了门部经书的其实是韦小宝。这么一来,我岂不成了老婊子?”康熙道:“老婊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此刻毫无线索可寻。她干此大事,必有同谋之人。她得到经书之后,必已陆续偷运出宫,要将这六部经书尽数追回,那就难得很了。好在太后言道,要寻找大清龙脉的所在,必须八部经书一齐到手,就算得了七部,只要少了一部,也是无用。咱们只须把康亲王和吴三桂手中的两部经书拿来毁了,那就太平无事。咱们又不是去寻龙脉,只消不让人得知,那就得了。不过失了父皇所赐的经书,倘若从此寻不回来,我实是不孝。哼,建宁公主这小......小......”康熙这一声骂不出口,韦小宝肚里给他补足:“小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