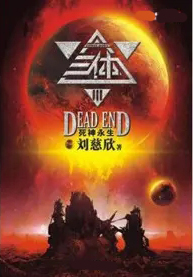第24章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话说在1932年夏末秋初,江青拿着几十元的积蓄,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她要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江青一路上心绪不宁,加之一个姓王的济南艺专的学生,一路上向她大献殷勤,江青看出他是不怀好意,就更加愁烦了。使她更想不到的,在前面等着她的那些混迹于十里洋场的一些人,更把她看作一块大肥肉。殊不知这个18岁的年轻女子,竟是一朵刺儿玫。于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最终酿出了一段几十年恩恩怨怨的历史公案。
话休絮烦,且说江青一到上海,就有人来接她。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拍摄了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著名导演史东山。史东山是奉左翼剧联之命,和前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教师李也非一起,来接这位青岛“海鸥剧社”的成员。江青上了史东山叫来的出租车,慌乱之中竟把一件行李忘在甲板上了。
江青到了上海才知道,党的临时中央已迁往江西瑞金根据地,上海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田汉、阳翰笙等人,整天东躲西藏,根本找不到。这样,江青只好暂且在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魏鹤龄家里住了下来。
江青通过在上海的俞珊的引荐,终于见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田汉,此时担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党的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江青来到田汉家里,田汉安排她和保姆同住一室。后来,江青到廖沫沙家借宿,她说:
“你不住在家,我在这里住几天可以不可以?”
廖沫沙说:
“我的内人回湖南马上就要回来了,她来了你就不能住了,她没回来之前你可以住。”
不久,廖沫沙的爱人回到上海,发现江青住在他们家里,很不高兴地对廖沫沙说:
“我们马上找个地方搬家,不住这里了。”
她几乎不容廖沫沙再拖延一天,立刻就跟着他去另租房子。他们当天在另一条弄堂里找了个过街楼。回去收拾东西搬家时,江青问他们搬到哪里了,还说:
“过几天我再去看望你们。”
廖沫沙原以为她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几天后她还真的找上门来,不好意思地说:
“廖先生,田汉干扰太大,你们这儿如果能住,我也想搬来,同你们住在一起。”
廖沫沙指指后面的厨房说:
“那你只能住那儿了。”
江青只好说:
“我先到一个朋友家看看,如果那儿能住下就不来了,住不下,我再来住厨房。”
后来,江青又千方百计地见到了周扬和阳翰笙。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8年出生,湖南益阳人,1927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带组织关系而脱党。1928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党,任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文化反“围剿”的斗争。周扬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因为保养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
江青急于见周扬,是要汇报自己在青岛的革命经历,请求恢复自己的组织生活,一来是因为漂泊不定,不能长期寄人篱下,二来是手头拮据,急于找份工作。但周扬和田汉却非常谨慎,没有答应她的要求,一是说她没有组织介绍信,二是说对她并不了解,只是和她谈一些在演艺方面的设想。倒是田汉的五弟剧联成员田沅对江青一见钟情,提出要江青到他工作的“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无奈,只好化名为“李鹤”,到上海西部北新泾镇“晨更工学团”店员识字班当了一名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
“晨更工学团”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一所专门为贫苦子女接受教育而设立的学校。后来成为王观澜夫人的共产党员徐明清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
“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这里聚集着一批热血青年,只是女教员不多,只有徐明清、江青和一个名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当时喊她“一冰”,她叫江青“小李”,而她俩都称李素贞为“宁波李”。她们3人同住一座小楼顶上的阁楼里,每天爬着竹扶梯上去,小阁楼里只有一扇老虎窗,没有床,3个人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觉。天天住在一起,徐明清跟江青慢慢熟悉起来。当时江青一头短发,一身蓝布旗袍,从不涂脂抹粉。徐明清记得,江青那时教唱歌、演戏,很活泼。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晨更工学团”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共产党员王洞若,担任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的左翼联盟的陈企霞,也都在这里工作。由于周扬、田汉等人没有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了解和接纳江青的党组织关系,江青不得不在“晨更工学团”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她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社。后来徐明清看江青表现不错,就作为她的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江青在“晨更工学团”不开心的事,就是田沅老在她屁股后头追着,弄得大家议论纷纷。江青就贸然给田汉写了一封信,说:“请把你弟弟调走吧,我不能工作了。”后来,田汉就把田沅调走了。
1934年,上海爆发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成为警察监视的重点,党、团组织只好进行转移,江青被安排到北平去暂避风头。她在北平待了3个月,到北大当了旁听生,系统地听了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
1934年5月底,“晨更工学团”党组织通知江青回上海,安排她在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化名张淑贞。这所夜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是由地下党组织控制。江青在这里度过了她在上海时期最愉快的时光。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中传唱;她拉的婉转悠扬的二胡独奏曲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她用张淑贞的名字公开发表了《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河山》等文章。
1934年9月,“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通过关系,了解到江青在青岛入党的情况,由孙达生为介绍人,重新吸收她入党。党支部书记王洞若和她谈了话,这才使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34年10月的一天,江青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那人也认出了她。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地下党员,江青来上海时,他也参加了送行。一晃一年多,两人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江青回到夜校后向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说,他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的组织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江青第二次和乐若见面时,因为彼此通过党组织相互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多了。乐若说江青不被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交代说:
“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
江青回去向党组织负责人说明情况,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她很多注意事项。江青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见面,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此时,特务出现了。
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叫声“快跑!”一溜烟逃脱了。江青由于路径不熟,被特务抓住了衣服。她大声喊:
“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
特务一巴掌打在江青的脸上,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江青仍然拼死挣扎,大声说:
“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证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就往警察局走。眼看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经黑了,江青装着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那张秘密表格放进嘴里吞了下去。到了警察局,特务头子听说乐若跑了,只抓了个不知任何情况的女人,大发雷霆。
江青在看守所里已经完全冷静下来,她知道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罪的。无论特务们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散步,自己有正当职业,是学校的老师。被看押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女工学员,是江青的学生,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江青托她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捎信,说明情况。因为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左翼联盟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又出面保释,江青于1934年12月初被无罪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