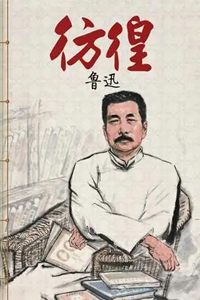日本文学界曾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日本历史要看司马辽太郎,中国历史要看陈舜臣。”
对于生活在昭和时代(1926—1989年)的日本人而言,这两个名字都不陌生,历史爱好者更是如此。巧合的是,这两位大文豪还是大学同窗兼好友。司马辽太郎擅长刻画默默无闻者如何在乱世中一步一步成为英雄,他笔下的坂本龙马、宫本武藏、西乡隆盛、十方岁三、伊贺忍者等形象深入人心。尽管他也写过《项羽与刘邦》这样以中国历史人物为主角的小说,但真正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大人物与小角色带进日本读者心中的,恐怕还是陈舜臣。甚至连司马辽太郎都说:“能让日本人真正了解中国历史的只有陈舜臣。”
陈舜臣原籍中国台湾,他出生于日本神户,并在那里接受了汉学教育。出身和成长环境的特殊性,注定了他在日本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徘徊,同时,对自我身份认定产生了迷茫。1994年,陈舜臣在小说《甲午战争》中文版座谈会上曾感叹:“我原该是中国台湾人,因甲午战争而成为日本人。大约二十岁时,又变回中国人。我实在想探究如此玩弄我命运的究竟是什么?”这种特殊历史命运转换所引发的漂泊感,使他的文学创作隐藏着一个主题,就连他自己也未曾察觉,却被某位日本评论家一针见血地指出:“陈舜臣的推理人物往往是在寻找自己的身世,这就是他大部分作品的主题。”
因此可以说,由于身份不断转换的迷茫,以及对这种迷茫的探求,使得他的作品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产生更丰富深远的内涵。正如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所说:“没有任何作家像陈舜臣那样,用在不同文化、不同民族夹缝中生存的刻骨铭心的生活体验去深入思考未来。他这样做的出发点自然是研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并从事创作活动。”司马辽太郎也曾评价说:“陈舜臣这个人,他的存在就是个奇迹。他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慈悲的眼光来看待的。同时,他也热爱中国,这种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加上他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一线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这是他的观察与思考呈现出多重性的一个要素。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合而为一,真叫人感到惊奇。”
陈舜臣笔下的中国史
在当代日本文学中,中国历史题材小说曾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景象。所谓“中国历史题材小说”,是指以中国历史为舞台、以中国历史人物为对象的小说,与“日本历史题材小说”相对应。战后半个多世纪来,日本的中国历史题材小说中,长篇作品有二百余种,短篇数量更是可观,被编辑成短篇集出版的便有上百种,其中陈舜臣的长篇历史小说约有三十部。这些小说中,不少获得了包括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在内的各种有分量的大奖,从畅销一时到长销不衰,对日本文学和日本读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陈舜臣之前,井上靖和海音寺潮五郎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天平之薨》《敦煌》《蒙古来袭》等作品,已经在日本读者心中刮起了阅读中国史之风,而陈舜臣的出现,则使其发展成为旋风,席卷整个日本。
梳理陈舜臣的生平不难发现,他并非一开始就写历史小说,事实上,他最初是以推理小说出道的。
大学期间,陈舜臣就几乎读遍了柯南·道尔的所有作品,这为他开始推理小说创作积累了素材。1960年,陈舜臣以笔名“陈左其”参加了第十届文学界新人奖的征稿,作品《在风中》(《風のなか》)进入最终候选阶段,虽无缘奖项,但这坚定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1961年5月,他的长篇小说《枯草之根》(《枯草の根》)获得了第七届江户川乱步奖。这一年,他36岁。接着,他陆续出版了《三色之家》(《三色の家》)《弓屋》(《弓の部屋》)《愤怒的菩萨》(《怒りの菩薩》)《分裂者》(《割れる》)《托月之海》(《月をのせた海》)等推理作品。从这些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陈舜臣卓越的推理能力以及对人性的洞察。
陈舜臣开始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是以1967年《鸦片战争》(《阿片戦争》)的出版为标志的。这部小说的意义不仅在于开辟了陈氏创作的新类型,也在于触及了其他日本历史小说家们在选材上规避的历史——中国近代史。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日本历史小说家们取材时多偏向古代中国。自中国文化和典籍传入日本之后,经过上千年的吸收与融合,许多中国历史中的人物、典故,都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再被视为纯粹的外来文化。尤其是受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以及曾先之的《十八史略》在日本的影响,小说家们选材时多偏向秦汉时期、三国时代和宋代相关的历史和人物。这既是受自身对中国历史知识掌握情况的限制,也是考虑到了日本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对中国近代史,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历史存在诸多误区,加上教育的刻意淡化,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相对薄弱。作为华裔作家,陈舜臣有意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有了《鸦片战争》以及之后一系列以中国近代史为舞台的小说,包括《甲午战争》(《江は流れず-小説日清戦争》)《太平天国兴亡录》(《太平天国》)《山河犹存》(《山河在り》)《走向辛亥:从孙文崛起看晚清日落》(《青山一髪》)等。许多日本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才对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当然,陈舜臣也写了大量取材于中国古代的小说,例如《三国史秘本》(《秘本三国志》)《曹操》(《曹操-魏の曹一族》)《诸葛孔明》(《諸葛孔明》)《十八史略》(《小説十八史略》)《郑成功》(《鄭成功-旋風に告げよ》)《成吉思汗》(《チンギス·ハーンの一族》)《耶律楚材》(《耶律楚材》)等。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可读性极强,这是因为他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他曾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也许是乱说,但我确实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中。”他又说:“历史时代要依靠史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他的创作风格在日本文学界可谓独树一帜,旅日作家李长声曾说他是“日本小说界无出其右者”。
除了历史小说,陈舜臣还创作了大量散文、随笔、游记等,且大多也是取材于中国历史文化,《史林有声》(《史林有声:中国歴史随想》)《随缘护花》(《随縁護花》)《一路向西:东西方3000年》(《シルクロードの旅》)等作品,对中日文化在琐碎日常中的诸多差异以及背后的渊源进行了挖掘与探究,也都为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开启了新的大门。
陈舜臣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写中国历史,是为了‘订正’(日本)对中国历史的某些误解。”出于这份责任,他对历史的考察是极其讲究的。“身为一个常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家,在史料调查方面,我建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谨记史料往往是胜利者的记录。胜利者常会将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抹除或重新修改。”他对于搜寻史料有着别样的执着,他从不假手于他人,先后多次赴北京、西安、敦煌、大连等地探寻古迹,亲自到现场感受穿越千百年的历史气息。
陈舜臣一生著作两百余种,题材广泛,获奖颇丰。可以说,在日本从未有任何一个外裔作家能够取得像他这样高的文学成就。他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一个以笔构建中日交流桥梁的时代。
陈舜臣笔下的秦始皇
两千二百多年前,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一位传奇的帝王。他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余年的纷争割据,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就是秦始皇——中国第一位皇帝。在日本,人们习惯称其为“始皇帝”。与他相关的徐福带领五百童男童女东渡的传说自古为日本百姓津津乐道。在京都右京区的太秦(即大秦),还有一座祭祀秦始皇的神社——大酒神社,秦始皇被尊为大酒大明神。此外,秦始皇也被日本漫画家、游戏设计者改编成各种现代化的新形象。可见,这位始皇帝在日本的人气之高。
对于秦始皇的生平,无论是《史记》等正史资料,还是影视剧的戏说,都不可避免地增添了来自后人的神话色彩。20世纪70年代以来,秦始皇陵、秦代简牍等考古资料的出土,为学者们研究秦始皇生平开启了新途径。这样一个谜团重重、颇具争议的帝王引起陈舜臣的兴趣可以说是情理之中的。
1995年1月,陈舜臣结束了长达五个月的病榻生活出院,半个月后发生阪神大地震,他去了冲绳疗养。尽管年事已高、身体抱恙,但他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这一年,他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并出版了文化随笔《随缘护花》以及人物传记《秦始皇》。
虽题为“秦始皇”,但陈舜臣的用意并不局限于展现秦始皇的生平事迹,而是想要通过这个典型的人物,一窥时代的真面目。这一点,他在序言中便有说明:“我写这本书,是想通过揭开时代的面纱,勾勒秦始皇的形象,再借助秦始皇这支璀璨夺目的明烛,照亮那个时代的真容。”
正文开篇即解释了“皇帝”一词的由来。作者借助史料的记载,对“王”“侯”“皇”“帝”等汉字的内涵进行了简单阐释,指出嬴政采用“皇帝”这个尊号的野心——超越三皇五帝。作者因考察“皇帝”一词,自然而然地对自古以来的尊号使用情况都进行了梳理,由此串起了整个秦朝以前的历史与文化。通过短短两千字的描述,读者便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不得不说作者叙事功底之深厚。接着,陈舜臣客观地罗列(而非评价)了秦始皇为了“大一统”而采取的举措,并得出一个结论——秦始皇最大的功绩不在于这些举措本身,而在于使“大一统”的思想深入人心并影响至今。秦之后的两千多年,中国几经分裂,但都复归统一,这与秦的统一密不可分。而后,陈舜臣对秦以前的历史进行了追溯,尝试从历史中找到秦之所以成为秦、秦始皇之所以成为秦始皇的原因。
对于秦始皇这个人本身,陈舜臣摒弃了“神化”倾向,而将其作为普通人来书写。他对史料进行筛选和串联,加以适当的推理,尤其是补充了人物的心理活动,从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立体饱满、有血有肉的嬴政。
陈舜臣认为,时势造英雄,任何个人,都必须放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考察才有意义,诚如他在后记中说:“我在这本书中讲述了秦国的诸多事迹。功过是非,黑白曲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把自己想象成秦始皇,沉浸到这段历史中去。英雄和伟人毕竟也是人。”
可以说,本书既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部先秦史。在网络尚不发达的1995年,这部作品的出版,为日本普通读者了解秦始皇以及先秦历史提供了一条便利的通道。由于陈舜臣对待史料时态度相当严谨,加上其独特的历史推理视角,他在这部作品中得出的某些结论与现阶段考古成果不谋而合。因此,即便放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秦始皇》也有其现实价值。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本书编校过程中,对于相关历史资料的表述与现今考古成果或主流说法有所不同的部分,都做了保留,加之批注、脚注以说明;对于书中没有详细展开叙述的内容,选取陈舜臣本人所著《中国的历史》(讲谈社文库,1990)中相关内容,以“陈说”形式为读者展开。
诚如作者所说,秦始皇死后,秦朝岌岌可危,二世而亡,以致秦朝并没有其自身编撰的史书流传于世。又因秦始皇统一六国而招致亡国之人的怨恨,流传至今的史料中多是对其不利的言论。而且,先秦史料纷杂,也多有相互矛盾之处。另外,本书起初是面向日本读者所写的,因而选取的一些对比举例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或许并不熟悉。对于上述种种矛盾或疑问,在此列举部分:
其一,第九章《民怨沸腾》中提到秦始皇陵被烧以及所藏珍宝尽数被盗一事,至今考古界仍有争议。项羽是否真的是火烧骊山陵的始作俑者,目前尚无定论。根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列项羽十大罪状,第四项为“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物。”其中并无项羽火烧骊山陵的记载。本书根据《水经注》中对“牧人寻羊烧之”的记载解释,是住在附近的牧羊人趁乱进入墓穴中盗走部分珍宝,并放火烧毁墓室。另有古籍记载说是有牧羊儿在附近放羊,因羊走丢而持火寻找,不慎导致墓中失火[《汉书·楚元王传》: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挥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同时,骊山陵是否被盗一空,经当代考古学家实地勘探,认为史籍所述被盗焚毁的,可能只是地面建筑和部分地下陪葬坑。另有新研究显示,皇陵核心“地宫”保存完好。
其二,第十章中将秦始皇收缴天下兵器一事,与丰臣秀吉的“刀狩令”做对比。有的读者或许对此不甚熟悉,在此简单说明。刀狩令是指收缴僧侣及平民的武器的政策,现存记录中,最早的是1228年北条泰时要求高野山僧侣交出兵器。丰臣秀吉所处的16世纪,近畿以及关东地区的平民在成人礼时,会得到一把胁差,象征平民的武装权以及成年男性的人格和名誉。丰臣秀吉在1588年颁行刀狩令,目的在于解决因持有武器而引起的暴力争端,同时推进全国兵农分离政策。丰臣秀吉的刀狩令共有三条:一、禁止平民持有及携带刀、弓、枪、铁炮等武器;二、所收缴的武器,用以铸造修建方广寺大佛所需要的钉子等物品;三、平民应持农具努力耕作,以为子孙后代安居之本。
其三,由于史料本身的矛盾和解释的差异,关于苏秦、张仪的年辈问题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苏秦早于张仪;一种认为苏秦晚于张仪。《史记》《资治通鉴》所记载二人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是战国合纵连横斗争的对手,苏秦稍早。但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却表示:苏秦的年辈比张仪晚,苏秦死于公元前284年,张仪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的主要活动均在张仪死之后,张仪在秦国任相时,苏秦还没有踏入政坛[此处引用自陈舜臣所著《陈舜臣说<史记>:帝王业与百姓家》的导读部分。]。文中所提及张仪在苏秦死后为宣传自己主张,暴露苏秦合纵政策的短处,以致苏秦风评不佳,仅为陈舜臣先生参考《史记》记载所述,实际情况有待考证。
其四,近年来《赵正书》的问世,使得胡亥与赵高篡改秦始皇遗诏一事,出现了新的解释。《赵正书》出自《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第三卷,其中大部分篇幅记录了秦始皇临终前与李斯的对话、李斯被害前的陈词以及子婴的谏言,估测成书年代约为西汉早期。《赵正书》部分内容与《史记》所记载的内容相似,但在胡亥继位一事上,说法截然相反。《赵正书》中称胡亥继位乃是秦始皇授意,并非密谋篡改遗诏。同时,根据《史记》记载: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可解释为:秦始皇病重,写了一封盖有皇帝玺印的诏书给公子扶苏,命其回咸阳为其送葬,主持丧礼。根据记载所述,秦始皇也并没有在诏书中立公子扶苏为太子。并且有关学者指出,有关秦朝末期的历史资料纷杂,汉初已有多种不同记述,《史记》所取只是其中之一。
陈舜臣本人对待历史有着极其严谨的态度,多方考证古迹资料,力求还原历史原貌。本着尊重陈舜臣创作的原则,并未在书中对有所争议的部分进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