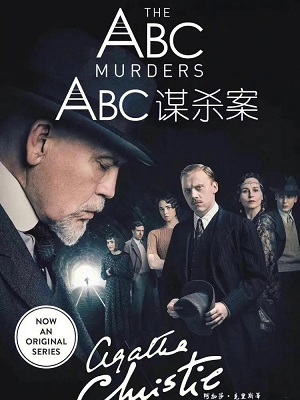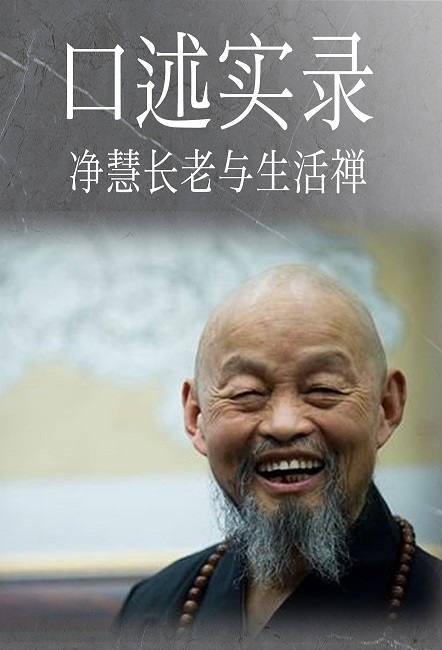苏轼幸已逃过谢景温诬告这一关,出为杭州通判。离京在即,回首从政以来,忽已十年,当初一心以为参加了匡时济世的大事业,不料自少至长,努力追求的政治生活,竟如儿戏一般荒谬,幻灭的悲哀,令他惘然若失。
人生真有命运这样东西,挡在前面,引领人懵懂前行吗?尽管有人不肯承认它,以为人自有力主宰一切,不幸有更多的经验事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人,实在很脆弱,常被命运所捉弄。
苏轼未第制科以前,声名先已上达九重,初次诣阙陛见,英宗皇帝即欲破格擢用为知制诰那样的御前重职,宰相韩琦提到“馆职必先试而后用”的规例,英宗还说:“不知能与不能,才要考试。如轼者,有所不能耶!”君主的信任达到如此深切的地步,不能不说是罕见的异数。然而,谁能想到英宗会那么短命,还来不及用他就已崩殂。
神宗是个对文字很挑剔的君主,他先已喜欢苏轼的文章,初次召见,听了他那明快的议论,认为足以破疑解惑,即欲拔置左右,委为修注官。无奈格于王安石的反对,以后又屡在御前谤毁他不是个纯正的学者,终以谢景温的诬告,逼得苏轼只好自请外放。
士人从仕,能得人主的知遇,该是多不容易的造化,而苏轼是既得其“知”,而无其“遇”。
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挈带一家大小——继室闰之夫人、发妻所生现已十三岁的长子苏迈、去年新生的次子迨等,乘舟出都。先到陈州去谒候张方平,与在陈州做学官的弟弟苏辙晤聚。
船中无事,做了八首小诗,其中有一首说:
鸟乐忘罝罦,鱼乐忘钩饵。
何必择所安,滔滔天下是。
刚从政治罗网里脱逃出来的苏轼,一出都城,便觉天地辽阔,心想另求一个安身之地,应该不难,实在觉得没有违心背性,非要做官不可的道理。
陈州城北有个柳湖,是当地的一大名胜。湖边古柳万株,树皆合抱,南山老松,蛟龙蟠屈,苏辙曾有《柳湖感物》之作。
苏辙诗鄙薄柳花的浮浪而爱松性的坚实,这见解很合乎他的个性。但是老兄以为不然,和诗说:“子今憔悴众所弃,驱马独出无往还。惟有柳湖万株柳,清荫与子供朝昏。”这样的好友,为何要讥评它?何况宇宙万物,四时各有盛衰,南山孤松如压在雪底,即使“抱冻不死”,人家看不到,它也无法表显于世,还有谁来赞扬它呢?苏轼今日自有这个感慨:物各有遇有不遇,但是千万不能被埋没。
苏轼在陈州弟家,盘桓了七十多天。张方平因反对新法,于熙宁三年正月出判应天府而至陈州,哪知陈州的监司官,现在也都换了一班新进的后生,趋时兴利,道不相谋,方平说:“吾衰矣,雅不能事少年,不如归去,以全吾志。”遂向朝廷再三要请以南京留台名义告了老。苏轼作《送张安道赴南都留台》诗说:“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
在陈州初遇张耒。耒字文潜,淮阴人,其时方从苏辙问学,所以起初别人都说他是“少公之客”。他的诗,学白乐天,务为自然平淡,尤精绝句,如《偶题》云:“相逢记得画桥头,花似精神柳似柔。莫谓无情即无语,春风传意水传愁。”苏轼称之曰:“文潜容衍靖深,独若不得已于书者。”至元祐中,苏轼在翰林,荐耒出任馆职,始为东坡门下四学士之一。
九月间,兄弟相偕同往颍州,晋谒致仕后闲居里第的欧阳老师。
欧阳修文章风节,负天下重望,但于英宗治平年间朝廷“濮议”中,被吕诲、彭思永攻击得灰头土脸。平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但被门生蒋之奇造作“帷薄不修”[蒋之奇诬欧阳修与自家的甥女通奸。]的蜚语,连遭污蔑,意冷心灰。自治平四年出知亳州后,就接二连三以体弱多病为辞,自请退休。到调知蔡州时,更是决心求去,门人蔡承禧劝他道:“公德望为朝廷所重,未及引年(规定告老的年纪),岂容遽去?”欧阳修叹道:“某平生名节,为后生描摹殆尽。惟有速退以全节,岂能更待驱逐乎!”
北宋士大夫间的风气,败坏到这个地步,也是苏轼所意想不到的现实。欧阳修一生更历忧患,精力早衰,他的头发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个,两耳重听,本来是深度的近视眼,这时候,几已接近失明了,仅辨黑白而已。最严重的是患有多年的消渴疾,即今之糖尿病,时发时愈,全身肌肉消瘦,自言“弱胫零丁,兀如枯木”,以致步履维艰,更形衰老。
苏轼认为欧阳的年纪还不算太老,身体之所以坏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忧劳过度之故,只看自己还只三十六岁,头上已生白发,忧劳伤身,真不值得。《颍州初别子由诗》说:“……我生如飞蓬。多忧发早白,不见六一翁。”
唐诗以抒写感情为主,几已写尽人类情绪上各种隐微曲折的变化,穷极工致,后人很难在这上面更有超越的成就。而宋代的散文非常发达,宋人就以锻炼文章的方法,用之为“知性之诗”,别辟途径,与唐诗争胜。所以,中国诗史中,咏物诗为宋人的特色。
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又是宋人咏物诗中的代表之作,自己是此中高手,这次却出个难题给苏轼,要他为所珍藏的石屏风赋一首诗,于是便有《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诗:
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
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
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
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
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
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
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
愿公作诗慰不遇,无使二子含愤泣幽宫。
物,本是“死”的东西,要将它写“活”,实在不大容易。苏轼早年在凤翔时,写过一首《石鼓歌》,将历代文字流变间的人物,一一引进诗中,便将活泼泼的生命赋予了死的石鼓,后世评者认为胜于韩愈的旧作。
石屏风这个题材,更是平凡,不过石上有纹,颇似松影而已。苏轼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出两个画松的古人,因这两个画家生前不遇,想象这块石上的松影,定是这毕、韦二人,含愤地下的精气,沦入石中所形成的画面。经此点染,便在这本是“块然一物”的石屏风里,添入了画师的灵魂,写成一篇非常生动的好诗。难怪欧阳为之大乐。
欧阳修虽然须发尽白,满身疾病,但据苏轼说,气色甚好,谈锋还是很健。苏轼劝老师道:“已将寿夭付天公,彼徒辛苦吾差乐。”那些当权的人,只有辛苦,哪里能如老师这样自由自在的快活,这是安慰老人的话,但也想不到未及一年,欧阳便在颍州谢世。
兄弟俩在颍州欧阳家住了二十天后,于此分手,在苏轼的感觉中,认为相较以前三次分别,此次滋味特别酸冷。
兄弟两人,虽然一样的不得意,但是苏辙走得早,毛羽未伤,所以苏轼称之曰:“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
苏轼自嗟临事如病热狂,不能节制进退,现在则像一个喝醉酒的人,摔了一个大跟头,幸而没有受伤,倒也吓醒了迷梦。《颍州初别子由》诗里,写尽只有兄弟二人自己才能体会的人生失意的哀伤。
苏轼自颍入淮,再过泗州时,记得五年前扶丧回蜀,在此遇到逆风,三日不能开航,船上人劝他向僧伽灵塔祷告,果有应验。苏轼认为只是“巧合”,大公无私的神明,何分厚薄,而做祷告的人,都只为了私自的方便。耕田的农夫希望下雨,而割草的人却要天晴,去舟要顺风,来船便将抱怨,假使人人都要祷告得称心如意,这神明岂不太难做了。
这次情形不同当年,万一再遭逆风,苏轼决定不再求神,怅然道:
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
行至龟山(今江苏盱眙),诗曰:
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
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
苏轼从中国西南的边城眉山出来,而今将往东南的海滨,已经走尽了半个中国的一条直径,如此奔波劳碌,真还不知所为何来。
在泗州与一旧识的庵僧重逢,别来不过五年,但却发现他的头上也有白发了。时间是造物主之极大的公平,无分贵贱,无分劳逸,到时候都将同样老去,奔走道路的劳人和闲卧庵中的和尚既然一样,则又何苦如此“徒劳”。
苏轼离京时,还是秋暑难当的七月,一路盘桓,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始抵杭州,途程几已半年。
杭州府衙,设于凤凰山之右麓,依山兴建,府廨左右,分设通判南厅北厅各一所,另一通判鲁有开住南厅,苏轼便居北厅。
住入官邸后,依照俗例,要祭灶,要请四邻吃酒,乃作绝句两首,代柬寄陈州苏辙:
眼看时事力难胜,贪恋君恩退未能。
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
圣明宽大许全身,衰病摧颓自畏人。
莫上冈头苦相望,吾方祭灶请比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