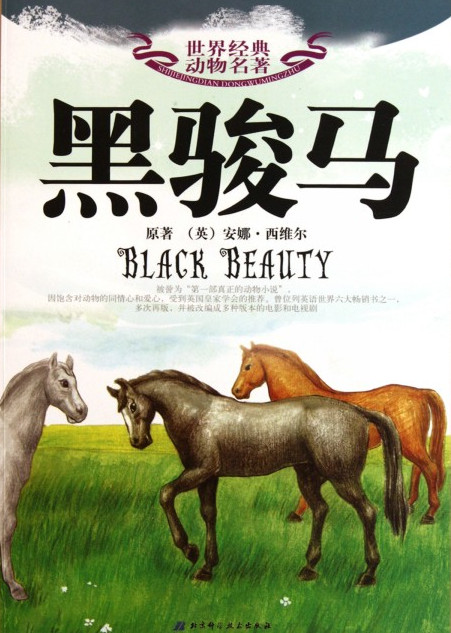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同(与可)殁于陈州。
苏轼在密州时,熙宁八年秋冬间,文同自京徙知洋州,即今汉中市洋县。文同将洋州园林池湖之胜,一一歌咏,得诗三十首,寄与苏轼,苏轼乃次韵唱和,恍若同游。文同是画竹名家,所以这三十个胜迹中,有竹者为多,如竹坞、霜筠亭、筼筜谷、此君庵等皆是。
文同在洋州,因论茶事,与提举、转运使意见不合,被迫罢任,次于陈州待命,非常贫困。上年正月,苏轼还写信去劝慰他,有道:
与可抱才不试,遁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米珠薪桂)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
苏轼论文同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与可引为知己,尝曰:“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
文同在洋州,于筼筜谷上,筑一亭子,朝夕在亭中观赏漫谷的翠竹,所以虽是文人水墨作画,以抒写性灵为主,但却仍是非常认真地下过写实工夫,潜观默悟,“胸有成竹”,写出其潇洒的风貌。
苏轼亦好画竹,从凤翔开元寺王维的壁画得到启示,从文同的教导得到技法,《筼筜谷偃竹记》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即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文同画竹,以淡墨为叶青,以深墨为叶面,此一技法,不但苏轼、米芾(初名黻,元祐六年改名芾,下文径称米芾),都遵为宗范,即使元代那么多的画竹名家,也都执此不变,称文湖州派,而文同则说:“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固已心许苏轼得其真传,而苏轼也坦然道:“吾墨竹尽得与可法。”不过后代的画评家却说:“笔酣墨饱,飞舞跌宕,虽派出湖州(文同)而神韵魄力过之。”(孙承泽《庚子消夏记》)又有论两人画竹之不同者,如“东坡墨竹,写叶皆肥厚,用墨最精。兴酣之作,如风雨骤至,笔歌墨舞,窃恐文与可不能及也”。(方薰《山静居画论》)此盖由于两人天生的性情不同,所表现于画面的精神,遂各有不同的境界。不过,文同筼筜谷上筑亭看竹,是实物写生,苏轼则独创新法,于月下取韵画竹,文同为之大惊。明清之际的画家恽南田在画跋中赞叹道:“盖得其意者,全乎天矣,不能复过矣!”
文同画竹,初不自重,然而声名日盛,四方之人,捧了白绢登门求画者,户限为穿,与可应接不暇,厌烦极时,将素绢扔在地上,骂道:“吾将以为袜!”士大夫间将这句话传说开来,引为口实。
与可致书苏轼说:“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书一诗,有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
苏轼抓他毛病道:“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老实认错,复道:“吾言妄焉,世岂有万尺竹者。”哪知苏轼此时,却又说“有的”,答诗曰: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
世间那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
与可得诗,大叹苏轼之辩,但他说:“如真有二百五十匹绢,我将买田归老,再也不在这里等派官了。”随将得意作双钩着色的《筼筜谷偃竹》一幅,寄赠苏轼。而苏轼也作了首《筼筜谷》回赠他:
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
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
事情就有这么凑巧,文同得书时,正在晚餐。这一日,恰与他的夫人同游谷中,烧笋佐餐,发函读得上诗,竟被苏轼料到,失声大笑,喷饭满桌。
苏轼得“偃竹图”后,并不满足,还写信去向与可讹索,致书曰: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题)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匹也。呵呵!
宋以前绘画,没有题诗画上的风尚,有则始自文同。文同不但自己题诗,还常常留下空白,嘱求画者道:“勿使他人书字,须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
如为京师道师王执中画墨竹一幅,即是如此。艺术真赏不易,知音难得。
不料可以如此放诞笑乐的朋友,音容笑貌都在眼前,忽尔讣告一到,突然人天永隔了,叫人怎能相信这是事实?苏轼说他整整三日三夜,不能睡觉,只是默坐,后来实在倦极了,偶然睡去,也没有一次不是梦醒,醒来,枕席上皆是泪痕。他想:人生百年,总有死亡的一日,但有文传世为不朽,有子嗣后为不死,世上富贵寿考的人,未必能二者兼有,所以文同是不死不朽的,而文同曾说:“身如浮云,无去无来,无亡无存。”那么,不死不朽,也都渺不足道了。
他们两人的情谊,不但是文学绘画等艺术上的知音,更重要的则是人格和为人风度的共鸣,如《祭文与可文》说:
……呜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忽收泪以自问,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乎?呜呼哀哉,孰能纯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辞如与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呜呼哀哉!
苏轼每一回想文同生平,常常心为不平,他是那么一个宽厚平和的人,却到处受人打击,遭人排挤,诗赋造诣那么高超,而世人短见,只看重他画的墨竹,生前被人嫌弃,百般委屈,死了,忽又人人惋惜起来。说到他自己,更是凄怆:“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友。……”文同身后萧条,全家侨寓陈州,无力归丧还蜀,苏轼致函在舒州的李常,因他也是文同的生前好友。略曰:
与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寿,又哀其极贫,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颇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贤而有文,久远却不复忧,惟目下不可不助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