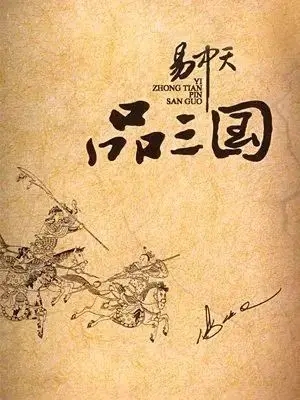苏轼自海外北归,还至仪真,听说故乡蟆颐山他家祖坟边的老翁泉,曾经一度枯竭,心里觉得很奇怪,写信去问数十年来代他照顾坟庄的杨济甫的儿子子微,书曰:
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现今如何?因见,细喻。
又有一个传说:“蜀有老彭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宋〕张端义:《贵耳集》。]传说这一年老彭山果然又长起草木来了。
这种传说的意思,是以老翁那股泉水,象征苏轼生命的源头。而老彭山杰秀之气,本来独钟苏轼一身,所以草木不生;现在泉水复溢、彭山复青,都是苏轼生命垂尽的兆头。
蜀中出了苏轼这样的一个人物,蜀人对他当然非常关切。苏轼刚向朝廷请准“致仕”,乡人父老,便纷纷表示希望他能还乡。没想到这时候,他的病势已很沉重,不久,逝世的噩耗,就接着来了。
苏轼逝世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浙西、淮南、京东、河北等,都是他曾经留下“甘棠遗爱”的地方,老百姓们哀悼这个肯替他们说话、能替他们做事的好官,奔走相告,嗟叹出涕。秦陇楚粤之间,只要是苏轼生前曾经到过的地方,大家觉得和他有那么一份渊源、一份情缘存在,同声痛惜。
文教界所受的冲击,当然更大。士人们邀约同道,私祭于家。如京师太学里的教授和学生,不顾政治干碍,数百人集合在慧林佛舍,举行饭僧之会。
京师内外的故交,纷纷祭悼。当时的士大夫以及苏轼的朋友和门生,撰述的纪念文字一定多得不可胜计。但因后来党祸复作,都不存稿,所以流传甚少,只有李廌在苏轼会葬的斋筵上,作致语曰:“……道大莫容,才高为累。惟才能之盖世,致忌嫉之深仇。久蹭蹬于禁林,遂飘零于瘴海。……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为天下所传诵。此因苏轼逝世时,李方叔还是一介布衣,顾忌较少,所以敢于直抒这番“士林公论”。[〔宋〕张端义:《贵耳集》。又见吕本中《紫微诗话》。]
做官的人,便不那样自由了。张耒当时,在知颍州任上,闻讣,举哀成服,自己掏出俸钱来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本来只是尽其门生的本分,致其师弟之哀而已,不料这也遭到台谏的议论,被贬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宋〕王称:《东都事略》。]
世以“苏黄”并称,但是黄庭坚本人,并不敢这样想。苏轼过世后,庭坚在宅内供奉他的画像,每日晨起,整肃衣冠,在遗像前上香恭揖。有人问道:“大家都以为你们二人,声名相上下耳,你以为如何?”庭坚惊惶起立道:“庭坚望能为东坡门下弟子,岂敢失尊卑之序!”[〔宋〕邵博:《闻见后录》。]
余如李昭玘、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苏门中人,终生废黜以卒。思想先驱者,生前要遭受现实社会的迫害,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而门下弟子也必须忍受池鱼之殃,则是政治的酷虐。
苏轼还没有下葬,党祸就发作了。
韩忠彦是个忠厚、懦弱的贵族子弟,实在不懂政治权术,大权旁落而不自觉,直到曾布布置完备,专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来与他抗衡,愤懑中更自放弃原则,认为:“尔主绍述,我觅一最善绍述者胜之。”一错再错,他把虎狼引进来了。
蔡京为开封府尹时,与宫廷内侍都有交情,后在杭州,又与宫廷供奉童贯勾搭上了,代他呈献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出入宫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刘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干。由此,宫妾宦官,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生长深宫的皇帝,大都欢喜听信妾宦的话,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作宰相了。
邓绾的儿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陈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彦是韩琦之子。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忠彦就变更神宗之法。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绍述先帝,何其悖逆。”故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便罢相了,并以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时,再经谏官彭汝霖发动,党祸复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彦既去,蔡京便正面攻击曾布以爵禄私其亲戚。布愤辩失仪,亦罢。七月,蔡京就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祸终于在蔡京手上发生了。朝廷诏籍元祐奸党九十八人。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以苏轼为首恶,苏辙名列宰臣之内,而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都列名在“余官”条下。罚状谓之奸党,请皇帝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已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诸人的文集。
然而,书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读书人秘密传诵,称苏轼为“毗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一则,可证其事: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政府的禁令,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了,不但毁版绝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携带。但是东坡文字,秘密中流传愈广,对它的崇拜也更热烈。费衮《梁溪漫志》有一则故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
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重籍奸党,将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时期的臣僚和上书人加了进去,又将他所厌恶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网打尽,所以人数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执群中改以司马光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中,首恶仍是苏轼。御书勒碑,置文德殿门东壁。蔡京又自写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众共见,说是“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其间,发生两则类似的故事,一见于《宋史》: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
无独有偶,还有个九江碑工李仲宁。王明清《挥麈三录》云:
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廷坚)太史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开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
政治权力,看似挟有雷霆万钧之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古往今来,邪恶的政权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战栗颓败。蔡京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郡县,遍立党籍碑,被以奸邪恶名,妄图传之“万世”,不料即使当时,人们的评价便已适得其反,魏了翁《鹤山题跋》云:
崇宁定元祐为奸党,元符上书人为邪等,以附元祐之末。且奸邪之名,人所甚恶;而子孙矜以为荣,作史者又以奸魁邪上为最荣。然则,谓随夷溷,谓跖蹻廉,千数百年间用事之臣,盖一辙也。
除出人们内心里一致的公意之外,还有天变。
崇宁五年(1106)正月,彗星出现于西方,尾长竟天,太白昼见。某夜,暴风雷雨大作,无巧不巧,单单将党籍碑打碎了。当风雷毁碑时,蔡京厉声道:“碑可毁,名不可灭!”但是,徽宗皇帝怕了,立即诏除朝堂外处的党禁石刻,下诏自咎,求直言,罢方田、岁贡、科敛、市易、香盐矾茶诸事。
二月,遂罢蔡京,畏天怒也。但所重用为右相的却是赵挺之。
政和改元,崇信道教的徽宗皇帝于宝箓宫内设醮祈禳,道士焚章伏地,历时甚久,才起来。皇上问是何故,答曰:“适才到了玉皇大帝殿上,恰逢奎星奏事,等他完事后,才得上达。”皇上问:“奎星何神?”答曰:“就是本朝的苏轼。”徽宗大惊,随即下诏追赠龙图阁待制,时在苏轼逝世后十年。
这是道士以神道设教的故技,谏诤皇帝的神话,徽宗也欢喜受骗。能够管束皇帝的,毕竟只有“天”。
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京师,移文开封府指名索取《东坡文集》、司马光《资治通鉴》诸书。大概因为金人都那么敬爱苏轼的著作,所以这一年又诏复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
宋高宗朝的建炎二年(1128),诏复苏轼为端明殿学士,尽还该得的恩数。绍兴元年(1131)特赠朝奉大夫,资政殿学士。绍兴九年(1139)诏赐汝州郏城县坟寺名为旌贤广惠寺。
宋孝宗说得上是苏轼的“异代知己”,他爱好苏轼的诗文,以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却能挪出时间来精读苏轼卷帙不少的全部著作,已经难得;又甚敬重他的高风亮节,欣赏他的才华与迈往之气。乾道六年(1170)以知眉州的何耆仲之请,赐谥文忠。复又感念苏轼生平“经纶不究于生前”的寂寞,决然要“议论常公于身后”,再崇赠太师;九年(1173)复诏有司重刊《东坡全集》,御笔亲撰序赞,弁于集前,书赐轼之曾孙苏峤。这时候,距苏轼之逝,已经七十多年了。
理宗端平二年(1235)正月,诏议胡瑗等十人从祀孔子庙庭,苏轼位列张载、二程之上。这是“春秋俎豆”的大事,对于终身服膺儒学的苏轼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认定,并不等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