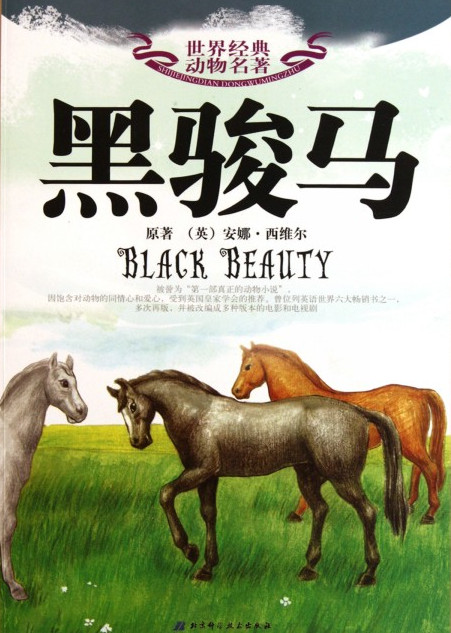赫尔克里·波洛是个不会忽略细节的人。
他动身前去拜访梅瑞迪斯·布莱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已然确信,梅瑞迪斯·布莱克和菲利普·布莱克两个人截然不同。这一次,想要速战速决是不会成功的,必须采取从容不迫的进攻手段。
赫尔克里·波洛知道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攻破这座堡垒。他必须带着适当的凭证去见梅瑞迪斯·布莱克,这些凭证得是社交上而非职业性的。所幸的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赫尔克里·波洛在很多地方都有朋友,德文郡也不例外。他坐下来回想着在德文郡有什么人脉关系,结果发现有两个人是梅瑞迪斯·布莱克先生的熟人和朋友。其中一个是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她是个和蔼的寡妇,只有微薄的收入,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另一个是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他们家在本郡定居已经有四代了。于是他就带着这两个人写的信搞了个突然袭击。
梅瑞迪斯·布莱克带着一种迷惘接待了波洛。
他近来常常感到世道变了。真是见鬼,私人侦探曾经就是私人侦探,你可以请他们在乡村婚礼的接待处给你看着贺礼,也同样可以在你不得已摊上龌龊事儿的时候一脸惭愧地去找他们帮忙。
不过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在信中这样写道:“赫尔克里·波洛是我多年的挚友,请尽最大可能给予他帮助,好吗?”而玛丽·利顿-戈尔可不是——绝对不是——那种你会把她和私人侦探之流联系起来的女人。海军上将克朗肖则写道:“很棒的家伙——绝对可靠。若你能尽量帮他我将不胜感激。他是个极其有趣的人,能给你讲很多好玩儿的事情。”
现在这个人就站在面前,看上去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衣服穿得完全不对路——还穿了双带扣子的靴子!——留着不可思议的胡子!和他——梅瑞迪斯·布莱克——根本就不是一类人。看起来他似乎从来没有打过猎或者开过枪,甚至也没参加过什么正经的娱乐活动。就是个外国佬。
赫尔克里·波洛不禁觉得有些好笑,因为他几乎可以分毫不差地猜透对方的心思。
当火车载着他进入西部乡村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对这件案子兴趣大增。如今,他终于可以亲眼看到多年以前事情发生的地方了。
就是这座汉考斯庄园,年轻的兄弟两人曾经在这里生活。他们常去奥尔德伯里,在那里嬉闹,打网球,还结识了年轻的埃米亚斯·克雷尔和一个叫卡罗琳的姑娘。在那个悲剧发生的早上,梅瑞迪斯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奥尔德伯里。那已经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赫尔克里·波洛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彬彬有礼却又带着几分局促不安的男人。
基本上,不出他所料,梅瑞迪斯·布莱克表面上看起来就和每一位英国乡村的绅士一样,手头不那么宽裕,喜欢在户外待着。
他身穿一件破旧不堪的哈里斯毛料大衣,一张饱经风霜的中年人脸庞上带着愉快的表情;一双蓝眼睛看上去颜色有些黯淡;嘴巴本就不大,还被乱蓬蓬的胡子挡住了一部分。波洛发现梅瑞迪斯·布莱克和他的弟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显得犹豫不决,心理活动显然也是慢悠悠的。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生活节奏也跟着慢了下来,他弟弟却反而越来越快。
波洛已经猜到,跟这类人打交道着急是没用的。那种英国乡村闲散自得的生活方式早就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面去了。
尽管按照乔纳森先生的说法,兄弟俩之间好像只差几岁,但侦探心想,他看上去可比他弟弟显得老多了。
赫尔克里·波洛很得意于自己知道如何利用这种“熟人关系”。现在不是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英国人的时候。绝不能,你必须做个外国人——坦诚地做个外国人——这样反倒能够得到对方宽宏大度的谅解。“当然,这些外国人并不太懂规矩,居然还会在早餐的时候和人握手。不过,还确实算得上是个体面的人……”
波洛开始有意给对方留下这种印象。两个人小心翼翼地从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和克朗肖海军上将谈起,其间也提到了一些其他人的名字。所幸的是波洛还真认识某某的表亲,也见过某某的嫂子之类的。这样一来他发现乡绅的眼神里逐渐显露出了热情,仿佛觉得这家伙似乎还颇认识些人。
然后波洛在不知不觉中很巧妙地表明了来意。并且对于意料之中对方不可避免的退缩给予了迅速的回应。哎呀,这本书就要开始写啦。克雷尔小姐——也就是现在的勒马钱特小姐——渴望他能够审慎地进行编纂。不幸的是,这件事本身家喻户晓。不过,如何去表述才能避免揭人伤疤,这个问题上倒是大有可为。波洛又小声补充说,以前他也曾经利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影响力删除过某本回忆录中夸张失实的段落。
梅瑞迪斯·布莱克的脸气得通红,装烟斗的时候连手都在微微颤抖。他有些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他们这样把事情又刨出来可真是有点儿残……残忍。毕竟已经十……十六年了。怎么就不能让这件事顺其自然地过去呢?”
波洛耸了耸肩膀,说道:“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你又能怎么办呢?总是会有这样的需求。况且任何人也都有重构一桩定案并且对它品头论足的自由啊。”
“在我看来这可不怎么光彩。”
波洛低声说道:“唉,我们可不是生活在那样一个精致的年代了……布莱克先生,你要是知道我曾经如何成功地把一些遣词用句很不客气的书,怎么说呢,润色得更加柔和,更能让人接受的话,你会大吃一惊的。因此我也很希望在这件事上能够尽我所能地保护克雷尔小姐的心理感受。”
梅瑞迪斯·布莱克喃喃自语道:“小卡拉!那个孩子!她已经长大成人了,真有点儿难以置信啊。”
“我明白。时光易逝啊,对不对?”
梅瑞迪斯·布莱克叹了口气,说道:“过得太快了。”
波洛说:“从我给你的那封克雷尔小姐的信里你应该已经看到了,她迫切地想要了解当年那出惨剧的前前后后,越详细越好。”
梅瑞迪斯·布莱克有点儿恼怒地说道:“为什么?为什么又要翻这些旧账?要是能忘得干干净净该有多好。”
“布莱克先生,你这么说是因为你对往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别忘了,克雷尔小姐可是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应该说,她所能知道的仅限于官方报告中的那些事情。”
梅瑞迪斯·布莱克皱起了眉头,说道:“是啊,我忘记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对她来说这种处境太糟糕了。得知真相时的那种震惊,还有那些关于审判的呆板乏味、冷漠无情的报告。”
“你永远都不可能,”波洛说道,“指望仅凭一份法律文档就得到事实真相。真正重要的反倒常常是那些被遗漏的事情。那种情绪,那种氛围,每个当事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那些可以使判决从轻的情节——”
他停了一下,而对方马上就像个轮到自己说台词的演员一样迫不及待地开口了。
“使判决从轻的情节!就是这个。要说真有什么能从轻判决的情节,也就是这个案子里会有了。埃米亚斯·克雷尔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两家又是世交,但是坦率地说,我不得不承认,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实在是离谱。当然,他是个艺术家,想必这个理由就可以解释一切了吧。但事实摆在那儿,他把自己卷到一系列太不同寻常的事情里去了,没有哪个普通的正派人会愿意自己陷入那种境地的。”
赫尔克里·波洛说:“你这么说让我觉得很有意思。那种情形一直让我困惑不解。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又见过世面的人不应该让自己摊上这些事儿啊。”
布莱克那张瘦削的脸上开始有了些生气。他说:“没错,但关键就在于埃米亚斯从来就不是个寻常之辈!你也知道,他是个画家,对他来说,画画是第一位的——有时候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理喻!当然了,我有一点儿理解克雷尔,因为我从小就认识他。他们家的人和我们家的人也都差不多。克雷尔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只是一旦涉及艺术的问题,他就不再循规蹈矩了。你瞧,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都不能算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可是一流的,真正的高手。有些人说他是个天才,也许他们说得没错。不过让我来说的话,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情绪才显得不那么稳定。当他在作画的时候,其他任何事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也绝不允许任何事情来妨碍他。他就像是在做梦一样,完全沉浸其中。只有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他才会从这种全神贯注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拾普通人的生活。”
他用探询的目光看了看波洛,后者点点头。
“我知道你能明白。所以呢,我觉得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形成了那种特别的局面。他爱上了那个女孩儿,想要娶她为妻,准备好了要为她抛妻弃女。不过那会儿他已经在这儿开始为她画像了,他想要完成这幅作品。任何其他事情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他也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这种状况对于当事的两个女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而他却似乎浑然不觉。”
“那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想法吗?”
“啊,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猜埃尔莎能理解。她对他的画作极其推崇,不过她的处境也很尴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卡罗琳嘛——”
他停下来,波洛说道:“是啊,卡罗琳怎么样?”
梅瑞迪斯·布莱克有些面露难色地说:“卡罗琳嘛——其实我一直——嗯,我一直都很喜欢卡罗琳。曾经有那么一阵子,我很想娶她。不过很快我也就断了这个念头了。不过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还是会全心全意为她效劳的。”
波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觉得从最后这句有些老派的话看来,面前的这个男人很有代表性。梅瑞迪斯·布莱克是那种很乐意为浪漫献身并且以此为荣的人。他会效忠于他心爱的女人,并且不求任何回报。没错,他实在是太符合这种特点了。
他字斟句酌地说道:“那么站在她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一定会对这种做派觉得很反感吧?”
“哦,当然,我很反感。实际上,我……我还就这个问题告诫了克雷尔呢。”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实际上就在之前的那天,我是指出事之前。你知道,他们那天都过来喝茶。我把克雷尔叫到一边,跟他把话挑明了。我记得我甚至说了,这样对她们两个人都不公平。”
“啊,你这么说了?”
“是的。不过你知道吗,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意识到。”
“可能是没有。”
“我跟他说,你这样等于是把卡罗琳摆在了一个完全无法忍受的位置上。如果他就是想跟那个女孩儿结婚,就不应该让她住在这栋房子里,而且还纵容她有意无意地在卡罗琳面前搔首弄姿。要我说,这根本就是一种让人忍无可忍的侮辱。”
波洛好奇地问:“他怎么回应的?”
梅瑞迪斯·布莱克带着厌恶的神情答道:“他说了:‘卡罗琳必须将就着忍着。’”
赫尔克里·波洛的眉毛抬起来了。
“这个回答,”他说,“可一点儿都没有同情心。”
“我觉得简直是太差劲了,就冲他发了脾气。我说毫无疑问,他根本就不介意给他的妻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因为他已经不喜欢她了。但那个女孩儿呢,总要为她考虑考虑吧?难道他就没意识到这种情况对她来说也是很难受的吗?结果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埃尔莎也必须忍着!
“然后他又说:‘看来你还是不明白,梅瑞迪斯,我正在画的这幅画是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我告诉你,它真的棒极了。不能因为两个争风吃醋的女人在那里吵吵闹闹就被搅乱了——不,绝不,门儿也没有。’
“跟他说话真是毫无用处。我说他看来根本不顾什么体面了。我告诉他,画画不是一切。结果他打断了我,说:‘啊,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我还是特别生气。我说他一直以来对待卡罗琳的态度都是极其可耻的。她跟他在一起简直是苦不堪言。他说他知道,并且也对此感到很抱歉。很抱歉!他说:‘我都知道,梅里[梅瑞迪斯的昵称],你可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我让卡罗琳的生活一塌糊涂,而她一直都那样隐忍。但我想她应该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坦白地告诉过她,我就是个该死的自私自利、放荡不羁的家伙。’
“我很强硬地对他讲明,他不应该破坏自己的婚姻生活,而且也要考虑孩子,以及其他的方方面面。我告诉他我能够理解像埃尔莎这样的女孩儿对男人的吸引力,但就算是为她着想,他也应该和她一刀两断。她太年轻了,别看她现在义无反顾,过后也许就会追悔莫及了。我问他怎么就不能咬咬牙狠狠心和她做个了断,然后回到他妻子身边去呢?”
“那他说什么?”
布莱克说:“他看上去只是一脸的尴尬,拍着我的肩膀说:‘梅里,你是个好人,只是太多愁善感了。等我把这幅画画完,你就得承认我是对的了。’
“我说:‘让你的画见鬼去吧。’接着他咧着嘴笑了,对我说全英国所有的神经质女人都没法阻止他。然后我说如果等画儿画完了他再把整件事告诉卡罗琳会更合适一些。他说那不是他的错,是埃尔莎非要抖搂出来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她觉得如果不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够坦诚。她想把所有事情都清清楚楚地摆在桌面上。唉,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能理解这种做法,而且单论这一点,这个女孩儿是值得尊敬的。不管她的行为有多么恶劣,她至少想要做个诚实的人。”
“很多本不必有的痛苦和悲伤都源于诚实。”赫尔克里·波洛评论道。
梅瑞迪斯·布莱克疑惑地看着他。他不太喜欢这个见解,叹了口气说道:“那是我们大家最——最不快乐的一段日子。”
“而唯一看起来不受影响的人是埃米亚斯·克雷尔。”波洛说。
“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他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我现在想起来了,他离开的时候还笑着对我说:‘别担心,梅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波洛咕哝道。
梅瑞迪斯·布莱克说:“他是那种不会把女人当真的人。我本来应该告诉他卡罗琳很绝望的。”
“是她这么跟你说的?”
“倒也没说这么多。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她那天下午的样子——面色苍白,神情紧张又强作欢颜。她不停地说笑,但她的眼睛里透着极度的悲苦,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同情的眼神。况且她还是个那么温柔的人。”
赫尔克里·波洛一言不发地看了他一小会儿。显然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不觉得这样评说一个第二天就蓄意杀害了自己丈夫的女人有什么不合适。
梅瑞迪斯·布莱克继续说着。到现在他已经基本上克服了开始时的那种满腹猜疑的敌意。赫尔克里·波洛有一种倾听的天赋。对于梅瑞迪斯·布莱克这样的人来说,重温往事是很有吸引力的。此时此刻,他与其说是在对客人讲话,莫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了。
“我想,我本应该有所怀疑的。就是卡罗琳把话题引到——引到我小小的爱好上去的。我必须承认,我对那个很热衷。你不知道,古老的英国草药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问。有太多曾经可以入药的植物现在都从官方的药典中销声匿迹了。然而说真的,仅仅是把某种药草煎煮一下就有可能产生奇效,这绝对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有一半的病人都不需要看大夫了。法国人比较懂这些事,他们的一些煎药绝对是一流的。”他已经跑题了,转而谈起了他的爱好。
“比如说蒲公英茶吧,就是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再比如说蔷薇果的汤剂,我前几天还在哪儿看到,说眼下医药界又开始流行用这个了呢。噢,我必须承认,我从自己做药的过程中能找到很多乐趣。按时令采集药材,把它们晾干,浸泡,还有其他一系列的事情。我有时候甚至都有些迷信,非要在满月或者任何前人建议的特定时刻采集药草根之类的。我记得那天我专门给我的客人介绍了斑毒芹。这种植物两年一开花。你需要在它们的果实成熟以后,变黄之前去采集。要知道,毒芹碱是一种已经被淘汰的药,我相信在最新的药典上你找不到任何跟它有关的官方制剂,但我已经证明了它对治疗百日咳有效,对于哮喘也是,就这一点而言——”
“所有这些你在实验室里都讲过?”
“是的。我带他们四处参观,给他们讲解各种药物,比如缬草和它能吸引猫的特点——闻一下就够它们受的了!然后他们问到了致命的茄科植物,我给他们讲了颠茄和阿托品。他们都兴趣盎然。”
“他们?这里面都包括谁?”
梅瑞迪斯·布莱克看上去有些意外,似乎已经忘了他的听众并没有亲眼目睹当时的场景。
“噢,我是指所有的人。让我想想啊,菲利普和埃米亚斯当时在,还有卡罗琳,当然,还有安吉拉,以及埃尔莎·格里尔。”
“这就是所有的人了?”
“是,我想是吧。没错,我确定,”布莱克好奇地看着他,“还应该有谁吗?”
“我想也许那个家庭女教师——”
“哦,我明白了。不,她那天下午没来这儿。我相信我现在已经忘记她的名字了。她人很不错,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我觉得安吉拉可没少让她操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她是个好孩子,只是被惯得有点儿野,总在想各种各样的坏点子。有一天她趁埃米亚斯在那儿专心画画儿的时候,把一只鼻涕虫放在了他后背上。结果他大发雷霆,到处追着她骂。也就是从那之后,他才坚持要把她送到学校去。”
“把她送到学校去?”
“是的。我并不是说他就不喜欢她了,只是他发现她有时候有点儿招人讨厌。而且我觉得——我总是想——”
“什么?”
“我觉得他也有些嫉妒。你知道吗,卡罗琳几乎整天围着安吉拉转,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把安吉拉放在第一位——而埃米亚斯可不喜欢这样。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我不想细说,只是——”
波洛打断了他。
“原因就是卡罗琳·克雷尔一直在为让这个孩子破了相感到自责吗?”
布莱克惊叫道:“哦,你知道这个?我本来不想提的,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但是没错,我觉得这就是她那种态度的根源。可以这么说,她似乎总是觉得为安吉拉做任何事情来弥补都不为过。”
波洛沉思着点点头。他问道:“那安吉拉呢?她对这个同母异父的姐姐是否还怀恨在心呢?”
“哦,不,别有这种想法。安吉拉很爱卡罗琳。我确信她从来都没想过那件陈年往事,只是卡罗琳自己无法原谅自己。”
“安吉拉喜欢这个要送她去寄宿学校的主意吗?”
“不,一点儿都不喜欢。她冲埃米亚斯大发脾气,卡罗琳站在她这一边,只是埃米亚斯心意已决。虽然埃米亚斯在很多方面还是个挺随和的人,可他是个火爆脾气,要是真生起气来,其他人都不得不让步。卡罗琳和安吉拉也只能屈从。”
“那她什么时候就该去学校了呢?”
“秋季学期,我记得他们在给她收拾行装。我想要不是发生了这桩悲剧,她应该在几天之后就动身离开了。就在出事的那天早上,他们还谈起给她打点行李的事儿呢。”
波洛说:“那家庭女教师呢?”
“家庭女教师?你问她是什么意思?”
“她愿意这样吗?这样一来她不就失业了吗,对不对?”
“是,没错,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的。小卡拉也经常和她学些功课,不过当然啦,那时她只有——多大来着?六岁左右吧。她还有一个保姆,他们不会为了她再继续雇用威廉姆斯小姐的。啊,就是叫这个名字——威廉姆斯。真有意思,当你说起他们的时候,这些事儿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确实如此。你现在已经回到过去了,对吗?你回想起那些场景,人们说过的话,他们的动作举止,以及他们脸上的表情了吗?”
梅瑞迪斯·布莱克慢悠悠地说道:“从某方面来说,是的……不过你知道,还是会有很多空白……有很多很多细节都忘记了。比如说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听说埃米亚斯要离开卡罗琳的时候有多么震惊,但我想不起来究竟是他还是埃尔莎告诉我的了。我清清楚楚记得为这件事情和埃尔莎争论,我就是想要告诉她这件事儿她做得有多缺德。但她只是像平时一样满不在乎地笑话我,说我太古板了。好吧,我可以说我就是古板,但我仍然认为我是对的。埃米亚斯有妻子有女儿,他理应忠于她们。”
“不过格里尔小姐觉得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
“是啊。我得提醒你,十六年前人们看待离婚可不像现在这样习以为常。但埃尔莎是那种很前卫的女孩儿。她的观点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幸福,那就还不如分开。她说埃米亚斯和卡罗琳从未停止过争吵,因此对孩子来说,避免在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更有利。”
“那她的理由没有能够打动你吗?”
梅瑞迪斯·布莱克慢条斯理地说:“我一直都觉得她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在说什么。她不假思索地背诵着那些从书里看到的或是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东西,就像是鹦鹉学舌一样。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奇怪,但不知怎么着,我觉得她挺令人同情的。那么年轻,那么自信。”他顿了一下,“波洛先生,青春本身就拥有一些东西,一种非常打动人的力量。”
波洛饶有兴趣地看着他,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布莱克继续说下去,更像是在对自己而非波洛说话。
“我想,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我为什么要阻止克雷尔。他比那女孩儿差不多大二十岁,看起来太不公平了。”
波洛低声说道:“唉,别人的劝阻很难管用的。当一个人决心已定的时候,让他回心转意可没那么容易。”
梅瑞迪斯·布莱克说:“千真万确。”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点愤愤不平,“我当然明白我的干涉是无济于事的。本来我也不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从来都不是。”
波洛迅速地瞥了他一眼。透过他语气中的酸涩,波洛看到了这个敏感男人对于自己缺少人格魅力的不满。他自己也承认布莱克刚才所说的话是真的。梅瑞迪斯·布莱克不是个能够说服别人去做或者不做什么事情的人。他善意的劝说总是会很随意地被当成耳旁风;他的话不会惹人生气,却又绝对会被放在一旁。因为他说话没有分量,从根本上来说他是个无足轻重的人。
波洛做出要改变这个痛苦话题的表示,说道:“你还留着你的实验室,还有里面那些药物和补品吗?”
“没有。”
这个词蹦出来得很突然,梅瑞迪斯·布莱克的脸涨得通红,几乎是带着痛苦的神情急速说道:“我把那些都扔掉了,把实验室也关了。我没法再接着做下去了,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还让我怎么继续下去?你瞧,可能有人会说这整件事情都是我的错。”
“不,不,布莱克先生,你太敏感了。”
“但你还不明白吗?要是我没有收藏这些该死的药呢?要是我那天下午没有刻意强调这些,吹嘘这些,让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药上面呢?只是我从来没有料到——做梦也想不到——我怎么可能——”
“是啊,怎么可能料到呢?”
“但我装作自己很懂的样子,为我知道的那点儿皮毛扬扬自得。真是个盲目自大的蠢货啊。我还专门指明了那该死的毒芹碱,甚至带着他们回到书房,给他们朗诵《斐多篇》[《斐多篇》,柏拉图的第四篇对话录,内容为苏格拉底饮下毒药前的对话]里描述苏格拉底之死的段落,真是要多蠢有多蠢。我一直都很赞赏那段话,写得美极了。但自那以后这段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
波洛说:“他们在毒芹碱的瓶子上发现谁的指纹了吗?”
“她的。”
“卡罗琳·克雷尔的?”
“是的。”
“没有你的?”
“没有。你瞧,我根本就没动过那个瓶子,只是指给他们看而已。”
“但你以前肯定也动过啊。”
“哦,那是自然,不过我隔几天就会给这些瓶子擦灰。当然我从不让仆人们进来,在出事之前四五天我刚刚擦过一次。”
“你平时都是把门锁好的吗?”
“总是锁着的。”
“那卡罗琳·克雷尔是什么时候从瓶子里拿走毒芹碱的呢?”
梅瑞迪斯·布莱克有些不情愿地回答道:“她是最后离开那个房间的。我记得我在外面叫她,她就急匆匆地跑出来了。她的脸颊微微泛红,眼睛睁得老大,看起来很兴奋。噢,老天爷啊,我现在仿佛都能看见她当时的样子。”
波洛说:“那天下午你和她说过话吗?我的意思是,你们讨论过她和她丈夫之间的事情吗?”
布莱克用低沉的声音慢吞吞地说道:“没有直接谈到过。我告诉你了,她看上去一副很难过的样子。有那么一会儿,差不多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的时候,我对她说:‘亲爱的,有什么麻烦事儿吗?’她说:‘所有事都很麻烦……’我真希望你能听见她话音中的那种绝望。那些话绝对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埃米亚斯·克雷尔就是卡罗琳的整个世界,无论如何都躲不开这一点。她说:‘一切都消失了,结束了。梅瑞迪斯,我完了。’然后她笑起来,转向其他人,突然之间变成很快乐的样子,只是看起来极其不自然。”
赫尔克里·波洛缓缓地点点头,看上去毕恭毕敬。他说道:“是啊,我明白,就像是……”
梅瑞迪斯·布莱克突然一拳捶在桌子上,他提高了嗓门,几乎是在叫嚷。
“我要告诉你,波洛先生,卡罗琳·克雷尔在审判的时候说她拿那东西是为她自己拿的,我可以发誓她说的是实话!那个时候她心里根本就没有谋杀的念头。我发誓没有。那是后来才有的。”
赫尔克里·波洛问道:“你确定后来就有了?”
布莱克瞪着眼睛,说道:“对不起,我不是很明白你的话——”
波洛说:“我问你是否确定她曾经有过谋杀的念头呢?你能够在内心里彻底说服你自己,卡罗琳·克雷尔是蓄意谋杀吗?”
梅瑞迪斯·布莱克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他说:“但如果不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是想说——啊,是某种意外?”
“也不见得。”
“这么说的话可就太离奇了。”
“是吗?你刚说过卡罗琳·克雷尔是个温柔的人。温柔的人会去杀人吗?”
“她是个温柔的人,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会吵得很凶,这个你知道的。”
“那时她就不是那么温柔了?”
“但她确实是——噢,想把这些解释清楚太难了。”
“我正在试着去理解。”
“卡罗琳的嘴很快,说话的时候容易激动。她可能会说‘我恨你,我巴不得你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并不等于说她就会付诸行动。”
“所以在你看来,谋杀极不符合克雷尔太太的性格,对吗?”
“波洛先生,你说话的方式真的是与众不同。我只能说,没错,在我看来确实不符合她的性格。我只能根据我自己的了解,认为这次的挑衅让她忍无可忍了。她深爱着丈夫。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女人也可能会杀人吧。”
波洛点着头。“没错,我同意……”
“我一开始听说的时候都惊呆了。我觉得那不可能是真的。而且也的确不是真的,如果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是说干这件事情的不是真正的卡罗琳。”
“但是你很确信,我是指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卡罗琳·克雷尔确实杀了人,对吗?”
梅瑞迪斯·布莱克又一次瞪着他。
“老兄,如果她没有——”
“对啊,如果她没有呢?”
“我想象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答案。意外?想必不可能吧。”
“要我说,可能性很小。”
“而且我也不相信自杀的说法。当时不得不提出这种理论,不过对任何了解克雷尔的人来说都是不足为信的。”
“确实如此。”
“那还有什么可能?”梅瑞迪斯·布莱克问。
波洛冷静地说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其他人杀了埃米亚斯·克雷尔。”
“但这太荒唐了!”
“你这么认为?”
“我确信无疑。谁会想要杀了他呀?谁又可能会杀了他呢?”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你该不会真的相信——”
“也许不会。但调查这种可能性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认真地考虑一下,然后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梅瑞迪斯瞪了他片刻,然后垂下了眼睛。过了一小会儿,他摇了摇头,说道:“我还是想不出任何其他的可能,我倒是希望能想出来呢。要是有任何理由能够怀疑其他人的话,我会很乐意相信卡罗琳是清白的。我不愿意认为是她干的。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但还有谁呢?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菲利普?克雷尔最好的朋友。埃尔莎?太可笑了。我自己?我看起来像个杀人凶手吗?正派且令人尊敬的家庭女教师?还是那几个忠实的老仆人?或许你是在暗示是安吉拉那个孩子干的?不,波洛先生,没有别的可能。除了他妻子,没有人会杀害埃米亚斯·克雷尔。但那是他迫使她那么干的。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算作自杀。”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死亡虽然不是他亲自动的手,却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
“是的,也许这是个有点儿怪异的想法。不过毕竟有因有果,你明白吧。”
赫尔克里·波洛说:“布莱克先生,你是否曾经考虑过,谋杀的原因几乎总是要靠研究被害人才能得知呢?”
“我确实没有考虑过,不过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波洛说:“只有先确切地搞清楚被害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弄明白罪案发生时的情形。”
他又补充道:“这就是我在探求,同时也是你和你弟弟给予我很多帮助的问题——重建埃米亚斯·克雷尔这个人。”
梅瑞迪斯·布莱克忽视了这句话的主要内容,他的注意力单单被一个词吸引住了。他迅速说道:“菲利普?”
“是的。”
“你也已经和他谈过了?”
“当然。”
梅瑞迪斯·布莱克尖刻地说道:“你应该先来找我的。”
波洛微微一笑,做了个礼貌的手势。
“如果按照长幼有序的规矩来说,确实如此,”他说,“我知道你是哥哥,但你要理解,你弟弟就住在伦敦附近,对我来说先拜访他比较方便。”
梅瑞迪斯·布莱克仍然皱着眉头,心神不宁地扭曲着嘴唇,然后重复道:“你应该先来找我的。”
这一次波洛没有回答,他等待着。没一会儿梅瑞迪斯·布莱克就继续说道:“菲利普,”他说,“怀有偏见。”
“是吗?”
“实话实说,他的偏见很深,而且向来如此。”他惴惴不安地瞟了波洛一眼,“他肯定会极尽所能地说卡罗琳坏话的。”
“这很要紧吗,尤其是在过了这么久之后?”
梅瑞迪斯·布莱克猛地长叹一声。
“我知道。我忘了已经过了那么久,所有事情都过去了。卡罗琳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意让你留下一个错误的印象。”
“那你觉得你弟弟可能会给我一个错误的印象吗?”
“坦率地讲,是的。要知道,他和卡罗琳之间——怎么说呢?——一直都有点儿水火不容。”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激怒了布莱克。他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事实如此。菲利普一有机会就找她的碴儿。我觉得在埃米亚斯娶她的时候他就很生气。有一年多的时间他都躲他们两人远远的。埃米亚斯可几乎是他最好的朋友啊。我猜这就是真正的原因所在。他觉得没有哪个女人好到能配得上他。而且他可能还觉得卡罗琳的出现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友情。”
“那么是这样吗?”
“不,当然不是。埃米亚斯依然很喜欢菲利普,从始至终都是。他总是挖苦他,说他掉到钱眼儿里去了,不光办了个公司,还变得很市侩。菲利普倒不在意。他听完顶多也就是一笑了之,还说埃米亚斯有他这么个体面的朋友终究是件好事。”
“你弟弟对埃尔莎·格里尔这件事有什么反应呢?”
“你知道吗,我发现这个很难说清楚。他的态度真的不太明朗。我想他很生埃米亚斯的气,觉得他在为了一个女孩儿犯傻。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埃米亚斯这样行不通,说他最终会后悔的。然而同时我还有一种感觉,没错,一种很明确的感觉,觉得他看见卡罗琳的那种失落,心里又会有点儿窃喜。”
波洛眉头一挑,说道:“他真是这样想的?”
“哦,别误会我的意思。我只能说我相信他心里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想法。菲利普和我截然不同,不过你知道,同胞之间还是会有某种联系的。兄弟中的一个人常常会知道另一个人在想些什么。”
“那悲剧发生之后呢?”
梅瑞迪斯·布莱克摇摇头。一阵痛苦的抽搐划过他的脸庞,他说道:“可怜的菲尔[菲利普的昵称]。他伤心欲绝,被这个消息打垮了。你知道的,他一直都很忠于埃米亚斯。我想,也许有一些个人崇拜的因素在里面。埃米亚斯·克雷尔和我同岁,菲利普比我们小两岁。他一直都崇拜埃米亚斯。没错,这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此他才会——才会那么强烈地指责卡罗琳。”
“那么,至少他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梅瑞迪斯·布莱克说:“我们所有人都毫不怀疑……”
一阵沉默。接着布莱克以一种软弱之人的哀怨口吻不耐烦地说道:“事情都过去了,大家本来都忘记了,可是现在你又来了,把这些事都翻出来……”
“不是我,是卡罗琳·克雷尔。”
梅瑞迪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卡罗琳?你是什么意思?”
波洛看着他,说道:“是卡罗琳·克雷尔二世。”
梅瑞迪斯的表情轻松下来。
“啊,是那个孩子。小卡拉。我刚才误解了你的意思。”
“你以为我指的是原本的那个卡罗琳·克雷尔吗?你以为她会——怎么说呢——死不瞑目?”
梅瑞迪斯·布莱克打了个激灵。
“别再说了,老兄。”
“你知道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女儿吗?那是她最后写下的话,信里说自己是无辜的。”
梅瑞迪斯盯着他,带着难以置信的语气说道:“卡罗琳是这么写的?”
“是的。”
波洛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让你很吃惊吗?”
“如果你见过她在法庭上的样子,你也会吃惊的。那是个可怜的、被人围捕却又毫无还手之力的人。甚至连挣扎都不挣扎一下。”
“一个失败主义者?”
“不,不,她不是那样的人。我想,是因为知道自己杀死了她所爱的男人吧,我觉得是这样。”
“你现在并不那么确定了,是吗?”
“临死之前,她还那么郑重地写下了这样的话。”
波洛提醒他说:“也许只是个善意的谎言。”
“也许吧,”但是梅瑞迪斯有些将信将疑,“不过这可不像——不像是卡罗琳……”
赫尔克里·波洛点点头。卡拉·勒马钱特也这么说过。卡拉有的只是她儿时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梅瑞迪斯·布莱克是非常了解卡罗琳的。这也是波洛得到的第一份证据,能够支持卡拉所持有的信念。
梅瑞迪斯·布莱克抬眼看着他,慢吞吞地说道:“假如——假如卡罗琳是清白的——那这整件事也太离谱了!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他猛然间转向波洛。
“那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又是一阵沉默。
“到现在为止,”波洛最终开口了,“我还什么都没想。我只是在收集各种印象。卡罗琳·克雷尔是什么样子,埃米亚斯·克雷尔是什么样子,其他当时在场的人又分别是什么样子,在那两天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不辞辛苦地逐一回顾所有事实。你弟弟已经要帮我做这件事情了,他会根据他的回忆,把当时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寄给我。”
梅瑞迪斯·布莱克尖刻地说:“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太多的东西。菲利普是个大忙人。很多事情一旦过去他也就忘记了,很可能他所记得的事情都是错的呢。”
“当然,肯定会有出入。这个我想到了。”
“我告诉你吧——”梅瑞迪斯突然停下来,稍微有点儿脸红地继续说道,“如果你愿意,我……我也可以写。我是说,这可以作为一种对照和参考,对吗?”
赫尔克里·波洛亲切地说道:“那可太有价值了,这是个绝好的主意!”
“好吧,我写。我还有一些以前的日记。不过我得提醒你,”他有些尴尬地笑笑,“我的文笔可不太好,甚至有时候拼写都会出错。你……你不会抱太高的期望吧?”
“啊,我需要的不是文风和文体。只要把你记得的每件事如实地写下来就可以了。每个人都说了什么,他们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只要把发生的事写下来就行。不要去想它是否和这件事有关系。可以说,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了解当时的那种氛围。”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要凭空想象出从未见过的人或者从未到过的地方,一定是很难的。”
波洛点点头。
“还有一件事我想要请求你。奥尔德伯里的庄园是和这里相邻的,对吧?我有没有可能去那里,亲眼看看悲剧发生的地方呢?”
梅瑞迪斯·布莱克慢条斯理地说道:“我马上就可以带你过去。不过当然啦,那里现在变化很大。”
“那里没有被盖满了房子吧?”
“没有,谢天谢地,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不过那儿现在是一家旅社之类的,被一个什么社团买下来了。到夏天的时候会有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来这里。当然了,所有的屋子都被分隔成了小房间,地面也做了很大的改动。”
“你不得不通过解释来帮我重现了。”
“我会尽力而为的。我希望你能看看它以前的样子,那是我所知道的最漂亮的庄园了。”
他带路从落地窗穿出去,开始沿着草坪的斜坡向下走。
“是谁负责把它卖出去的?”
“是代表孩子的遗嘱执行人。克雷尔的所有东西都归那个孩子继承。他死前没有立遗嘱,所以我猜想应该是自动地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而卡罗琳的遗嘱也把她的所有东西都留给了孩子。”
“什么都没给她同母异父的妹妹吗?”
“安吉拉自己有一笔钱,是她爸爸留给她的。”
波洛点点头。“我明白了。”
然后他忽然叫出声来。
“你这是把我带到哪儿了?前面可是海边了呀!”
“啊,我得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里的地形。你马上就能亲眼看见。你瞧,这儿有一条流向内陆的小溪,他们叫它骆驼溪,看起来就像个河口一样,但其实不是,那就是大海。要到奥尔德伯里的话,如果从陆路走,你得一直往内陆去,绕过这条溪。但是我们两家之间最近的路是从这条溪最窄的地方划船过去。奥尔德伯里就在对面——喏,穿过这片树林你就能看见那栋房子。”
他们来到一小块海滩上。正对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海岬,一栋白色的房子在树林的上方若隐若现。
海滩上停放着两只小船。在波洛笨手笨脚的帮助下,梅瑞迪斯·布莱克拽过来一只,推入水中,随即他们向着对岸划去。
“以前那些日子里,我们总走这条路。”梅瑞迪斯解释道,“当然,除非赶上刮大风或者下大雨,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开车过去。不过你要是那么走的话,差不多要远上三英里呢。”
他灵巧地把船靠到对岸的石头码头上,不屑地看了一眼岸上那排小木屋和混凝土台阶。
“这些都是新盖的。以前是船屋,破烂不堪,没别的东西。我们从前都是沿着岸边走,然后到那边那块大石头下面去嬉水。”
他扶着他的客人下了船,把船拴紧,领着他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了上去。
“别指望我们能碰见谁,”他扭过头说道,“四月份谁也不来这儿,除了复活节的时候。就算碰见了也没关系。我和邻居们的关系很好。今天太阳真不错,就跟夏天似的。那天天气也很好,不像九月,倒更像是七月天。阳光明媚,只是有点儿小凉风。”
小路穿出树林,绕过一块凸出地面的岩石。梅瑞迪斯用手指着,特别强调了一下。
“那儿就是他们称作巴特利花园的地方,我们现在差不多是在它下面了,绕过去吧。”
他们又一次扎入树林之中,接着小路转了个急弯,一扇开在一堵高墙上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小路继续蜿蜒向上,梅瑞迪斯打开门,两个人走了进去。
从外面的树荫里刚走进来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波洛觉得很晃眼。巴特利是个人工开辟出来的平台,周围有带垛口的围墙,垛口上架着加农炮。给人的感觉是这里突出于海面之上,上方和后面都有树丛,但临海的这一边除了下方耀眼的湛蓝海面之外,什么都没有。
“迷人的地方。”梅瑞迪斯说。他有些轻蔑地冲着一个背靠后墙的像亭子之类的东西点了点头。“当然了,以前没有那个,只有一个又老又破的棚子,埃米亚斯把他画画的废料、一些瓶装的啤酒和几把折叠躺椅放在那儿。那时候也不是混凝土的。以前还有一条长椅和一张桌子,都是铁制的,上了漆。就这些东西,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他的声音有些发抖。
波洛说:“命案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
梅瑞迪斯点点头。
“椅子在那边——挨着棚子。他就手脚摊开地躺在上面。有时候他画画的时候也会躺在那儿——就是突然地躺下,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然后又会突然一下跳起来,像个疯子似的在画布上作画。”
他顿了一下。
“你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看上去几乎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仿佛刚刚睡着了似的。但他的眼睛是睁着的,而且他——他变得僵硬了,你知道吗,就像是突然瘫痪了。应该没有什么痛苦,这也是我一直——一直觉得比较欣慰的地方……”
波洛问了一个他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是谁发现的他?”
“是她,卡罗琳。在午饭以后。我猜我和埃尔莎是最后看见他活着的人。那时候肯定已经开始发作了。他——看起来很奇怪。我实在不想谈论这个了,我还是写下来给你看吧,那样比较容易一些。”
他猛然转过身,走出了巴特利花园。波洛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
两个人沿着曲折的小路往上走。比巴特利花园高一些的地方另有一块小空地,那里绿树成荫,也有一条长椅和一张桌子。
梅瑞迪斯说:“他们没把这里做太多的改动。不过这些长椅以前可不是用老木料做的,都是上了漆的铁家伙。坐起来有点儿硬,但是很好看。”
波洛表示了赞同。从树杈之间,他可以越过巴特利花园,向下一直看到小溪口。
“我那天上午在这里坐了一会儿。”梅瑞迪斯解释道,“那时候树还不像现在这样茂密,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巴特利花园围墙上的垛口。你知道吗,埃尔莎就在那儿摆着姿势。坐在其中一个垛口上,头转向一边。”
他的肩膀轻轻地抽动了一下。
“想不到树长得这么快,”他自言自语地说,“唉,可能是我老了吧。走,我们到上面房子那儿去。”
他们继续沿着小路走,一直来到房子跟前。这是一栋很精致的老房子,属于乔治时代风格。现在已经被扩建过了,在它旁边的绿色草坪上搭建了约莫五十个供沐浴使用的木质小屋。
“小伙子们睡在那边,姑娘们睡在屋里。”梅瑞迪斯解释道,“我觉得这儿没有什么你想看的东西。所有的房间都被分割过了。以前这里还加盖过一个小温室。后来这些人把这儿弄成了乘凉的走廊。啊,我猜他们一定很享受他们的假期。很遗憾,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保持原状的。”
他突然转过身去。
“我们从另一条路下去。你知道吗,所有往事都浮现在我脑海里了。鬼魂,到处都是鬼魂。”
他们从一条绕得更远、更不好走的路返回了码头。一路上两个人都没说话。波洛很顾及同伴的心情。
当他们再一次回到汉考斯庄园的时候,梅瑞迪斯·布莱克突然开口说道:“你知道吗,我把那幅画买下来了。就是埃米亚斯当时正在画的那幅。一想到它会因为这件事的新闻价值而被高价卖掉,然后被一大群居心叵测的畜生不怀好意地盯着看,我就无法忍受。这幅画真是杰作,埃米亚斯说这是他所有作品里最好的。如果他说的是事实,我也丝毫不会意外。实际上他几乎已经完成了,只是想再花个一两天润饰一下而已。你……你想要看一下吗?”
赫尔克里·波洛马上说道:“当然,非常乐意。”
布莱克带路穿过大厅,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他打开一扇门,两人走进了一间相当大、满是灰尘气味的房间。房间的窗户紧闭着。布莱克走到窗边,打开了木质的百叶窗,然后有些费力地推开一扇窗户,顿时,一缕带着春天气息的清新空气飘入房中。
梅瑞迪斯说道:“这样就好些了。”
他站在窗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波洛也走了过去。不用问也能知道这房间原来是做什么的。架子上空空荡荡,但是依然能分辨出摆过瓶子的痕迹。靠着一面墙有一些废弃的化学仪器和一个水池。房间里积满了厚厚的尘土。
梅瑞迪斯·布莱克看着窗外说道:“要回想起这些往事是多么容易啊。站在这儿,闻着茉莉花香,然后不停地说啊,说啊……我就是个该死的大笨蛋,光知道说我那些宝贝药水和提取液!”
波洛心不在焉地从窗户中伸出一只手去,摘下了一簇刚刚从木质茎上长出来的茉莉叶子。
梅瑞迪斯·布莱克毅然走过房间,墙上有一幅被落满了灰尘的单子盖着的画,他一把就把单子扯下来了。
波洛顿时屏住了呼吸。目前为止,他已经看过了四幅埃米亚斯·克雷尔的画作:两幅在泰特美术馆,一幅在伦敦的一个商人那里,还有一幅就是玫瑰的静物画。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艺术家本人视为自己最好作品的画作,波洛立刻就体会到这个男人是一位多么杰出的艺术家。
这幅画表面上看具有那种旧时的平整光洁。第一眼感觉就像是一张海报,颜色反差似乎也并不讲究。一个女孩儿——穿着淡黄色衬衣和深蓝色宽松长裤的女孩儿,坐在艳阳下灰色的围墙之上,背景是波涛汹涌的蓝色海面。正是那种海报常用的题材。
但第一印象是靠不住的,画中自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失真——那光线之中的耀眼和澄澈令人惊艳。而那个女孩儿——
是的,这就是活力。所有的一切都展现出活力、青春和勃勃生机。那张面孔栩栩如生,还有那双眼睛……
太多的活力!如此激情满溢的青春气息!那就是埃米亚斯·克雷尔在埃尔莎·格里尔身上看到的,以至于使他对身边温婉的妻子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埃尔莎就代表着活力,埃尔莎就代表着青春。
这是个相貌出众、身材苗条、性情直率的姑娘。她的头转向一边,带着傲慢的神情,眼神中透出胜利者的不可一世,就那样看着你,盯着你——等待着……
赫尔克里·波洛摊开双手说道:“真是幅杰作——真的,实在是棒极了——”
梅瑞迪斯·布莱克话里有话地说道:“她那么年轻——”
波洛点点头,开始思考。
“大多数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年轻。几分天真无邪,几分令人心动,几分柔弱无助。但青春并非如此!青春是原始的,青春是坚定的,青春是强壮有力的——也是残酷无情的。而且还要加上一点——青春是脆弱的。”
他跟随着主人来到门边,此时心里对于下面将要拜访的埃尔莎·格里尔的兴趣锐增。也不知道岁月会给当年这个热情奔放、得意扬扬的率真女孩儿带来什么变化呢?
他又回头看了看那幅画。
那双眼睛。注视着他……注视着他……仿佛要对他诉说什么……
假如他无法领会这双眼睛想要告诉他的事情,那么这双眼睛的主人能不能告诉他呢?还是说这双眼睛想要诉说的事情,连它们的主人都不知道?
如此傲慢,又对胜利充满如此的期待。
接着死神插手了,把猎物从那双渴求的、紧握的、年轻的手中硬生生夺走了……
那双激情四射、充满期待的眼睛中的光芒就此消失了。埃尔莎·格里尔现在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子呢?
他走出房间之前又看了最后一眼。
他想:“她实在是太有活力了。”
他觉得——有那么一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