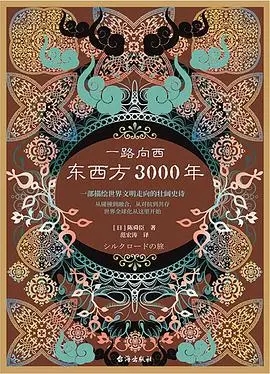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祁寯藻,而历史学家朱东安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蕴章。
不论哪个人,都是曾国藩的对头。
祁寯藻(1793—1866)是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首揆席”[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第344页。],用他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军机大臣。
此人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也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却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
往在京师,如祁(寯藻)、杜(受田)、贾(桢)、翁(心存)诸老(皆为大学士—作者注),鄙意均不以为然,恶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曾国藩全集·书信》2,岳麓书社,2011年,第675页。]
从曾国藩的这段话,可以看出祁氏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并激化。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际,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史载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会试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出自曾国藩弟子黎庶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这是他一贯的“和稀泥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祁氏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和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与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退缩,琐屑”,祁氏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习一弊疏》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谐媚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恭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曾国藩全集·奏稿》1,岳麓书社,2011年,第26页。],实际上也是批祁,因为他入军机十多年,一直没有什么建树。
虽然当初是祁氏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然而,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对此没有任何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曾国藩对祁寯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此老是没有丝毫好感的。
但是在“谐媚软熟”的同时,祁氏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祖制成法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不能更动。

祁寯藻画像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满汉一家,不分轻重。然而实际上,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政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抚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巴蜀书社,1988年,第2页。]。在军事上,满人更是绝对的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二百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世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先皇措注之深意,盖谓疏戚相维,近远相驭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畛犹严,如岳襄勤公之服金川,二杨侯之平教匪,虽倚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旗籍当之,斯制所由来旧矣”[薛福成著,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0页。]。在咸丰以前,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员参与兵事,亦不过仅“供奔走之役”。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当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奕山和隆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助手;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扬威将军奕经、文蔚、特依顺,皆是宗室或亲贵。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后来同治年间,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任陕西巡抚时,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蓉,说刘蓉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尤而效之,将成尾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行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颠倒黑白,令人愤悒”[《曾国藩全集·日记》3,岳麓书社,2011年,第227页。]。而祁氏却在日记当中说:
陈小舫廷经御史驳刘中丞蓉折,言虽太尽,义则凛然。中外相维,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折骄帅,亦不为过也。(《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日)
由此可见,祁寯藻一直是非常注意“中外相维,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官员太大的权力。
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这些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了。祁寯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说话小心并不是不说话,关键是说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要值得。
所以祁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鞋穿,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祁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祁氏肯定说过其他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中说进此谗言的是祁寯藻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祁文端公所抵排。”[马忠文、任青编:《薛福成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7页。]《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祁氏“抑曾国藩,世颇讥其偏”。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祁寯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问题上,他与肃顺产生了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
“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初起,肃顺力言其可用,上向之,寯藻皆意与龃龉,屡称病请罢。”[《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4页。]可见他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
因此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后,提到祁寯藻时仍然难以保持平和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莫子偲、穆海航来看病,畅谈,语次有讥讽祁春浦,过于激厉,退而悔之。”[《曾国藩全集·日记》2,岳麓书社,2011年,第239~240页。]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祁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字。可见两人芥蒂之深。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彭蕴章,主张和祁寯藻大同小异。彭是江苏人,和祁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祁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蕴章传》称:“蕴章久直枢廷,廉谨小心,每有会议,必持详慎。”[《清史稿》13,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019页。]也是曾国藩所说的“谐媚软熟之人”。茅海建说,他后来能在祁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达”。[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