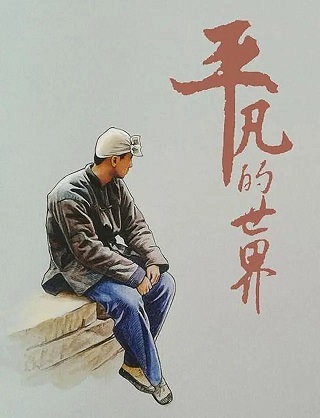天津三岔口有一座西洋哥特风格的教堂,是1869年(同治八年)由法国传教士建成的。法国人名之为“圣母得胜堂”(据说这名字中含有征服者的炫耀之意),中国人则叫它“望海楼教堂”。教堂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在附近低矮的中国传统建筑中显得鹤立鸡群,另类而醒目。
说来也巧,就在这座教堂落成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九年,河北一带出现了严重的旱灾。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这是令全社会各阶层共同焦虑的大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后来说:“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8页。]连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曾国藩都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在书房里一圈圈地踱步,担心会发生什么重大的祸变:“天气亢旱,绕室忧皇,如有非常祸变者。”[《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14页。]
有些人把法国教堂建立和天旱不雨这两件事联系了起来。“初七这一天,四乡百姓进城赴庙求雨,行抵一处天主教堂,见房顶上耸立着高高的十字架,议论纷纷,以为久旱无雨,系天主教堂十字架之故。”[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天津教案三十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其前奏也非常相似。当时华北各地同样发生旱灾,人们同样把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老天爷”,和天主教所称的“天主”,显然很难和谐相处。洋鬼子的教堂尖顶如同利剑一样,直刺苍穹,老天爷当然要生气了。
就在这时,又一桩不幸的事件发生了。
望海楼教堂隔河相望,有一座由五名法国修女建起来的慈善机构,叫仁慈堂,老百姓叫它育婴堂,里面收养了一百五十多名弃婴。1870年春夏之交,就在干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育婴堂内暴发了传染病,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
按理来说,修女们来中国从事慈善事业,收养无家可归的弃婴,看起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她们的活动却受到众多中国人的怀疑。中国有一句俗语:“无利不起早。”为什么这些洋鬼子要万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大施慈悲?这其中是不是包藏着什么祸心?
和往常一样,修女们雇人把这些死去的孩子埋葬在河东荒地。由于死的孩子太多,受雇者埋得非常草率,他们走后,薄薄的棺材很快被野犬扒开。鹰啄狗刨之下,残缺不全的尸骸零落遍地,招来大量的人围观。一个流传已久的谣言似乎因为这个悲惨的场景得到了印证:这些孩子是因法国教士“采生折割”致死,传教士们剜走了这些孩子的心,挖去了他们眼,用来做药材,然后把他们弃尸荒野。这就是西药那么灵验的原因。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挖眼剜心用来做药或者炼金之类的说法,早就在中国流传甚广。有人说,明代利玛窦等人来到中国,没有什么谋生手段,生活水平却很高,因为他们会炼银术,而炼银之术,就是靠挖死人的眼睛:“明季,其国人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先后来中国,人多信之。……善作奇技淫巧及烧炼金银法,故不耕织而衣食自裕。……或曰: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梁章钜:《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在天津教案发生的时候,这类传说已经传遍中国大小城市。所以,当残缺不全的儿童尸体暴露在荒野当中时,天津人认为传说已经得到了印证。
就在天主教堂挖眼剜心传说在天津城上空飞翔,全天津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紧张气氛的时候,一桩拐卖儿童案发生了。两名人贩子在天津静海拐走了一个姓李的小男孩,在西关被人查获。
这个案子似乎契合了挖眼剜心传说的另一部分:长久以来,人们就在传说,天主教堂一直在花钱雇用多人迷拐孩子,供作药用。此案一发,民情汹汹,全天津都在议论此事。
天津知府张光藻连夜和知县刘杰会审,地方官动用肉刑,以致案犯很快承认自己迷拐孩子是为雇主药用,但是案犯并没能“供出教民”。甚至连两名人贩的名字都没审出来。据案卷记载,这两名人贩,名字分别叫“张拴”“郭拐”。这显然不是他们的真实名字。
虽然并没有真正破案,但是官员把“从重从快”处理作为“平息民愤”的有效手段,十四日,两名人贩被砍了脑袋。随后,一张署名天津府的告示张贴到了天津大街小巷。告示说: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英国议会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6册,中华书局,2006年,第377页。]
这张告示,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个关键点。
虽然审得不清不楚,但是天津府却在公文中正式声明,迷拐幼童,用来配药,是确有其事的,并且以“受人嘱托”四个字,将幕后的主使明确指向了教会、教士和修女。
这张告示反映了晚清官员阶层对西方势力包括传教势力的反感。发布这道告示的天津知府张光藻,是进士出身,做过数任知县。由于为官廉正,1870年(同治九年)初,刚刚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天津府知府。和当时绝大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一样,张光藻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和捍卫儒教文化的本能。中国古人向来自认为居天下之中,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族群,其他国家和民族都是未开化的蛮夷。然而基督教文化的个性也异常傲慢。传教士们随炮舰而来,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粗暴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企图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竖立起光辉的十字架”[何晓明:《中华文化事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57页。]。这当然引起读四书五经出身的中国官员的本能反感。
张光藻的这道告示,让法国教堂有组织地大规模拐卖中国儿童这一传闻变成“板上钉钉”的可怕事实,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整个天津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家家房门紧闭,把儿童藏在家里,不准外出。民间兴起一股自发组织捉拿人贩子之风。
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生了作为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
五月二十日傍晚,据说一个叫武兰珍的人在天津某村迷拐了一位少年,被人捉住。在愤怒的乡民的“审问”下,案犯供述说,他是受教堂中一个叫王三的教民指使才做的这个事。“伊系赵州宁晋(津)人,帮船户拉纤来津,有教民王三将伊诱入堂中,付伊药包,令其出外迷拐男女。”[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法国鬼子提供迷药,迷拐中国人挖心作药,看来已经有了“铁证”。让这样的禽兽在中国横行,岂有天日吗?我们中国人必须采取行动了!从此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很多人跑到育婴堂和教堂门口喧闹,山雨欲来风满楼,在天津的外国人个个心惊胆战。
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刘杰和张光藻认为事关重大,不敢轻举妄动,如何办理,应请示驻扎天津专管中外交涉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决定。崇厚听取案情后,也感觉事情重大,如果不查明的话无法平息百姓的怒火。于是他派人与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沟通,商定由人贩子与法国传教士公开对质。
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上午九点多,天津官员带着“拐犯”武兰珍来到天主教堂。他们“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把教堂里的所有人一一传来,都看过了,也并没有找到王三其人。而且关键是教堂的建筑结构与武兰珍供述并不相同。武兰珍说他进入过教堂,在哪里哪里与王三交接,然而堂内并无武兰珍所说的栅栏、天棚,“门庭径路与犯供不符”[《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台北,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4467页。《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第207页。],“该犯原供有席棚栅栏,而该堂并无所见,该犯亦未能指实”[《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479页。]。显然他没有进过这里。所谓迷拐传闻更是遭到神父谢福音的矢口否认。传教士谢福音说,教堂收养的都是弃婴,乃是慈善事业。拐卖儿童,与教堂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官员对天主教印象恶劣,但很多人对神父谢福音个人并无恶感,这个人一贯谦逊诚恳,待人非常温和,樊国梁主教对他的评价是:“和于接人,智于处事,人皆乐与之游。”[《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9页。]他的辩护很有说服力。事实上,教案发生后,天津知府张光藻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知谢某忠厚和平,似不肯做此等事。”[《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
事情至此,可谓一无所获,官员们面面相觑,感觉案子无法再查下去了,此事只能不了了之。然而,已经激动起来的天津百姓却不想不了了之。得知对质消息,早已经有大批的民众前往望海楼,围观的群众达到万余人。天津地方官员带着案犯离开之时,并没有向百姓解释教士的清白,也没有发表任何安抚性讲话。因此官员们走了之后,情绪激动的群众仍然不愿散去,不少人围在天主堂门口,“见有教民出入则齐声讥诮”[戚其章、王如绘编著:《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有一些人还前往附近的法国领事馆去找法国外交官们算账。“下午两点钟攻打开始。法国领事丰大业先生的窗户被人用石头砸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0页。]
驻扎在这里的法国领事丰大业(Fontanier,Henri Victor,也有人译为丰大烈),这一年四十岁。他本来就是一个性格暴烈外向、容易激动的人,又具有那个时期典型的驻华外交官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在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时经常出言不逊。中国“暴民”威胁到自己的安全,这令他感觉无比愤怒。“他感到自己受威胁,便穿着制服带着秘书西蒙离开领事馆……前往崇厚的衙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0页。]
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据崇厚的汇报,丰大业“脚踹仪门而入”,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破口大骂。崇厚满面赔笑,“告以有话细谈”,丰大业如同没听见,从身上拔出手枪,对着崇厚就开了一枪。“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吓得马上跑到“后堂暂避”。
据崇厚汇报,经过衙门里众巡捕的好言相劝,丰大业悄悄平静了一点,于是崇厚奓着胆子从后堂走出来,“复出相见”,丰大业一见,又“大肆咆哮”,说:“尔百姓在天主堂门外滋闹,因何不亲往弹压?我定与尔不依。”并且表示要去亲自弹压。崇厚向他通报了“民情汹涌,街市聚集水火会已有数千人,劝令不可出去,恐有不虞”。[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72页。]
天津的“水会”,又叫“火会”,是一个民间“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专为救火而设,其首领是地方绅士:“不同的火会和志愿队(‘义民’)都由士绅担任其首领,这些名字登记在衙门中。”他们也参与维持治安,急公好义,保卫乡里。这次听说中国大臣被法国人打了,绅士们不约而同鸣起水会铜锣,积蓄已久的水会会众满面怒容,手执刀枪,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涌来,齐集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门外。
因此崇厚劝丰大业不要此时出去。据说丰大业的反应是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怒气冲冲,手持刀枪而出。
丰大业来到教堂前面的浮桥,恰与前来处理聚众事件的天津知县刘杰迎面相遇。二人开始对话。法方资料说,丰大业要刘杰平息暴民,知县答说:“这不是我的事。”于是。丰大业拔出手枪向刘杰开枪,打伤了他的跟丁高升。
中国民众压抑多日的情绪在这一瞬间被点燃。
“于是,人们的愤怒再也无法忍耐,如潮水决堤般迸发出来,一齐动手将丰大业、西蒙(丰大业的秘书)打死。”[朱东安:《晚清政治与传统文化》,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33页。]“众眥皆裂,万口齐腾,谓领事无状若斯,曷共殛之。潮涌坌集,白梃如雨,丰大业登时倒毙。”[萧一山编:《清代通史》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
据说两个人死得很惨:“丰大业头面被刀劈裂,脑浆迸流,复被长枪匕首刺穿右胁,锋锷深入于腹。西蒙与凶徒力战逾时,浑身寸磔。”[《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愤怒的人们接着又冲向了法国教堂。
“暴动开始了,时在午后,谢神父和吴文生神父正在用膳,忽然城内四面锣声大作,救火队员、捣乱分子手执刀剑,向圣堂冲来。
“群众已经涌至天主堂前,此时二百余名凶手冲过群众,门紧闭,他们用力敲门。门将破,谢神父决定自己去开门,与群众理论。初,群众看见神父温良可亲,一时犹疑不知所措,但神父一张口说话,群众就进入堂院里大呼。谢神父与吴神父一同逃至圣堂中,将门关上,彼此念《赦罪经》。一门被武力推开,二人乃逃至更衣所,由窗门跳入领事馆,藏在大石后边,凶手追至,将二神父杀害。”[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
在教堂中,一共有六名外国神职人员被杀死,至于被同时杀死的中国仆役等后来没有具体统计数字。
当时的场景相当恐怖。“谢、吴二司铎被凶徒剖开胸腹,脏腑尽涂于地。凶徒等见六人俱死,即褫其衣履,将尸抛于三岔河中。复将领署与天主堂抢掠一空,举火焚毁。”[《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焚毁了教堂之后,愤怒的人群又冲往仁慈堂,报复修女们。
还有大量人流一齐涌向领事馆。领事馆里的人早已逃散一空。大家扯碎了大门上的法国国旗,将里面的东西打得稀巴烂。领事馆旁边的公馆、洋行、美国和英国的几处讲书堂也统统被砸得一塌糊涂。随即人们将天主堂、仁慈堂及法商开办的富昌洋行拆毁焚烧。事后查明,纷乱之中共打死外国人二十名(法国领事一人,随员一人,法国教士和修女十一人,比利时二人,“俄国之行路人被杀男女三名”[《湘乡曾氏文献》第7册,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一名)。
除此之外,还有多名中国教民以及教会的中国仆役被打死(然而这些人的死亡并没有被充分重视)。当然,还有大量财物遭到抢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巧合的是,就在教堂被焚毁后的第三天,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开始,直隶全省下起了一场大雨。曾国藩在当天日记中记载说:“自去年四月亢旱至今,十三个月未得大雨。本日未刻起……”一开始还是小雨,到了晚上雨势转大,“灯后大雨”。
保定距天津是三四天的路程,曾国藩此时还不知道天津教案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雨不止,为之快慰。”[《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他哪里知道,在数百里之外的一场大祸,马上就要把他拖到人生最大的一场挫折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