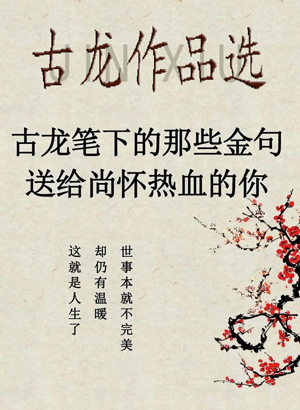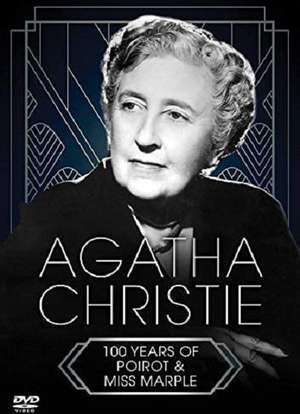曾国藩投入巨大精力,调查挖眼剜心一事,结果却受到舆论如此猛烈攻击。
在抓捕“凶犯”方面,曾国藩进展也不顺利,多次受到朝廷批评。
天津教案发生后,另一个重点是缉凶严惩。这是清政府承认必须做的。
天津教案中共有20名外国人被杀,其中法国人13名,俄国人3名,比利时人2名,意大利和爱尔兰人各1名。如果说丰大业首先开枪,罪有应得的话,其他人毕竟都是无辜的。案发后,外国政府强烈要求缉拿真凶,清政府也下谕旨明确指示:“外国之人无故被害若干,皆须切实查明;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尤为目前要务。”[《燕京开教略》下篇,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7页。]曾国藩也认为“拿凶为最要关键”。所以他一边调查事实真相,一边开始搜捕凶手。中国司法习惯是以命抵命,因此曾国藩认为“查出二十一人,一命抵一命,便可交卷”。[《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24页。]
然而天津教案爆发之时,场面异常混乱,参与者达上万人之多,事后想确认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到底是谁所致,绝非易事。而且行凶者都被民间目为英雄,无人出面检举,所以“缉凶之说,万难着笔”[《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27页。]。尽管曾国藩想尽办法,还是只抓获了十余人,而且在严刑之下,均坚不吐供。
就在曾国藩承受着各方面巨大压力的时候,法国外交官又提出了非常不合理的要求。曾国藩一到天津,就宣布撤去三位地方官的职务。这得到了法国人的认可。所以在十九日法国公使罗淑亚到达天津开始交涉的时候,“词气尚属和平”。
然而,过了两天,罗淑亚突然态度大变,宣称一定要杀掉天津知府、知县和陈国瑞这三名官员,否则就要发动战争。“罗酋十九日抵津相见,词气尚属和平。二十一二忽改初态,照会敝处欲将府县及陈国瑞抵偿人命,不然即欲动兵。”[《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05页。]并且明确要求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先行在津立即正法”。外国人一直认为,中国官员在贯彻条约、保护在华外国人方面表现不力,因此想通过这个案子杀一儆百。
但是,中方无论如何不能答应这一点。对大臣生杀予夺这一极为重要的权力,不可能由外国人操纵。更何况无论怎么说,三名地方官罪不至死。曾国藩坚持不肯答应法国的要求。
法国人于是加大战争威胁。七月二十六日,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天津。外国军舰也一艘艘驶来。“外国军队的庞大舰队眼下已在天津附近。六艘炮艇—法国和英国各三艘—已经停泊在天津河道;一艘法国小型护卫舰在白河口的沙洲外面,英国和法国海军中队的旗舰,以及其他一些舰艇,则在烟台靠泊。此外,北德意志的两艘小型护卫舰和俄国北太平洋舰队的部分舰只,将于近日抵达烟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选译》,《清末教案》第5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
重压之下,曾国藩旧病复发。二十六日下午崇厚来到曾国藩行馆,传达罗淑亚的最后通牒,声称到次日(二十七日)四时,清方如无切实回答,法国公使及所有在京法国人将一并撤往上海。曾国藩听后大受刺激,“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510页。],“历三时之久,卧床不起,据医家云脉象沉重”。[《清末教案》第1册,转引自解成编著:《基督教在华传播系年(河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6页。]
二十八日,曾国藩自度病体不支,又一次想到了他的学生李鸿章。他希望朝廷命李鸿章带兵来天津,一方面可以武力震慑法方,表明中方的备战决心,另一方面,有着丰富外交经验的李鸿章还可以做曾国藩的助手,直接帮助他处理此事,了此一段残局。因此与崇厚密商后,曾国藩向朝廷建议:“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510页。]在同一天致李鸿章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发出“四顾茫茫,自阁下外,未知巨艰更将谁属”[《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25页。]的感慨。崇厚也专上一折,说“曾国藩触发旧疾,病势甚重”[《曾国藩全集·奏稿》11,岳麓书社,2011年,第514页。],请再派重臣前来帮办。
就在李鸿章还没有前来的时候,七月二十六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两江总督位置出缺。八月初四日,对曾国藩已经非常不满的慈禧太后下旨,令曾国藩调补两江总督,而以李鸿章补授直隶总督。
接到东下天津的命令,李鸿章十分兴奋。
如前所述,“剿”捻结束后,朝廷一度采取“扬曾搁李”政策,居“头功”的李鸿章只获得协办大学士的虚衔。不仅如此,朝廷还命李鸿章入陕协助“剿回”,与极难相处的左宗棠打交道,李鸿章十分不愿意,消极应付,百般拖延。不料此时接到东调的命令,诚可谓天遂人愿。李鸿章在致丁日昌信中十分高兴地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销差,泯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对于天津教案,他在局外观察已经很久了。早在曾国藩动身赴天津之前,就曾写信给他,请这位“熟悉夷情”的老部下出主意。李鸿章作为门生旧故,当然义不容辞,因此他迅速回复,判断法国方面必定要求以中国官员抵命,而中国政府对此点肯定不能同意。如果发生战争,必然因此而起。所以他劝告老师,还是要做一定的军事准备:“固不必张皇六师,致人疑衅,但防备不可不严,可否酌带劲旅护卫。”[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3页。]应该说,李鸿章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军事出现紧张,他有可能被老师调到天津附近。
因此接到命令后,他就开始向河北方向进发。一边进发,他一边通过书信给老师提各种建议,准备充当老师的得力助手。
结果,还没等李鸿章到达河北,就接到了直隶总督的任命,他一下子接替老师,成了天下疆臣领袖。
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说:“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5页。]
李鸿章很快就于十二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望,徘徊不前。因为他不想一下子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词堂皇地宣称:直豫晋交界处间有游勇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
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初政即犯众恶”[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0·信函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92页。]。因此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
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卸在即,务当遵奉昨日谕旨,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构获。”[《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37页。]要求他先把缉凶的事办好,才能离开。曾国藩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津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津接篆以后,臣仍当暂留津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圣厘。”[《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42页。]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八月十九日,已经拿获疑犯八十多人。但是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窒碍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所谓“变通办理”就是凡群殴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本人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二十人,军徒者二十五人。
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谳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可想而知。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事后,曾国藩偷偷发给每名人犯家里“恤家银”五百两,以为安慰。《李兴锐日记》说:“人给恤家银五百两。杀之而又怜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为此曲突徙薪,就案办案耳。”
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七月六日(公历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他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称:“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忧方急,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轻解此灾厄。”[《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33页。这封家书的日期有误,应该是写于初十日和十一日。见张晓川:《从中西电报通讯看天津教案与普法战争—兼谈曾国藩一封家书的日期问题》,载于《近代史研究》2011年01期。]果然,不久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易办理。”[《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17页。]因此两名地方官由部议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
曾国藩此前曾嘱幕僚汇银三千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及至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87页。],曾国藩又筹集白银一万余两,作为“到戍后收赎及一切路费”[《曾国藩全集·书信》10,岳麓书社,2011年,第391页。],以弥补自己的遗憾。
曾国藩经手的津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八月二十二日从保定出发,二十五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九月六日,双方交接关防印信。
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
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儿。”[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第122页。]
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
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二十人死刑。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死俄国人而被判正法的四名“凶犯”,获改判轻刑。这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
至于其他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争议。奕䜣称:“除拿获正凶议抵外,中国自应设法体恤。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曾国藩全集·奏稿》12,岳麓书社,2011年,第66页。]
最后,议定赔偿费及抚恤费共五十余万两了结。此外达成的一致是要重建教堂,派遣崇厚赴法道歉。
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奉旨在津将另外十六名“凶犯”斩首。十一月十四日,又将二十五名从犯分判军杖、徒各刑。天津教案至此结束。
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终于结束了津案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陛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
查翁同龢日记,十月初六日(公历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乡,颇诮其津事。”[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二卷,中西书局,2012年,第836页。查曾国藩当日日记,只有“坐见之客”几次之记载,并未提及翁同龢之名。]而当时敢于当面诮讽曾国藩的,当不止翁氏一人。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曾国藩的部下李兴锐在曾国藩的推荐下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夷务者,什九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夷务,清议莫不归咎曾中堂。甚矣!任天下之重,岂不难哉!”“众论咎侯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谅局中苦心,可叹之至。”[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湘军7·日记·地方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3~324页。]在这样的氛围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
陛见之后黯然南返的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一件难堪的事。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
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然者。[《曾国藩全集·家书》2,岳麓书社,2011年,第564页。]
陈由立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由立四千两薪水不给。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让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路宿平原腰站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三天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者,为之局促不安,如负重疚,年老位高,岂堪常有咎悔之事?”《曾国藩全集·日记》4,岳麓书社,2011年,第366~368页。
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心尝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负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
光绪四年(1878),朝廷简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
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
曾纪泽的这番议论,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曾纪泽免冠叩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曾纪泽:《使西日记(外一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页。]
天津教案之后三十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父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看到三个大瓮,一贮人血,一贮人心,一贮人眼。拳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腊。遇粤之荔枝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詈西人,暴其惨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御前会议上,有大臣们说,义和团不能避枪炮,“臣曾微服往东交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伏尸遍地,并不能避枪炮,究不足恃”。慈禧却加以反驳。“太后云,此系土匪,绝非团民;若系团民,绝不至中枪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164页。]
慈禧太后和奕譞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二十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这种战争却成为现实。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在1900年夏天的战争中死亡。这是天津教案的扩大版。在运动中,户部主事万秉鉴称,基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卖国表现,应该取消他的恤典:“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恤,而夺国藩恤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上,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李鸿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