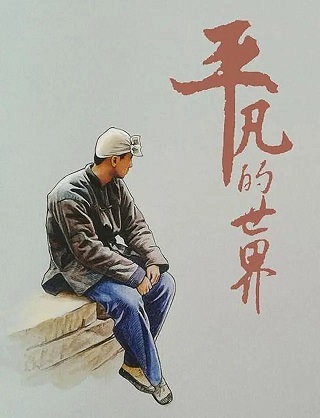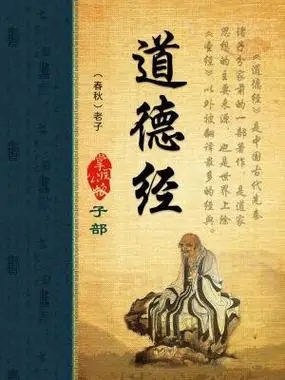人是非团结不能生存的。当用何法团结呢?过去的事情,已非我们所能尽知;将来的事情,又非我们所能预料。我们现在只能就我们所知道的,略加说述而已。
在有史时期,血缘是人类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恒狃于其所见闻,遂以此为人类团结唯一的因素,在过去都是如此,在将来也非如此不可了。其实人类的团结,并非是专恃血缘的。极远之事且勿论,即上章所说的以年龄分阶层之世,亦大率是分为老、壮、幼三辈(间有分为四辈的,但以分做三辈为最普通。《礼记·礼运》说:“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论语·雍也篇》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亦都是分为三辈),而不再问其人与人间的关系的。当此之时,哪有所谓夫妇、父子、兄弟之伦呢?《礼记·礼运》说: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左传》载富辰的话,也说“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僖公二十四年)。可见亲族关系,是后起的情形了。
人类愈进步,则其分化愈甚,而其组织的方法亦愈多。于是有所谓血族团体。血族团体,其初必以女子为中心。因为夫妇之伦未立,父不可知;即使可知,而父子的关系,亦不如母子之密之故。如上章所述,人类实在是社群动物,而非家庭动物,所以其聚居,并不限于两代。母及同母之人以外,又有母的母,母的同母等。自己而下推,亦是如此。逐渐成为母系氏族。每一个母系氏族,都有一个名称,是即所谓姓。一姓总有一个始祖母的,如殷之简狄,周之姜嫄即是。简狄之子契,姜嫄之子稷,都是无父而生的。因为在传说中,此等始祖母,本来无夫之故。记载上又说她俩都是帝喾之妃,一定是后来附会的(契、稷皆无父而生,见《诗·玄鸟》、《生民》。《史记·殷周本纪》所载,即是《诗》说。据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所考证,太史公是用鲁诗说的。姜嫄、简狄,皆帝喾之妃,见《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亦用其说)。
女系氏族的权力,亦有时在男子手中(参看下章),此即所谓舅权制。此等权力,大抵兄弟相传,而不父子相继。因为兄弟是同氏族人,父子则异氏族之故。我国商朝和春秋时的鲁国、吴国,都有兄弟相及的遗迹(鲁自庄公以前,都一代传子,一代传弟,见《史记·鲁世家》),这是由于东南一带,母系氏族消灭较晚之故,已见上章。
由于生业的转变,财产和权力,都转入男子手中,婚姻非复男子入居女子的氏族,而为女子入居男子的氏族(见上章)。于是组织亦以男为主,而母系氏族,遂变为父系氏族。商周自契稷以后,即奉契、稷为始祖,便是这种转变的一件史实。
族之组织,是根据于血缘的。血缘之制既兴,人类自将据亲等的远近,以别亲疏。一姓的人口渐繁,又行外婚之制,则同姓的人,血缘不必亲,异姓的人,血缘或转相接近。所谓族与姓,遂不得不分化为两种组织。族制,我们所知道的,是周代的九族:一、父姓五服以内。二、姑母和他的儿子。三、姊妹和他的儿子。四、女儿和他的儿子。是为父族四;五、母的父姓,即现在所谓外家。六、母的母姓,即母亲的外家。七、母的姊妹和她们的儿子。是为母族三;八、妻之父姓。九、妻之母姓。是为妻族二。这是汉代今文家之说,见于《五经异义》(《诗·葛藟疏》引),《白虎通·宗族篇》同。古文家说,以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为九族,此乃秦汉时制,其事较晚,不如今文家所说之古了。然《白虎通义》又载或说,谓尧时父母妻之族各三,周贬妻族以附父族,则今文家所说,亦已非极古之制。《白虎通义》此段,文有脱误,尧时之九族,无从知其详。然观下文引《诗》“邢侯之姨”,则其中该有妻之姊妹。总而言之:族制是随时改变的,然总是血缘上相近的人,和后世称父之同姓为族人,混同姓与同族为一不同,则是周以前所同的。九族中人,都是有服的。其无服的,则谓之党(《礼记·奔丧》郑《注》),是为父党,母党,妻党。
同姓的人,因人口众多,血缘渐见疏远,其团结,是否因此就松懈了呢?不。所谓九族者,除父姓外,血缘上虽然亲近,却不是同居的。同姓则虽疏远而仍同居,所以生活共同,利害亦共同。在同居之时,固有其紧密的组织;即到人口多了,不能不分居,而彼此之间,仍有一定的联结,此即所谓宗法。宗法和古代的社会组织,有极大的关系。今略述其制如下:
(一)凡同宗的人,都同奉一个始祖(均系此始祖之后)。
(二)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自此以后,嫡长子代代承袭,为大宗宗子。凡始祖的后人,都要尊奉他,受他的治理。穷困的却亦可以受他的救济。大宗宗子和族人的关系,是不论亲疏远近,永远如此的,是谓大宗“百世不迁”。
(三)始祖之众子(嫡长子以外之子),皆别为小宗宗子。其嫡长子为继祢小宗。继祢小宗的嫡长子为继祖小宗。继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曾祖小宗。继曾祖小宗的嫡长子为继高祖小宗。继祢小宗,亲兄弟宗事他(受他治理,亦受他救济)。继祖小宗,从兄弟宗事他。继曾祖小宗,再从兄弟宗事他。继高祖小宗,三从兄弟宗事他。至四从兄弟,则与继六世祖之小宗宗子,亲尽无服,不再宗事他。是为小宗“五世则迁”(以一人之身论,当宗事与我同高、曾、祖、考四代的小宗宗子及大宗宗子。故曰:“小宗四,与大宗凡五。”)
(四)如此,则或有无宗可归的人。但大宗宗子,还是要管理他,救济他的。而同出于一始祖之人,设或殇与无后,大宗的宗子,亦都得祭祀他。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则活人的治理、救济,死人的祭祀问题,都解决了。所以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大宗宗子无后,族人都当绝后以后大宗。
以上是周代宗法的大略,见于《礼记·大传》的。《大传》所说大宗的始祖,是国君的众子。因为古者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诸侯(《礼记·郊特牲》谓不敢立其庙而祭之。其实大宗的始祖,非大宗宗子,亦不敢祭。所以诸侯和天子,大夫和诸侯,大宗宗子和小宗宗子,小宗宗子和非宗子,其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国君的众子,要别立一宗。郑《注》又推而广之,及于始适异国的大夫。据此,宗法之立,实缘同出一祖的人太多了,一个承袭始祖的地位的人,管理有所不及,乃不得不随其支派,立此节级的组织,以便管理。迁居异地的人,旧时的族长,事实上无从管理他。此等组织,自然更为必要了。观此,即知宗法与封建,大有关系。因为封建是要将本族的人,分一部分出去的。有宗法的组织,则封之者和所封者之间,就可保持着一种联结了。然则宗法确能把同姓中亲尽情疏的人,联结在一起。他在九族之中,虽只联结得父姓一族。然在父姓之中,所联结者,却远较九族之制为广。怕合九族的总数,还不足以敌他。而且都是同居的人,又有严密的组织。母系氏族中,不知是否有与此相类的制度。即使有之,其功用,怕亦不如父系氏族的显著。因为氏族从母系转变到父系,本是和斗争有关系的。父系氏族而有此广大严密的组织,自然更能发挥其斗争的力量。我们所知,宗法之制,以周代为最完备,周这个氏族,在斗争上,是得到胜利的。宗法的组织,或者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有族制以团结血缘相近的人,又有宗法以团结同出一祖的人,人类因血族而来的团结,可谓臻于极盛了。然而当其极盛之时,即其将衰之候。这是什么原因呢?社会组织的变化,经济实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进化尚浅之时,人类的互助,几于有合作而无分工。其后虽有分工,亦不甚繁复。大家所做的事,既然大致相同,又何必把过多的人联结在一起?所以人类联结的广大,是随着分工的精密而进展的。分工既密之后,自能将毫不相干的人,联结在一起。此等互相倚赖的人,虽然彼此未必相知,然总必直接间接,互相接触。接触既繁,前此因不相了解而互相猜忌的感情,就因之消除了。所以商业的兴起,实能消除异部族间敌对的感情。分工使个性显著。有特殊才能的人,容易发挥其所长,获得致富的机会。氏族中有私财的人逐渐多,卖买婚即于此时成立。说见上章。于是父权家庭成立了。孟子说:当时农夫之家,是五口和八口。说者以为一夫上父母下妻子;农民有弟,则为余夫,要另行授田(《梁惠王》及《滕文公上篇》),可见其家庭,已和现在普通的家庭一样了。士大夫之家,《仪礼·丧服传》说大功同财,似乎比农民的家庭要大些。然又说当时兄弟之间的情形道:“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则业已各住一所屋子,各有各的财产,不过几房之中,还保有一笔公款而已。其联结,实在是很薄弱的,和农夫的家庭,也相去无几了。在当时,只有有广大封土的人,其家庭要大些。这因为(一)他的原始,是以一氏族征服异氏族,而食其租税以自养的,所以宜于聚族而居,常作战斗的戒备。只要看《礼记》的《文王世子》,就知道古代所谓公族者,是怎样一个组织了。后来时异势殊,这种组织,实已无存在的必要。然既已习为故常,就难于猝然改革。这是一切制度,都有这惰性的。(二)其收入既多,生活日趋淫侈,家庭中管事服役的奴仆,以及技术人员,非常众多,其家庭遂特别大。这只要看《周官》的《天官》,就可以知道其情形。然此等家庭,随着封建的消灭,而亦渐趋消灭了。虽不乏新兴阶级的富豪,其自奉养,亦与素封之家无异,但毕竟是少数。于是氏族崩溃,家庭代之而兴。家庭的组织,是经济上的一个单位,所以是尽相生相养之道的。相生相养之道,是老者需人奉养,幼者需人抚育。这些事,自氏族崩溃后,既已无人负责,而专为中间一辈所谓一夫一妇者的责任。自然家庭的组织,不能不以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为范围了。几千年以来,社会的生活情形,未曾大变,所以此种组织,迄亦未曾改变。
看以上所述,可见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因为经济是最广泛,和社会上个个人,都有关系;而且其关系,是永远持续,无时间断的。自然对于人的影响,异常深刻,各种上层组织,都不得不随其变迁而变迁;而精神现象,亦受其左右而不自知了。在氏族时代,分工未密,一个氏族,在经济上,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团体。生活既互相倚赖,感情自然容易密切。不但对于同时的人如此,即对于以往的人亦然。因为我所赖以生存的团体,是由前人留遗下来的。一切知识技术等,亦自前辈递传给后辈。这时候的人,其生活,实与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人关系深,而与空间上并时存在的人关系浅。尊祖、崇古等观念,自会油然而生。此等观念,实在是生活情形所造成的。后人不知此理,以为这是伦理道德上的当然,而要据之以制定人的生活,那就和社会进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了。大家族、小家庭等字样,现在的人用来,意义颇为混淆。西洋人学术上的用语,称一夫一妇,包括未婚子女的为小家庭;超过于此的为大家庭。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赵翼《陔余丛考》,尝统计此等极大的家庭(第四种),见于正史孝义、孝友传的:《南史》三人,《北史》十二人,《唐书》三十八人,《五代史》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自然有(一)不在孝义、孝友传,而散见于他篇的;(二)又有正史不载,而见于他书的;(三)或竟未见记载的。然以中国之大,历史上时间之长,此等极大的家庭,总之是极少数,则理有可信。此等虽或由于伦理道德的提倡(顾炎武《华阴王氏宗祠记》:“程朱诸子,卓然有见于遗经。金元之代,有志者多求其说于南方,以授学者。及乎有明之初,风俗淳厚,而爱亲敬长之道,达诸天下。其能以宗法训其家人,或累世同居,称为义门者,往往而有。”可见同居之盛,由于理学家的提倡者不少),恐仍以别有原因者居多(《日知录》:“杜氏《通典》言:北齐之代,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将近万室。《北史·薛胤传》:为河北太守,有韩马两姓,各二千余家。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复绝。”陈宏谋《与杨朴园书》“今直省惟闽中、江西、湖南,皆聚族而居,族各有祠。”则聚居之风,古代北盛于南,近世南盛于北,似由北齐之世,丧乱频仍,民皆合族以自卫;而南方山岭崎岖之地进化较迟,土著者既与合族而居之时,相去未远;流移者亦须合族而居,互相保卫之故)。似可认为古代氏族的遗迹,或后世家族的变态。然氏族所以崩溃,正由家族潜滋暗长于其中。此等所谓义门,纵或有古代之遗,亦必衰颓已甚。况又有因环境的特别,而把分立的家庭,硬行联结起来的。形式是而精神非,其不能持久,自然无待于言了。《后汉书·樊宏传》,说他先代三世共财,有田三百余顷。自己的田地里,就有陂渠,可以互相灌注。又有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这是因其生产的种类较多之故)。课役童隶,各得其宜。”(分工之法)要造器物,则先种梓漆。简直是一个大规模的生产自给自足的团体。历代类乎氏族的大家族,多有此意。此岂不问环境所可强为?然社会的广大,到底非此等大家族所能与之相敌,所以愈到后世,愈到开化的地方,其数愈少。这是类乎氏族的大家族,所以崩溃的真原因,毕竟还在经济上。但在政治上,亦自有其原因。因为所谓氏族,不但尽相生相养之责,亦有治理其族众之权。在国家兴起以后,此项权力,实与国权相冲突。所以国家在伦理上,对于此等大家族,虽或加以褒扬,而在政治上,又不得不加以摧折。所谓强宗巨家,遂多因国家的干涉,而益趋于崩溃了。略大于小家庭的家庭(第二、第三种)表面上似为伦理道德的见解所维持(历代屡有禁民父母在别籍异财等诏令,可参看《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实则亦为经济状况所限制。因为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儒者以此等家庭之多,夸奖某地方风俗之厚,或且自诩其教化之功,就大谬不然了。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制度果然自己站得住,何须如此扶持呢?所以到近代,除极迂腐的人外,亦都不主张维持大家庭。如李绂有《别籍异财议》,即其一证。至西洋文化输入,论者更其提倡小家庭,而排斥大家庭了。然小家庭又是值得提倡的么?
不论何等组织,总得和实际的生活相应,才能持久。小家庭制度,是否和现代人的生活相应呢?历来有句俗话,叫做“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可见所谓家庭,实以扶养老者、抚育儿童,为其天职。然在今日,此等责任,不但苦于知识之不足(如看护病人,抚养教育儿童,均须专门知识),实亦为其力量所不及(兼日力财力言之。如一主妇不易看顾多数儿童,兼操家政。又如医药、教育的费用,不易负担)。在古代,劳力重于资本,丁多即可致富,而在今日,则适成为穷困的原因。因为生产的机键,自家庭而移于社会了,多丁不能增加生产,反要增加消费(如纺织事业)。儿童的教育,年限加长了,不但不能如从前,稍长大即为家庭挣钱,反须支出教育费。而一切家务,合之则省力,分之则多费的(如烹调、浣濯)。又因家庭范围太小,而浪费物质及劳力。男子终岁劳动,所入尚不足以赡其家。女子忙得和奴隶一般,家事还不能措置得妥帖。于是独身、晚婚等现象,相继发生。这些都是舶来品,和中国旧俗,大相径庭,然不久,其思想即已普遍于中流社会了。凡事切于生活的,总是容易风行的,从今以后,穷乡僻壤的儿女,也未必死心塌地,甘做家庭的奴隶了。固然,个人是很难打破旧制度,自定办法的。而性欲出于天然,自能把许多可怜的儿女,牵入此陈旧组织之中。然亦不过使老者不得其养,幼者不遂其长,而仍以生子不举等人为淘汰之法为救济罢了。这种现象,固已持续数千年,然在今日,业经觉悟之后,又何能坐视其如此呢?况且家庭的成立,本是以妇女的奴役为其原因的。在今日个人主义抬头,人格要受尊重的时代,妇女又何能长此被压制呢?资本主义的学者,每说动物有雌雄两性,共同鞠育其幼儿,而其同居期限,亦因以延长的,以为家庭的组织,实根于人类的天性,而无可改变。姑无论其所说动物界的情形,并不确实。即使退一步,承认其确实,而人是人,动物是动物;人虽然亦是动物之一,到底是动物中的人;人类的现象,安能以动物界的现象为限?他姑弗论,动物雌雄协力求食,即足以哺育其幼儿,人,为什么有夫妇协力,尚不能养活其子女的呢?或种动物,爱情限于家庭,而人类的爱情,超出于此以外,这正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论者不知人之爱家,乃因社会先有家庭的组织,使人之爱,以此形式而出现,正犹水之因方而为圭,遇圆而成璧;而反以为人类先有爱家之心,然后造成家庭制度;若将家庭破坏,便要“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礼记·乐记》:“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真是倒果为因。殊不知家庭之制,把人分为五口八口的小团体,明明是互相倚赖的,偏使之此疆彼界,处于半敌对的地位,这正是疾病之所以不养,老幼孤独之所以不得其所。无后是中国人所引为大戚的,论者每说,这是拘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义(《孟子·离娄上篇》)。而其以无后为不孝,则是迷信“鬼犹求食”(见《左传》宣公四年),深虑祭祀之绝。殊不知此乃古人的迷信,今人谁还迷信鬼犹求食来?其所以深虑无后,不过不愿其家之绝;所以不愿其家之绝,则由于人总有尽力经营的一件事,不忍坐视其灭亡,而家是中国人所尽力经营的,所以如此。家族之制,固然使人各分畛域,造成互相敌对的情形,然此自制度之咎,以爱家者之心论:则不但(一)夫妇、父子、兄弟之间,互尽扶养之责。(二)且推及于凡与家族有关系的人(如宗族姻亲等)。(三)并且悬念已死的祖宗。(四)以及未来不知谁何的子孙。前人传给我的基业,我必不肯毁坏,必要保持之,光大之,以传给后人,这正是极端利他心的表现。利他心是无一定形式的,在何种制度之下,即表现为何种形式。然而我们为什么要拘制着他,一定只许他在这种制度中表现呢?
以上论族制的变迁,大略已具。现再略论继承之法。一个团体,总有一个领袖。在血缘团体之内,所谓父或母,自然很容易处于领袖地位的。父母死后,亦当然有一个继承其地位的人。女系氏族,在中国历史上,可考的有两种继承之法:(一)是以女子承袭财产,掌管祭祀。前章所述齐国的巫儿,即其遗迹。这大约是平时的族长。(二)至于战时及带有政治性质的领袖,则大约由男子尸其责,而由弟兄相及。殷代继承之法,是其遗迹。男系氏族,则由父子相继。其法又有多端:(一)如《左传》文公元年所说:“楚国之举,恒在少者。”这大约因幼子恒与父母同居,所以承袭其遗产(蒙古人之遗产,即归幼子承袭。其幼子称斡赤斤,译言守灶)。(二)至于承袭其父之威权地位,则自以长子为宜,而事实上亦以长子为易。(三)又古代妻妾,在社会上之地位亦大异。妻多出于贵族,妾则出于贱族,或竟是无母家的。古重婚姻,强大的外家及妻家,对于个人,是强有力的外援(如郑庄公的大子忽,不婚于齐,后来以无外援失位);对于部族,亦是一个强有力的与国,所以立子又以嫡为宜。周人即系如此。以嫡为第一条件,长为第二条件。后来周代的文化,普行于全国,此项继承之法,遂为法律和习惯所共认了。然这只是承袭家长的地位,至于财产,则总是众子均分的(《清律》:分析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但以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量与半分。无子立继者,与私生子均分)。所以中国的财产,不因遗产承袭,而生不均的问题。这是众子袭产,优于一子袭产之点。
无后是人所不能免的,于是发生立后的问题。宗法盛行之世,有一大宗宗子,即生者的扶养,死者的祭祀,都可以不成问题,所以立后问题,容易解决。宗法既废,势非人人有后不可,就难了。在此情形之下,解决之法有三:(一)以女为后。(二)任立一人为后,不问其为同异姓。(三)在同姓中择立一人为后。(一)于情理最近,但宗祧继承,非徒承袭财产,亦兼掌管祭祀。以女为后,是和习惯相反的(春秋时,郑国以外孙为后,其外孙是莒国的儿子,《春秋》遂书“莒人灭郑”,见《公羊》襄公五、六年。按此实在是论国君承袭的,乃公法上的关系,然后世把经义普遍推行之于各方面,亦不管其为公法私法了)。既和习惯相反,则觊觎财产的人,势必群起而攻,官厅格于习俗,势必不能切实保护。本欲保其家的,或反因此而发生纠纷,所以势不能行。(二)即所谓养子,与家族主义的重视血统,而欲保其纯洁的趋势不合。于是只剩得第(三)的一途。法律欲维持传统观念,禁立异姓为后,在同姓中并禁乱昭穆之序(谓必辈行相当,如不得以弟为子等。其实此为古人所不禁,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见《公羊》成公十五年)。于是欲人人有后益难,清高宗时,乃立兼祧之法,以济其穷(一人可承数房之祀。生子多者,仍依次序,分承各房之后。依律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皆以大宗为重,为大宗父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此所谓大宗,指长房,所谓小宗,指次房以下,与古所谓大宗小宗者异义。世俗有为本生父母及所兼祧之父母均服三年的,与律例不合)。宗祧继承之法,进化至此,可谓无遗憾了。然其间却有一难题。私有财产之世,法律理应保护个人的产权。他要给谁就给谁,要不给谁就不给谁。为后之子,既兼有承袭财产之权利,而法律上替他规定了种种条件,就不啻干涉其财产的传授了。于是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私有财产制度,发生了冲突。到底传统的伦理观念是个陈旧不切实际的东西,表面上虽然像煞有介事,很有威权,实际上已和现代人的观念不合了。私有财产制度,乃现社会的秩序的根柢,谁能加以摇动?于是冲突之下,伦理观念,乃不得不败北而让步。法律上乃不得不承认所谓立爱,而且多方保护其产权(《清律例》:继子不得于所后之亲,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及所亲爱者,不许宗族以次序告争,并官司受理)。至于养子,法律虽禁其为嗣(实际上仍有之),亦不得不听其存在,且不得不听其酌给财产(亦见《清律例》)。因为国家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兼顾全国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不能专代表家族的排外自私之念。在现制度之下,既不能无流离失所之人;家族主义者流,既勇于争袭遗产,而怯于收养同宗;有异姓的人肯收养他,国家其势说不出要禁止。不但说不出要禁止,在代表人道主义和维持治安的立场上说,无宁还是国家所希望的。既承认养子的存在,在事实上,自不得不听其酌给遗产了。这也是偏私的家族观念,对于公平的人道主义的让步,也可说是伦理观念的进步。
假使宗祧继承的意思,而真是专于宗祧继承,则拥护同姓之男,排斥亲生之女,倒也还使人心服。因为立嗣之意,无非欲保其家,而家族的存在,是带着几分斗争性质的。在现制度之下,使男子从事于斗争,确较女子为适宜(这并非从个人的身心能力上言,乃是从社会关系上言),这也是事实。无如世俗争继的,口在宗祧,心存财产,都是前人所谓“其言蔼如,其心不可问”的。如此而霸占无子者的财产,排斥其亲生女,就未免使人不服了。所以有国民政府以来,废止宗祧继承,男女均分遗产的立法。这件事于理固当,而在短时间内,能否推行尽利,却是问题。旧律,遗产本是无男归女,无女人官的(近人笔记云:“宋初新定《刑统》,户绝资产下引《丧葬令》;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此《丧葬令》乃《唐令》,知唐时所谓户绝,不必无近亲。虽有近亲,为营丧葬,不必立近亲为嗣子,而远亲不能争嗣,更无论矣。虽有近亲,为之处分,所余财产,仍传之亲女,而远亲不能争产,更无论矣。此盖先世相传之法,不始于唐。”按部曲、客女,见第四十章)。入官非人情所愿,强力推行,必多流弊,或至窒碍难行(如隐匿遗产,或近亲不易查明,以致事悬不决,其间更生他弊等)。归之亲女,最协人情。然从前的立嗣,除祭祀外,尚有一年老奉养的问题。而家族主义,是自私的。男系家族,尤其以男子为本位,而蔑视女子的人格。女子出嫁之后,更欲奉养其父母,势实有所为难。所以旧时论立嗣问题的人,都说最好是听其择立一人为嗣,主其奉养、丧葬、祭祀,而承袭其遗产。这不啻以本人的遗产,换得一个垂老的扶养,和死后的丧葬祭祀。今欲破除迷信,祭祀固无问题,对于奉养及丧葬,似亦不可无善法解决。不有遗产以为交易,在私有制度之下,谁肯顾及他人的生养死葬呢?所以有子者遗产男女均分,倒无问题,无子者财产全归于女,倒是有问题的。所以变法贵全变,革命要彻底。枝枝节节而为之,总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症疗法。
姓氏的变迁,今亦须更一陈论。姓的起源,是氏族的称号,由女系易而为男系,说已见前。后来姓之外又有所谓氏。什么叫做氏呢?氏是所以表一姓之中的支派的。如后稷之后都姓姬,周公封于周,则以周为氏;其子伯禽封于鲁,则以鲁为氏(国君即以国为氏);鲁桓公的三子,又分为孟孙、叔孙、季孙三氏是。始祖之姓,谓之正姓,氏亦谓之庶姓。正姓是永远不改的,庶姓则随时可改。因为同出于一祖的人太多了,其支分派别,亦不可无专名以表之,而专名沿袭太久,则共此一名的人太多,所以又不得不改(改氏的原因甚多,此只举其要改的根本原理。此外如因避难故而改氏以示别族等,亦是改氏的一种原因)。《后汉书·羌传》说:羌人种姓中,出了一个豪健的人,便要改用他的名字做种姓。如爰剑之后,五世至研,豪健,其子孙改称研种;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又改称烧当种是。这正和我国古代的改氏,原理相同。假如我们在鲁国,遇见一个人,问他尊姓,他说姓姬。这固然足以表示他和鲁君是一家。然而鲁君一家的人太多了,鲁君未必能个个照顾到,这个人,就未必一定有势力,我们听了,也未必肃然起敬。假若问他贵氏,他说是季孙,我们就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正卿的一家。正卿的同族,较之国君的同姓,人数要少些,其和正卿的关系,必较密切,我们闻言之下,就觉得炙手可热,不敢轻慢于他了。这是举其一端,其余可以类推(如以技为官,以官为氏,问其氏,即既可知其官,又可知其技)。所以古人的氏,确是有用的。至于正姓,虽不若庶姓的亲切,然婚姻之可通与否,全论正姓的异同。所以也是有用的。顾炎武《原姓篇》说春秋以前,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在室冠之以序,如叔隗、季隗之类。出嫁,更冠以其夫之氏族,如宋伯姬、赵姬、卢蒲姜之类。在其所适之族,不必举出自己的氏族来,则亦以其父之氏族冠之,如骊姬、梁嬴之类。又有冠之以谥的,如成风、敬姜之类),这不是男子不论姓,不过举氏则姓可知罢了。女子和社会上无甚关系,所以但称姓而不称其氏,这又可以见得氏的作用。
贵族的世系,在古代是有史官为之记载的。此即《周官》小史之职。记载天子世系的,谓之帝系;记载诸侯卿大夫世系的,谓之世本。这不过是后来的异名,其初原是一物。又瞽矇之职,“讽诵诗,世奠系”(疑当作奠世系)。《注》引杜子春说:谓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世系而可诵,似乎除统绪之外,还有其性行事迹等。颇疑《大戴礼记》的《帝系姓》,原出于小史所记;《五帝德》则是原出于瞽矇所诵的(自然不是完全的),这是说贵族。至于平民,既无人代他记载,而他自己又不能记载,遂有昧于其所自出的。《礼记·曲礼》谓买妾不知其姓,即由于此。然而后世的士大夫,亦多不知其姓氏之所由来的。这因为谱牒掌于史官,封建政体的崩溃,国破家亡,谱牒散失,自然不能知其姓氏之所由来了。婚姻的可通与否,既不复论古代的姓,新造姓氏之事亦甚少。即有之,亦历久不改。阅一时焉,即不复能表示其切近的关系,而为大多数人之所共,与古之正姓同。姓遂成为无用的长物,不过以其为人人之所有,囿于习惯,不能废除罢了。然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姓氏之所由来,虽不可知,而其在实际上的势力自在。各地方的人,也还尊奉他。在秦汉之世,习为固然,不受众人的注意。汉末大乱,各地方的强宗巨家,开始播迁,到了一个新地方,还要表明其本系某地方的某姓;而此时的选举制度,又重视门阀。于是又看重家世,而有魏晋以来的谱学了。见第四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