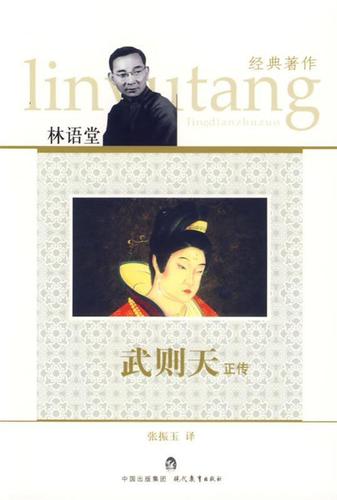八
自从列文看见他亲爱的垂死的哥哥那一瞬间,他第一次用他称为新的信念来看生死问题,这种信念在他二十岁到三十四岁之间不知不觉地代替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信仰,——从那时起,死使他惊心动魄的程度还不如生那么厉害,他丝毫也不知道生从哪里来的,它为了什么目的,它如何来的,以及它究竟是什么。有机体及其灭亡、物质不灭、能量不灭的定律、进化——是代替了他往日信念的术语。这些术语和与此有关的概念对于思考问题倒很不错;但是对于生命却毫无作用,列文突然感觉得自己像一个脱下暖和的皮大衣换上薄纱衣服的人一样,他一走进严寒里,毫无疑问立刻就确信了,不是凭着推论,而是凭着他的亲身感受,他简直就像赤身裸体一样,而且他不可避免地一定会痛苦地死去。
从这时起,虽然他对这事还没有多加思索,而且照旧像以往一样生活着,但是列文却不断为了自己的无知而感到恐惧。
除此以外,他还模糊地意识到他所谓的那种信念不但是无知,而且还是那么一种思想方法,靠这种思想方法要取得他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在他结婚后的初期,他所体验到的新的快乐和新的责任完全扑灭了这些思想;但是后来,自从他妻子怀孕以后,他无所事事地住在莫斯科的时候起,这个需要解决的疑问就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执拗地呈现在列文的心头。
对于他,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我不接受基督教对于生命问题所做的解答,那么我接受什么解答呢?”在他的信念的整个库房里,他不但找不到任何回答,他简直找不出一个像样的答案。
他的处境正像一个在玩具店或者兵器店里寻找食物的人一样。
不由自主地,无意识地,他现在在每一本书籍中,在每一次谈话里,在他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探求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寻求它们的解答。
最使他惊异和迷惑的是那些大多数同他年龄相仿、气味相投的人,也像他一样用他那样的新信念代替了他们从前的信仰,却都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可苦恼的地方,而且还十分满足和平静。因此,除了主要的问题,列文还被另外一些问题苦恼着:这些人是诚实的吗?他们不是在做假吧?否则就是他们对于科学所给予他所关心的问题的答案了解得和他不同,而且比他更清楚?于是他就费尽心血去研究这些人的意见和那些登载着他们的答案的书籍。
自从这些问题开始盘据在他的心头以来,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根据他青年时代大学圈子的回忆而设想宗教已经过时了、再也不存在的想法是错误的。所有那些过着善良生活的、他所亲近的人都信教:老公爵、他那么喜爱的利沃夫、谢尔盖·伊万内奇,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信教。而他的妻子信教就像他幼年时候一样,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民,所有那些博得了他无限尊敬的人,也都信教。
另外一件事是,浏览过许多书籍以后,他确信了那些同他观点一致的人并没有任何远见卓识,什么也不说明,只是干脆把他觉得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那些问题置之不顾,却企图解决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不能使他发生兴趣的问题,例如,有机体的发展,灵魂的机械式的解释,等等。
除此以外,在他妻子分娩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他,一个不信教的人,开始祈祷起来,而在祈祷的时候就有了信仰。但是那种时刻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够在生活中给予他当时体验到的心情任何地位。
他不能承认他那时认识了真理,而现在是错了;因为只要他平心静气地回想一下的话,这一切就全粉碎了。但是他又不能承认他那时犯了错误,因为他很珍视当时他的心情,要是承认那是意志薄弱的结果,就会玷辱了那种时刻。他处在一种痛苦的自相矛盾的状况中,竭尽心力要摆脱这种状况。
九
这些思想折磨着他,苦恼着他,有时松弛些,有时强烈些,但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他读书,思索,他读得和想得越多,他就觉得自己距离他所追求的目的越远了。
最近在莫斯科和在乡间,既经信服了他在唯物主义者那里得不到解答,于是他就反复阅读柏拉图、斯宾诺沙、康德、谢林、黑格尔和叔本华的著作,这些哲学家并不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人生。
当他阅读,或者自己想法驳倒别的学说,特别是唯物主义的时候,他觉得他们的思想很有效用;但是当他一读到,或者自己想到人生问题的解答的时候,就又百思不得其解了。当他遵循着类似·精·神、·意·志、·自·由、·本·质这些意义含糊的字眼的定义,而且故意陷入哲学家为他布置的或者他自己布置的文字罗网的时候,他似乎开始有所领悟。但是只要他一忘记那种人为的思路,从现实生活中又回到他认为满意的思路上去,而且按照这种思路思索,这种人为的建筑物就突然间像座纸房子一样倒塌下来,显则易见这种建筑物是由那一套颠来倒去的字眼构成的,与生命中比理智更重要的东西没有关系。
有一个时期,在读叔本华的时候,他用·爱这个字代替了·意·志这个字,而在他还未摆脱开这种新奇的哲学的时候,它曾经慰藉了他一两天;可是当他用现实生活的观点来观察它的时候,它也立刻瓦解了,变成了毫不保暖的薄纱衣裳。
他哥哥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劝告他阅览霍米亚科夫①的神学著作。列文读了霍米亚科夫著作的第二卷,尽避他那种能言善辩的、华丽的、妙趣横生的笔调最初曾使他感到厌恶,但是里面有关教会的学说却打动了他的心。最初打动他的思想是,领悟那份天赋神圣真理并非赐予孤立的个人,而是赐予由于爱而结合起的团体——教会——的。使他高兴的是,他想到相信一个包罗了所有人的信仰,以上帝为首的,因而是神圣和绝对正确的,现在的教会,从而信仰上帝、创造世界、堕落、赎罪等等宗教信念,比从上帝,从一个神秘莫测的、遥远莫及的上帝和从创造世界等等开始要容易一些。但是后来,在阅读罗马天主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和希腊正教作家所写的教会史的时候,却发现这两个实质上都绝对正确的教会却是互相排斥的,于是他对霍米亚科夫的论教会的学说感到失望了;而这幢建筑物也像那幢哲学建筑物一样倒塌下来了——
①霍米亚科夫(1804—1860),诗人,政论家,斯拉夫主义最大的代表人物。他的神学著作于一八六七年在布拉格发表。
一春天他都茫然若失,经历了一段可怕的时刻。
“不知道我是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是无法活下去的。但是这个我又不能知道,因此我活不下去,”列文自言自语。
“在无限的时间里,在无限的物质里,在无限的空间里,分化出一个水泡般的有机体,这水泡持续了一会就破裂了,这个水泡就是——我。”
这是一种使人苦恼的曲解,但是这却是人们在这方面若干世纪来苦心思索所获得的唯一的最终的结果。
这是最终的信仰,差不多一切流派的人类思想体系都是以此为依据的。这是一种占主宰地位的信仰,而在一切其他的解释中,列文不由自主地,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地,偏巧挑选了这个,好像这无论如何也是最明晰的。
但是这不仅是曲解而已,这是对于一种邪恶势力——一种人不可能向它屈服的、凶恶的、而且使人厌弃的力量——
的残酷的嘲弄。
必须摆脱这种力量。而逃避的方法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中。必须停上对这种邪恶力量的依赖。而这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死!
列文,虽然是一个幸福的、有了家庭的、身强力壮的人,却好几次濒于自杀的境地,以致于他把绳索藏起来,唯恐他会上吊,而且不敢携带枪支,唯恐他会自杀。
但是列文并没有用枪自杀,也没有上吊,他继续活着。
十
当列文想到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他找不到答案,于是陷入悲观失望;但是当他不再问自己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反倒好像知道他是什么和为什么活着了,因为他坚决而明确地生活着和行动着;最近他甚至比以前更坚定明确得多了。
六月初他回到乡间的时候,他又回到他日常的工作。农务,同农民和邻居们交往,经管家务和他姐姐和哥哥托付给他的家产,同妻子和亲属的关系,照顾婴儿和从今年春天起他就迷恋上的新的养蜂爱好,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
这些事情引起了他的兴趣,倒不是因为像他以前那样,根据什么公认的原理才认为它是正确的;恰恰相反,现在,他一方面由于他以前在公共福利事业方面的失败而觉得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忙于思考和应付从四面八方压到他身上的大宗事务,因而他完全不再想到公共福利,他对这件事情发生兴趣,只是因为他觉得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得这么做不可。
以前(这差不多从童年就开始了,到他完全成人)当他尽力做一些对所有的人、对人类、对俄国、对全村有益处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察出这种想法倒是令人愉快的,而这种活动本身却总是令人不满意的,而且他总也不十分相信这种事情确实是需要的,而这种活动本身最初看上去似乎是那么重大,却越来越微不足道,直到化为乌有为止;可是现在,自从他结婚以后,当他越来越局限于为自己而生活的时候,虽然想起自己的活动再也体会不到什么快乐,但是他却坚信自己的事业是万不可少的,而且看出它比以往进展得顺遂多了,而且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了。
现在,好像不由自主一样,他像一把犁头似的,在地里越掘越深,不耕出一条条犁沟是拔不出来的。
像祖祖辈辈那样过着家庭生活,那就是说达到一样的教育水平,而且使子女们受到同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这就像饿了需要吃饭一样;因此就像需要准备饭食一样,同样也需要把波克罗夫斯科耶的农事经管得能够产生收益才行。就像一定要偿还债务一样,同样一定也需要把祖传的田产保管到这种程度,使得他的儿子继承的时候,会为了他所兴建和培植的一切,感激他的父亲,像列文感激他的祖父一样。为了做到这种地步,他必须不出租土地,一定要亲自耕作,饲养家畜,往田里施肥,而且种植树木。
不照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他姐姐的和那些习惯于向他请教的农民的事务是不可能的,就像把抱在怀中的婴儿抛掉是不可能的一样。必须照顾请来作客的姨姐和她的孩子们以及他妻子和婴儿的安适,每天不花费一点时间来陪他们也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再加上他的打猎的爱好在养蜂的新爱好,就占满了列文的那种他一想起来就觉得没有一点意思的全部生活。
但是除了明确地知道他必须做·什·么以外,列文同样也知道这一切他必须·怎·么做,事情当中哪一样是更重要的。
他知道他一定要尽量廉价雇佣工人;但是用奴役办法来雇人,以预付的方式压低他们应得的工资,却是不应该的,虽然那样有利可图。在缺货的时候卖给农民稻草是可以的,虽然他替他们很难过;但是旅馆或者酒店,虽然很赚钱,也一定要取消。砍伐树木一定要尽量从严处分,但是农民们把牲口放到他的地里却不能处以罚款;虽然这使看地的人很发愁,而且使农民们无所畏惧,他却不能扣留人家走失的牲畜。
彼得每个月要付给债主百分之十利息,他必须借给他一笔钱,好把他解救出来;但是拖欠了地租的农民们却不能不交地租或者延期交租。不割草场上的草,使草都糟蹋了,是不能饶恕避家的;但是种着小树的八十亩地上的青草却不能割。一个雇工在农忙季节,因为父亲死去回了家,无论他是多么可怜,也是不能饶恕的,而且为了那些宝贵的月份他旷了工,一定要扣除他的工钱;但是却不能不按月发口粮给对他毫无用处的老仆人们。
列文也知道,一回到家首先就得去看他那身体不舒服的妻子,而等待了三个钟头要见他的农民们却是可以再稍候一会的;而且他知道,尽避往蜂房里收蜂群是一种乐趣,但是他却得放弃这种乐趣,让管蜂的老头一个人去收蜂群,而去和到养蜂场来找他的农民们谈话。
他做得对不对,这他可不知道,现在他不但不打算加以证实,而且避免谈论和想这件事。
推究把他引入了疑惑之中,妨碍他看清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但是当他不动脑筋,只是这么活着的时候,他就不住地感觉到他的心灵里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审判官,在评判那可能发生的两种行动,哪样好,哪样歹;而他刚一做了不该做的事,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他就这样活着,他不知道,而且也看不出他有可能知道他是什么和他为什么活在世界上,而且他因为这种愚昧无知痛苦到那种地步,以致他简直害怕他会自杀,同时他却在坚定地开辟着他自己特殊的确定的人生道路。
十一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来到波克罗夫斯科耶的那一天,是列文最苦恼的一天。
这是一年中最紧张的农忙季节,那时候,所有的农民在劳动中都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自我牺牲的紧张精神,那是在任何其他的生活条件下都没有表现过的,要是露出这种品质的人们自己很看重它,要是它不是年年如此,要是这种紧张劳动的成果不是那么平常的话,那它就会得到很高的评价的。
收割或者收获黑麦和燕麦,装运,割草,翻耕休耕地,打谷子和播种冬小麦——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简单平凡;但是要干完这一切,就需要全村的人,老老少少,毫不间歇地劳动三四个星期,而且比往常要艰苦三倍,靠着克瓦斯、葱头和黑面包过日子,夜里打谷和搬运谷捆,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内睡不到两三个钟头。全俄国每年都是这样干的。
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乡下度过,而且同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大忙的时刻,列文总感觉得农民们这种普遍的兴奋心情感染了他。
一大早,他就骑马到第一批播种黑麦的地方,然后又到运去燕麦堆成垛的地方去,当他妻子和姨姐起床的时候就回家去和她们一道喝咖啡,接着又步行到农场,那里安装好的一架新打谷机就要打谷了。
一整天,当他同管家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当他在家中跟他妻子、多莉、她的孩子们和他的岳父谈话的时候,除了农务以外,列文翻来覆去老想着他当时很关心的那个问题,在一切里寻找着同这个问题有关系的东西:“我到底是什么?我在哪里呢?我为什么在这里?”
列文站在一所新盖好房顶的谷仓——尚未落尽树叶、还散发着香气的榛树枝作板条,茅屋顶用新剥去皮的白杨木做房梁——透过敞开的大门凝视着打谷时回旋飞扬的干燥而刺鼻的灰尘,时而凝视着被炎热的阳光照耀着的打谷场上的青草和刚刚从谷仓里搬运出来的新鲜麦秆;时而凝视着长着花斑头顶和白胸脯的燕子,它们啁啾着,鼓动着翅膀飞进房檐下,歇落在门口的亮处;时而凝视着在阴暗的、尘土飞扬的谷仓里奔忙着的人们,于是他心上产生了无数的怪念头:“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想。“我为什么站在这里,强迫他们劳动呢?他们为什么全都这样卖力,而且极力在我面前表现得非常勤奋呢?我认识的这位马特列娜老婆婆这么拚命干什么(失火的时候一根大梁打中了她,我曾为她医治过)?”他想,望着一个瘦削的农妇,她正用耙子把谷子耙拢来,她的晒得黑黝黝的赤脚在高低不平的坚硬打谷场上吃力地走着。“当时她身体复原了,但是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十年之内,人们就会埋葬她,于是她什么都不会遗留下来,而那个以那样灵活而细气的动作扬掉麦穗上的谷壳、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也什么都不会留下来。人们也会埋掉她,还有那匹斑马,那是不久的事了呢,”他深思着,望着一匹肚皮一起一伏、鼻孔胀大、呼吸急促的马,它正踩着在它身下转动着的斜轮子。“他们会埋葬了它,而那个正在把谷子放进机器里、鬈曲的胡须上落满糠皮、白肩膀上的衬衫破了一大块的费奥多尔,也会被人们埋葬掉。而他却还在解谷捆,吩咐什么、对妇女们吆喝着、手脚麻利地把转动着的轮子上的皮带整理好了。况且,不仅仅是他们,我也会被人们埋葬掉,什么也不留下来呢。这都是为了什么呢?”
他想着这个,同时看了看表,计算他们一个钟头之内可以打多少。他必须知道这个,好据此来定每天的工作定额。
“快一个钟头了,他们才开始打第三垛,”列文想,走到正在把谷物放进机器里的那个人跟前,用压倒机器的轰隆声的声音叫他每次少往里面放一点。
“你一次放进去的太多了,费奥多尔!你看,都堵塞住了,所以就不顺畅了。要放得均匀!”
费奥多尔,被粘在汗淋淋脸上的灰尘弄得漆黑,喊了句什么作为回答,但是仍旧不照列文希望的去做。
列文走到机器跟前,把费奥多尔推到一边,亲自动手把谷物放进机器里去。
一直干到农民们快吃午饭的时候,他和费奥多尔才一起离开谷仓,站在打谷场上一堆新收割下来的、留做种籽的、整齐的黄色黑麦旁边,交谈起来。
奥费多尔来自一个遥远的村落,就是列文以前按照合作经营方式出租土地的那个地方。目前他把那块土地租给一个打扫院子的人了。
列文和费奥多尔谈起这块地来,打听那个村落里的一个富有的、人品很好的农民普拉东,明年会不会租那块土地。
“地租太高,普拉东缴不起,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那个农民回答,从被汗水湿透的衬衫怀里摘下黑麦穗。
“但是基里洛夫怎么缴得起呢?”
“米秋赫(那个农民这样轻视地称呼那个打扫院子的),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他怎么会缴不起呢!这家伙很会压榨别人,他还会从中捞一把哩。他连个基督徒都不可怜的!可是福卡内奇大叔(他这样称呼普拉东老头),难道他会剥削别人吗?他借钱给别人,有时就算了,有时不要全部归还。这全看是什么人呀!
“但是他为什么不要人家还钱呢?”
“哦,可见人跟人不同啊!有一种人只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活着,就拿米秋赫说吧,他只想填满肚皮,但是福卡内奇可是个老实人。他为了灵魂而活着。他记着上帝。”
“他怎么记着上帝呢?他怎么为灵魂活着呢?”列文几乎喊叫起来。
“您知道怎么样的,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您要知道,人跟人不同啊!譬如拿您说吧,您也不会伤害什么人的……”
“是的,是的,再见!”列文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于是扭过身去,拿起手杖迅速地走回家去了。一听到那个农民说普拉东为他的灵魂正直地、按照上帝的意旨活着,一些模糊的、但是意义重大的思想就涌上他的心头,好像从封锁着它们的地方挣脱出来一样,全都朝着一个目标冲去,在他的脑海里回旋着,以它们的光彩弄得他头昏目眩。
十二
列文沿着大路迈开大步走着,他所留意的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他还不能清理出个头绪),毋宁说是那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
那个农民所说的话在他的心里起了像电花一样的作用,把那些不住地萦绕在他的心头的、散漫的、无力的、各别的思想突然改变了和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思想,甚至在他谈论出租土地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盘据在他的心头了。
他感觉得自己的心灵中有某种新的东西,他愉快地探索着这种新的东西,但是却还不知道它是什么。
“活着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上帝!为了什么上帝呢?还有比他所说的话更无意义的吗?他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那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为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所迷恋的、我们所渴望的东西活着,而是为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为了谁也不了解,谁也无法下定义的上帝活着。这又是什么呢?我不明白费奥多尔这些荒谬无稽的话吗?明白了的话,我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吗?我认为它们是愚蠢的、含糊的、不确切的吗?
“不,我了解得完全跟他了解的一样,比我了解人生中的任何事情都透彻,都清楚哩!这一点我一生都没有怀疑过,而且也不可能怀疑。非但我一个人,所有的人,全世界都充分理解这个。人难免对别的东西发生怀疑,但却没有人怀疑过这个,而且大家总是同意这个的。
“费奥多尔说基里洛夫,那个打扫院子的,是为了他的肚皮活着。这是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我们所有的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都不得不为自己的肚皮活着。而突如其来的,这位费奥多尔却说为了肚皮活着是错误的,应该为了真理,为了上帝而活着,而他略一暗示我就领悟了。我和千百万人,千百年前的人和那些现在还活着的人:心灵贫乏的农民们和深思熟虑过、而且论述过这事的学者们,全都用含糊的言语谈论着这件事情——而那件事我们全都同意的:我们应该为什么活着,什么是好的。我和所有的人只有一种确切的、不容怀疑的、清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不能用理智来说明的——它是超乎理智的,不可能有任何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如果善有原因,那就不是善了;如果善有结果——有报酬,那也就不是善了。因此善是超出因果关系的。
“而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而我却在寻找奇迹,因为看不见能使我信服的奇迹而感到遗憾!物质的奇迹会诱惑我。但这里,就在我周围,却有一种奇迹,一种唯一可能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奇迹,而我却没有注意到。
“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奇迹呢?
“难道我找到了这一切的解答吗?难道我的痛苦真的结束了吗?”列文一边想,一边沿着灰尘弥漫的道路大步走着,忘却了炎热,也忘却了疲倦,感到一种解除了长期苦痛的轻快之感。这种感觉是那么令人愉快,使人简直都难以置信了。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再也不能往前走了,于是他离开大路,走进树林里,坐在白杨树荫里未割的草地上。他把帽子从冒汗的额头上取下来,支着胳臂肘,躺在多汁的、宽叶的树林里的草地上。
“是的,我一定要冷静地想想,弄明白,”他想,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他前面未践踏过的青草,注视着一只绿色甲虫的一举一动,它正沿着一株速生草的草茎爬上去,在爬的时候被茅草的叶子阻挡住了。“一切从头做起,”他自言自语,把茅草的叶片扳到一边,使它不致挡住甲虫的路,又弄弯了一个叶片,使那只虫子可以从上面过去。“是什么使我这样高兴呢?我发现了什么呢?”
“以往我总说,在我的身上,在这棵青草上和那只甲虫(你看,它并不想到那棵草上去,却展开翅膀飞走了)身上,按照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定律,正在发生物质变化。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白杨、云彩和星云在内,都在进化的过程中。从什么进化来的?进化成什么呢?永无休止的进化和斗争……好像在无穷之中可能有什么趋向和斗争似的!而使我惊奇的是,尽避我尽力沿着这条思路深思熟虑,但是人生的意义,我的冲动和欲望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向我显示。我的冲动的念头是那么明显,使得我总是按照它生活,而当那位农民对我说他‘为了上帝,为了灵魂活着’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惊奇又高兴了。
“我什么都没有发现。我不过发现了我所知道的东西。我了解了那种不但过去曾赋予我生命、而且现在也在赐给我生命的力量。我从迷惑中解脱出来,认识了我主。”
于是他简略地在心里回顾了一遍他最近两年来的整个思路,那是随着看见他的没有希望痊愈的亲爱的哥哥而产生的清晰而明显的死的念头开始的。
那时他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在所有人面前,在他自己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世间忘却以外一无所有,于是他断定这样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要么得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要像是什么恶魔的恶意嘲笑,要么就得自杀。
但是他既没有做这件事,也没有做那件事,反而继续活下去,继续思考和探索着,甚至同时还结了婚,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乐趣,而且当他不考虑他的生命的意义时他还是很幸福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生活得很好,可是思想不对头。
他靠着随着他母亲的乳汁一同吸进去的精神上的真理而生活着(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思想上他不但不承认这些真理,而且还费尽心机来回避它。
现在他明白了,多亏把他教养成人的信仰,他才能够活下去。
“如果我没有这些信仰,而且如果不知道一个人应该为上帝活着,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活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且我会怎么度过我的一生呢?我一定会抢劫、说谎和杀人!惫成我的生活中的主要快乐的东西也就根本不会存在了。”虽然他拚命想像,但是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如果他不知道他为了什么活着,他会成为一个怎样兽性的东西。
“我找寻我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思想却不给予我的问题一个答复——它和我的问题是不相称的。生活本身给予了我这个答案,从而我认识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这种知识我是用什么方法也得不到,但是却赐给了我,就像赐给了所有的人一样,所以赐给我,就是因为我从任何地方也不能够取得它。
“我从哪里得到的呢?凭着理智我能够做到一定要爱自己的邻居,而不要迫害他们的地步吗?我小的时候人们就对我这么说,而我就高兴地相信了,因为他们对我说的是已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的东西。但是谁发现的呢?不是理智!理智发现了生存竞争和要求我们迫害所有妨碍我们满足欲望的东西的法则。这就是理智所作的推论。但是爱人如己的法则是理智不可能发现的,因为这是不合理的。”
“是的,骄傲!”他自言自语,翻过身去趴在地上,动手把叶片打成一个结子,极力不要把它折断。
“不但是心灵上的骄傲,而且是心灵上的愚蠢。而主要是欺诈,简直是心灵上的欺诈。就是心灵上的欺骗,”他重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