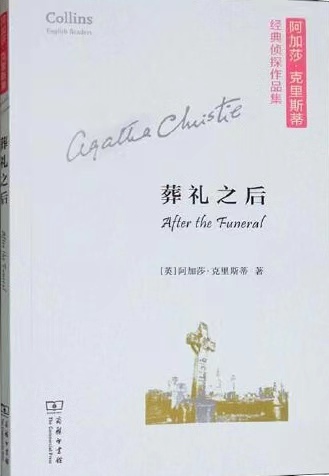开宝 9 年(973 年),陈桥兵变后 13 年,群臣按惯例请宋太祖接受尊号,见到上呈的尊号里的有“一统”二字,太祖反问群臣道,“幽燕未定,何谓一统?”此时南方的地方政权吴越,南唐虽然还未归顺,但平定南方已是指日可待。但是位于山西一带的北汉政权仍依靠着契丹的势力威胁着中原王朝,而后晋时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还有十四州未收复,因此赵匡胤才说出了这句类似骠骑将军霍去病曾说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话。三年之后,宋太祖在斧声烛影的迷雾中去世,年仅 50 岁。38 岁的弟弟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
与过去的五代的王朝面临的问题一样,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仍是悬在宋朝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般强大的外部安全威胁,不免影响到了宋朝的内政。此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已非那些于春秋战国时期所鄙视不开化的蛮夷,他们在于与汉民族的交往中,已经开始了文治武功的政权建设。我们今天在山西的云冈石窟,可见不同时代风格的壁画,雕塑,有中原风格,也有来自欧陆或印度的样式,这样的文化交流与共相发展,使得在西晋覆亡后,公元五世纪到六世纪间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才能有能力入主中原并建立相对稳定的政权。
五代时期,于中原各势力的角力间,强大的契丹便成为改变天平往那一方倾斜的重要势力。后晋石敬瑭于 937 年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就是希望借割让此北方战略屏障,以期换取辽国的信任,并与辽结盟,换取外援,协助其武力夺取后唐政权。
所以,固守华夷之辩是错误的,契丹族早在唐初就于当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并在 907年其领袖阿保机正式即皇帝位。而此后长期威胁宋朝西北的西夏,也早于唐末就是一个稳固的割据政权。此后当元昊自称大夏皇帝时,也效仿中原王朝定年号,追封自己的父亲,祖父帝号和庙号,可见其政制已深受中原文明影响。而在西南方向,我们不要忘记,在云南,还有一个南诏政权。今日在巍山古城的拱辰楼上的“魁雄六诏”四字,或是在云南博物馆内大量的錾金佛像,让今日的我们可想象其当日风华。
所以,如傅海波教授所说的,此时宋代面对的不再是松散的游牧民族联盟,而是在中国文化体系下逐步发展起来的稳固的,长期于中原王朝共存的“包括汉人在内的多种族边疆政权”。
强邻不可轻犯,需待数年积累之功。从战争中成长且曾领兵与辽作战的赵匡胤清楚地明白这点。所以宋初的统一战争,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先易后难。加之南方是富庶之地,可以征调南方的赋税来支持军费。太祖曾建立“封桩库”,希望将来用这些财政盈余来赎回燕云十四州(因为其中东边的瀛洲和莫州在后周时代已经收复)。因此从太祖时期到宋太宗初年,宋辽关系还是处在一个温和的对峙状态,双方正常遣使交聘。
但是在 979 年,当太宗征服了契丹辽国保护下的北汉后,宋辽关系便破裂了。太宗在公元 979 年高粱河(即在今北京西直门外)对辽一战失败后,心仍不甘,未考虑现实情况,仍坚持要收复幽州一带。于是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于 986 年再次北伐,在岐沟关(河北涿州)战役中再次大败。
战败之后,赵普劝他,“何必到穷边极塞,去和戎人争个胜负呢?”大臣们也劝他,“兵久则变生”。太宗或许此时想起在高粱河一战失败后孤身逃亡,军队寻不到太宗时,有大将便意图立太祖次子李德昭为帝的变故。自此宋太宗便改变方略,开始了“守内虚外”的方针,即对辽国采取守势战略。此后近二十年间里,直到真宗在位的 1004 年澶渊之盟签订前,宋辽的边境上时虽有战事发生,互有胜负,但总体还是回复到早前的温和的对峙状态。
太祖与太宗,花了大概 20 余年的时间,从逐步完成了国内统一,消除了唐朝末年以来中央和地方分裂的态势,重新恢复了中央的权威,使整个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但是由于幽云十四州仍处于辽国控制中,造成华北再无地形屏障优势可以有效抵挡北方强邻的快速入侵。今天,我们从北京往南就可以发现,离开燕山余脉,便是千里平原,无险可依。
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农耕地带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正如同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垂涎也是片刻未忘。因此,虽然宋辽双方短暂地维持着平衡,但宋廷从未要忘记收复幽云十四州,重建藩篱。而辽国自然也从未忘记富庶的南方。
这种平衡忽然于 1004 年被打破。
9 月,辽军一改过去攻城略地的打法,他们不计一城一池得失而是长驱直入到黄河边上的澶州(即今日的河南濮阳)。此时如果没有黄河天险的阻挡,离首都东京就只剩几日的行程(两地距离只有大约 300 里)。面对辽军的来势汹汹,出生在太平时代,此时已 36 岁的太祖的继承者宋真宗显得异常怯弱,毫无太祖太宗的雄主之态。身边大臣如陈尧叟,劝真宗逃到四川,而王钦若则劝真宗到南京,同样也是想避敌失地逃亡。幸有当时宰相寇准的力主抵抗,真宗才勉强到澶州亲征鼓舞士气。由于辽方统帅萧挞览的意外阵亡,加之真宗的亲临前线。在双方实力均等,僵持不下的态势下,最后和议达成了互称兄弟之国,撤兵,宋付岁币三十万,开市贸易等协议后辽军退兵,史称澶渊之盟。
当宋辽相持都无法征服对方时,这纸盟约是现实主义的胜利。相互之间的称谓并无问题,而岁币三十万也是一个小数目,因为单单从和平时期的宋辽贸易中,一年的净利润就远超这个数字,更遑论为维持边界而投入的巨大军费开支。当时还有人故作姿态的说 30 万太多了,殊不知,宋真宗派去谈判的曹利用回来汇报时,真宗问他岁币多少,曹伸出三个手指头,真宗感叹到,太多了。因为真宗误以为是三百万。但是他又马上说,算了,这也可以。时任宰相毕安士清醒地指出,“如果不依这些条件,合议恐怕无法持久,因为契丹不会满足。”
澶渊之盟中,由于定义了宋辽维持现有边界,因此,也就直接承认了辽对燕云十四州的控制权。可如此现实主义般的绥靖,从后来的实际结果看,确实为宋朝赢得了约一百多年的和平时光。我们可以在后来的记录中看到每年的节日或双方主政者生日等,双方都互派高规格使团,现实双方互尊条约,关系融洽。在盟约签订后,辽国也停止了对宋的侵扰,因为经过数十年的战争,加之国内其他民族的叛乱如高丽,渤海等,造成了人民的极度困苦。因此,辽国开始其国内秩序的重建而非对外征伐。
签约条约的这年是 1005 年,离党项族西夏正式建立政权并开始大规模侵扰宋朝西北边境还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这样外部安全压力减少的情况下,宋朝开始了一段政治的稳定期。
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真宗开始意得自满,开始了所谓天降祥符等奢靡无用的举措。真宗发现他做为皇帝,竟然还有一位契丹的皇帝与他相埒,因为盟书上写者,他是大宋皇帝,而还有一个“大契丹皇帝”,可中原王朝历来有夷夏之分的原则,这如何能接受呢?当时还未做宰辅,时任馆阁的王曾就说,“中国一向是尊中国,贱夷狄,即使汉朝时被迫和匈奴和亲,礼数上也不见得均等,”因此王曾反对称契丹为北朝,认为应该还是称为契丹。王钦若为诋毁寇准而说澶渊之盟是寇准安排下的深为其辱的城下之盟。他劝真宗只有引天命以为重,戎狄闻之,便不敢轻视中国。也唯有求天的感应,才能表现出自己天子的正宗,镇服海内,夸示夷狄。
于是真宗决定借天降天书祥瑞的幌子,大搞崇神,封禅泰山等运动以示他是唯一的天子。朝中大臣虽不乏反对之人,但当真宗快意于那些荒诞无稽的仪式时,也只能保持缄默。
比如时任宰相王旦,本想劝谏,但在受真宗丰厚赏赐后,只能言听计从,安于禄位。他忘了他读过的《春秋》所说的“国之将兴,听于人,国之将亡,听于神“。王旦的苟且于他自己心里也是沉痛无奈的,因此在他去世前,回想起真宗刚即位,而他刚任执政时,宰相李沆告诉他的话,“皇帝认为朝廷不可以用浮薄好说喜事的人,这是治理的基础。皇上还是少年,必须要让他知道四方艰难, 不然,他血气方刚,一旦声色犬马,便大事休矣。” 只是李沆可能不会想到,真宗的作为,比声色犬马还要逾矩。
真宗为了彰显他贵为天子,为这些上帝赐予的祥符大建宫室,比如玉清宫等宫殿群,便花费了十四年的时间,拥有数十座宫殿,规模宏大环丽,耸耀京都,所费自然不赀。南宋的朱熹一针见血地指出,“真宗东封西祀,靡费巨万计,却不曾做得一实在事。”当时的礼部尚书张咏指责道:“近年国库虚空,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
在澶渊之盟的十八年后,1022 年,54 岁的真宗驾崩,留下了一个国用无余财的朝廷,还有年仅 13 岁的继位者仁宗,朝廷则由章献刘太后摄政。
刘太后虽曾意图长期把持朝政,但由于武则天的殷鉴不远,加之宋代立国后的士风以逐步摆脱了五代时的猥琐不堪,于是当朝官员对于刘后为刘氏立宗庙等逾矩行为,都能大胆提出反对而不怕遭受残酷的迫害。刘太后在仁宗前期长达 10 年的垂帘听政,虽然无大的建树,但也总算是平稳地把政权交予仁宗。
虽然刘太后摄政期间有各种的政策冲突,但朝政总体是静态的。在这样的静态里并无法推动什么。他唯一的后果就是让原有的问题在看似平静无事的过程中继续深化着。比如从真宗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冗官和冗兵现象。这些问题,加上财政的危机,直到仁宗亲政后的康定年间发生的外部军事压力便全部暴露出来,于是催生了庆历新政。但是,如果没有宋自开国一来就延续的养士的国策和宽松的思想环境。这样的改革想法,也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