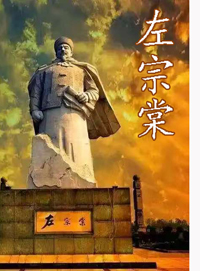5月19日军队第一次试图实施戒严时是在夜间行动,他们错误地以为人们都在睡觉,没有想到北京市民会借着月光涌上街头。军队领导人第二次采取行动时选择了6月3日夜间,按阴历这应该是最黑的一个夜晚。这个日子还有一个好处,因为6月4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这一天得以恢复,那么混乱就基本上被控制在周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邓小平在6月3日承认,即使天安门广场和整个北京的秩序大体得到恢复,也需要几个月甚至数年时间才能改变人们的想法。他并不着急,并且觉得没有必要谴责那些参加绝食、示威或请愿的人。他命令军队只把违法者和试图颠覆国家的人作为目标。他告诉他们,镇压的理由是,为了继续改革开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环境。
在解释动用军队的理由时,邓小平承认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如果让示威和贴大字报的现象继续下去,就没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说,党的领导人要解释恢复秩序的决定,说服各级干部,让他们相信对抗议者采取行动是正确的。
在6月3日之前的几天里,学生开始觉察到军队调动的一些迹象,但是他们不清楚已经有多少士兵渗透进市中心。此外,大多数学生无法想象他们的抗议会导致开枪。在6月3日之前,学生有几次投票表决是否继续占领广场。大多数人都投票赞成留下,因为主张离开的人已经用脚投了票。但是在6月4日前的几天里,一些学生领袖害怕受到惩罚,试图与政府谈判。他们说,离开广场的条件是保证他们不受惩罚,并且学生组织得到正式承认。但他们没有获得这样的保证。
6月2日夜里,街头传出了一些部队正在开进北京的传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处传话,结果,军队试图进城时有很多部队车辆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烧毁。同时,政府官员则要求继续推进。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的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了邓小平,立刻得到批准。领导人在6月2日估计会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们低估了对抗的强度。据陈希同说,人们“围困并殴打解放军。⋯⋯还有暴徒抢夺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中央机关和一些重要部门遭到冲击”。抵抗的规模和决心让李鹏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乱”的说法,这意味着要像对待敌人那样对付抵抗者。他说:“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去镇压首都这场反革命暴乱。我们对付这一小撮暴乱分子不可手软。授权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公安必要时运用任何方法去对付阻挠这项任务的人。”
6月3日各集团军司令也在北京军区司令部开会,研究了进攻计划的细节:将用机动车把士兵分三批运进北京,每一批部队都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行动。第一批将在下午5点到6点半之间从三环和四环出发,第二批在7点到8点之间出发,第三批在9点到10点半之间出发。早到的卡车上有些并不会配备武器,但前三批军队之后将有两批武装军人赶到:一批将在10点半出发,另一批午夜后出发。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广场。
行动按计划进行。6月3日下午6点半,广播和电视发布了紧急通告,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工人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中央电视台不停地播放这条通告,广场上的大喇叭也同样广播。但是通告没有具体说明部队就要进城。由于政府已多次发出其他警告,很多人并没有足够重视“保护你们的生命”这句话。
6月2日和3日,抗议的学生采用了他们自5月19日以来学会的策略。尽管有对讲机的人很少,但他们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车来传递部队移动的消息。数百名称为“飞虎队”的骑摩托车者向各个地点传送消息,告知部队的动向,使人们能够及时设置路障。当路障迫使领头的卡车停下来时,人们便一拥而上,割破轮胎或放气,使卡车无法继续前进。然后人们又割断线路或拆卸零件,开始嘲弄车上的士兵,并朝他们扔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攻击坐在卡车后面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了第一批卡车,而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不能动弹的车队。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发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凌晨天安门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这里离木樨地不远,附近的高层住宅楼居住着很多退休的高干。38军的部队在晚上9点半到达木樨地时,看到数千名市民聚集在这里阻止他们前进。公交车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挡住了装甲车前行。解放军先是放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但没有多大效果,人们大胆地向部队投掷石块和杂物响应。有个军官用扩音器命令人群散开,也没有奏效。由于38军军长徐勤先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带兵,这支从西面开过来的军队就像在中国内战中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一样,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忠诚的特殊压力。大约10点半前后,木樨地附近的部队开始朝空中鸣枪,投掷眩晕手榴弹,但并未造成死亡。
夜里11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90发子弹的AK-47自动步枪。有人中弹时其他人就会将伤者搬离危险区,把他们抬上救护车或放在自行车和三轮车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复兴医院。解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哩的路程。
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半夜之前到达的部队人数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几小时前就已经来到这里。晚8点,灯光照亮了广场和东长安街,到晚9点时这条大街上已几乎空无一人。装甲车和坦克开始载着部队进入广场。在数英哩之外,当军队从东边向广场开进时,一些步枪子弹击中外国摄像师和记者们所在大楼的窗户——军队这是在警告他们不要靠近窗口,因为那里可以拍摄到广场附近的屠杀画面。一些穿便衣的军官挡住外国人,告诉他们离开大街以免受伤,并警告他们不要拍摄军事行动的照片。很多拍摄者的照相机和胶卷被没收。
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10万名示威者。6月4日即星期日凌晨1点,军人们开始从不同方向到达广场。在广场四周、长安街和人民大会堂前,士兵开始朝着向他们谩骂、扔砖头并拒绝离开的平民开枪。抗议者没有想到士兵会用真枪实弹对付他们,当一些被打死或打伤的抗议者被抬走时,剩下的人才变得恐慌。
到凌晨两点时广场上只剩下几千人。学生领袖柴玲宣布,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刘晓波等几位著名知识分子早在6月2日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他们都认为这可能是学生占领广场的最后几天。侯德健用麦克风警告仍然留在广场上的人说,武装部队正在向广场推进。他说,现在听他讲话的人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但是血已经流得够多了,留在这里的人应该和平撤离,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当作武器的东西。
当部队步步逼近时,侯德健和另外三个人于3点40分左右与戒严部队见面,协商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经过简短的谈判之后,解放军军官表示同意。凌晨4点广场灯光关闭。侯德健返回后不久就通过话筒宣布了他们达成的协议,让留在广场的学生马上离开。大约3,000人跟随着侯德健匆匆离开了广场。4点半军队和军车向前推进,留下来的学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5点20分时大约只剩下200名无畏的示威者。他们被部队强行赶走时,是黎明之前,5点40分,正如清场命令所要求的那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
据一些目击者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4点半到5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地承认了此前和此后可能有人遭到射杀。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6月4日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军人和23名学生,大约2,000人受伤。李鹏在7月2日对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死了310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军战士和36名学生。遇害人之一的母亲丁子霖后来试图搜集当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为止她总共搜集到近200个姓名。据38军政委李志远的报告,除了死伤的士兵外,有65辆卡车和47辆装甲运兵车被毁,另有485辆军车受损。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300人到2,600人之间,有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11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478人死亡,920人受伤。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些医院纪录的数字,因为一些家庭担心伤者或家人受到长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疗,或通过非常规渠道处理了死者的尸体。
解放军和警察在清场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清扫示威期间遍地垃圾的广场并捣毁了民主女神像。虽然与当地市民发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镇压之后,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示威的学生领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还有一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譬如在广场上劝说学生撤离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监禁。邓小平亲自决定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满后仍然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赵紫阳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监禁,一些示威者在20多年后仍未获释。通过“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处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帮助,包括柴玲和吾尔开希在内的一些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和陈一咨那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设法成功逃往国外。而王丹被监禁几年后获释,他流亡到西方,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业。
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
参加1989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1940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1980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生,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的20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年6月4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例如,1947年2月28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1980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1989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即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捍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学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 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世界报道。
在1989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1989年4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布消息的异见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1989年4月15日到6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学生毫不掩饰的大力支持,使记者和学生都难以想象政府会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很多记者事后自我批评说,他们像自己所报道的学生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以至于看不到潜在的危险,未能让西方观众对后果有所准备。
到5月底时,西方的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已经完全认同为民主而战的学生,因此他们把血腥的结局视为镇压“我们的”学生,学生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民主女神像尤其让美国人感到亲切,因为它显然是对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观众看来,无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独裁者射杀的。记者看到自己刚刚结识的学生被打击和枪杀,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夸大了恐怖。有人报道被杀害的示威者多达5,000人甚至10,000人。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6月9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导人时仍是如此。但对于客观的观察者来说,局势此时显然已经稳定下来。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外国媒体成为了推波助澜的“黑手”, 因为中国的酒店职员、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华人,都能够收听收看到这些节目。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CNN)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自由报道他们所见所闻的西方记者,并在自己写报道时试图扩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门事件之后,那些相信美国出于国家利益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学者和美国政府官员,很容易就会被指责为跟北京的“邪恶独裁者”沆瀣一气。在冷战就要结束之际,很多敢言的美国自由派主张:我们的政策应当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应当纵容独裁者,而是应当站在民主和人权一边。表达西方人对这些理想的信念,还有比谴责天安门镇压的责任人更好的方式吗?因此,邓小平在“六四”后所面对的敌意,不但来自义愤填膺的中国年轻人和市民,而且来自与示威者秉持同样价值观的西方官员。
假如?
这场造成如此严重的人道灾难并被全世界所见证的巨大悲剧,使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都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场大灾难是否可以避免?寻找悲剧直接原因的人将其归咎于邓小平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广场的决定。批评邓小平的人说,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没有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付“动乱”,假如他更愿意听听学生的意见,或者,假如他能够用尽一切非暴力手段,那么天安门清场就不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丧失。批评赵紫阳的人认为,假如他对学生少一些鼓励,以更果断的方式对待他们,假如他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开明领导人”形象,最后的悲剧也许能够避免。批评李鹏的人称,假如他没有如此顽固地拒绝与学生对话并体谅他们的关切,如此急迫地谴责他们,如此断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论”并给学生贴上“动乱”分子的标签,如此僵化地轻蔑学生且缺乏起码的同情心,那么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批评陈希同和李锡铭的人则说,假如他们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汇报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和外国势力卷入的程度,邓小平等老干部也许不会觉得必须作出如此强硬的反应。
批评学生领袖的人说,假如他们不那么虚荣,不那么自视过高,对他们造成的危险不那么无知,悲剧可能不会发生。还有人认为,假如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月20日没有阻挡试图以和平方式恢复秩序的部队,政府也许能够避免在两周之后开枪。批评西方人的中国人认为,假如没有西方人对学生的抗议煽风点火,没有外国“黑手”试图颠覆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示威活动绝对不会失去控制。
寻找深层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8年放任通货膨胀加剧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愤怒和焦虑。还有人批评高层官员滥用权力和特权,恐吓群众,毫无必要地严密监控个人生活,让自己的亲友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保守派谴责市场改革走得太快,从而助长贪婪,导致了官场腐败。还有人相信,邓小平没有使国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1986年没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场冲突的最终原因。邓小平确实认为,处于最高层的干部有责任作出决定,尽管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但最终必须做他们认为对国家长远利益有帮助的事。有些人说,假如邓小平进行更多的选举试验,削弱集权主义领导体制的禁锢,引入法治,惩治贪官,国家也许能够进步得更快,从而避免来自学生的挑战。
还有一些干部赞赏邓小平处理天安门示威的方式。他们认为,当1989年5月底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开始失控时,邓小平采取的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很多干部认为,在邓小平无法用不向人群开枪的戒严令恢复秩序之后,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以他最终所采用的方式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当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骚乱作出的反应与戈巴卓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时,他们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坚信,中国仍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假如领导人让知识分子享有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中国不可能维持统一。他们也承认1989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相信,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作为学者,我们和其他关心人类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样,都很想找出这场悲剧的明确原因,然而事实是我们谁也无法断定,假如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毕竟,这一事件才过去20年,对邓小平的决策所造成的长期影响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这条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苏联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答案。
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为发生更大抗议的可能危险而紧绷着神经,但是中国在“六四”之后的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今天,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比他们在1989年时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都得到了更多的国际信息和观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寿命也在继续迅速提高。由于诸如此类的原因,中国人对民族成就的自豪感远超上个世纪。
我们也知道,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们的政府仍然怀着深切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支持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