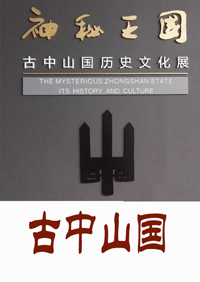“爸爸……爸爸,是我呀,萨莎!”
她小心翼翼地解开勒在肿胀得可怕的下巴上的粗帆布系带,从父亲头上取下钢盔,又将手指伸进他湿漉漉的头发,扯下防毒面罩,扔到一旁,远远看去像是从俘虏头上剥下来的头皮。他的胸口高高隆起,手指抠住花岗岩地面,泡肿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她。他不回答。
萨莎将背囊垫在父亲头下,朝门口走去。她用瘦弱的肩膀顶住钢铁门,深吸一口气,将牙齿咬得咯吱直响。数吨重的钢铁门极不情愿地屈服了,开始缓慢移动,最后轰然复归原位。萨莎咣当一声插上门闩,瘫软在地上。但她只坐了短短一分钟,一口气还没喘匀,就又朝父亲走来。
每一次新的出征,都让父亲付出比前一次更大的代价,而那些微薄的战利品根本不足以补偿他所耗费的精力。为了这些远行,他在过度透支自己的生命,不是以天,而是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他不得不这样做,如果他们没有任何东西拿来卖,那就只剩下一条出路:吃掉自己驯养的那只小老鼠——这个贫瘠的车站上唯一的一只,然后饮弹自尽。
萨莎很想替父远征。她恳求过父亲无数次,让他把那件防毒面罩给她,由她上到地表,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因为他很清楚,那件破旧防毒面罩里的过滤装置早就堵满了,作用不比那些辟邪符坠强到哪儿去。但他从来没对她这样讲过。他总是骗她,说自己会清洗过滤装置,说他即便在地表溜达一小时也没什么大碍,说他只想一个人静静,其实是怕她撞见自己吐血。
弱小的萨莎无力改变现状。那些将他们父女二人驱逐到这个偏远小站的人,之所以没对他们赶尽杀绝,并非出于怜悯,而是出于邪恶的捉弄。他们相信,父女俩在这儿连一个星期也撑不过去,但父亲凭借意志和坚忍,一撑就是好几年。那些人对他们既敌视又鄙夷,但偶尔也会接济他们一下,当然,并非无偿的。
在远征的间隙,难得有珍贵的闲暇,父女俩会围坐在一小堆暗弱的篝火旁,父亲会给萨莎讲从前的事。还在几年前他就想通了,自己已经时日无多,没必要再自欺欺人了。所幸,往事是任凭谁也无法从他生命中夺去的。
父亲说:“从前,我的眼睛跟你的一样,也是天空的颜色。”萨莎总感觉,自己记得那些日子。那时父亲的甲状腺还没有肿大,他的眼睛也还没有失去光彩,和她的眼睛一样明澈。
父亲所说的“天空的颜色”,当然是指他记忆中的那片蔚蓝色天空,而非如今每天夜里上到地表时,笼罩在他头顶的那片暗红色天空。他已经足足二十年没见过白昼了,而萨莎则只在梦里见过,但谁敢肯定,她梦里见到的天空是不是那个样子呢?就好比一个天生的盲人,他梦里的世界会和常人一样吗?再者说,他们到底会不会做梦呢?
****
当小孩子们闭上眼睛时,会觉得黑暗笼罩了全世界,会以为周围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看不见东西了。而置身于隧道的成年人就像这些小孩子一样弱小而天真。他们手里把玩着手电筒,自诩光明与黑暗的操纵者,殊不知,即便周遭最无法穿透的黑暗里也有可能隐藏着很多双眼睛。自从遭遇了那些食尸者之后,这个念头就再也挥之不去了。“别想了。”荷马劝自己,“想点别的吧。”
真奇怪,猎人怎么会不知道纳希莫夫大道站有什么东西呢?当队长两个月前出现在塞瓦斯托波尔站时,所有哨兵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大块头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了北部隧道里所有哨卡的?好在上校没向值班人员追问此事。
如果他没走纳希莫夫大道站,那他是怎么到塞瓦斯托波尔站的呢?其他出入地铁站台的通路早就被切断了。久已荒废的卡霍夫卡站也可以排除,由于某种众所周知的原因,那里的隧道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一个生物了。切尔坦诺沃站吗?也不可能,纵然是这样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也绝无可能单枪匹马突破那个被诅咒的车站;再说,想要到达那里,只能取道塞瓦斯托波尔站。
排除了周边四个方向,荷马只能设想,这个神秘来客是从地表潜入塞瓦斯托波尔站的。尽管通往地表的所有出入口都被严密封锁并昼夜监视,但是……他完全有可能,比方说,打开封闭的通风竖井。反正塞瓦斯托波尔站人打死也想不到,在那些被烧为灰烬的预制板居民楼里还会有智能生物,能够切断他们的报警系统。
地表那些星罗棋布的居民小区,早在二十年前就被坠落在城市的核弹头碎片辐射污染,人类居民或死或逃,无一留存。如今,那里已经被丑陋可怖的物种占据,新的主人设立了新的秩序。人类已经再没机会夺回失地了。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突然偷袭,搜罗尚未彻底腐烂的一切有用之物,在原本属于自己的住宅进行仓促而可耻的劫掠。穿上辐射防化服的潜行者上到地表,第一百次地毯式搜索附近的预制板楼房的残骸,但从不敢对新住民发起正面战斗。他们能做的无非是狠狠射上一梭子子弹泄愤,然后立即躲进沾满老鼠屎的房间里,瞅准时机向通往地底的救命坡道紧急撤退。
莫斯科的老地图早就失去了一切现实意义:原先动辄堵车数公里的主干道,如今也许是一条深深的鸿沟,也许是一片黑黢黢的莽林;居民住宅楼也许变成了烂泥塘,也许变成了一片焦土。即便最勇敢无畏的潜行者也顶多敢在本站台一公里范围内探索地表,其余潜行者的活动范围比这还要小得多。
位于纳希莫夫大道站之后的纳戈尔诺站、纳加金诺站和图拉站,都没有通往地表的出口,那里的居民也没有胆量出入地表,这些站台上方的地表区域一片荒芜。荷马想不通,那里怎么可能会冒出个大活人来。但不管怎样,荷马仍然愿意相信,猎人正是从地表潜入他们站台的。
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可能性。这个念头不由自主地钻进了荷马这个无神论者的头脑里。猎人的黑色剪影几乎足不点地向前飞掠,荷马气喘吁吁,勉强跟上。
——难道,他来自更深的地底?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阿赫梅特压低声音,以免被走在前面的队长听见,“我们来得不是时候。你应该相信我,我护送商队来过这儿无数次了。纳戈尔诺站今天不适合去……”
那些平日里杀人越货,闲时在远离环线的偏远小站安营扎寨的一小撮匪帮,已经很多年不敢打塞瓦斯托波尔站商队的主意了。只要一听到齐刷刷的钉了铁掌的皮靴声,宣告着重步兵的靠近,他们就慌忙夹着尾巴让路,唯恐避之不及。
因此,塞瓦斯托波尔站商队的失踪肯定不是这些流寇所为,也不会是因为纳希莫夫大道站的那些食尸者。塞瓦斯托波尔站的护送队训练有素,悍勇无畏,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合拢成一只铁拳,将一切有形的威胁消灭在猛烈的火力中。在从塞瓦斯托波尔站至谢尔普霍夫站的整段线路上,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无可匹敌的隧道主宰——假如没有纳戈尔诺站的话。
尽管纳希莫夫大道站的噩梦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但无论是荷马还是阿赫梅特,都丝毫没有感觉到轻松——同样因为纳戈尔诺站。这个站台既简陋又难看,毫不起眼,却成了很多麻痹大意的漫游者的终点站。那些偶然造访邻站——纳加金诺站的可怜人,提心吊胆地缩成一团,尽量远离通往纳戈尔诺站的隧道口,以为这样就能侥幸逃过一劫……但那些在南部隧道出没的恶魔,为了捕获适合口味的猎物,从来不会在意这段距离。
在通过纳戈尔诺站时,只能寄希望于运气,因为这个车站不遵守任何规律。有时它会大发慈悲,放你通行,只用那些骇人的血掌印吓唬吓唬你,它们被烙在墙上或者槽纹铁柱上,似乎有人绝望地想要爬到高处逃命。但仅仅几分钟之后,下一拨过路者也许就会被迫留下新的血掌印,能有一半人逃出生天就谢天谢地了。
这个站台从不餍足,它神秘莫测,通吃一切。对于附近所有站台的居民而言,纳戈尔诺站便是命运主宰的化身;而对于从环线往返塞瓦斯托波尔站的人来说,纳戈尔诺站同样是最严峻的考验。
“单是纳戈尔诺站,未必能干成这件事。”和众多迷信的塞瓦斯托波尔站人一样,阿赫梅特在提及这个站台时,总会将其等同于有生命的活物。
荷马也正在思忖这个问题,便随口附和道:“就是,商队和那些搜救队这么多人,一下子都吞了,还不得撑死?”
“别瞎说!”阿赫梅特被荷马亵渎的话吓坏了,恨不得给这个没轻没重的老头儿来上一个脖儿拐,“吃掉你绰绰有余!”
荷马咽下了侮辱,没有吭声。他根本不相信纳戈尔诺站会听到他们并记恨在心,至少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绝对不会……迷信,全是迷信!地底世界的各路神魔太多了,想全部顶礼膜拜根本不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冒犯到谁。对于这一点,荷马早就不再纠结了,而阿赫梅特却不这么认为。
阿赫梅特把手探到粗呢上装口袋里,摸到一串用圆头手枪弹壳穿成的念珠,一边转,一边念念有词,为荷马的亵渎向纳戈尔诺站祈求原谅。可惜,站台似乎听不明白他所说的,又或者此时请罪为时已晚。
猎人的超自然感觉似乎捕获到了什么信息,将戴着手套的大手一摆,放缓了速度,悄无声息地蹲下身去。
“那边有雾,”他随口说着,用鼻孔吸了一口空气,“那是什么?”
荷马跟阿赫梅特对视一眼。他们两个都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狩猎正在进行中。想要活着通过纳戈尔诺站,除非上帝和魔鬼同时庇佑。
“怎么说呢,”阿赫梅特不情愿地开了口,“那是它呼出的气……”
“它是谁?”队长漫不经心地问着,将背包从肩头抖落,大概想在自己的小型军火库里寻找合适口径的武器。
“纳戈尔诺站。”阿赫梅特以极低的声音回答。
“走着瞧。”猎人鄙夷地撇了撇嘴。
就在这一瞬间,荷马恍惚觉得,队长那张丑陋的脸上闪过一丝兴奋。但这只是光影造成的错觉,事实上那张脸仍跟往常一样,如同石刻。
又行进了一百米左右,荷马和阿赫梅特也看见了:一股股湿重的淡白色烟雾贴着地面朝他们爬过来,先是舔住了他们的皮靴,接着抱住了他们的膝盖,随后又没过了腰际……他们仿佛正缓步走入一片冰冷漠然的幻影之海,踩着充满欺骗性的缓慢斜坡,每走一步就陷得愈深,直至混浊的海水完全没过头顶。
能见度极低。手电筒光线被这诡异的迷雾吞噬,如同苍蝇被缚在了蛛网上。光束只能勉强突围到几步开外,随后便成了强弩之末,跌落在虚空之中。声音的传播同样异常艰难,像被蒙在羽绒被子里一样。就连动作都变得更加吃力,好像不是走在枕木上,而是跋涉在河底的淤泥中似的。
呼吸也变得十分沉重,但不是由于湿度过大,而是由于空气中夹杂着一股呛鼻的邪味儿。荷马极不情愿地把它吸入肺里,随后涌上一股摆脱不掉的感觉,仿佛这真的是某个庞然大物的呼吸——它将空气中的氧气一吸而光,全部换成了自己有毒的恶气。
为谨慎起见,荷马戴上了防毒面具。猎人瞟了一眼老人,也将大手探入肩下的粗麻布袋,掏出一个橡胶面罩,套在普通面罩外面。只有阿赫梅特一个人没有防毒用具,只好再次用胳膊肘挡住了口鼻。
队长又一次停住脚步,将自己的残耳转向纳戈尔诺站方向,但越发稠密的白色雾瘴妨碍了他,让他没法分辨从站台断断续续传来的声响,从中组织起完整画面。那声音听上去仿佛某辆满载货物的列车在不远处被掀翻,又像是某种生物在以低得过分的音调发出长长的喟叹,又或者是某只巨手将墙边的钢筋管道拧成了麻花。
猎人像要甩掉脸上的泥浆一样猛一甩头,麻利地将手里的短自动步枪换成了双弹匣带枪榴弹的AK自动步枪。
“终于来了。”猎人含糊不清地说。
尚未来得及察觉,他们已经进入了站台区域。纳戈尔诺站被猪奶一样浓稠的迷雾湮没了,荷马透过蒙着水汽的玻璃眼窗察看着站台,感觉自己像个蛙人,潜入了一艘沉没的远洋巨轮。
站台墙壁上的浮雕装饰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相似度,那是用模压方式刻在金属上的海鸥造型,看上去更像是夹在岩层中的古生物化石。“变成化石——这就是人类及其艺术创作的必然命运。”荷马脑海中闪过这样的念头,“只是,会有人挖掘吗?”
环立四周的海市蜃楼在流动,在颤抖。其中不时地隐约闪现一些黑色形体,乍一看去,像是扭曲变形的车厢和锈迹斑斑的值勤岗亭,随后又觉得像是长满鳞片的庞大身躯和神秘怪兽的巨大头颅。荷马想想都觉得可怕:盘踞在这艘失事二十余年的远洋巨轮里的,究竟是什么怪物?关于纳戈尔诺站他耳闻已久,但正面遭遇还是头一回……
“它在那儿!右面!”阿赫梅特惊叫着,拽了拽荷马的衣袖。
话音未落,便爆出一声被自制消音器压住的沉闷枪响。
荷马以风湿病患者最为忌讳的速度将身子猛然一拧,将手电筒循声刺过去。但变钝的手电筒光束只照出一小块铁皮棱柱。
“后面!柱子后面!”阿赫梅特边喊,边打出一个短点射。
但他的子弹仅仅击碎了站台墙壁上残存的大理石贴面。阿赫梅特在流动的雾瘴中捕捉到的那个未知身形,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下完蛋了……”荷马心想。
就在这时,他的眼角余光似乎扫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庞然大物,蜷曲在对它而言过于低矮的四米高的站台顶棚之下。较之于庞大身形,它的动作敏捷得不可思议,从雾瘴中探出身形,旋即又退回雾瘴之中,荷马都没来得及将自动步枪对准它。
荷马仓皇无助地四下寻找队长,却哪儿也看不见他的身影。
****
“没事……没事……别怕……”父亲每说两个字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但仍勉力安慰着女儿,“你知道吗……地铁里有些地方,人们所面对的比这要可怕得多……”
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但那笑容看上去很骇人,像是颌骨从颅骨上脱落了一般。萨莎微笑着回应,抹了烟黑的颧骨上却淌过一颗明亮的泪珠。不管怎么说,父亲总算醒过来了,在他昏迷的这漫长的几个小时中,她已经什么情况都设想过了。
“这次非常不顺,原谅爸爸。我打算走到汽车房那儿,但那儿有点远。我找到了一个还好着的不锈钢门锁,砸不开,我废掉了最后一发子弹。本指望里头能有汽车、零配件什么的。进去一看,空的,什么都没有。空的你锁它干什么,浑蛋!刚才那一枪动静太大了……我拼命祷告,求上帝保佑谁也别招来。出来一看,围了一群野狗。我心说,完了,这下完蛋了。”
父亲合上眼皮,不作声了。萨莎慌了,忙抓住父亲的胳膊,父亲没睁眼,只微微摇了摇头——别担心,我没事。他完全没有力气说话,但他想对女儿解释,自己为什么会两手空空地回到家里,想请她原谅,这个星期他都站不起身子,他们要饿肚子了。但没等说完,就又昏睡过去了。
萨莎察看了父亲受伤的小腿上缠的绷带,已经被温热的黑血浸透了。她给父亲换上新的绷带,然后站起身,走到老鼠窝前,打开窝门。小老鼠犹疑地向外张望,本想藏起来,但终于还是给了萨莎一个面子,跑到外面来舒展筋骨。老鼠的敏觉是不会错的,眼下隧道里平安无事。萨莎放了心,走回父亲身边。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还会继续远征的。”她对父亲低声说,“你肯定会找到一个车库,里面会有一辆完好的汽车。我们一起开着车,离开这里,走到十站地、十五站地以外,找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车站,重新开始。那里不会有人排挤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地方的……”
她向父亲复述的这个美好的童话故事,父亲曾经给她讲过无数遍。如今,当这个支撑父亲信念的故事从自己口中讲出时,她对它的信仰增强了一百倍。她一定会治好父亲的伤,让父亲康复的。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能找到一个没人挤对刁难他们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将过上幸福生活。
****
“它在那儿!那儿!它在盯着我!”
阿赫梅特的尖叫中充满难以形容的恐惧,仿佛他已经被捉住,正在被拖走似的——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尖叫过。自动步枪的弹匣又打光了。阿赫梅特一改往日的镇定,浑身哆嗦着,手忙脚乱地更换新弹匣。
“它选中了我……我……”阿赫梅特喃喃自语。
不远处什么地方响起了另外一支自动步枪的噗噗声,停顿一秒钟,又开始噗噗噗,有节奏的三发连射——是猎人,他还活着!也就是说,他们还有希望。枪声忽远忽近,很难确定有没有射中目标。荷马竖起耳朵,期待听到怪物负伤之后暴怒的咆哮,但终究未能如愿。站台重新陷入令人压抑的死寂,那神秘莫测的怪物要么是钢筋铁骨,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形体。
在月台另一端进行的战斗十分诡异,时而猛射,时而哑火,仿佛队长正陶醉于跟幽灵的缠斗,完全不顾及部下的生命安危。
……荷马浑身上下的皮肤、头顶、脖颈上的每一根寒毛,都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一种目光的压迫,那目光冰冷而极具威慑力,让他忍不住想要抬眼望去。漫长的几个瞬间之后,他终于再也压制不住这种不祥的预感,深吸一口气,缓慢而僵硬地抬起头……
在他头顶高处,透过雾瘴,从车站顶棚垂下一个头颅。那头颅如此巨大,以至于荷马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那是什么东西。巨兽的身体仍然隐藏在站台的雾瘴之中,只探出一只脑袋,微微摇晃着,高悬在渺小人类的头顶上方,看着他们摆弄可笑的玩具枪,却并不急于发动攻击,似乎想让他们多活一会儿。
老人被吓傻了,顺从地跪倒在地,自动步枪从手中滑落,掉在铁轨上,发出可怜的叮当声。阿赫梅特扯破喉咙嘶喊起来。巨兽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峭壁般庞大的黑色身躯填满了整个视野。荷马闭上眼睛,准备受死。他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一个遗憾,他的意识完全被一种痛苦的思绪占据:“没写完……”
就在这时,一枚枪榴弹爆炸了,爆炸波在耳边炸裂,震耳欲聋,只听见绵延不绝的尖细鸣音,烧着的肉块纷纷坠落。阿赫梅特率先回过神来,一把抓住老人的后脖领子,拽起来就跑。
二人没命地朝前跑,无数次绊倒在枕木上,无数次立刻爬起,根本觉不出疼。他们抓紧彼此的手,因为在这惨白的迷雾中,一臂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他们逃得如此绝望,仿佛追赶他们的不仅仅是死亡,而是比死亡更可怕一千倍、一万倍——那是没有轮回的彻底消亡,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毁灭。
看不见的、几乎也听不见的怪物阴魂不散地紧跟在一步开外,却并不急于攻击,好像在戏弄自己的猎物,故意让他们心生获救的幻想。
墙壁上破碎的大理石贴面终于变成了隧道的弧形拼板,他们从纳戈尔诺站逃出来了!守护站台的巨兽,仿佛被与站台等长的锁链拴住了,停止了追杀。但现在还不能停下……阿赫梅特走在前面,摸索着墙壁,在前方开路,不停地催促落在后面、大口喘气的荷马。
“队长怎么办?”荷马哑着嗓子问,边走边把令人窒息的防毒面具扯下来。
“走到前边雾散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等等他。很快就到了!也就还剩下二百米……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走出雾瘴,走出雾瘴……”阿赫梅特像念咒语一样重复着,“我来数步子……”
过了二百米,三百米,笼罩周身的雾瘴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要是这雾瘴已经蔓延到了纳加金诺站怎么办?”荷马想,“要是它已经吞没了图拉站和纳希莫夫大道站怎么办?”
“不可能啊……不会的……就快到了……”阿赫梅特第一百次这样嘟囔着,突然停在原地。
荷马收步不及,一头撞在他身上,两人双双倒地。
“路走到头了……”阿赫梅特怔怔地摸着枕木、铁轨、潮湿粗糙的混凝土地面,似乎害怕地面也会背信弃义地从脚底消失,就像原本在前方延伸的隧道一样。
荷马闻言吃了一惊,连忙伸手在周边摸索,过不多时,摸到一块弧形拼板,抓住,小心地站起身,如释重负地喘了口气:“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咋了?”
“对不起……”阿赫梅特如梦初醒,难为情地说,“你知道吗,刚才在车站……我以为我永远也出不来了。它那样地盯着我看……盯着我,你明白吗,它决定带走我。我以为自己要永远留在那儿了……连葬礼都不会有……”
这番话令他很难启齿,犹豫了好久才说出来。他为自己刚才女人似的号叫感到羞耻,想为自己辩解,但他知道,这种事越描越黑。
荷马摇摇头:“得了。我都被吓得尿裤子了,那又咋了?走吧,这回应该真没多远了。”
索命的厉鬼已经停止了追杀,可以喘口气了。再说,他们也实在跑不动了,只能摸着黑扶着墙壁,一步一步脱离险地。最可怕的已经被甩在后面了,尽管雾瘴还不打算退去,但凛冽的隧道穿堂风迟早会将它咬死,撕碎,拖进通风竖井。他们迟早会逃出生天,然后等候耽搁在后面的队长归队。
事情来得竟然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快——莫非迷雾中的时间和空间都会变形?——墙边出现一道竖着的铁梯,那是通往月台的。隧道的浑圆剖面被方形剖面所取代,铁轨之间开始出现一些凹槽,那是为不慎从月台坠落的乘客预备的临时避难所。
“看那儿……”荷马不由得欢呼,“好像是站台!站台!”
“喂!有人吗?”阿赫梅特用尽全身力气高喊,“兄弟们!有人吗?”喊完,阿赫梅特突然爆发出一阵兴奋狂喜的大笑。
发黄暗弱的手电筒光线从雾气弥漫的黑暗中照出墙壁上剥落的大理石贴面,纳加金诺站的彩色马赛克却一块都看不见,贴着石砖的圆柱也看不见。这是怎么回事,难道……
得不到回应的阿赫梅特仍在呼喊,狂笑。他们大概是被吓昏了头,在雾瘴中跑得过远了,跑到了另外一个站台,但这完全不能影响他死里逃生的狂喜。而生性谨慎的荷马却用手电筒在墙上探来探去,不安地寻找着什么,心中的疑虑吓得他浑身发冷。
终于被他找到了:在布满裂缝的大理石墙壁上,有几个醒目的铸铁大字——
“纳戈尔诺站”。
****
她父亲相信,回归从来不是偶然的,一定是为了改变什么,纠正什么。有时,上帝会亲自拎起我们的后脖领子,将我们放回那个我们曾经偷偷溜走的地方,以便执行它的判决,或者给予我们第二次机会。
因此,父亲解释说,他再也没法从流亡途中回归从前的车站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报复,去斗争,去证明了。他也再不需要任何人的悔过。他说,在那段消耗了他的整个过往,甚至差点要了他的命的遥远往事中,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应得的。冥冥之中,他们注定要永远流亡,父亲自己不想回去纠正任何东西,而上帝绝不会注意到这个偏远小站。
在地表找到历经二十余年仍未朽烂的汽车,将它修好,加满油,逃出命运划定的怪圈——这场救赎计划,早就变成了父亲讲给女儿的睡前故事。
对于萨莎自己而言,还有另外一条出路,那就是进入中心地铁。当她按照约定日期来到贸易点,用勉强修好的电器、发黄暗淡的首饰、发霉的书籍交换食物和少量弹药时,经常会收到一些前景诱人的提议。
当轨道车探照灯照出萨莎那瘦弱的身板时,倒爷们总会相互使个眼色,吧唧着嘴,把她叫到跟前,对她做出许诺。但这个小妮子野得很,总是皱着眉头,一声不吭地瞪着他们,身体绷紧,背在身后的右手里抓着一把匕首。松松垮垮的男式工作服掩饰不住她的曼妙身姿;抹在脸上的污泥和机油使得她那双蔚蓝色的大眼睛变得更加明亮,逼得人不敢直视;浅色头发略微盖过了耳朵,是她自己用那把永远藏在右袖筒里的匕首随便修剪的;紧闭的嘴唇从不微笑。
轨道车上的人当即明白,光用肉骨头是无法驯服这匹小母狼的,于是便拿自由来诱惑她,但她从来没有回应过。他们怀疑小女孩是个哑巴,那样的话就更好办了。而萨莎心里却明镜似的:不管她答应什么,都绝不可能换回两张轨道车票,将父亲一起带走,父亲与太多人的恩怨纠缠是没法清算的。
这些戴着黑色军用防毒面罩、看不清面目、鼻音浓重的人,在她看来不仅仅是敌人,甚至是洪水猛兽。她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人性,找不到任何令她心存幻想的东西,哪怕是在夜梦中。
因此,她每次都将电话、电烙铁、电茶壶等物件放在枕木上,退到十步开外,静等买主自己取走货物,然后将一小包风干猪肉或者一小把子弹扔在车道上。他们扔子弹时故意一颗一颗扔得遍地都是,然后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看着她跪下双腿,将它们一一捡起。
然后,轨道车就慢慢悠悠地驶向真正的世界了,而萨莎只得落寞地回到家中,那里等待她的是堆积如山的破旧用具,一柄螺丝刀,一架电焊机,以及一辆被改造成直流发电机的破自行车。她骑在上面,闭上眼睛,飞出去好远好远,几乎忘记了它永远无法挪窝。是她自己拒绝赦免的——每每想到这点,她就又会增加些许力量。
****
这是什么鬼?!他们怎么又回到了这个站台?荷马惊慌失措,找不到合理的解释。阿赫梅特看见荷马手电筒光束照出的字,顿时呆若木鸡。
“它到底不肯放过我……”阿赫梅特用嘶哑的、低不可闻的声音说。
笼罩周身的雾瘴变得如此黏稠,二人几乎看不见彼此。无人造访时酣睡打盹儿的纳戈尔诺站如今苏醒过来了,湿重的空气以不易察觉的波动对二人的话语做出回应,形同鬼魅的影子在迷雾深处时隐时现。哪儿也看不见猎人的身影……血肉之躯不可能战胜怪影,等站台跟他玩腻了,便会用毒气将他熏死,生吞活剥。
“你走吧,”阿赫梅特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凛然对荷马说,“它要的是我。你不了解它,你不经常来这儿!”
“少说屁话!”荷马突然怒叱,嗓音之高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咱们不过是陷在雾里了,往回走!”
“咱们俩是走不掉的。如果你跟我一起,就算再怎么跑,到头来还是得回到这儿。除非你把我留下,自己一个人冲出去。走吧,算我求你了……”
“够了!走!”荷马一把抓住阿赫梅特的手腕,拽向隧道口,“一小时之后你就会感谢我了!”
“请你转告我——”
话音戛然而止,一股难以想象的可怕力量将阿赫梅特的手腕从荷马手中挣脱,猛然拽向上方,瞬间消失在迷雾与虚无之中。阿赫梅特连喊都没来得及喊,就这样没了,仿佛分裂成了原子,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悲愤哀惧的老人发出骇人的哀号,端起自动步枪,疯狂地原地转圈,将珍贵的弹药尽数射出。
突然,他的后脑勺遭受了致命一击,力量之大只有这里的恶魔才有可能拥有。
整个宇宙随之坍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