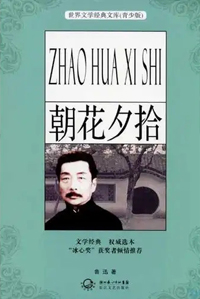鼠笼还躺在胖子将它从萨莎手上打掉的地方。笼门半开着,老鼠已经跑了。“让它走吧,”萨莎想,“老鼠也应该获得自由。”
萨莎没有别的选择,只得套上那个死胖子的防毒面罩。防毒面罩里似乎还残留着死人腐臭的呼吸,但萨莎已经足够庆幸了,幸好胖子在被射杀之前就把它摘了下来。
走到铁路桥中段,辐射再次激增。
她身上套着肥大的防化服,活像一只蟑螂幼虫在卵鞘里挣扎。而被胖子的大脸盘和厚嘴唇撑大的防毒面罩,却严丝合缝地贴在她脸上。萨莎使劲儿呼气,尽力赶走软管和过滤器里残存的空气,那是属于那个死人的。当她透过玻璃视窗向外看去时,她一直无法摆脱一种感觉,就是自己不仅钻进了别人的防化服,甚至还钻进了别人的身体。就在一小时前,这里面裹着的还是那个狩猎自己的冷酷恶魔。而现在,为了跨越地铁桥,她不得不自己化身恶魔,用恶魔的眼睛注视世界。
那些将他们父女二人驱逐到科洛姆纳站,并将其囚禁于此那么多年的人也长着这样的眼睛,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因为贪婪盖过了仇恨。难道说,为了混迹于这些人中间,萨莎自己也不得不戴上这样的橡胶面具,伪装成别的什么人,没有面孔、没有感情的人?假如这样做能将她的回忆清零,萨莎也并不反对,她愿意相信,没有什么不可挽回,一切还能从头开始。
萨莎愿意设想,这两个人的到来不是偶然,他们就是被派到这儿来救她的。但她很清楚,事实并非如此。她不知道他们为何带上了自己——为了寻开心?出于可怜?还是为了向彼此证明什么?在老人向她抛来的只言片语中,隐约能够察觉到一丝同情,但他每次跟自己说话都支支吾吾,还不停地看同伴的脸色,像害怕为此招致责难似的。
而他的同伴,在答应将她带到最近的有人居住的站台之后,再没有朝她这边看过一眼。萨莎故意放慢脚步,让他走到自己前面一点,好让自己看清他的背影。但他似乎能觉察到她的目光,每次都会将身子绷紧,脑袋猛然一晃,却从不回头,不知是有意纵容少女的好奇心,还是不愿意流露自己对她的注意。
这个光头男人的魁梧身躯和野兽习性,让胖子将其误当成了熊,也令萨莎感觉他像一头独狼。不光是他的块头或者宽厚肩膀,还有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一种力量,即使他瘦小干巴,那力量也会同样可触可感。这样的人几乎能够让所有人臣服,任何违拗者都将被立刻消灭。
早在萨莎抑制住自己对他的恐惧之前,早在她试图看清他、进而看清自己之前,一个在她内心深处刚刚觉醒、尚不熟悉的女人的声音就明白无误地向她宣告:她也已经臣服于他了。
****
轨道车以惊人的速度向前疾驰。荷马几乎没有感受到任何来自摇臂的阻力,全靠队长一力承担了。尽管荷马的双臂也在象征性地一起一落,但毫不费力。
敦实的地铁桥像一条巨大的蜈蚣从黑色黏稠的河面上空爬了过去。混凝土肉块从它的钢铁骨骼上剥落,步足发软无力,两条脊椎之一断裂坍塌了。这座地铁桥纯粹是实用主义的,千篇一律,和围绕在其周围的所有建筑以及整个呆板的莫斯科郊区一样,完全不具备任何优雅之美。但即便如此,行驶在桥上的荷马仍然兴奋地四下环顾,脑海中浮现出了圣彼得堡神奇的开合大桥,以及乌黑镂空的克里木大桥。
在地铁世界度过的二十余年间,老人总共只上过地表三次。每次他都尽量看到更多的东西。他试着复活自己的回忆,用被岁月混浊的眼睛审视故城,试图打开视觉记忆生锈的阀门,收集足够多的印象留待余生回味。万一他今后再没机会上到地表了呢?科洛姆纳站、河运站、暖营站以上的地表,都让他觉得美得不可思议,而在从前,老人和大部分莫斯科人一样,竟然对它们全都不屑一顾。
年复一年,他的莫斯科在不断老去,逐渐破碎,风干。荷马情不自禁地想要伸出手去,抚摸日渐腐朽的地铁桥,就像女孩在科洛姆纳站最后一次亲吻血已流干的男人一样。地铁桥,工厂的灰色墙角,人去巢空的居民楼……老人怎么也看不够。他想要触摸它们,以便确信,自己真真切切地站在它们中间,而非置身于梦境中。他想向它们告别,也许,这次真的是永别了。
能见度极低,银色月光无法穿透层层云翳,老人并不能将那些风景看得真切,多半都是靠猜。但这并不碍事,他本就擅长以幻想替代现实。
荷马完全放任自己的遐想,忘记了他要编造的传说,忘记了最近几个小时一直萦绕不去的那本神秘日记。他就像一个参观展览的小孩子,被形形色色的展品搞得眼花缭乱,好奇地四下张望,兴奋地自言自语。
而其他两人却似乎没有感到任何愉悦。队长脸朝前坐着驱动摇臂,只是偶尔停住动作,侧耳倾听从下方传来的声响。剩余时间里,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个遥远的、只有他一个人能看见的黑点。在那里,轨道将再次钻入地底。女孩则坐在猎人身后,双手紧紧抓住捡来的防毒面罩。
很显然,她在地表很不自在。当三人在隧道中行进时,女孩显得个子很高,但一来到地表,她整个人就蜷缩起来,仿佛钻进了无形的贝壳中,就连从胖子尸体上扒下来的肥大的防化服也无法使她看起来更高大一些。对于桥上呈现的美景她完全无动于衷,眼睛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身子前方的路面。
轨道车驶过了技术园站的废墟,这个车站是战争之前不久才仓促修建的,它之所以坍塌并非因为轰炸,而是因为时间的侵蚀。终于快接近隧道了。
在朦胧的暗夜中,隧道的洞口被深邃的黑暗掩盖。荷马感觉身上的防化服变成了真正的铠甲,而他本人则变成了中世纪骑士,正要闯入盘踞着恶龙的神秘洞穴。轨道车在寂静深夜发出的噪声于洞口处戛然而止,猎人下令丢弃轨道车,改为徒步。现在他们只能听到三位步行者窸窣的脚步声,偶尔交换的只言片语,以及撞碎在弧形拼板上的回声。但这段隧道的声响似乎有些反常,连荷马都清晰地感觉到了空间的封闭性,仿佛他们正穿过瓶颈,走进一个玻璃瓶中。
“前边堵住了。”队长证实了荷马的担忧。
队长的手电筒光束探到了瓶底:远处,封锁的气密门像一堵墙堵住了去路。被气密门截断的铁轨隐隐泛光,粗重的铰链上涂着褐色润滑油。门旁地面上还胡乱堆放着一些旧木板、折断的枯枝、炭火块,似乎有人不久前在这里烤过火。气密门显然处于使用状态,但看样子只出不入,因为外侧没有任何门铃之类的通报装置。
队长扭头盯着女孩:“这里一直是这样吗?”
“里面的人有时会出来,到我们那儿去,买卖东西。我想,今天……”
看她的样子像在辩解。难道她早就知道这里过不去,却隐瞒没说?
猎人抽出砍刀,用刀背照准气密门,敲锣似的猛捶了一下,但发出的并非尖锐的锣音,而是沉闷的鼓声。钢板太厚了,就算门后有人,这声音也未必传得过去。
猎人不死心地连敲了几下,却始终无人回应。
****
萨莎抱着一丝渺茫的希望,祈祷这两个人能够打开大门。她没敢告诉他们这扇门是关闭的——万一他们决定走另一条路,而把她扔在原地呢?
但大地铁里没有人在等待他们,而气密门是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光头检查了一下门扇,试图找到薄弱点或者暗锁,但萨莎知道,门这侧没有任何机关,只能从另一侧开启。
“你们在这儿等着,”光头对老人和女孩说,“我去那边侦察,看看第二隧道的闸门,找找通风竖井,”沉默片刻,他又补充道,“我一定会回来的。”说完,很快就消失了。
老人将四周散落的木板和枯枝拢在一处,点起一堆微弱的篝火。他一屁股坐在枕木上,双手探进背包,翻腾起来。萨莎在他身旁坐下,暗自观察。老人上演了一出奇怪的哑剧——不知是为她表演的,还是为了自己:只见他从背包里掏出一本破破烂烂、脏兮兮的笔记本,警惕地瞅了萨莎一眼,侧身挪到离她稍远的地方,垂下头去看本子,随即又以超乎年龄的敏捷跳了起来,蹑手蹑脚地朝隧道深处走了十步左右,确认光头真的走了,这才如释重负地走回原地,背靠着气密门,用背包隔住萨莎的视线,一头扎进本子里。
但这出哑剧还没演完:只见他满脸焦虑,嘴里含混地嘟囔着什么,随后摘下手套,取出水壶,朝纸页上蘸水;又读了一阵,忽然在裤腿上使劲儿搓手,懊恼地拍了一下脑门,又莫名其妙地摸了一下防毒面罩,连忙继续读下去。萨莎也不由得被他的焦虑传染了,抛下了自己的思绪,挪得近了些,但老人读得过于投入,并未察觉。
他那双黯淡的绿色眼睛里灌满了篝火的火光,透过视窗玻璃狂热地闪烁着。他像一个潜水者,时不时浮出水面,换口气,担心地朝隧道尽头的漆黑夜空张望,确认没有光头的身影,便又一个猛子扎进笔记本里。
她终于知道老人为何用水沾湿纸页了:有些纸页黏在一起了,得把它们揭开。看得出来并不好揭,有一回他突然低呼一声,像手指被割到似的,原来是不小心扯坏了一页。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发现女孩正疑惑地望着自己,微微一怔,整了整防毒面罩,但一言未发,直到全部读完。
他走到篝火旁,将笔记本扔进火堆。从始至终,他一眼也没看萨莎。直觉告诉女孩,问也白搭,老人要么不会说,要么不会说实话。再者说,眼下她还有更值得担忧的事呢。光头走了怕有一个小时了,他会不会把他们两个累赘给扔下了?萨莎朝老人身边挪了挪,低声说:“第二隧道也是封锁的,附近所有的通风井也全都堵死了,只有这一个入口。”
老人茫然地看了她一眼,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己所听到的,笃定地说:“他会找到办法进去的,他有魔法。”
老人不再言语了,过了一分钟,像是为了避免失礼似的问:“你叫什么名字?”
“亚历山德拉,小名萨莎。”女孩认真地回答完毕,又问,“你呢?”
“尼古拉……”老人边说边伸出手去,但还没等萨莎握住,又突然神经质地抽了回去,改口说,“荷马,我叫荷马。”
“荷马?真是有趣的绰号。”
“这是真名。”荷马郑重其事地说。
她该不该告诉他,只要他们把自己带在身边,门就永远不会开启?倘若只有他们两个,大门原本完全有可能是四敞大开的。是科洛姆纳站不肯放走她,它要惩罚她对父亲的背叛。她仿佛被无形的锁链锁着,无论跑出多远,都无法挣脱。科洛姆纳站已经将她抓回去过一次,一定还会有第二次……
这些想法和形象像一群吸血的蚊虻,被她赶得狠了,便暂避到一臂之外,但没过一会儿就又飞回来,围着她转啊,转啊,刺入她的耳朵、眼睛。
老人又问了萨莎些什么,但她没再回应,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耳朵里萦绕着父亲的声音,那声音一直在重复:“没有什么能比人命更宝贵。”这一刻,她真正地理解了父亲这句话。
****
图拉站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荷马来说这已不再是个秘密。真相比他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也可怕得多。然而破解这本日记之后,他才意识到更可怕的事情现在才刚刚开始。对于荷马而言,这本日记本变成了一个黑暗符咒,一张死亡车票,一旦抓在手里就再也摆脱不掉,哪怕将其烧成灰烬也无济于事。
除此之外,如今也有了更加确凿的证据,让他加重了对猎人的怀疑,尽管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在日记本里读到的全部内容,都和猎人的说法截然相反。猎人在撒谎,而且是有意为之。老人必须查清楚,猎人撒谎的目的何在,是否正当。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自己要不要继续跟他走下去,也决定这场冒险究竟会变成一首英雄史诗,还是一场噩梦般的、不留任何活口的血腥屠杀。
日记本上最早的文字是在商队顺利通过纳戈尔诺站,进入图拉站那天留下的,商队一路上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直至图拉站,隧道几乎全部是安静而空旷的。行进速度很快,这是好兆头。指挥官计划最晚明天返回。”已经死去的通信兵这样写道,“图拉站的入口无人把守,我们派出了侦察兵,但失踪了。”之后几个小时,他开始担忧,“指挥官决定所有人一起向站台进发,准备强攻。”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写道,“我们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向当地人了解了情况。情况很糟糕。发生了疫病。”紧接着他解释道,“站台上有几个人染上了……未知的疾病……”商队显然试图给病人医治,但“随队医生找不到解药”。他说:“看着像狂犬病……患者感觉疼得要命,无法自制……表现出了攻击性。”紧接着,“患者被疾病折磨得十分虚弱,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但麻烦在于……”接下来的几页偏偏粘在了一起,荷马只得蘸着水耐着性子将其揭开,“畏光,恶心,口腔出血,咳嗽,然后浮肿……变成……”后面那个词被重重地涂抹掉了,“如何传染尚不明确,空气?接触?”这已经是第二天的记录了,显然商队也被困在此处。
“为什么没有报告呢?”老人自问,随即想起,似乎在什么地方已经读到过答案,便向后翻了几页——“通信断了。电话没有声音。可能是敌特破坏。是被驱逐者在报复吗?疫病在我们来之前就被发现了,最早一批被感染者被撵进了隧道。是不是这些人切断了电话线?”
读到此处,荷马将视线抬离纸页,茫然地看着前方。就算电话线被切断了,为什么他们不返回塞瓦斯托波尔站呢?
“情况更糟糕了。病情发作之前会潜伏一个星期,但万一更久呢?离发病到死亡只有两个星期。无法确定谁被感染了,谁是健康的。什么药都不管用,无药可救。死亡率百分之百。”一天之后,通信兵记下了另外一则笔记,荷马之前已经读到过,“图拉站一片混乱。进入地铁的通道没了,汉萨封锁了,家回不去了。”隔了一页,他继续写道,“健康的人开始射杀感染者,尤其是那些具有攻击性的……设置了疫病隔离区……感染者反抗,要求释放他们。”接下来是简短、骇人的字眼,“人们相互撕咬……”
通信兵也很害怕,但护卫队有效地阻止了恐惧升级为恐慌。即便在致命疫病的病源地,塞瓦斯托波尔站的护卫队仍然严守铁律:“控制住了局面,封锁了站台,推举了指挥官。”荷马读道,“我们的人情况都还好,但毕竟现在还没过去多久。”
塞瓦斯托波尔站派出的搜救队也顺利抵达了图拉站,然后,自然也陷在这里。“人们决定留在这里,等疫病潜伏期过去,以免将病毒带回家……也许会永远留在这里。”通信兵绝望地写道,“陷入绝境,无人支援。请示塞瓦斯托波尔站,就会害死自己人……只好忍耐……多久?”
这么说来,与猎人在图拉站气密门旁对话的守卫也是塞瓦斯托波尔站人?难怪他们的声音荷马觉得那么熟悉:就在几天前,他们还一起抵御过来自切尔坦诺沃站方向的吸血蝙蝠!这些勇猛无畏的战士自愿拒绝返回,以免疫病传染自己的站台……
“通常是通过接触传播,但眼下看来,空气传播也有可能。不过,个别人似乎免疫。最初疫病暴发于两个星期之前,感染人数不多……但死亡人数越来越多。站台变成了停尸房。”通信兵匆忙写道,“下一个死的是谁?”写到这里,通信兵大概不禁发出了一声无助的哀号,但他很快便稳住了心神,继续写道,“必须采取行动,向站台预警。不必回到站台,只要找到电话线断口,接通站台就行!我去做!”
又过了一个昼夜,在此期间,通信兵可能一直在与指挥官交涉,跟其他战士争辩,与不断加深的绝望做斗争。通信兵想要传达给塞瓦斯托波尔站的所有信息,都被记录在了这本日记上:“他们不明白,站台会怎么想!我们已经被困了一个星期了。站台又派出了新的三人小组,他们也回不去了。接着站台会宣布总动员令,率大部人马强攻。所有前来图拉站的人,都会有生命危险。万一有人感染了,又跑回站台,那就全完了!必须预警,阻止强攻!可他们就是不同意,怕我偷跑回去……”
通信兵又一次试图劝说长官,但跟之前一样徒劳无功:“不放我去……都疯了。我不去谁去?必须跑出去。”
一天之后,他又写道:“我装作不再坚持,同意等待,去气密门旁执勤。我喊了一声,说找到电话线断头了,拔腿就跑。他们朝我背后开枪,我中了一弹。”
荷马翻过一页。
“我这么做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娜塔莎,为了儿子。我自己根本就没想过要活命,但只要他们能活下来,只要儿子……”写到这儿,笔尖从虚弱的指间滑落。这句话也许是后来才加上去的,因为纸张用完了,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再往下,被打乱的时间重新接上了:“纳戈尔诺站放我通过了,谢谢。我已经没有力气了。走啊,走啊。我昏了过去,睡了多久?不知道。这血是肺里头的吗?是弹伤,还是疫病?找……”弯曲的笔画延伸成一条直线,仿佛濒死者的脑电图,但他终于还是醒过来了,写完了这句话,“找不到断口。”
“纳希莫夫大道站。终于到了。我知道这里哪儿有电话。要通知站里的人……不可以!救救……娜塔莎……想你们……”通信兵的话越发不连贯,喷在纸上的血块也越来越多,“接通了。他们听到了吗?我就要死了。奇怪。我会睡过去。没子弹了。赶快死掉,趁那帮畜生……它们就在周围等着……我还没死,走开!”
日记本的最末一页似乎是提前写好的,字迹工工整整:“千万不要强攻!”落款是日记本主人的姓名,为这句话,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荷马感觉,在生命终止之前,通信兵来得及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还没死,走开!”
****
挤在火堆旁的两个人被沉重的寂静笼罩了。荷马没再去宽慰女孩,只是默默地用木棍翻挑着篝火堆,看着被打湿的日记本一点一点被火舌吞噬,静静等待着内心呼啸的暴风雨停息。
真是命运的捉弄。他之前是多么渴望破解图拉站之谜!当他发现这个日记本,想到自己将率先揭开纷繁复杂的全部谜团时,他是何等骄傲和得意!可现在呢?当一切问题的答案都摆在面前时,他却开始咒骂自己——好奇害死猫。
没错,当他在纳希莫夫大道站捡起那个日记本时,是戴着防毒面罩的,现在他同样穿着密闭防化服。可是,没有人确切知道疫病是如何传播的!
他以前真是个十足的大傻瓜,竟会以来日无多吓唬自己!没错,这的确鞭策了他,帮助他克服了懒惰和恐惧。但死神是最讨厌受人摆布的。如今,死神借由日记本对他宣判了死期:自感染到死亡总共只有两三个星期,就算一个月吧,可在这短短的三十天内他要做多少事情啊……
该怎么办?向自己的同伴坦承,自己感染了致命疾病,然后独自去科洛姆纳站等死——死于疫病,或者饥饿与辐射?但假如可怕的疫病已经感染了他,那猎人和这个姑娘肯定也逃不掉,毕竟他们跟他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特别是猎人,他在图拉站的气密门前还跟那些卫兵说过话,离他们那么近。
还是说,心存侥幸,不露声色,静观其变?当然,这并不仅仅为了苟且偷生,而是为了能够继续跟猎人历险,继续从中获取灵感。
要知道,假如说随着死亡日记被开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这个糟老头子、百无一用的地铁居民、曾经的助理司机、只能在地上爬的毛毛虫死去了,那么荷马——编年史作家、神话创造者、绚丽的蜉蝣才刚刚羽化而出。或许,他生来就是为了完成这部旷古烁今的悲剧的,问题仅仅在于,他能否在上天给他限定的三十天内将其付诸纸笔。
他难道有权利放弃这个机会吗?他难道应该独自躲起来,忘掉自己的传说,自愿放弃真正的不朽,也让所有同时代人都无缘这些传奇吗?哪个才是更大的罪过、更大的愚蠢——将瘟疫传遍半个地铁,还是烧掉自己的手稿,同时也焚毁自己?
作为一个虚荣而怯懦的人,荷马已经做出了选择,现在他需要做的,只是为自己的选择寻找支撑。躲在科洛姆纳站的墓室里,与两具尸体为伴,将自己也活活变成一具干尸,对他有什么好处?他可不是为了牺牲才生下来的。身陷图拉站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士们选择了自我牺牲,那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但至少,他们不必独自一人面对死亡……
再者说,就算他牺牲了自己,又能有多大意义呢?猎人他是无论如何都阻止不了的。就算他扩散了疫病,也纯属无心之举,而猎人早就心知肚明。难怪他坚决主张清除图拉站的所有居民,甚至包括塞瓦斯托波尔站的商队;难怪他还提到了喷火兵……
假如他们两个都已经感染,那么疫病不可避免地会在塞瓦斯托波尔站扩散开来。首先就是那些他们在返回后接触过的人——站长、上校、站长副官、叶莲娜。这就意味着,三个星期之后,站台就会群龙无首,陷入一片恐慌,随后,疫病就会吞噬其他所有人。
猎人呢,他何以确定自己没被感染呢?他又为何要冒着已经被感染的风险,坚持返回塞瓦斯托波尔站呢?荷马已经看清,猎人的行动并非下意识的,他在按部就班地实施某项计划。至少到目前为止,老人还没有打乱他的牌局。
如此说来,塞瓦斯托波尔站注定在劫难逃,而整个探险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但是,就算是为了能够回到家中,与叶莲娜相拥而死,荷马也不得不将自己的冒险坚持到底。光是从卡霍夫卡站到卡希拉站的通道就把防毒面罩给废掉了,而身上的防化服恐怕已经吸收了数十伦琴、数百伦琴射线,必须尽快脱掉它们。原路返回已经绝无可能了,该怎么办?
女孩睡着了,身子蜷缩成一团。篝火终于完全吞噬了感染瘟疫的日记本,烧光了最后一根枯枝,渐渐熄灭了。为了节省手电筒电池,荷马黑着灯坐在那里。
不,他必须继续跟队长走下去。但他会尽量避免跟其他人接触,将自己的背包连同包里所有东西全部扔在这里,销毁自己的衣物,以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风险……他将祈求宽恕,开启为期三十天的生命倒计时,他会每日不间断地写作,毫不懈怠。“事情总会得到解决的,”老人鼓励自己,“最重要的是跟定猎人,寸步不离。”
当然,前提是猎人还会出现……
距离猎人消失在隧道尽头的朦胧天光中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荷马嘴上安慰着女孩,自己心里其实也在打鼓,队长会不会回来找他们。
关于猎人知道得越多,老人就越看不懂他。老人既无法完全质疑他,也无法彻底信任他。他神秘莫测,全无正常人的情绪。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无异于听天由命。但荷马已经这样做了,再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寂静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密不透风了。透过它那坚硬的外壳,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啄壳而出,似有遥远的哀嚎,窸窸窣窣……那声音让老人联想起食尸者一溜歪斜的脚步,纳戈尔诺站幽灵巨怪的滑行,以及濒死者的呻吟……没过十分钟,老人再也挺不住了。
他“咔嗒”一声打开手电筒,当即被吓得猛一激灵。
在他两步开外,猎人正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盯着熟睡的姑娘。猎人抬手遮住一时难以适应的光线,平静地说:“门就要开了。”
****
萨莎梦见自己又独自一人留守在科洛姆纳站,等待父亲“散步”归来。父亲耽搁了,但她一定要等到他回来,好帮他脱下防化服,摘掉防毒面具,陪他吃饭。午饭早就准备好了,她完全没有其他事可做。她不敢从通往地表的大门前走开——万一父亲就在这时候回来了呢?谁来给他开门呢?她只好坐在门口冰冷的地板上,等啊,等啊,几小时过去了,几天过去了,父亲仍没回来,但她绝不会离开,直到大门打开……
她被门闩开启的叮当声吵醒了,那声音跟科洛姆纳站气密门发出来的一模一样。她笑着醒来了,是父亲回来了。她四下一看,立刻醒透了。
在迅速挥发的梦境中,唯一真实的只有沉重的铁门插销发出的响声。一分钟之后,门闩颤动起来,开始缓慢移动。逐渐开启的缝隙中射出一束光线,飘出柴油机的烟气。进入大地铁的入口开启了……
气密门被移向一旁,顶进卡槽,现出一条深邃的隧道,通往汽车厂站,继而通往环线。铁轨上停着一辆马达轨道车,发动机轰鸣着,车头亮着探照灯,车上坐着几名士兵。透过机枪瞄准镜,轨道车上的人发现了两个过路人,眼睛被车头灯刺得眯缝着。
“举起手来!”车上的人喝令。
萨莎学着老人的样子,顺从地举起了双臂。这辆马达轨道车正是每逢贸易日开到桥那边去的那辆,车上的人对萨莎的身世了如指掌。这个名字怪怪的老头马上就要后悔了,自己怎么会随随便便就带上了一个被铐在荒废站台的陌生姑娘,甚至都没有盘问清楚,她是怎么出现在那儿的……
“脱掉防毒面罩,出示证件!”车上的人又命令道。
萨莎一边摘下面罩,一边责骂自己愚蠢。没有任何人能够释放她,父亲的刑罚尚未赦免,而她与父亲是捆绑在一起的。她怎么会天真地以为,凭这两个人就能把她带到大地铁呢?她怎么会指望着在边界不会被人发现呢?
“喂,你!你不能进去!”车上的人立刻把她给认出来了,“给你十秒钟,立刻消失。这人是谁?他是你——”
“这是怎么回事?”老人莫名其妙地问萨莎。
“不要!别开枪!他不是!”萨莎急忙大喊。
“赶紧滚!”自动枪手冷冰冰地说,“不然我们现在就……”
“连女孩儿也要杀?”另一个声音犹豫地问。
“我说过了!……”自动枪手拉开了保险栓。
萨莎后退一步,眯起眼睛,短短几小时之内第三次做好了面对死亡的准备。只听见噗噗噗噗几声急促的低响。射击命令终究未能发出,萨莎等得心里发虚,微微睁开了一只眼睛。
柴油机仍旧突突突突冒着烟,瓦灰色的烟团从探照灯的白色光柱中飘过,但那光柱不知为何是射向顶棚的。现在,当探照灯光柱不再刺向萨莎的眼睛时,她终于看清了车上那些人。
所有人都像稻草人一样歪七竖八地倒在车厢里或者车旁的轨道上。双臂无力地垂下,脖子不自然地扭曲着,身体被射穿了。
萨莎扭过头,光头站在她身后,正拎着手枪,仔细察看已经变成了运尸车的马达轨道车,突然举起枪管,又一次扣动了扳机。
“好了。”他心满意足地嗡嗡说道,“扒下他们的防化服和防毒面罩。”
“为什么?”老人的面孔极度扭曲。
“换装,开他们的轨道车通过汽车厂站。”
萨莎怔怔地看着这个杀手,心绪复杂——既有恐惧,也有崇拜;既有厌恶,也有感激。他一出手就结果了三条人命,违背了父亲最重要的信条。但他这么做是为了救自己,救老人。他又一次救了自己,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她是否错将坚毅当成了残忍?
只有一点她确定无疑:他的无畏掩盖了他的丑陋。
光头第一个走近轨道车,开始从被消灭的敌人身上扒战利品。突然,他惊呼一声,像看见了魔鬼一样,慌忙从马达轨道车旁跳开,连连后退,低头盯着摊开的双手,嘴里不断重复着一个词:
“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