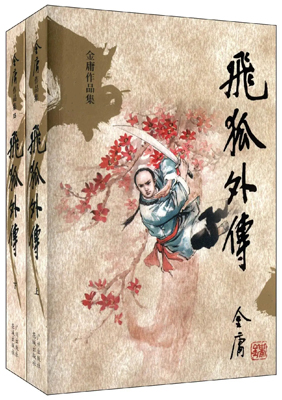科洛姆纳站距离地表很近,只有五十六级台阶,而帕维列茨站则要深得多。当萨莎沿着轧轧作响、布满弹痕的扶梯向上攀爬时,她几乎看不到扶梯的尽头。她的手电筒只能勉强从黑暗中照出被打碎的照明灯,生锈的广告牌上几张黯淡的面孔,以及拼凑成无意义话语的巨大字母。
她为什么要上去?为什么要上去送死?
但下面有谁会需要她呢?——不是作为还没写完的书里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
还有必要继续自我欺骗吗?
当她留下父亲的尸体,走出荒凉的科洛姆纳站时,她原本觉得自己正在执行她和父亲早就一起制订的逃亡计划。她将父亲的一部分带在自己身上,想至少以这种方式帮助他逃脱。但从那时候起,她便再没有梦见过父亲一次,而当她试图从想象中召唤出他的形象,好和他分享自己的见闻和感受时,他总是显得虚无缥缈,无声无息。父亲无法原谅她,也不稀罕这样的救赎。
父亲捡回来的那些书籍,在被拿去交换食物和弹药之前,每一本她都会先翻看一遍,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本旧植物学手册。里面的插图虽然只有一些暗淡发黄的黑白照片和铅笔画的简图,较之于其他一幅插图都没有的书,这本书自然成了她的最爱。而在所有的植物中间,她最喜欢的便是牵牛花。不,准确地讲,不是喜欢,而是觉得亲切,因为她在牵牛花身上看见了自己。她跟牵牛花一样需要支柱,以便爬到高处,够到阳光。
求生本能要求她必须找到粗壮的树干,好让她紧紧依附,拥抱,缠绕,但不是为了汲取汁液,而是为了吸收光和热。这是因为,她自身过于柔弱、纤细,无法抵挡风雨,若是独自生长,恐怕只能永远在地面匍匐。
父亲对萨莎说,她不应该依赖任何人,不能指望任何人。要知道,除了父亲之外,在那个被人遗忘的荒凉小站,她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指望,而父亲毕竟不可能永远陪她走下去。父亲不希望她长成一藤牵牛花,而是希望她长成一棵坚韧的青松,但他忽略了,这是违背女人天性的。
没有父亲,萨莎或许也能活下来;没有猎人,萨莎或许照样能活下来。然而,与另一个人的融合,在她看来,正是憧憬未来的唯一理由。那天她在轨道车上抱住猎人时,她感觉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新的支柱。她明知道信赖别人是危险的,依赖别人是可鄙的,但她仍然说服了自己,向猎人表白了。
萨莎想依附到猎人身上,而猎人却不愿意被她拖住后腿。她失去了支柱,并被踩进了泥里,她不愿再屈辱地继续寻找。他不是让她去地表吗,那有什么,去就是了。假如她在地表遭遇什么不测,罪过全在他身上,也只有他才能阻止她。
台阶终于走完了。萨莎来到了一间宽敞的大理石大厅,一部分铁皮棚顶已经坍塌了。透过远处顶棚上的窟窿,夺目的灰白色强光鞭打下来,光斑甚至射到了萨莎所在的角落。萨莎关闭手电筒,屏住呼吸,蹑手蹑脚朝前走去。
扶梯旁的墙壁上弹痕累累,说明人类曾经来过这里,但仅在几步开外,便进入了其他生物的领地。一坨坨风干的粪便,随处散落的森森白骨都在表明,萨莎正置身于某种怪兽的巢穴。
萨莎用手遮住眼睛,以免被强光灼伤,接着朝大厅出口走去。萨莎越靠近光源,她走过的那些角落里的黑暗就越浓稠,她的眼睛在适应强光的同时,被削弱了感知黑暗的能力。
大厅里到处是倾塌的岗亭、一堆堆的废铜烂铁和废弃的电气设备。她明白了,人类曾经将帕维列茨站的地表大厅当成了中转站,用来堆积从周边运来的战利品,直至更加强悍的物种将他们驱逐。
萨莎隐约感觉黑暗的角落里似乎有微弱的蠕动,但她总将其归咎于自己越来越差的视力。盘踞在那里的黑暗过于浓稠,她完全没能辨识出正在打盹的怪兽的轮廓,它们完全与废墟融为了一体。
穿堂风单调的呜咽声掩盖住了怪兽沉重的呼哧声。当萨莎意识到这个声音时,已经从微微蠕动的庞然大物身边走过了几步。她定住脚步,屏息凝神地听了片刻,朝一旁倾塌的售货亭望去,在其背后发现了一个奇特的隆起……
那个隆起的小山包在呼吸。周围其余的“土堆”也在呼吸,而她被围在中间。为了确认,萨莎““咔嗒”一声打开手电筒,将光束对准其中一个。苍白的光柱打在白色的皮肤褶皱上,顺着硕大无朋的躯干向下滑动,还没等移到尾部,萨莎就彻底被吓傻了。这正是在帕维列茨站差点杀死萨莎的白色巨兽的同类,而且比那头还大。
这些畜生似乎正在休眠,并没有注意到萨莎。但离她最近的一头突然醒转,很响地用歪斜的鼻孔呼吸着空气,动了起来……萨莎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忙收回手电筒,尽量不出声地从它身边逃开。但在这骇人的怪兽巢穴,每踏一步都万分凶险。而且,离扶梯越远,巨兽就越密集,就越不好下脚。
此时想回头已经晚了。萨莎只盼着这些怪兽不要醒来,把她从这里放出去,到外面碰碰运气,至于能否安全返回地铁她根本没有考虑。她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喘,甚至尽量停止思绪——万一它们能够觉察到人的思想呢?她极其缓慢地朝出口靠近。破碎的地板砖不时在脚下发出该死的声响,也许只要再踏错一步,这些怪兽就会被吵醒,瞬间把她撕成碎片。
但萨莎忽然想起,就在今天,她已经在休眠的怪兽中间走过一遭了……至少,这种奇特的感觉令她没来由地十分熟悉。想到这儿,她不由得呆立在原地。
萨莎知道,后脑勺有时也能感知别人的目光。这些怪兽虽然没有眼睛,但它们用来感知周围空间的那个器官,却比任何目光都更加可靠,更加顽固。
她不用回头也能知道,一头怪兽正死死地“盯”着她的后背,尽管她再怎么小心,还是惊动了它。
但她终于还是转过了头……
****
姑娘不见了,但那时的荷马万念俱灰,完全没有急着要去找她的念头。
通信员的日记本来还给他留了一丝幻想——疫病也许会绕开自己,但猎人残忍地剥夺了这最后的一线希望。当他跟苏醒过来的队长进行那场精心设计的对话时,他仿佛在为自己的死亡判决进行申诉,但队长却并不打算赦免他,事实上,他也没法赦免。对于荷马即将承受的结果,只能怪他自己。
他的故事只写满了十页纸,还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争分夺秒地压缩,塞入笔记本剩余的空白页。这已经不再单纯是愿望,更是职责。之前的短暂休整已经结束了,他翻开笔记本,打算从上次被医生的呼唤中断的地方继续写下去,但笔尖却不由自主地写下了之前反复思忖的那句话:
“在我死后,会留下什么?”
那些被困在图拉站的不幸的人,他们死后又会留下什么呢?他们也许已经绝望,也许仍然抱有希望,但无论如何都逃不过残忍的清洗。记忆吗?但事到如今,又有几个人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呢?
再者说,记忆也是个极不牢靠的坟冢。老人很快就不在了,他认识的所有人都会随他而去,连他的莫斯科也会随之化为乌有。
他现在在哪儿?帕维列茨站吗?站台上方的花园环路如今已是光秃秃一片,死气沉沉。在世界末日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装甲战车将其清除、封锁,以便救援队和救护车能够通行。大街小巷上的住宅东倒西歪……老人轻易便能想象出那里的景象,尽管他从来没从这个站台上到过地表。
但在战争之前他经常到这里来,他跟未来的妻子经常在这个地铁站旁的餐馆共进晚餐,随后去附近的影院看晚场电影。考驾照时浮皮潦草的付费体检,也是在这附近做的。另外,他还从这里的车站跳上电车,去夏天的树林里跟同事们一起享用烧烤……
他盯着方格纸,眼前却浮现出了车站前广场,沐浴在秋日的晨雾中,两栋楼房在雾气中若隐若现,那是风格浮夸的办公楼,他的一位朋友曾经在那里工作。更远处是一座豪华宾馆的尖顶,宾馆旁边就是昂贵的高档音乐厅。荷马曾经打听过票价,比他半个月的工资还多一些。
他看见甚至听见了蓝白相间的有轨电车,车里密密匝匝地挤满了乘客。而花园环路本身,喜庆地闪耀着成千上万的车头灯和转向灯,构成了一个闭合的灯串。还有不合时宜的雪,怯生生的,还未落到黑色沥青上便消融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看似杂乱无序,实则各自按着既定轨道在前进。
他看见了由斯大林式楼房构成的隘口,花园环路如同一条大河,缓缓从隘口流向广场。道路两侧是成百上千扇灯火通明的窗子。此外还有很多霓虹灯招牌和巨大的广告牌,遮住了丑陋的伤口,那里计划植入几层楼高的假体……
但计划被永远搁浅了。
他看着看着,逐渐明白,仅用言语根本无法描述这一幅雄伟画面。难道说,所有这一切,真的只剩下长满青苔、坍塌的墓碑了吗?
过了一个小时,三个小时,姑娘仍没回来。荷马坐不住了,找遍了整个通道,问遍了所有的摊贩和乐手,询问了汉萨卫队的队长。然而一无所获,姑娘仿佛凭空蒸发了。
荷马手足无措,只好又来到队长的病房门前。这是最后一个他能指望的人。他咳嗽一声,朝病房里面望去。
猎人躺在床上,艰难地呼吸着,眼睛盯着天花板。完好的右手从罩布下面露出来,握紧的拳头上带有新鲜的擦伤,伤痕并不深,却淌着脓血,弄脏了床铺,猎人却浑然不觉。
“你打算什么时候走?”猎人问荷马,但没有扭头看他。
“我,现在就可以。”老人结结巴巴地说,“那个……有件事……那个姑娘不见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得了吗……”
“我死不了,”猎人回答,“死并非最可怕的。收拾东西,我一个半小时之后就能上路。我们去多勃雷宁站。”
“我有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我得找到她,我想让她继续跟我们一起走……我需要她,你明白吗?”荷马焦急地说。
“我一小时之后出发,”猎人的口气不容置辩,“你走不走随便……她也是。”
“我完全想不出她会去哪儿!”老人痛心地叹了口气,“要是你知道的话……”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猎人语气平淡地说,“但单凭你是救不了她的。收拾东西吧。”
荷马不由得后撤一步,眨了眨眼。尽管他已经习惯于信任队长的第六感,眼下却不肯相信。万一他又在撒谎呢,万一他还是想摆脱多余的累赘呢?
“她对我说,你需要她……”
“我需要的人是你,”猎人把头稍微转向荷马,“而你也需要我。”
“为什么?”荷马声音极低,但猎人还是听见了。
“很多事情都取决于你。”猎人缓慢地眨了眨眼,但老人忽然觉得,冷酷无情的队长刚才向他使了个眼色,这让他霎时冒了身冷汗。
病床好一阵吱吱呀呀,猎人咬紧牙关,坐了起来。
“去吧,”他请求荷马,“抓紧收拾东西,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走的话。”
荷马没有立即转身走开,他捡起了那个孤零零躺在角落里的塑料香粉盒。盒盖上有几条裂纹,环扣脱落了,两半分离开来,那面小镜子被摔得稀碎。
老人猛然转向队长:“没她我是不会走的。”
****
无眼怪兽几乎整整高出萨莎一倍,它的头颅顶到了天花板,巨爪抵在地板上。萨莎见识过这些庞然大物闪电般的移动和攻击。它也许只需动动爪子便能抓住萨莎,一击毙命。
但不知为何,它并不急于出手。
开枪射击是毫无意义的,再者说,萨莎恐怕连端枪都来不及。于是,萨莎迟疑地向着出口后退了一步。怪兽发出一声不大的咕噜,朝姑娘这边晃了一下……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怪兽仍然待在原地,但“视线”却牢牢地锁定萨莎。
萨莎鼓足勇气,又撤了一步。又一步。她没有转过身去背对怪兽,以免暴露自己的恐惧,而是后退着逐渐靠近出口。怪兽像被施了魔咒一样,亦步亦趋地跟着萨莎,但一直保持一定的距离,像在护送萨莎一样。
直到离明晃晃的出口只剩下十来米,萨莎再也按捺不住,转身疾跑,怪兽咆哮一声,也向前突蹿。萨莎飞奔到外面,一下子被阳光刺得眯起眼睛,没头苍蝇似的朝前乱跑,忽然脚下一绊,跌在了粗糙坚硬的地面上……
她认命了,等着怪兽抓住自己,大卸八块。但怪兽不知为何放过了她。过了漫长的一分钟,又一分钟……周围一片寂静。
萨莎没敢睁眼,先从背包里摸出了从哨兵那儿买来的自制太阳镜,镜片由两个透明的绿色酒瓶底充当,用两个铁环箍住,拴在止血带上。萨莎将眼镜绑在防毒面罩外面,两个镜片刚好盖住玻璃视窗。
现在她可以睁眼了。她缓慢地睁开眼睛,起初凝神戒备,随后越来越大胆地环顾着周围这个陌生环境。
在她头顶上方是天空,真正的、明亮的、高远的天空。整个天空散发着绿幽幽的光泽,有些地方塞着些低低的云朵,有些地方则呈现出无底的深邃。
太阳!她看见了纤薄云层后面的太阳,圆圆的,如此光辉夺目,比任何一盏探照灯发出的光还要强烈数万倍,几欲将萨莎的太阳镜烧出两个窟窿。她吓得连忙移开视线。稍等了片刻,到底忍不住又用眼角瞟了一眼。照理说,太阳有什么的呢,不过是天上的一个刺眼的窟窿而已,有什么值得人崇拜的呢?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它充满诱惑,让人迷恋,令人激动。对于习惯于地底黑暗的眼睛来说,兽巢的门洞几乎同样刺目,萨莎忽然心念一动:太阳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个出口呢,能够通往一个永远不会有黑暗降临的地方?如果能够脱离地面、飞到太阳上去该有多好,就像她刚才从地底下钻出来那样。此外,太阳还散发出微弱的热量,像是活的一样。
萨莎站在石头荒野的中央,周围净是半坍塌的老建筑,黑洞洞的窗窟窿叠加了足有十层之多,那些楼房便是如此之高。它们多得不可胜数,拥挤在一起,彼此遮挡着,好奇地盯着萨莎看。高楼后面还有更高的楼在窥视,而在更高的楼后面是摩天大楼的身影。
真是不可思议,萨莎看到了这一切!尽管它们也同样带着傻乎乎的绿色,跟脚下的大地,跟身边的空气,跟疯狂的、闪耀的、深邃的天空一样,但现在,她看到了令人向往的远方。
尽管萨莎出生在地底,但她的眼睛并不是为黑暗而生的,无论她为了让它们适应黑暗付出了多少努力。夜里,站在地铁桥的断口处,她只能看见距离气密门几百米远的丑陋建筑,再往远处黑暗就变得过于浓稠,无法穿透了。
萨莎以前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每次想到这个问题时,她总会设想一个不大的昏暗蚕茧,两侧各有几百米远,在此之后便是世界的边缘,宇宙的尽头,绝对黑暗的开端。
尽管她知道,真正的地球要比这大得多,但她完全想象不出它的样子。现在她明白了,假如没有亲眼见过的话,是永远无法想象的。
奇怪的是,站在这无边无涯的空旷之中,她竟然一点也不害怕。以前,从隧道钻出地铁桥的断口处时,她总感觉自己像脱掉了铠甲,而现在她却感觉自己像小鸡钻出了蛋壳。在光天化日之下,任何危险都可以早早发现,萨莎有充足的时间躲藏起来或者准备防御。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羞怯的、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她感觉自己像是回家了。
穿堂风呜咽着吹过楼房间的缝隙,推着萨莎的后背,怂恿她去大胆探索这个未知的新世界。
事实上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想要重返地铁,她必须再次走进怪兽盘踞的建筑物,而现在它们已经全被惊醒了。建筑物出口处时不时便会有白色身形一闪而过,显然,它们十分畏惧阳光。但黑夜降临了会怎样呢?在天黑之前,假如她想看见老人绘声绘色地向她描述的任何东西,她必须尽量远离这里。
于是,萨莎鼓起勇气向前走去。
她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渺小。她无法相信,这些巨大的建筑是跟她一样高的人类修建的,他们建这么高的楼房干什么呢?也许,是末日战争前的几代人发生了蜕变,身量变小了吧——那是大自然在帮助他们准备适应未来逼仄的地下世界?而这些建筑物则是人类的远祖留下的遗产,那时的人类顶天立地,就和他们住的房子一样。
她来到一片宽敞的空地,这里没有楼房,地面上覆盖着坚硬而龟裂的灰色地皮。世界突然一下子变得更加广阔,在这里视线可以抵达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至于萨莎不由得心里发紧,脑袋发晕。
萨莎靠着覆满霉菌和青苔的墙壁坐下,抬眼望着高耸入云的钝角钟楼,开始想象这座城市生前的样子……
街道上——现在她所在之处无疑正是一条街道——应该漫步着高大、俊美的人类,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漂亮衣服,跟它们比起来,连帕维列茨站居民最好的衣服也显得寒酸、滑稽。在亮丽的人群中间,汽车往来穿梭,它们长得跟地铁机车一模一样,只是要小得多,只能容下四名乘客。
那时的楼房也不像眼下这么暗淡。窗洞不是黑黢黢的,而是镶着锃光瓦亮的玻璃。不知为何,萨莎还看见了数不清的小栈道,架设在不同的高度,将相对而立的楼房连接起来。
那时的天空也不像如今这样空旷,而是不疾不徐地游弋着无数巨大的飞机,低得几乎触到了楼顶……父亲曾经给她解释过,飞机在飞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扇动翅膀,但在萨莎的想象里,它们长着蜻蜓一样的翅膀,几乎是透明的,只是微微反射着绿莹莹的阳光。
还有,天上在下雨。
看起来不过是水从高处流泻而下,但感觉非比寻常。天上的雨水不仅洗刷了灰尘和疲惫——澡堂生锈的水管里流出的热水同样能够做到这些——还能净化人的内心,宽恕他们犯下的罪过。这神奇的沐浴能够涤荡心头的苦楚,令人焕然一新,重新获得活下去的愿望与力量,就像老人所说的那样……
萨莎如此热忱地相信这个世界,在她儿童般诚挚的恳求之下,这个世界竟然真的在周围搭建起来。她现在已经能够听到高空透明机翼的轻微颤动,人群七嘴八舌的喧闹,车轮的轧轧滚动,温热雨滴的滴答。她的耳畔不由得响起了此前在通道里听过的那段旋律,那旋律毫不违和地加入了周围的声响中……她的胸口突然一阵刺痛。
她跳起身,沿着街道中央,逆着人流跑去,绕过忙碌的微型机车,仰面去接那沉重的雨滴。老人是对的,这里的确如童话般美好,美得令人不可思议。只消将时间留下的铜锈和霉菌擦掉,过往便会重新熠熠生辉,就像荒废站台上的彩色马赛克和青铜雕饰一样。
她来到一条绿色的河流前,河上的桥梁如今已经断裂,她无法过到河对岸去。魔法消失了,那幅一秒钟前还栩栩如生、多姿多彩的图画,一下子变得苍白暗淡,破灭了。眼前重新出现了空旷、荒凉的古旧建筑,龟裂的路面,路边两米多高的荒草,前方一望无际的莽林——这就是那个美妙的奇幻世界剩余的全部。
萨莎忽然感觉无比委屈,因为她从未目睹那样的景象,因为她只能在死亡和返回地底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再没有衣着光鲜的巨人了……还因为,在这通往远方的宽阔道路上,除了她之外,再没有一个活人了。
天气好得出奇,晴朗无雨。
萨莎甚至不愿哭泣,现在最好干脆死去。
仿佛听到了她的愿望一样,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她头顶高处展开了翅膀。
****
假如逼他做出选择,他该怎么做?离开队长,放弃自己的著作,留在站台,直到找到失踪的姑娘为止?还是忘掉姑娘,追随猎人,将姑娘从自己的小说中抹去,再伺机寻找新的女主人公?
理智禁止荷马离开队长,否则他的远征还有什么意义?他怎能让自己和整个地铁冒如此致命的危险呢?他又怎能放弃自己的著作呢——这可是唯一能够补偿一切牺牲的东西,既包括已经付出的,也包括即将付出的。
然而,当他从地板上捡起那面被摔碎的镜子的那一瞬间,荷马意识到,不顾女孩的死活,径自离开帕维列茨站将是真正的背叛。而背叛行径,或早或晚,终将损害他本人以及他的著作。他已经永远无法将萨莎从自我记忆中抹去了。
不管猎人对他说什么,荷马仍然决心尽一切努力找到女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老人开始加倍努力地搜索,不时向路人询问时间。
去环线是不可能的——没有证件,她不可能进入汉萨。而通道下方的那排房间和病房,荷马则从头找到了尾,向每个路人打听有没有见过女孩。终于,有人说好像见过,穿着一身防化服……荷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一路寻到了扶梯底部岗哨。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她自己要上去的。我还让给她一副好眼镜呢。”哨兵懒洋洋地说,“你不能再上去了,就这我已经挨了班头的骂。这上面是怪兽的老巢,没有人会上去的。她起初跟我说的时候,我还觉得好笑呢。”他的眼珠瞪得足有手枪枪口那么大,滴溜乱转,就是不看老人,“你也赶紧回通道去吧,天马上就要黑了。”
猎人早就知道!他还说,自己救不了她。这么说,她还活着?……
荷马慌里慌张,跌跌撞撞地朝队长的病房跑去。他钻过低矮的暗门,踉踉跄跄地爬过狭窄的楼梯,门也没敲就闯了进去……
但房间里空荡荡的,猎人不见了,他的武器也不见了,只有散落在地板上的带有褐色血迹的绷带,以及孤零零躺在地板上的空的军用水壶。辅助用房里粗略清洗过的防化服也不见了。
队长就这样把老人抛下了,如同抛下了一条犯倔的老狗。
****
她的父亲一直坚信:人会收到各种预兆,只需要学会发现并解读它们。
萨莎一下子就愣住了。假如真的有谁想给她传达预兆,恐怕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富于想象力的了。
在断桥不远处,黢黑的莽林中凸显出一座古老的塔楼,浑圆的塔身,奇异的塔顶,是周边所有建筑中最高的。由于年久失修,塔身裂开了一道道深深的缝隙,严重倾斜。若非奇迹,这座塔楼恐怕早就倾塌了。
塔身密密匝匝地缠绕着牵牛花。牵牛花藤自然比塔身纤细不知多少,但它们的厚度和强度足以将快要分崩离析的塔楼维系在一起。这种神奇的植物螺旋地抱住塔楼,从主茎之外又探出无数支茎,支茎之外又生了很多细茎,合起来编织成了一张密密麻麻的巨网,将塔身牢牢箍住。
毫无疑问,牵牛花曾经也是那么柔弱和纤细,跟如今这株花藤上最柔嫩的幼芽一样,不得不紧紧依附在看似坚不可摧的塔楼上。若非塔楼如此之高,牵牛花也断然不可能长得这么粗大。
萨莎痴痴地看着牵牛花,看着被牵牛花拯救的建筑。对她而言,一切又重新获得了意义,她再次萌生了抗争的愿望。说来奇怪,她的生命中似乎什么也没改变,只是突然之间,如同一株牵牛花顶破了绝望的灰色土层,希望钻进了她的内心,转眼便郁郁葱葱。
就算有些事情她无法左右,有些行为她无法阻止,有些话她无法收回,但在眼下的故事里,仍有很多事情是她足以改变的,尽管她现在还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最重要的是,她重新获得了力量。
现在萨莎隐约猜到了,残忍的怪兽何以会放过她:是某个看不见的人用铁链锁住了怪兽,好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对此感激不尽。为此她愿意宽恕,愿意再次去证明、去争取,只要猎人能给她一个最最含糊的暗示。
斜坠的夕阳猛然熄灭,旋即再次亮起。萨莎抬起下巴,眼角余光扫到了一个迅疾的黑色剪影,从头顶上方一掠而过,霎时遮住了阳光,转瞬又消失在视线当中。
犀利的呼哨和嚎叫撕裂了空气,一个黑影如巨石一般劈头盖脸向萨莎压下来。在最后的一瞬间,本能促使萨莎扑倒在地,这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前所未见的怪兽张开翅膀贴着地面滑行了一段,振翅一拍,再次飞起,开始在半空盘旋,伺机重新发动攻击。
萨莎慌忙爬起身,抓起自动步枪,但随即便放弃了无用的抵抗。就算迎面打出一梭子子弹也未必奈何得了这样的飞兽,再说恐怕根本打不中它!仓皇间,萨莎扭头朝来时的方向跑去,忘记了大厅里还有一群无眼巨兽在等着她。
飞兽发出一声呼啸,再次俯冲下来。萨莎被不合身的裤子一绊,扑通摔倒,忙翻过身,胡乱打出一个短点射。飞兽吃了一惊,但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利用这赢得的几秒钟,萨莎爬起身,朝最近的楼房跑去。
半空中已经有两个黑影在盘旋,宽大的膜状羽翼沉重地拍击着空气。萨莎的计划很简单,后背紧紧贴在任何一栋建筑的墙壁上,这样的话,过于庞大和笨拙的飞兽便够不到她了,至于接下来……反正她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藏身。
她终于跑到了一栋建筑跟前,后背紧贴墙壁,祈祷着飞兽会放过自己。但她的算盘落空了,这些飞兽比她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两头飞兽一先一后降落在距离萨莎二十步开外的地面,收拢翅膀,不慌不忙地向她逼近。
萨莎绝望地射出一梭子子弹,非但没有起到恐吓的效果,反而激怒了它们。子弹像是卡在了飞兽厚重的兽毛上,丝毫没有伤到皮肉。走在前面的那头飞兽恶狠狠地冲着萨莎嘶吼,外翻的黑唇下面露出了钉子般锋利的獠牙。
“趴下!”
萨莎下意识地卧倒在地,甚至没来得及反应,这个遥远的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有什么东西在她近前爆炸了,冲击波的热浪令她浑身一震。紧接着第二声爆炸,随后响起飞兽狂暴的哀嚎和逐渐远去的翅膀拍击声。
她惊恐地抬起头,被呛得咳嗽着,挥掉飞扬的灰尘,四下环顾。离她不远处的路面上多出了一个新鲜的弹坑,溅满了黏糊糊的黑血,旁边散落着一只被烧焦的皮革状翅膀,周围还有几块被烤煳的肉。
从地铁入口大楼方向,一个身穿防化服的伟岸身躯,迈着坚毅的步伐朝萨莎缓步走来。
是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