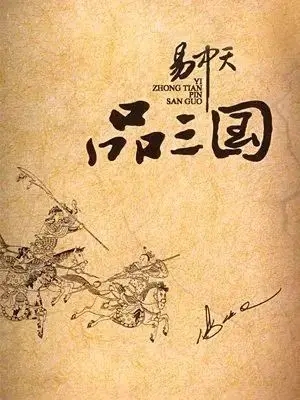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汇报!”
别的且不说,搞突击可是指挥官的拿手好戏。卫戍部队里流传着各种关于他的传说。这位前雇佣兵精通各种冷兵器,擅长在黑暗中隐身。很久以前,在他还没定居塞瓦斯托波尔站时,他曾经单枪匹马干掉过很多个敌人的岗哨,哪怕敌方哨兵有那么一丁点麻痹大意,就会让他钻了空子。
阿尔乔姆一下子跳起来,用肩膀把话筒夹在耳边,向指挥官敬了个礼,因为计数被打断而颇为懊恼。指挥官走到值日表前,对了对时间,在日期(十一月三日)旁边画了个标记—922,签了个字,扭头看着阿尔乔姆。
“无人接听……嗯,一个人也没有。”阿尔乔姆汇报说。
“没人回应?……”指挥官吧唧两下嘴,扭了扭脖子,把颈椎弄得嘎巴直响,“我不信。”
“您不信什么?”阿尔乔姆小心地问。
“我不信多勃雷宁站这么快就玩完了,难道说疫病已经蔓延到汉萨了吗?假如汉萨也被感染了,你知道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吗?”
“没准儿已经感染了呢?”阿尔乔姆不确定地说,“通信不是已经断掉了吗?”
“如果只是电话线断了呢?”指挥官低下头,用指关节在桌面敲打着。
“如果是电话线断了,那就和基地一样,”阿尔乔姆将头摆向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站的隧道方向,“电话拨过去什么声音都没有。可这里不一样,还有嘀嘀声,说明电话还能工作。”
“既然再没有人来过这里,那看来塞瓦斯托波尔站是放弃我们了,要么就是站台已经不存在了,多勃雷宁站也没了。”指挥官语气平淡,“听着,波波夫……如果那里一个活人都不剩了,那我们很快也就要死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的。那样的话,隔离也是白费劲。也许,我们该去他娘的,爱谁谁?啊?”他说着,又吧唧了两下嘴。
“绝对不行,必须隔离。”阿尔乔姆慌忙画了个十字,脑补了一个指挥官处置逃兵的画面:先照逃兵的肚子开一枪,然后宣读判决书。
“必须隔离。”指挥官若有所思地重复着,“今天又有三个人病了,两个当地人,一个我们的人,阿科波夫。阿克肖诺夫死了。”
“阿克肖诺夫?”阿尔乔姆艰难地咽了口吐沫,皱起眉头。
“他说他脑袋疼得厉害,撞铁轨死了,”指挥官的语气依旧平淡如水,“他不是头一个这么干的。你想想看,脑袋得疼到什么份上,才能逼得人跪在铁轨上,拿脑袋撞铁轨,一撞半个小时,硬生生把脑壳撞碎,啊?”
“是……”阿尔乔姆听着指挥官的描述,不由得一阵恶心。
“你有没有呕吐乏力的症状?”指挥官关心地问着,将手电筒光束打到他的脸上,“张开嘴,说‘啊’……好样的。所以,波波夫,你最好还是趁早接通多勃雷宁站,打听到一些好消息。比如汉萨已经有疫苗了,他们的医疗救护队很快就到,会把我们这些健康的人救出去,把感染者治好。我们不会永远困在这地狱里,很快就能回家去找各自的老婆,你去找你的加利娅,我去找我的薇拉。明白了吗,波波夫?”
“明白!”阿尔乔姆连连点头。
“稍息。”
****
猎人的砍刀没能承受住压在他身上的无眼巨兽的重量,齐根折断。刀锋砍入巨兽体内太深,甚至无法将刀抽出。猎人自己也被巨兽抓得遍体伤痕,已经昏迷了三天三夜。
萨莎一点也帮不上忙,但她仍然忍不住要来看他。至少得对他说声谢谢,哪怕他根本听不到。但医生不让萨莎进入猎人的病房,说病人现在需要静养。
光头为什么要杀死轨道车上的人,她并不确知。假如他是为了救自己,那她就应该原谅他。她很想这样认为,但她做不到。更接近真相的是另外一种解释:跟请求相比,光头更喜欢也更擅长杀戮。
但在帕维列茨站所发生的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毫无疑问,他就是来救萨莎的,甚至准备为她牺牲性命。这就是说,她并没有猜错,他对自己确实萌生了某种情愫?
当他在科洛姆纳站叫住她时,她原以为等待她的会是一颗子弹,完全没想到他会同意自己跟他们继续同行。而当她顺从地转过身时,立刻发现他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尽管他那张骇人的脸看上去依旧冷漠无情,但透过那双坚毅的黑色瞳仁的缝隙,却似乎有另外一个人在向外张望,一个对她感到好奇的人。
一个两次救了她性命的人。
她在想,要不要把那只银戒指送给他作为暗示,就像当年母亲对父亲所做的那样?但她又害怕光头猜不透。除此之外,她还能怎样表达谢意呢?也许该送他一把刀——他那把不是为了救她而折断了么。
当她站在武器摊前突然想到这个主意时,踌躇了许久,心里只盘算着该怎么送给他,而他会用怎样的眼神看着她,对她说些什么……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打算给杀手买武器,而他将用这把刀割断别人的喉咙,豁开别人的肚子。
在那一刻,他在她的眼里不是匪盗,不是杀手,而是英雄,是战士,但最主要的,是男人。除此之外,在她脑海里还萦绕着另一个没有说出口,甚至没想通透的念头:他的刀断了,而他自己则身负重伤,很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假如他的刀没断,或许他也会平安无事……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她终于还是买了。
眼下,她正站在他的病床前,把礼物藏在身后,耐心地等待他感受到自己,或者至少感受到刀刃的气息。光头身子猛一抽搐,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似乎在说什么,但终究没能醒过来——黑暗将他包裹得太紧了。
到目前为止,萨莎一次也没叫过他的名字,甚至没在心底默念过。在叫出声来之前,她低声念叨着,熟悉着,许久才鼓足勇气,大声地喊出口:
“猎人!”
光头顿时安静下来,倾听着这声遥远的呼唤——似乎声源在非常遥远的地方,传到他耳畔的只有依稀可辨的回声——但终究没有回应。萨莎又喊了一声,声音更大,语气更为坚决。在他醒来之前,她会一直这样喊下去。她要做他的隧道萤火。
走廊里突然传来一声惊呼,随即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萨莎连忙蹲下身,将刀放在猎人床头柜上,说:“这是给你的。”
萨莎的手突然被一只铁钳紧紧箍住,几乎将她的骨节捏碎。重伤的猎人抬起眼皮,眼球茫然无神地四处乱转,在任何东西上都不作停留。
“谢谢你——”萨莎说着,并没有试着挣脱。
“你在这儿干什么?!”一个白大褂上沾满油污的男护理员跳过来,对准光头扎了一针,光头的大手立刻软软地垂了下去。护理员一把拽起萨莎,咬牙切齿地骂道:“你怎么回事?他现在这种情况……医生不是说了吗……”
“你不明白!他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撑,你们给他扎针只能让他消沉……”
护理员使劲将萨莎朝门口一推,萨莎踉跄了几步,站定身,扭过头,倔强地盯住他。
“别让我在这里再看见你!……这又是什么鬼?”他发现了床头柜的那把刀。
“这是他的……我给他带来的。”萨莎结结巴巴地说,“要不是他……我早就被那些怪物撕成碎片了。”
“要是让医生知道了,被撕成碎片的就是我了!”护理员吼道,“够了,走吧!”
萨莎又迟疑了一秒钟,终于走向被药品麻醉的猎人,说完了那句话:“谢谢你救了我。”
她转过身,刚走出病房,便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我只是想……杀死它……那畜生……”
她猛然扭过头,但门“砰”的一声在她脸前关死,锁孔里发出钥匙转动的声音。
****
那把刀别有用途,荷马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听见姑娘是怎样呼唤仍在昏迷中挣扎的队长,那声音里充满了急切、柔情和哀求。他本想出面劝阻,却忽然一阵发窘,又打了退堂鼓。他的存在显然是多余的。眼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离开,别惊动萨莎。
也许她是对的,猎人真的需要她?毕竟,在纳加金诺站,猎人完全置同伴于不顾,任凭他们被怪兽撕碎,可为了她却甘愿牺牲。难道说,这个姑娘在他心目中真的占有一席之地吗?
荷马沉思着,沿着走廊走回自己的病房。一位男护理员慌慌张张地迎面跑来,肩膀狠狠地撞在了他身上,但荷马连看也没看一眼。他估摸着,萨莎这时应该在给猎人送刀了吧。
荷马回到病房,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包,捧在手里端详。没过几分钟,萨莎也闯了进来,满脸愤恨,茫然无措。她一下子扑倒在床上,脸冲着墙壁。荷马静静地等待,不确定暴风雨会不会降临。但萨莎只是默不作声,开始啃手指甲。荷马知道,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我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荷马从桌子后面绕出来,将那个纸包放在萨莎身边。
“为什么?”她又咬了一下手指,仍没从自己的壳里钻出来。
“送礼物还用为什么吗?”
“为了还人情。”萨莎确定地说,“要么是已经欠下的,要么是即将欠下的。”
“那就算我还你的人情吧。”荷马笑道。
“我对你有什么人情?”萨莎问。
“我的书啊。我已经准备把你写进去了。我得答谢你,我不想欠人情。好了,赶紧地,拆开看看。”荷马特意加入了一些玩笑的语气。
“我也不喜欢欠人情,”萨莎边说,边拆开纸包,“这是什么?哇哦!”
那是一个红色的塑料圆盒,揭开盖子,盒底被平分成两半,盖子内侧镶嵌着一面小镜子。那原是一个姑娘们用的随身香粉盒,一半装香粉,一半装胭脂,香粉和胭脂自然早就空了,但那面小镜子却还好好的。
“这可比水汪里照得清楚多了,”萨莎滑稽地鼓起眼睛,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影像,“你为什么要送我这个?”
“人偶尔需要从旁边看看自己,”荷马笑道,“这样有助于了解自我。”
“我需要了解自己什么?”萨莎警觉地问。
“有些人从来没见过自己的影像,一辈子都会把自己当成某个旁人。人的内心通常看不清自己,又不会有旁人提示,他们便会一直错下去,直到无意间碰到一面镜子。甚至当他们见到镜中的影像时,还经常无法相信,他们看见的正是自己。”
“不是自己还会是谁呢?”萨莎反问道。
“你来告诉我。”荷马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就是自己……嗯,一个小女孩。”为了确定,她先将半边脸转向镜子,然后另半边。
“是一个姑娘,”荷马纠正她说,“而且是个相当邋遢的姑娘。”
她又将脸来来回回扭了好几次,然后将目光射向荷马,像要问什么似的,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沉默片刻,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吐出一句将荷马呛得咳嗽的话:
“我丑吗?”
“说不好,”老人好不容易才绷住笑,“脸上有泥,看不出来。”
“就因为这?”萨莎剑眉一挑,“你们男人难道感应不到女性的美吗?非得一样一样给你们展示?”
“恐怕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男人才经常上当受骗。”荷马笑道,“化妆品能在女人脸上创造出真正的奇迹。但具体到你,需要做的不是肖像画的修复,而是挖掘。就好比一尊希腊雕像,单凭露出地面的脚后跟很难判断它的美丑。”说罢,他又宽容地补充了一句,“不过,基本可以断定是美的。”
“什么叫‘希腊’?”萨莎问。
“就是‘古老’的。”荷马有意逗她。
“人家才十七岁好吗!”萨莎抗议。
“这要等挖掘出来才能断定。”老人不动声色地走回桌旁,坐下,将笔记本翻到写满的最后一页,开始重新审视写下的内容,脸色渐渐凝重起来。
挖掘……或许,有朝一日,这个姑娘,他自己,连同其他所有人都会被挖掘出来。他曾经这样设想过:或许,几千年后,未来人类的考古学家在研究古代莫斯科的废墟时——那时莫斯科恐怕连名字都剩不下了——他们可能会找到一个入口,进入这座地下迷宫,那时他们会做何设想呢?他们也许会认为,这是一座庞大的集体墓坑。估计没人会相信,人类能够在地底生活。他们会断定,曾经高度发达的文明穷途末路,头领们被葬在这些墓坑中,他的家具、武器、奴仆和妻妾则作为陪葬。
他的笔记本还剩下八十多页空白。这些纸够他写完两个世界吗?——地表那个,以及地下这个?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萨莎碰碰他的胳膊说。
“嗯?对不起,走神了。”荷马擦擦额头说。
“那些古老的雕塑真的美吗?我是说,从前人们觉得美的,现在还一样美吗?”
“是的。”老人耸了耸肩。
“那将来也是喽?”
“也许吧,如果将来还有人会去鉴赏的话。”
萨莎不说话了,像在思考什么。荷马重新浸入了沉重的思绪之中,没有急于搭话。
“就是说,如果离开了人,那美也就不复存在了?”沉默了一会儿后,萨莎道出了心中的疑问。
“应该是。”荷马漫不经心地回答,“如果没有人鉴赏的话……动物是不懂得欣赏美的……”
萨莎沉吟道:“假如动物和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动物不懂得欣赏美,那就是说,假如没有美,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对吗?”
“不是,”老人摇摇头,“很多人根本就不需要美。”
姑娘将手插入口袋,从里面掏出了一样东西:一个带有图案的方盒,不知是聚乙烯的还是塑料的。她带着羞怯而又骄傲的神情,像在展示奇珍异宝一样,把那东西送到荷马面前。
“这是什么?”荷马问。
“你来告诉我。”萨莎狡黠地一笑。
“嗯,”他小心翼翼地接过方盒,看了看上面的文字,还给萨莎,“一个茶叶盒子,还有图案。”
“是图画,”她郑重其事地说,“一幅美丽的图画。要不是它,我早就……疯了。”
荷马怔怔地看着她,突然鼻子一阵儿发酸,眼泪就要溢出眼眶,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伤感的老傻瓜,他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假咳了几声,叹了口气。
“你之前从来没上去过,到过城里,除了这次以外?”老人的语气充满同情。
“那又怎么了?”萨莎将盒子重新藏好,“你想告诉我,地上的一切跟图画上的完全不一样?图画上那些根本就不存在?这我都知道。我知道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房子、桥梁、河流,可怕又空旷。”
“正好相反,”老人说,“我从没见过比这座城市更漂亮的地方。你刚才所说的,好比通过一根枕木评判整个地铁。我甚至都没法跟你描述。那里的楼房高过任何一座山,街道像山涧一样喧闹流淌。天空永远不会熄灭,雾气中透着灯光……这座城是爱慕虚荣的,昙花一现的,就像它千百万居民中的任何一个,匆匆忙忙,庸庸碌碌。整座城市是由不可融合之物融合而成的,它的建设没有任何规划。它绝不是永恒的,因为永恒过于冰冷和迟钝,而它是那么生机勃勃!”他攥紧拳头,猛然一挥,“这些你是没法理解的,除非你亲眼看见……”
在那一刻,他几乎确信,假如萨莎能够上到地表,她同样能够看见这座城市的幻影。但他全然忽略了,想要看见城市的幻影,必须得见过城市活着时的样子。
****
荷马费了好大力气,总算疏通好关系,让萨莎通过了汉萨的边防线。她假装自己要被拉去枪毙,被几名士兵押送着穿过了整座站台,进入了当地公共澡堂所在的办公区域。
换乘站帕维列茨站拥有两个站台,两者的共同之处只在于名字。好比一出生就被分别领养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一个到了富贵人家,一个到了穷苦人家。辐射线的站台虽然高大宽敞,却又脏又乱;环线的站台虽然低矮狭小,却锃光瓦亮,一尘不染,盛气凌人。眼下这个点儿,环线站台上几乎没什么人,除了在站台工作的人,其余人似乎都更喜欢辐射线站台的随意自由,而不是环线站台的严苛压抑。
更衣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墙壁上整齐地镶着瓷砖,地板花砖很多都碎了,装衣服和鞋子的铁箱全都喷上了油漆,乱麻似的电线上亮着一盏灯泡,两条长凳包着人造革……
萨莎兴奋得无以复加。
干瘦的女服务员递给她一方白得离奇的毛巾和一小块坚硬的灰色肥皂,嘱咐萨莎将浴室从里面插上插销。
毛巾的粗糙触感,肥皂呛鼻的气味,全部属于遥远的过去,那时萨莎还是汽车厂站卫戍司令的掌上明珠。她几乎已经不记得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了。
萨莎解开因太久没有清洗污垢而变得梆梆硬的工作服,麻利地从里面钻出来,扯下汗衫,脱下短裤,连蹦带跳地来到锈迹斑斑的水管旁。水管上挂着一只自制喷头,她紧紧握住灼热的铁阀门,费了好大力气才放出热水——好烫!她连忙身子贴墙,以免被开水溅到,又旋开了另一个阀门。终于将冷热水调到了合适的比例,她不再躲闪,整个站到水流之下。
浇在她身上的水浑浑的,夹杂着灰尘、烟黑、机油、鲜血——她自己的和其他人的鲜血,以及疲惫、绝望、愧疚、焦虑……流了好久好久,才渐渐清亮起来。
这回老人就不会再打趣她了吧,萨莎想着,以旁人的目光凝视着自己被泡软的粉红色脚掌和白得有些不习惯的手掌。这样一来,男人就能发现她的美了吧?也许,荷马是对的,她真不该那样蓬头垢面地去探视猎人?这些东西也许真得好好学学。
他会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变化呢?她拧紧阀门,趿拉着鞋走到更衣室,打开荷马送她的那面小镜子……不可能注意不到的。
热洗澡水使她肌肉松泛,也打消了她心头的疑虑。光头说的那句关于怪兽的话并非想要推开她,他只是还没有完全清醒而已;他也不是在对她说,而只是在继续噩梦中的激烈争吵。她只需要耐心地等他醒过来,她必须守在他身边,好让……好让他第一眼就能看见自己,立刻就能明白。接下来呢?她完全没有必要操心,他经验丰富,她可以全心全意地信赖他。
想到光头在昏迷中胡言乱语的情形,萨莎凭直觉感到,他恰恰在寻找她,因为只有她能够抚慰他,减轻他的高烧,帮他找回平衡。她越是这么想,就越是浑身发烫,也像发了高烧似的。
女服务员将她肮脏的工作服收走了,说帮她洗一洗,给她留下了一条浅蓝色单裤和一件破了洞的高领毛衣。这身新衣服让她觉得拘束和不自在。更讨厌的是,在她从浴室回医务室的一路上,几乎所有男人的目光都黏到了她身上,等她躺到自己病床上时,都恨不得再去重新冲个澡了。
老人没在病房里,然而还没等她感到无聊,门“吱呀”一声,医生探进头来。
“恭喜恭喜,你可以去探视了。他醒了。”
****
“今天几号了?”
猎人一只胳膊肘撑起身,艰难地转动着脑袋,眼睛盯住荷马。荷马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腕,才发现早就没戴手表了,只得无奈地两手一摊。
“二号,十一月二号。”男护理员说。
“三天三夜。”猎人缓缓地躺到枕头上,“浪费了三天时间,我们快赶不及了,必须即刻上路。”
“你这样是没法走的,”护理员劝阻道,“你身上的血几乎流光了。”
“必须走,”队长根本没理睬他的话,“时间不多了……匪帮……”说到这儿,他突然顿住了,盯着荷马问,“你戴防毒口罩干什么?”
荷马早就想好了说辞。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他已经布置好了防线,策划好了反攻。猎人的昏迷让他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交代,现在可以代之以编造好的谎言。
“根本就没有什么匪帮,”他低声说着,俯身到伤者床前,“你昏迷的时候……一直在说胡话,我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猎人一把锁住老人的领口,将他拽向自己。
“关于图拉站的瘟疫……”见护理员想要跳过来制止猎人,老人恳求地冲他摆摆手,说,“没事的,我能搞定。我们需要谈一谈,能不能请您……”
护理员不情愿地点点头,将注射器针头罩上套子,走出了病房,留下二人独处。
“除了图拉站……”猎人狂暴、通红的眼睛仍死死地盯住老人,攥紧的手却慢慢松开,“没有别的了?”
“没了。我只知道图拉站是某种未知传染病的疫区,这种传染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我们的人设置了检疫,在等待支援。”
“嗯……”猎人终于将他松开,“没错,是疫病。你害怕被我感染?”
“小心无大错。”荷马谨慎地回答。
“嗯。没事的。我当时靠得并没有很近,而且风是朝他们那边吹的……我应该不会感染。”
“你为什么要编造关于匪帮的谎话?你想怎么做?”老人鼓起勇气问。
“先去多勃雷宁站,我们需要喷火器,清洗整个图拉站。只有这一个办法……”
“你要把全站台的人活活烧死?那我们的人呢?”老人仍抱有幻想,队长关于喷火器的说法同样是他临时编造的谎话,跟他对塞瓦斯托波尔站领导说的匪帮一样。
“谁说是活活烧死呢……是焚毁尸体。没有其他出路。所有感染者,所有接触者,整个空气都需要清洗。我之前听说过这种疫病……”猎人闭上眼睛,舔了舔皲裂的嘴唇,“无药可治,两年前就暴发过……死了两千人。”
“但上次不是阻止住了吗?……”
“就是靠封锁、喷火器。”队长将被烧焦的半边脸转向老人,“没有其他办法。只要有一个人逃出来……所有人都得完蛋。没错,我是撒谎了,否则伊斯托明是不会同意的,他太优柔寡断了。”
“可是,万一有人可以免疫呢?”荷马怯懦地说,“万一那里还有健康的人呢?我是说……万一有办法治愈呢?”
“不可能有人免疫,所有接触者都会感染。那里没有健康的人,只有还没发病的。”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但他们更不幸,现在就是活受罪。相信我……让他们早点解脱,也是为他们好。”
“但你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老人为提防队长再次出手,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
但猎人只是疲惫地合上了眼睛。荷马又一次发现,他被烧毁的半边脸上的那只眼睛没办法完全闭合。他许久都没有吭声,老人几乎要跑去叫医生了。
但就在这时,猎人像被催眠师送回到无限遥远的过去寻找失落的回忆一般,缓缓地、一字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我必须,保护人们,排除任何危险。仅此而已。”
****
他发现那把刀了吗?他猜到那是我给他的了吗?万一他没看见呢?万一他看见了却猜不到呢?萨莎沿着走廊飞奔,脑子里一团乱麻,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真可惜,他怎么没等我赶到就醒了呢?
萨莎无意中听到了光头和老人的整场对话,当听到杀人时,她一下子愣在了门口,随即躲到一旁。她自然无法理解全部信息,但最重要的话她已经听到了。再没必要继续等下去了,萨莎用力地敲了敲房门。
老人迎面站起身,脸上写满了绝望。他脚步虚浮,像是也被人打了一针镇定剂似的,瞳仁里的灯捻也像是被人掐灭了。走到萨莎面前时,他机械地、像受绞刑者被人勒紧了绞索那样冲萨莎点了点头,走出了病房。
萨莎坐在被焐热的圆凳边沿,轻轻咬住嘴唇,屏住呼吸,一狠心,踏入了全新的未知隧道。
“你喜欢我送你的刀吗?”
“刀?”光头向四周环视一圈,看见了黑色刀锋,却并没有伸手去摸,而是警惕地注视着萨莎,问道,“这又是哪一出?”
“这是给你的,你那把不是断了吗,当你……救我……”
“除了你,恐怕再不会有人送刀给我了。”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说。
萨莎在这些话里听出了某种模糊的暗示,意味深长。她接受了游戏,却还不熟悉游戏规则。她试探着挑拣合适的字眼,但她很不擅长这样做,似乎她的话语根本无法描述内心翻涌的思绪。
“你也觉得,我身上有你的一小部分?从你身上被撕下的那个部分,你一直在寻找它,而我能够将你补充完整?”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光头兜头朝她泼了一瓢冷水。
“就是的,你也能感觉到,”萨莎蜷起身子,坚持道,“和我在一起你会变得完整,我可以而且应该和你在一起。不然你为什么要把我带上?”
“是老头子的主意。”光头的声音冷冰冰的。
“那你为什么要为我杀死轨道车上的人?”
“杀人不需要理由。”
“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从怪兽手里救出来?!”
“畜生必须被消灭。”
“你还不如让它把我吃掉!”
“活下来你还不乐意吗?”光头冷漠地反问,“那你就顺着升降梯上到地表去好了。不是想找怪物吗?那里还有的是呢。”
“我……你想让我……”
“我不想让你做任何事。”
“我能帮助你停下!”
“你不要缠着我。”
“你难道感觉不到吗?”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他的话里透露出一股锈水的气息。
即使是无眼怪兽的巨爪也没有伤她那么深。萨莎跳起来,心里滴着血,跑出了病房。幸好,她的房间里没人。她蜷在墙角,缩成一团。她在兜里摸索那面小镜子,想把它扔掉,却没找到,可能是掉在光头的床边了。
当眼泪流干之后,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她很快就收拾好了东西,老人会原谅自己偷走他的自动步枪的——她做什么他都会原谅她。洗净消毒的粗帆布防化服无力地从辅助用房的挂衣钩上垂下,正在等她。好像哪位巫师对那个该死的胖子施了诅咒,让他在死后也要处处追随萨莎,帮她完成她的愿望。
萨莎钻进防化服,来到走廊,穿过通道,走上了月台。走到半路,一串美妙的音符如山涧般朝她奔涌过来,但源泉仍旧没有发现。眼下她也没工夫去找。她只是驻足了几秒钟,便克制住了诱惑,继续朝既定目标走去。
白天看守扶梯的只有一位哨兵,地表的怪物从来不会在白昼期间侵扰站台。
她没用五分钟就通融好了,萨莎给这位好说话的哨兵送了一个半空的弹匣,一脚踏上了通往地表的头一级台阶。
她提了提松松垮垮的裤子,向上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