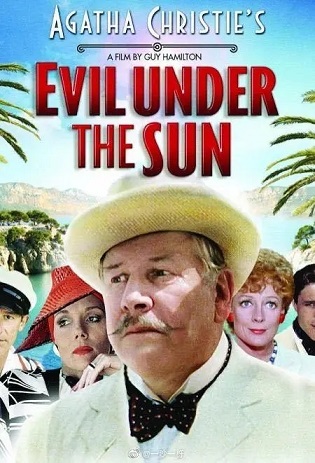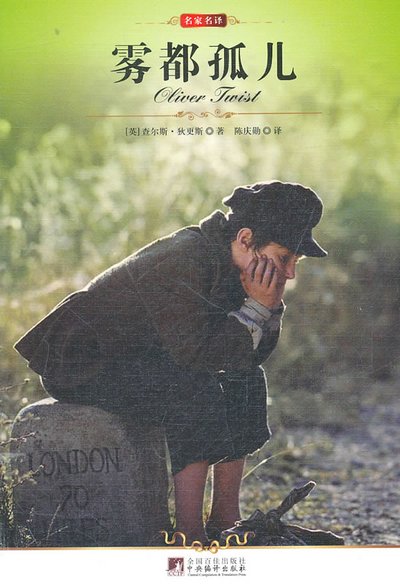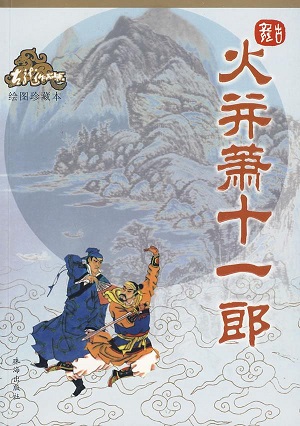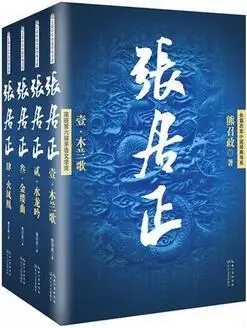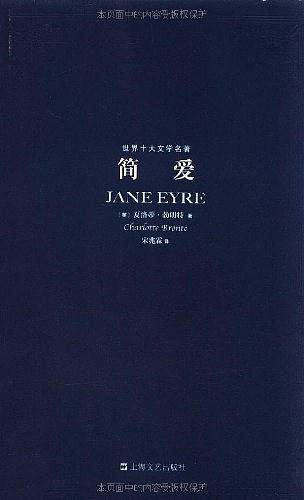的确,到底是什么使人变成了人呢?
人类在地面游荡已经超过一百万年了,但从机灵的群居动物到史无前例的全新物种,这个进化仅仅源自大约一万年前的神奇蜕变。想想看,人类历史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都蜗居在洞穴,茹毛饮血,不会生火,不会制造工具和武器,甚至没有语言!就连他们所能体验到的情感也跟猴子和狼没什么差别:饥饿、恐惧、依赖、关心、满足……
但人类何以在短短几个世纪之内便学会了思考,学会了记录、表达自己的想法,学会了发明和改造周围的物质世界?人类何以会想到绘画,又如何发明了音乐?人类何以能够征服整个世界,并按照自己的需求对其加以改造?在一万年前,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种动物如此神力?
是火吗?它教会了人类控制光和热,帮助人们熬过黑暗与寒冷,让人们能够吃上熟肉。但这又改变了什么呢?无非是帮助人类征服了更多的土地而已。但耗子即便没有火,照样遍布全球,可耗子依旧是耗子,一种贼眉鼠眼的小型群居哺乳动物。
肯定不是火,至少不光是火。乐手是对的,还有其他什么……到底是什么呢?
语言吗?这无疑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大区别。将天然的思想原石打磨成钻石般的话语,让它们变成通用货币,在世界各地流通。语言不仅能够表达心中所想,而且能够帮忙理顺思路,将液态金属般无序流动的形象铸造成固定形状。语言还能让人头脑清醒明晰,从而准确传达命令与知识。组织能力、调动军队和建设国家的能力同样源自于此。
然而,蚂蚁完全没有语言的辅助,却照样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真正都市以及复杂有序的等级体制,并且能够准确地传达信息和指令,调动成百上千万勇敢无畏、纪律严明的蚂蚁军团,在微型帝国之间展开无声无息却残酷无情的战争。
也许,是文字?
没有文字,知识便无法累积。文字正是世界文明赖以搭建通天塔的砖石。倘若没有文字,一代人获得的智慧只能随着一代人化为尘土,每一代人都只能从头开始修建,世世代代在废墟上忙碌,终其一生无法达到新的高度。正是在文字的辅佐之下,人类才得以将积累的知识转移到大脑之外,毫不曲解地传给子孙后代,好让他们避免低级重复建设,而在先辈留下的坚实地基之上添砖加瓦。
可是,总不该仅仅是文字吧?
假使狼会书写,它们能够创造类似于人类的文明吗?
狼一旦吃饱肚子,便会丧失斗志,嬉戏打闹,直到饥饿再来驱使它们。而人一旦吃饱肚子,便会陷入另一种不可言喻、难以捉摸的饥饿,这种饥饿驱使他们一连几个小时仰望星空,用赭石颜料在洞穴墙壁上涂涂画画;不是去加固堡垒围墙,而是去雕饰战船、建造巨大的太阳神石像;不是去训练击剑本领,而是将生命耗费在精粹语言艺术上。也正是这种饥饿怂恿荷马——这位曾经的助理司机——将自己的余生耗费在阅读和收集素材、写作上。这种饥饿究竟是什么呢?为了消除这种饥饿,衣衫褴褛的民众会去崇拜流浪的小提琴手,高高在上的君主会封赏游吟诗人、赞助画家,而蜗居在地底的女孩会年复一年抱着一个空茶叶盒看。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难以抗拒的召唤,甚至可以盖过生理上的饥饿——这才是只有人类才具备的。
是否正是这种非生理的饥饿,在其他动物的情感之外,额外赋予了人类梦想的能力、希望的勇气和宽恕的力量?爱与同情,通常被认定为人类独有的特质,但事实上并不专属于人类。狗同样会爱,会同情,当主人生病时,它会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一旁。更有甚者,狗会将另一个生物视为自我生命的意义,在主人去世之后,它甚至会不吃不喝,追随主人而去。
然而,狗却不懂得美。
如此说来,让人之所以为人的,恰恰是对于美的追求与鉴赏?将鲜花、声音、线条和词汇进行排列组合,并从中汲取养分和慰藉的神奇能力?这种灵魂上的共鸣能够激发任何一个心灵,让其得到洗涤,不管那心灵是堆满脂肪的、长满老茧的,还是布满伤痕的。
也许。但这同样不全面。
有时,为了掩盖射击的枪声和被枪决者的哀号,射击者会特意将瓦格纳雄壮的音乐放到最大音量。两者并不发生冲突,一者只不过是为了强调另一者。
那么,还有什么呢?
即便作为生物学物种,今天的人类幸存者能够熬过现世的地狱,但他能否保持那个脆弱的、几乎感受不到却无疑存在的分子,那个在一万年前将半饥半饱、眼神混浊的野兽变成全新物种的火花呢?对于这个物种而言,心理的饥饿更甚于生理上的饥饿,他们永世游荡于精神崇高与卑鄙的两极,反复于无法解释的慈悲与无从辩解的残暴,人类的慈悲固然是野兽所不及的,但人类的残暴也是连低等的昆虫世界都没有的。人类建造了雄伟的宫殿,绘制出不可思议的画卷,与上帝比试创造纯粹之美的技艺;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发明了毒气室和氢弹,以便弹指间就将一切造物和同类化为灰烬。人类辛辛苦苦在海滩上建造起沙堡,随后又疯了似的将它们摧毁。人类在任何事情上都不知道限度,他们毫不餍足,永远无法消除自己那奇特的饥饿,尽管终其一生都在试图这样做。
那个火花,还会不会留下?
还是说,火花在短暂的燃烧之后便会熄灭,变成历史,让人类退回曾经永恒的蒙昧,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毫无长进地彼此更迭,让一万年、十万年、五十万年的光阴毫无痕迹地流逝?
****
“那是真的吗?”萨莎突然问。
“你指什么?”列昂尼德笑着问。
“翡翠之城,诺亚方舟?地铁里真的有这样的地方吗?”萨莎若有所思地问,眼睛瞅着脚下。
“据说是的。”列昂尼德含糊其词地回答。
“要是能去那儿看看就好了。”萨莎拖长声音说,“你知道吗,当我在地面的时候,我为人类感到十分委屈。就因为他们犯了一次错误……就永远无法找回曾经的一切了。而那里之前是多么美好啊……嗯,我虽然没亲眼见过,却能猜到。”
“错误?那可不是错误,那是罪孽,滔天大罪。”列昂尼德严肃地说,“将整个世界毁灭了,杀死了六十亿人,这难道仅仅是错误?”
“就算是吧……但难道我们就不能被原谅吗?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重造自己,改正一切,从头来过,哪怕是最后一次机会。”萨莎沉默了片刻,继续道,“我真的想亲眼看看,地表以前究竟是什么样的……早先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我只是害怕,觉得那里的一切都很可怖,可事实上,我只是去的地方不对而已。我太蠢了……地表那座城市,就像我之前的人生,没有未来,只有回忆,还是别人的回忆,只有鬼魂。但上次在地表时,我明白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吗……”萨莎有些难为情地说,“希望,就像血液。只要它还在你的血管里流淌,你就还活着。我愿意葆有希望。”
“你为什么想要去翡翠之城?”列昂尼德问她。
“我想看一看,感受一下人类曾经的生活……你不是说了吗……那里的人也许真的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既没有忘记昨天,又在期待明天的人,肯定会是别的样子的……”
萨莎和少年不疾不徐地在多勃雷宁站大厅闲逛,三位卫兵在一旁凝神戒备。荷马去找站长接洽了。临走前他十分不情愿留下萨莎和那个小子独处,眼下却不知为何迟迟未归。猎人则至今仍未露面。
多勃雷宁站的大理石站台的构造令萨莎心有触动:这里有一道道大理石贴面的拱门,高矮相间,一道高的,一道矮的,又一道高的,又一道矮的,仿佛相互挽着胳膊的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萨莎突然也很想把自己的小手放到一张宽厚有力的男人的大手中,哪怕在里面藏上一小会儿。
“这里同样可以建设新生活,”列昂尼德说着,对萨莎挤了挤眼,“不一定非要去别的什么地方……幸福无须远寻,就在你的眼前。”
“眼前?”萨莎疑惑地环顾四周。
“就是在下。”乐手假装害羞地垂下眼皮。
“不害臊。”萨莎终于回了他一个微笑,“我很喜欢听你的音乐,跟其他人一样……那些子弹你完全用不着吗?为了能让我们到这儿来,你把它们全花光了。”
“我只要够吃饭的就行,我从来不缺钱。再说,为钱演奏未免太无趣了。”
“那你是为了什么而演奏呢?”
“为了音乐,不,为了人们……不,也不对,准确地说,是为了音乐能够带给人们的。”
“音乐能够带给人们什么?”
“泛泛地说,一切。”列昂尼德的神情再次变得凝重,“我的音乐有些能让人想去爱,有些能让人想哭。”
萨莎疑惑地看着列昂尼德,问:“上次你吹的那个,无名曲,它能让人怎样?”
“这个吗?”列昂尼德用口哨吹出了前奏,“它能止痛。”
****
“喂,大叔!”
荷马合上笔记本,在硌屁股的木头板凳上动了动。勤务兵端坐在一张小写字台后面,桌面几乎被三台黑色电话整个占满了,电话机上既没有按键,也没有转盘。其中一个上面闪烁着一盏小红灯。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有空了,他有两分钟时间接待你,进去之后别拖泥带水,长话短说。”勤务兵板着脸正告老人。
“两分钟可不够。”荷马叹了口气。
“反正我已经提醒过你了。”勤务兵耸耸肩。
别说两分钟,五分钟都不够。老人既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既不知道该询问什么,也不知道该请求什么,但除了多勃雷宁站站长,他实在没有人可以求助了。
站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是个大胖子,身上的制服都系不上扣了。这会儿正急躁得浑身冒汗,根本没耐心听老人絮叨。
“你懂不懂事?!我这儿都火烧眉毛了,八个人被杀了,你却跟我讲什么疫病!这里什么疫病都没有!够了,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赶紧给我出去!”站长如鲸鱼出水一般从办公桌后面猛然站起,险些将桌子撞翻。勤务兵探头探脑地朝办公室望了一眼。
荷马忙从又矮又硬的会客椅上站起身,连声说道:“好好好。可是,您为什么要派兵去谢尔普霍夫站呢?”
“关你什么事?!”
“站台上的人说……”
“说什么?说什么?!你少给我在这儿制造恐慌……巴沙,把他给我关起来!”
勤务兵应声而入,一把将老人拽出了办公室,啪啪两个大耳光就将荷马的防毒面具给扇掉了。老人试图屏住呼吸,心口却挨了一拳,吃力地咳嗽起来。站长走到办公室门槛前,肥胖的身躯堵住了整个门洞。
“先把他关起来,回头再收拾他……你是怎么回事,有预约吗?”他扯着嗓子对下一位访客喊道。
荷马趁机回身看了一眼。
离他三步远,一位彪形大汉抱臂而立,正是猎人!他穿着从别人身上扒下来的紧身制服,脸藏在钢盔面甲的阴影里,似乎并没有认出老人,也并不打算出手干涉。荷马原本以为,他会像屠夫一样浑身沾满血污,但他衣服上唯一的血迹是从他自己肩膀上的伤口渗出的。猎人将石头一样的目光转向站长,缓步朝他走去,就像是打算径直穿过他的身体。
站长被猎人的气场震慑,嘟嘟囔囔地回撤一步,让开了路。勤务兵和荷马抱在一起,瞠目结舌。猎人跟随胖站长挤进办公室,一声狮吼便让对方乖乖闭上了嘴,随后开始低声吩咐些什么。
勤务兵扔下荷马,慌里慌张地跑进站长办公室,当即被胖站长骂了出来。
“把那个造谣者放掉!”胖站长像被催眠了似的,重复着别人的指示。
勤务兵像只被烫熟了的大虾,在身后关上办公室门,茫然地走向自己的座位,一头扎进包装纸印刷的新闻传单中去。当荷马壮着胆子从他身边走向站长办公室时,他只是将脑袋更深地埋入纸页中去,意在声明眼下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干系。
荷马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缩头缩脑的勤务兵,终于有机会好好端详一下桌上的电话机了。在那台一直闪个不停的电话机上,贴着一块脏兮兮的白色胶布,上面用蓝色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图拉站。”
“我们一直跟游骑兵保持着联络,”办公室内,胖站长大汗淋漓,不敢正眼看猎人,“这次行动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我自己无权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就打电话给上级,”猎人说,“我们有时间商量,但不多。”
“他们是不会同意的,这将威胁到汉萨的稳定……您难道不知道,现在汉萨最重要的是什么吗?而我们站台目前还一切正常。”
“还他妈谈什么稳定?!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
“目前局势稳定,我不知道您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胖站长固执地摇晃着大脑袋,“所有出口都严防死守,连只老鼠也跑不出来。我们还是再等等吧,事情会自行解决的。”
“不可能自行解决!”猎人咆哮道,“早晚会有人跑出来,跑到地面上,或者其他站台。图拉站必须清洗!严格按照守则!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直到现在都还没这样做!”
“可是,站台上也许还有没染病的呢!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难道要我下令枪杀自己的弟兄,焚毁整个图拉站?要不要把谢尔普霍夫站也一起干掉?不行!枪杀感染者,绝对不行!就算当年白俄罗斯站闹猪瘟的时候,也没有把所有的猪统统杀掉,而是将它们一头一头地隔离开来,让瘟猪自行死掉,而健康的猪就让它活下来。”
“那是猪,这是人。”猎人语气平淡地说。
“不行,不行,”胖站长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大颗的汗滴甩得到处都是,“我不能这样做,这是不人道的……这会让我良心不安,我可不想一辈子做噩梦。”
“不用你动手,自会有不怕做噩梦的人去做。你只需要放我们过去就行了。”
“我已经派人去波利斯询问疫苗的事了。”胖站长用袖子擦掉脑门上的汗水,“还有希望……”
“根本就没有疫苗,没有任何希望!不要再做鸵鸟了!为什么这里还没有汉萨派来的卫生队?!为什么你不肯打电话过去,申请为游骑兵开放通道?!”
胖站长一言不发,莫名其妙地开始扣制服上衣的扣子,但手指止不住地哆嗦,没过一会儿就放弃了。他走到褪色的餐具橱前,倒了一小杯芳香四溢的露酒,一仰脖喝了下去。
“你根本就没有知会汉萨……”猎人猜测道,“他们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你的邻站发生了疫病,而他们却还什么都不知道……”
“这可是掉脑袋的罪过,”胖站长嘶哑地说,“谢尔普霍夫站的疫病意味着革职……”
“谢尔普霍夫站也有了?!”猎人眼中凶光一闪。
“不是……目前还一切正常,但我反应得太迟了……没有及时应对,可谁又能料到呢……”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解释的?为何出兵中立站台、封锁隧道?”
“说有匪盗、暴动者。这是常有的事,不会有人起疑的。”
“可现在再想承认已经晚了……”猎人推测道。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革职的事了,”胖站长又倒了一杯,一饮而尽,“这已经够极刑的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猎人逼问。
“等,”站长一屁股坐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万一有转机呢?”
“那你为什么不接他们的电话?”荷马插嘴道,“你们的电话一直在响,是图拉站打过来的。万一有转机呢?”
“不会响的,”胖站长哑着嗓子说,“我把声音关掉了,只会亮灯。只要灯还亮着,就证明人还活着。”
“那你为什么不接?!”荷马愤怒地质问。
“你让我跟他们说什么?让他们再忍忍?祝他们早日康复?告诉他们救援马上就到?!建议他们自行了断?!光跟难民谈话就够我受的了!”胖站长歇斯底里地喊。
“闭嘴!”猎人低声喝令,“听着。我一天之后带着人回来。你要保证我的人畅通无阻地通过所有岗哨,谢尔普霍夫站要保持封锁状态。我们前往图拉站,清洗站台。如有必要,也会顺带把谢尔普霍夫站清洗一遍。对外就宣称是一场小规模战役,你可以不必通报汉萨。你完全不用做任何事情,全部由我自己来……我会帮你恢复稳定。”
胖站长像条被撒了气的自行车内胎,无力地点了点头。他又倒了一杯露酒,嗅了嗅,低声问道:“你的双手会沾满血。你难道不害怕吗?”
“冷水一洗就掉了。”猎人冷冷地说。
当他们从办公室走出时,胖站长深吸了一口气,将勤务兵喊了进去。勤务兵钻进办公室,门咣当一声在身后关闭。
荷马故意落在猎人后面,弯腰从办公桌上摘下了那台一直在闪烁的电话的听筒,放到耳边。
“喂?喂?有人吗!”他压低声音冲着话筒急喊。
听筒那头一片寂静,但不是电话线被切断的那种无声无息,而像是听筒已经被人拿起,只是无人回应一样。似乎有人等他接电话等了好久,终究没能等到;似乎那侧的话筒正在向死人耳朵里传达着老人的追问。
猎人不悦地瞪了荷马一眼,荷马小心地将听筒放回原位,顺从地跟在猎人身后。
****
“波波夫!波波夫!起床!快!”
指挥官的强光手电筒刺痛了阿尔乔姆·波波夫的眼皮,透过瞳仁往他脑子里燎了一把火,强有力的大手摇晃着他的肩膀,随后在他胡子拉碴的脸上抽了一巴掌。阿尔乔姆眨着眼睛,揉揉火辣辣的脸颊,一骨碌从床上滚下地板,立正敬礼。
“你的武器呢?带上枪,跟我来!”
战士们睡觉从来不脱衣服,都是整装待发。阿尔乔姆抖开一块破布,拿起裹在里面当枕头的自动步枪,踉踉跄跄地跟在指挥官后面。他睡了多长时间?一小时?俩小时?脑袋嗡嗡直响,喉咙干得冒烟。
“开始了……”指挥官回过头,朝他喷出一口酒气。
“什么开始了?”阿尔乔姆惊恐地问。
“马上你就看见了……再给你一个弹匣,用得上。”
图拉站十分宽敞,没有圆柱,看上去像个无比臃肿的隧道顶棚,眼下几乎整个淹没在黑暗之中。几束微弱的手电筒光线痉挛似地扫来扫去,移动轨迹全无规律,毫无章法,仿佛手电筒被拿在小孩子甚或猴子手里似的。真是好笑,哪儿来的猴子呢……
阿尔乔姆猛然一惊,顿时明白了什么,慌忙检查起步枪来。守不住了!还是说,还不算晚?
另有两个士兵从守卫室里蹿出来,来到他们跟前,两人脸上的皮肤都有些浮肿,睡眼惺忪。指挥官一路拽起了所有还走得动路、拿得起枪的士兵,其中有些已经开始出现咳嗽症状了。
沉重压抑的空气中回荡着奇怪的声音,那不是喊叫,不是哀号,不是喝令……而是从数百个喉咙里汇聚而成的呻吟,充满了绝望和恐怖。呻吟伴着零星的金属撞击声和摩擦声,同时从两个、三个、十个方位传来。
月台上堆满了破破烂烂、团在地上的帐篷,以及歪倒在地的窝棚,都是用金属板、列车铁皮、贴面板和废弃的家具拼成的……在这堆东西中行进的指挥官活像一艘破冰船在前面开路,阿尔乔姆和另外两名战士则紧随其后。
一辆被斩断的机车从后边隧道的黑暗中凸显出来,仅剩的两节车厢里的灯全都熄灭了,敞开的门用可移动障碍好歹拦住,车厢里面……深色车窗玻璃后面,是拥挤、沸腾的可怕人群,数十双手臂抓住脆弱的金属格栅,猛烈摇晃。安插在每个通道口处的戴防毒面罩的士兵时不时就会跑到门洞旁,挥舞着枪托,但并不敢真打下去,更别说开枪射击了。别的卫兵则在努力劝说、安抚着被塞进铁皮罐头里的汹涌人潮。
只是,车厢里的人还听得懂人话吗?
他们之所以被关进车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开始从安置在隧道里的隔离舱中逃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数量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未感染者。
指挥官大步走过了第一节车厢、第二节车厢,阿尔乔姆这才明白,他们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最后一道门,这才是破脓的地方。从车厢里不断拥出一些奇特的生物,他们勉强撑着身子,面部浮肿到几乎无法辨认,四肢肿胀得像打足了气。但目前还没有人来得及逃跑——门口已经集结了所有待命的冲锋枪手。
指挥官挤过围堵的士兵,上前喊道:“我命令,所有感染者立刻回到原位!”边喊边将斯捷奇金手枪从枪套中拔了出来。
离他最近的一位感染者艰难地,用了好几个分解动作才抬起肿得像个皮球似的大脑袋,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有气无力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你们是知道的,你们感染了不明病毒。我们正在寻找解药……你们需要忍耐。”
“你们在寻找解药……”病人轻蔑地一笑,“真是好笑。”
“请立即回到原位,”指挥官拉开保险栓,“我数十个数,然后就下令开枪射击。一。”
“你们不过是在糊弄我们,好让我们乖乖听话,直到一个个完蛋……”
“二。”
“已经一天一夜没给我们送水了,当然了,谁会舍得把水给死人喝呢……”
“卫兵不敢靠近车厢,已经有两个卫兵被感染了。三。”
“车厢里已经堆满了尸体,我们走路只能踩着人脸走。你知道鼻梁骨被踩断的声音吗?如果是小孩子,是这样的……”
“尸体没地方安置!我们又不能将他们焚毁。四。”
“隔壁车厢拥挤到什么地步,人死了都倒不下去,继续跟活人肩并肩站在一起。”
“五。”
“上帝啊,你们开枪打死我吧!我很清楚,根本没有解药。我快要死了,我受不了了,我感觉五脏六腑被巨大的砂轮碾碎了,然后往上面浇上酒精……”
“六。”
“然后再点着。我感觉脑袋里有数不清的蠕虫,正一点一点蚕食我的大脑、灵魂……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七!”
“你们这帮浑蛋!放我们出去!让我们有尊严地死去!你们凭什么这样折磨我们?你们自己没准儿也已经被——”
“八!一切都是出于安全考虑!为了让其他人活下来。我自己死不足惜,但是你们,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准备射击!”
阿尔乔姆举起自动步枪,锁定最靠前的一位病人……上帝啊,好像是一位妇女:汗衫下面隆起的是鼓胀的胸脯。阿尔乔姆眨眨眼睛,将枪口转向了一个打摆子的老头。丑陋的人群不满地嘟囔着,后退了一步,想退入门内,但已经退不回去了,更多的感染者已经拥到了门口,呻吟着,哭泣着。
“残忍的军阀!你想干什么?!你现在是对着活人扫射,我们可不是丧尸!”
“九!”指挥官的声音死气沉沉。
“放我们出去吧!”一个病人拖长声音喊着,朝指挥官伸出双手,就像一个指挥家,引得整个人群骚动起来,在他手指的挥动下,集体向前迈出一步。
“开火!……”
****
只要列昂尼德的嘴唇一沾到自己的乐器,人群便立即朝他围拢过来。光是笛管发出的头几个用来调试乐器的音符,已足以令围观人群发出赞叹的微笑,鼓掌喝彩,而当长笛的声音变得清亮纯粹,人们的脸上开始洋溢着光彩,仿佛全身的污垢都被涤荡了。
萨莎这次的位置与众不同,她站在乐手身旁。数十双眼睛不仅注视着列昂尼德,有些发亮的目光也投射在她身上。起初她颇有些难为情,觉得自己配不上众人的关注和赞赏,但很快,旋律便托着她从花岗岩地板腾空而起,脱离了周围的人群,像沉浸在一本好书或一个故事里一样,令她物我两忘。
空气中流淌着的还是那段旋律,列昂尼德自创的无名曲。他每次演出都会以这首曲子开场和压轴。它能够舒展听众脸上的皱纹,擦掉蒙在双眼上的阴翳,在心头点亮一盏灯。尽管这首曲子萨莎已经听过很多遍,但乐手的每次演绎都能为她打开新的密道,激发新的感触。她仿佛正久久地凝望着天空……忽然,在白云之间,一道无限深邃的柔绿一闪即逝。
她突然被刺痛,重重地从云端坠落,慌乱地四处环顾。在那儿!——在围拢的听众之外,高出众人一头,一个人昂首而立,正是猎人。他那尖锐的目光直直地刺向她,随即又猛然扎向站在她身旁的乐手。但乐手对光头的逼视毫不在意,至少没有表露出任何慌乱。
猎人既没有转身走开,也没有试图带走萨莎或者中止演出。他耐心地将曲子听完,后撤一步,迅速消失了。萨莎立即抛下列昂尼德,挤过人群,朝光头追去。
猎人在不远处一个长凳旁停下,长凳上坐着垂头丧气的荷马。
“你都听见了,”猎人嘶哑地对荷马说,“我现在就走。你要跟我一起吗?”
“去哪儿?”老人抬眼朝走过来的萨莎虚弱地笑笑,对猎人说,“她也都知道了。”
猎人又盯了萨莎一眼,点点头,仍旧一句话也没对萨莎说。他又转向老人,说:“就在附近,但我……我不想一个人去。”
“那就把我带上吧。”萨莎下定决心。
光头深吸一口气,将手指攥紧,又松开,终于说:“谢谢你的刀,帮我杀了人。”
姑娘像被刺到了一样,身子不由得一颤,但很快又鼓起勇气,反驳道:“刀怎么用,完全取决于你。”
“我别无选择。”
“现在你有了。”她咬住下嘴唇,皱着眉道。
“现在也没有。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应该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我为什么要去图拉站,十万火急……”
萨莎看见他的手指在微微颤动,肩膀上的深红色在不断渗出,她现在不仅害怕他,更为他感到担心。
“你应该停下来。”她温柔地劝阻。
“不可能。”猎人的口气不容商量,“这件事总得有人去做,我不去谁去?”
“你会把自己害死的。”姑娘试探着伸手去拉他的胳膊,但猎人像躲避毒蛇一样躲开了。
“我必须去。这里管事的都是孬种。再耽搁下去,我会害了整个地铁。”
“万一还有别的机会呢?万一有药可治呢?那样的话你就没有必要……”
“还要我重复多少遍……这种病根本没药可治!要是有药的话……”
“有药的话就怎样?”萨莎紧紧抓住猎人的胳膊。
“没有药!”猎人用力甩开萨莎的手,扭头冲老人大吼,“我们走!”
“为什么你不肯把我带上?!”萨莎大喊道。
“……我害怕。”他说这话的音量极低,站在身边的萨莎勉强才能听清。
说罢,猎人猛转过身,阔步向前走去,同时头也不回地告知老人,他有十分钟时间准备出发。
“是我听错了,还是有谁生病了?”萨莎身后有人问。
“什么?!”萨莎猛一回身,和列昂尼德撞了个满怀。
“我好像听你们在谈论什么疾病。”列昂尼德一脸无辜地笑道。
“你听错了。”萨莎不想向他透露任何事情。
“我还以为是传言被证实了呢。”列昂尼德自言自语似的说。
“什么传言?”萨莎皱着眉头问。
“关于谢尔普霍夫站的临时隔离,还有什么无药可治的传染病,真是荒谬……”列昂尼德一边说,一边仔细盯着萨莎,捕捉着她嘴角眉梢的每一个细微变化。
“你一直在偷听?!”她满脸通红地喊。
“我也不是故意的,谁叫我耳力好呢。”他双手一摊,满脸无辜地说。
“他是我的朋友,”萨莎不知为何朝猎人的背影扬扬头,对列昂尼德解释说。
“不错。”列昂尼德含糊其词地说。
“你刚才说‘荒谬’是什么意思?”
“萨莎!”荷马从长凳上站起身,眼睛却一直警惕地盯着列昂尼德不放,“你过来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接下来怎么办……”
“再等一小会儿好吗?”列昂尼德礼貌地朝老人笑笑,跳到一旁,招呼萨莎过去。
萨莎迟疑地走过去,她有种感觉,跟猎人这一回合的较量她还没输,假如她现在追上去,猎人也许不会再赶她走。这样她就能够帮到他,尽管现在她还不清楚该怎么做。
“你信不信,我听说这种传染病比你要早得多?”列昂尼德注视着萨莎的眼睛,低声说,“这种病不是头一次暴发了,有种神奇的药物可以治愈。”
“可是他说,无药可治……必须把他们……”萨莎同样低声说。
“清除吗?”列昂尼德替她说出了那个可怕的字眼,“是你那个朋友说的?那我就一点都不奇怪了。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一位职业医生告诉我的。”
“你想说……”
“我想说,”列昂尼德将一只手搭在萨莎肩头,把嘴巴贴到她的耳边,低声轻语,“这个病可以治,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