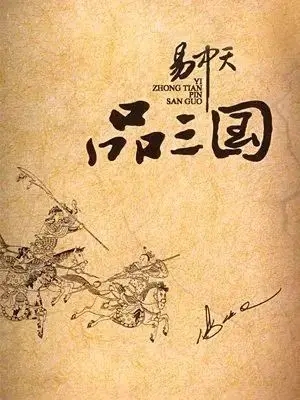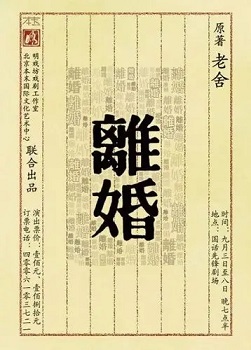到引水管站的路,阿尔乔姆不是自己走的。
飞鼠将他背在背上。他们走的是地面,不敢再下到地铁了。
阿尔乔姆已经开始咳出一些铁锈色黏液。他耷拉着双腿趴在飞鼠背上,非要下来自己走。可刚一放下,立马就跪倒在地。他用来上劲儿的发条已经松弛,而后背的发条钥匙也停止了转动。
但当他们到达花卉站时,胸口的某根小弹簧又活动起来,决定再多支撑片刻。阿尔乔姆挥手驱散眼前飘动的红影,挺直身子。他心里明白:自己来不及做很多事情,只能做完一件,最重要的一件。他抚摸一下纳甘枪的枪把。对不对?纳甘枪默认。
“带我去见萨莎,廖哈。你还记得路吗?”
“咋?你想做个风流鬼?这么急着找姑娘?不行,得先找人把你的窟窿给补补!”
补补窟窿也好。
花卉站到处是一片奇特景象。
整个站台挤满了逃亡的帝国公民,他们如丧考妣,可怜兮兮,狼狈不堪。酷似铁路工作者的帝国制服显然是湿透了又用身体烘干的,皱皱巴巴,而且显得小了,好像原本是供小孩子们玩过家家的戏服,结果大人们却披在身上当起真来。他们一个个鼻青脸肿,沾满了泥巴,钉了铁掌的皮靴也开裂了。
“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廖哈向相识的妓女们打听。
“帝国全淹了,普希金站塌了。都怪塔吉克人,挖洞时挖偏了。普希金站一塌,其他站也跟着塌了,帝国整个都被淹了。”
“塔吉克人挖偏了……”阿尔乔姆歪嘴一笑,“把错全推到塔吉克人身上,这帮下三滥。”
“所有人都跑出来了。特维尔站的跑到了马雅科夫斯基站,契诃夫站的就跑到这儿来了。”
“那战争呢?”
“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活该,阿尔乔姆想。说不定,上帝真的能够听见人们的咒怨。有人,也许就是阿尔乔姆帮忙收尸的那个女人,在被看守用钢筋敲碎脑壳之前向上帝打了小报告。上帝掐指一算,帝国有多少罪人,又有多少无罪者,然后命令将帝国关闭查封。只是早知如此,当初为什么要让它开张呢?
荷马怎么样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老头,从契诃夫站来的?”阿尔乔姆扯住一位帝国制服问,“他叫荷马。”
被问话的人一个个匆忙躲避。
阿尔乔姆被带到了之前那位女医生那儿,她在阿尔乔姆背部的伤口中发现了一些出血的溃疡,伤口来自带刺钢鞭,而溃疡则来自铁锥子一样的地表辐射。她说,活不久了,需要立即输血,但她只是性病医生,没法输血,也没血可输。她把子弹头抠出来,一边责骂阿尔乔姆,一边用酒精纱条给他塞住伤口,还给他吃了一些过期的止痛片。吃完阿尔乔姆感觉好些了。萨韦利的药片原来是从这儿拿的。
“我们现在怎么办?”飞鼠问,“应该给你找个像样的医生。我把你的血还给你,连本带利一起。”
“不,我要去找萨莎,”阿尔乔姆吃完止痛片,长了精神,“完事再说输血的事。”
“我也去,嘿嘿,”廖哈挤眉弄眼地说,“我也需要输点液。”
“我要是你,阿尔乔姆,我就会祷告。”飞鼠摇着头说。
“别说这些丧气话。”阿尔乔姆说。
“给你点儿子弹。”
阿尔乔姆收下了。
“你要回去自首?”阿尔乔姆盯着飞鼠的斗鸡眼问。
“不,老头子是不会宽恕逃兵的。”
“要是你把我交出去呢?”
“那你的阿妮娅还不得把我给活剥了,那样更惨……好吧,我在这儿也有个相好的,就在那边。等你完事,就来找我。”
“要我送你吗?”廖哈问阿尔乔姆。
“不用。我想起路来了。”
三人就此分手。
阿尔乔姆一瘸一拐地走开,直到隐没在人群中才回头查看:他们真的走了吗?眼下这件最重要的事,他不希望任何人插手。花卉站鱼龙混杂,谁知道哪个是红线克格勃,哪个是游骑兵特工,哪个是汉萨间谍呢?他们都在搜捕他,毫无疑问。
阿尔乔姆将右手插进裤袋,紧紧握住纳甘枪。
不料,萨莎的房间上着锁,里面没人。
他担起心来:不会是别索洛夫把她抓走了吧?还是遭遇了更坏的事?
斜对面有一个仅容二三酒客的小酒馆,门帘用干草结成,从顶棚垂到地面。坐在里面可以透过干草门帘监视萨莎的房间,还不容易被人发现。
阿尔乔姆坐在酒馆里,监视着上锁的房门。他本来想着萨莎,结果却想到了阿妮娅。符拉迪沃斯托克,海洋,真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她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呢?要是他早知道这些,也许他们会过得更融洽些。
旁边有两个落汤鸡一样的帝国公民在絮絮叨叨。他们不住地用狐疑的眼光打量阿尔乔姆。阿尔乔姆试图激起对他们的仇恨,却怎么也做不到:情绪储备早在共青团站就已经耗尽了。为了打消怀疑,他点了一杯酒来辅助止痛片。至于食物,非但不能看,想想都觉得恶心。
“迪特马尔……”这个字眼从断断续续的谈话声中传到了阿尔乔姆耳朵里。
迪特马尔……
阿尔乔姆犹豫了一下,终于下定决心。
“你们认识迪特马尔?”
“你是谁?”
“有个叫伊利亚·斯捷潘诺维奇的人为他做事,要帮他写一本书,跟他一起的还有一个人,名叫荷马,是我朋友。”
“我问你是谁。”
“我为迪特马尔执行过任务,”阿尔乔姆压低声音说,“在大剧院站。”
“特工?”其中一个士兵坐到身边来。
“破坏者。”
“迪特马尔已经英勇——”
“我知道。”
“他所有的下线都转移到我这边了,今后你跟我做事,我叫迪特里赫。”
阿尔乔姆听起来觉得好笑。他现在看迪特里赫的视角,几乎是从云端俯视的。从那个高度看去,很多事情都显得好笑。
“老兄,”阿尔乔姆用手背擦了擦嘴角,给迪特里赫看了看他稀薄的血液,“让我安安生生地死吧。”
“辐射病?”迪特里赫会意地起身离开,“你就是那个被雇用的潜行者?”
为防不测,阿尔乔姆在桌子底下将裤袋里的左轮手枪往外拽出一点,以免击锤钩住衣服。
“你知道荷马吗?”
“你难道没死在大剧院站?”
“你不是看见了么?”
看来,迪特马尔是擅作主张将他关进“生存空间”的。
“好吧,既然你给帝国效过力……”
“小声点,隔墙有耳。”
“他们也在这儿。都逃出来了,就在旁边喝酒呢,两个都在,也是我的属下。我带你过去?”
“好。”
荷马还活着。感谢上帝。我得先找到他,等着我好吗,萨莎?
大限将至的人是他,阿尔乔姆,而荷马并不急于离开人世。至少应该告诉荷马,让他记到自己的笔记本里:关于无线电塔,关于尸坑,关于黑暗隧道,关于蘑菇,关于子弹,关于卖身投靠的游骑兵,还有最主要的、最神圣的——世界还活着。
你不是想要历史吗?这就是历史。
闹了半天,老人就坐在离他二十米远的地方。他正和伊利亚·斯捷潘诺维奇一起,愁眉苦脸地喝着闷酒。
一看见阿尔乔姆,老人立刻两眼放光。
老人蓬头垢面,银白色头发在秃了顶的脑袋周边围了一圈,被昏黄的灯光一照,俨然金色光环。他看上去状态不错,怀里仍然抱着奥列格那只母鸡,它没被人拗断脖子,也没被人炖了鸡汤,它甚至被帝国的饲料喂肥了,油光发亮的,小畜生。
阿尔乔姆走上前去,抱住了老人。俩人多长时间没见了?有一年了吧?
“你还活着,大爷。”
“你也是,阿尔乔姆。”
“你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就这样呗。我们开始跟伊利亚……工作了。”荷马望了一眼阿尔乔姆身边的迪特里赫,“您好。”
“进展如何?”阿尔乔姆问伊利亚。
“很好,”伊利亚看着迪特里赫回答,“正在写,很顺利。”
“那就好。走吧,大爷,咱们走走?谢谢,”阿尔乔姆冲迪特里赫点头致意,“没齿难忘。”
迪特里赫本来打算监听二人的谈话,但他在酒馆里点的蘑菇眼看就要凉了,更何况现在连帝国似乎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许离开站台半步!”他严厉命令道,“等待进一步指示。”
二人走过一个个小房间,走廊里的妓馆如同珠串一般。上哪儿去找个僻静的角落?
“书在写吗?”阿尔乔姆向荷马确认。
“不太顺。”
“为什么?”
“伊利亚的妻子,纳丽奈,上吊死了。他现在整天醉酒。”
“什么时候死的?”
“嗯,我们刚写了两天,可是……元首要求……他每天都亲自来视察,阅读,询问进度。我只好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不过伊利亚答应,可以把我算作合作者,封面署名什么的。可以吧?”
“嗯,”阿尔乔姆看着荷马,“元首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怎么说呢……就日常而言……很普通。”
“很普通,好吧,真是再普通不过了。”阿尔乔姆冷笑一下,又问,“书里快写到变种人了吗?”
“还没有,”荷马将视线投向旁边,“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写完。所有人都跑散了,帝国快完了,元首也躲起来了。”
母鸡伸展翅膀,作势飞起,熟知它恶习的荷马将手臂伸直,把它抱远些。母鸡身子一缩,在地上拉了一坨屎。
“还下蛋吗?”阿尔乔姆问。
“不下,闹情绪呢。”老人无奈地笑了,“鸡蛋壳都不知道吃了多少了,可就是不下蛋。”
二人边走边聊,走过了很多愁眉苦脸的帝国公民和精神焕发的妓女,耳边传来嗯嗯啊啊的叫喊。
“至少你良心上不用感到不安,”阿尔乔姆感觉倾诉的欲望压倒了疲惫,“现在你可以着手写你自己的书了,你的夙愿。”
“没有人会刊印的。”
“这要看你写什么了。”
“我能写什么呢?”
似乎有人在跟踪他们。阿尔乔姆回头,再回头,但那人好像凭空蒸发了一样。也许他并非在跟踪他们,而是来寻花问柳的,要么就是躲起来了。
阿尔乔姆把手放到纳甘枪上。
“你找到你的萨莎了吗?”
“萨莎?没有。你……”
“她就在这儿,大爷,昨天还在。我跟她讲过话,提起过你。”
“你知道她在哪儿?”
“知道。”
“她还好吗?我们去哪儿找她?她,她在这儿……干什么?”
“女人在这儿还能干什么,大爷?工作。”
“胡说!萨莎?……我不信。”
“好吧。”
“这不是真的!”
“那你告诉我……猎人的事是真的吗?他酗酒的事?我之前都不知道你们俩认识。”
“猎人?你认识他?怎么会?”
“就是他派我去远征、去寻找导弹的,就是对抗黑暗族那次。我没跟你说过?他也没说过?他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才酗酒的?因为黑暗族?还是另有原因?”
“我不知道。他……我跟他其实很少说话。说得不够多。”
“你那本书不就是写他的么,笔记本上那个。那是怎么回事?”
“那个,他,你知道么……不是真正的英雄?但我想把他塑造成英雄,好让人们读完之后受到鼓舞。”
“所以你才把他写成不酗酒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告诉你了么,都是萨莎跟我讲的?你难道不信?”
“我要去见她,我要亲眼见到她。”
“稍后再说,再等等。我有重要事要讲。嗯,这里好像没人……进来。等一下,我先检查一下……”
“至于猎人……没错!可谁愿意看一个酒鬼的故事呢?又有谁会想要追随他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需要为人们创造神话,美丽的神话。人们活在黑暗中,没有希望,他们需要光,不然他们会完全堕落的。”
“明白。现在你听我说。”阿尔乔姆凑向老人,对着他的耳朵热切地低声说,“人们之所以生活在黑暗中,大爷,是因为有人把光藏起来了。西方没有毁灭,大爷,俄罗斯也没有完全毁灭,还有其他幸存者,几乎整个世界都幸存下来了。我虽然不知道他们那里过得怎么样,但是……符拉迪沃斯托克、你的极地曙光城、巴黎、美国,都还活着。”
“什么?!”
“它们全被藏起来了。有人设置了无线电干扰器,莫斯科周围全是,用无线电塔将来自其他城市的信号全屏蔽掉。”
“什么?”
“是汉萨干的。游骑兵也知道,他们给汉萨做事,把所有来自外部世界的人都清除掉。他们到处搜捕,然后消灭,所有试图跟外界联络的人都被灭口了,所以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而红线,据我猜测,帮汉萨建了风力发电机,在巴拉希哈。那里有很多巨大的风力发电机,负责给干扰器供电。他们还用挖土机挖了一个庞大的基坑,里面填满了尸体,五条腿的野狗不断啃噬他们。死人里有建筑工人,也有外来人。作为回报,汉萨向红线支付子弹,两万发子弹,你能想象得到吗!红线就用这些子弹屠杀暴动的饥民,朝着人群扫射,人们迎着机枪走,乞求蘑菇,成片成片地倒下去……他们什么都听不进去。我朝他们喊:‘你们可以离开这里,逃离地铁!地面上有活生生的世界!走吧!’可他们非要去汉萨,迎着子弹……你必须把这些全部记下来,记到笔记本里。对了,还有,他们对所有人撒谎,说什么必须把人们藏起来,因为周围全是敌人,说什么战争仍在继续,但这全是扯谎,我敢肯定。至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顺利的话,我会查清楚的。但你暂时先这么写,好吗?写下来,好让人们知道。这很重要。”
荷马把耳朵移开,认真地凝视阿尔乔姆,仿佛正在凭借触感排除牵引地雷一样。他极力隐藏着流露出的些许同情,因为他明白,同情最容易上钩。
“你感觉怎么样?”荷马问,“老实说,你看上去很糟糕。”
“我活不久了,也许就还剩下一个星期了。所以你一定要写下来,大爷。”
“写什么?”
“我刚才跟你说的一切。”
“好吧。”荷马点了点头。
“你都听明白了?要不要我再讲一次?”阿尔乔姆用那条好腿支撑着站起身,探身朝过道望了一眼。
“不完全明白。”
“哪里不明白?”
“嗯,那个……都不太……听起来有点奇怪……我说实话。”
阿尔乔姆将原本前倾的身子坐直,从一定距离审视老者。
“你不相信?你也认为我是疯掉了?”
“我没这么说……”
“听着。我知道这一切听起来很疯狂,但这才是真相,明白吗?相反,你所知道的关于地铁的一切,什么地表没有生命,我们无处可去,什么红线反对汉萨,汉萨全是好人,所有这一切,全是谎言!只不过我们在谎言中生活了太久……”
“要是有那么一两个城市幸存倒还罢了……”荷马皱起眉头,尽力试着去相信阿尔乔姆的话,“但整个世界?还有干扰器,汉萨……”
“无所谓。你就先记住我说的,以后再写下来也行,好吗?我很快就要死了,大爷。我不希望这些都随着我消失。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听见了吗?这些都是我查出来的。如果你——你!——不把这些写进你的笔记本里,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今天我就要……不提了,也许我做不到。但是你,你可以做出一些改变。你会这样做吗?会写吗?”
老者吧唧着嘴,抚摸着母鸡。母鸡昏昏欲睡。
“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有谁会刊印这种东西呢?”
“你管它会不会印呢?”
“不印,人们上哪儿知道去呢?”
“大爷!难道就非得刊印不可吗?荷马——那个真正的荷马——他甚至连写都没写,他是个瞎子!他只是用嘴讲述,歌唱……而人们听他讲,听他唱。”
“那个荷马,的确,那个真正的荷马。”老人苦笑着重复说,“好吧,我会写。而你需要去看医生。你说的那叫什么话——什么就还剩一个星期!我们现在……你带我去见她好吗?”
“谢谢,大爷。我回头再告诉你……详情,等我搞明白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我给你口述。”
荷马一路上都没说话,舌头上像沾了什么东西似的,一直不停地嘬舌头,终于还是怯懦道:“有这么个事,我给他们的报纸写了两篇小文章,被逼的,你知道的……关于席勒站的爆炸……”
“又不是你自愿的。”阿尔乔姆说。
“不是自愿的。”
****
他们回到小酒馆。
迪特里赫和同伴已经吃完饭,离开了。萨莎的小房间里传出窸窣的声音。她没出事,一切正常。
“萨莎就在里面。”阿尔乔姆说。
两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在干草门帘后面坐下,各自盯着自己的杯子。荷马如坐针毡,不住地咳嗽。阿尔乔姆倾听着自己的内心:他听见风在呼啸,转动铁的桨叶,吱呀作响,转化为力量,支撑他在世界上再多活一段时间。你们在哪儿呢,白肚子的空中飞船?你们要顺着这股风飞去哪里?他吞一口酒,将杯子里的粉红色液体搅动得四散开来,而在阿尔乔姆的内心深处,是如同私酿酒一般的混浊液体。一阵睡意汹涌袭来。他有多长时间没睡了?一天一夜?
声音止息了,一个糟老头子提着裤子走出来,脸上带着征服者的笑容。
荷马腾的一声站起身,扔掉母鸡,朝萨莎奔去。
“萨莎?!”
“荷马……你?……”
阿尔乔姆坐着没动。这场对话与他无关,但也没法充耳不闻。
“上帝啊……你真在这儿。为什么?萨什卡……”
“我挺好的。”
“我……我还以为你死了……我在图拉站找了你那么久……”
“对不起。”
“你为什么没跟我说?没来找我?”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阿尔乔姆,你认识他吗?他带我来的。”
“他在这儿吗?”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萨莎?为什么干这种肮脏勾当?”
“谁说这就肮脏呢?”
“你不能这样,不能做这个,你去……收拾东西,我们离开这儿。”
阿尔乔姆抚摸着纳甘枪的转轮。现在还不行,大爷。得等明天,后天,等别索洛夫来找她,逼他说出答案,然后再随便去哪儿。好吗?母鸡看着他,歪着脑袋。
“去哪儿?我哪儿也不去。”
“为什么?有人不放你走?你被奴役了?我们可以……我去求……”
“不必。”
“我不明白!你可以干别的挣钱……是需要拿钱赎身吗?”
“我没有被奴役。”
“那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
“我属于这里。你还是说说你自己吧,你怎么样?嗯……猎人呢?”
“我不知道,上帝……什么叫你属于这里?”
“这里有人需要我。”
“你说什么蠢话!你还没到十八岁呢!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这里是妓馆!窑子铺!所有这些臭男人……我不能再让你这么下去了!我们走!”
“不。”
“跟我走!”
“放开我!”
母鸡在一旁为荷马提心吊胆,而阿尔乔姆却袖手旁观。他无权干涉。再说,他该站在哪一边呢?
“你不应该!你没有权利干这个!”
“说得好像这是地底下最糟糕的事似的。”
“你……可怜的孩子,我把你弄丢了……是我的错……”
“不是你的错,你又不是我爸爸。”
“我……你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你不应该!”
“你不是以为我死了么?那你就当我死了好了。妓女不妓女的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是!妓女!”
“那我是谁?”
这时一个人走到门口停下。后脑勺剃得精光,满是褶子,上身穿着立领皮夹克。他是保镖吗?来给主人探路的?阿尔乔姆揉揉眼睛,身子稍向前倾,左右看了看,试图在人群中寻找别索洛夫——黑发,分头,眼袋。
“你总不该为了子弹就……让人……你之前不是这样的!”
“好吧。可我现在就是这样的,行了吧?”
“不行!这太脏了!”
“那你就把我写成另外的样子好了,照你喜欢的样子写。我靠什么为生,又有什么区别呢?猎人到底怎样,又有什么区别?”
“这跟猎人有什么关系?”
“你的书写完了吗?结局是什么?图拉站发生了什么?”
“洪水!发大水了。”
“你不是说发生了‘奇迹’么?”
“那个不是最终版。”
“但你终究还是把屠杀改成了奇迹。那就把我也改改好了,把我改成圣女。对不起,我的客人马上要到了,我是按预约登记接客的,跟医生一样,你把我改成医生也行。”
“我不走!”
后脖子满是褶子的人听完二人的对话,啐了一口,走掉了。阿尔乔姆瘫软下来,用手指抚摸着母鸡丽巴。母鸡在打盹,而纳甘枪却清醒着。
****
止痛片和酒精的双重作用使眼前的一切天旋地转,也摇晃着阿尔乔姆脖子上没有安牢的脑袋。荷马终于出来了,魂不守舍,如同被兜头浇了一瓢冰水,又或者被电流击中了一般。
“她为什么要这样?”
“你去吧。走吧,大爷。让我来跟她谈谈,回头我们再碰面。就还在那个小酒馆好了,你跟伊利亚喝酒的那个。代我向他致哀。”
“你、你也跟她……?”
“你看看我这个样子,我能行吗?我有话对她讲。”
“带她离开这儿,阿尔乔姆,你是个正直的好小伙子。带她走。”
“正直……好吧。”
阿尔乔姆敲敲门。萨莎已经听到他说话了,因此并不意外。他踉跄着走进屋。
“你好。”
“你回来了!你去过巴拉希哈了?”
“去过了。”
“你脸色好差,快坐下。想喝点什么吗?水?到这边来。”
她看上去出人意料地干净、清新,什么脏东西都沾不到她身上。就在刚才,她还在被人蹂躏,可只消整整头发,她就又焕然一新了。她是怎么做到的?
“那里……那里有干扰器,在巴拉希哈。”
“什么干扰器?”
“萨什卡,那个男人,你管他叫主人的那个……别索洛夫……”
“等会儿,你这儿是怎么了?上帝啊,多么可怕的溃疡,还有这儿……你好烫,你在发烧。”
“等等,你在听吗?那个别索洛夫,他是什么人?”
“你带了枪。”
“他什么时候来?”
“真可怜。你身体更差了,是吗?”
“那个变态,那天晚上是不是他,利用了你,也利用了我,看着我俩那个?”
“应该说,是介绍我俩认识。”
“听着,你听我说,他什么时候会来?我要和他谈谈,必须谈谈。”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那个,是他在操控这里的一切:红线,帝国,连梅尔尼克都被他捏在手心里。我必须搞清楚,他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把我们都关在地铁里,他有什么计划,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
“你看,你的烫伤疮痂已经干结了,我帮你揭下来?”
“你之前说……这是我自己烫的?”
“对。”
“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为什么?”
“你跟他,跟阿列克谢,聊完天,就这么做了。”
“聊完天?就是说……因为游骑兵?我把游骑兵的誓言烫掉……因为他告诉了我游骑兵现在干的勾当?”
“想起来了?”
“这么说,你全知道?”
“阿尔乔姆,你想躺一会儿吗?你都快站不稳了。”
他贴着墙壁蹲了下来。
“为什么你不跟我说?为什么打发我去巴拉希哈?”
“你在这儿什么都做不了,阿尔乔姆,除了偶尔用烟头烫烫自己,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关于干扰器,关于幸存的世界,你都知道?”
“是的。”
“他什么时候来?啊?!”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不是说你能感应到他吗?告诉我!”
“你想把他怎么样?”
“你把我藏起来,求你了,把我藏在这里。”
“好。”她在他身边蹲下,轻柔地抚摸着他光秃的双鬓、头顶,“你就坐在布帘后面好了。”
萨莎拉上了布帘。
“还来得及。一切都还来得及……”阿尔乔姆低声念叨。
他凝视着布帘上无数的花朵,每一朵花的中央都能看见一个后脑勺,汇成了一片后脑勺的花海。那是密密麻麻的红线饥民,无面人,他们活着只为了一个目的,就为了有朝一日有人冲他们的后脑勺开枪。
“为什么,”阿尔乔姆硬撑着眼皮自言自语,以免睡过去,“就算你是主人,就算你是魔鬼……你也得给我讲明白,凭什么这样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对人们……为什么我们要窝在这里……你要是不说,我就冲你脑门来上一枪……用你的纳甘枪……正中眉心……混蛋……”
说着说着,他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