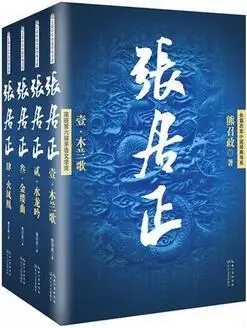足足有十五分钟没人说话。
布克先生和康斯坦汀医生尽量按波洛说的做。他们努力从迷宫一样的矛盾的细节中找到一个清晰且突出的结论。
布克先生的脑海中是这么想的:
“我的确得思考,可是那些问题我已经想过了呀……很明显,波洛认为那个英国女孩跟本案有关系,可我总觉得这不可能……英国人都非常冷漠,可能是因为他们身材不美。但这不是重点。看样子那个意大利人不可能这么做——真可惜。我觉得那个英国男仆说他房间里的另一个人从未离开过,应该没有撒谎。可是他怎么会杀人呢?贿赂英国人可不容易,他们那么难以接近。整件事简直倒霉透顶。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总得做一点救援工作。这些国家做事这么慢……做什么事之前先得想上几个小时。还有这些国家的警察,他们最不好应付了——自高自大,暴躁易怒,还摆出一副有尊严的样子。他们会把这件事闹大,因为他们难得有这么个机会。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刊登着……”
接下来,布克先生的思路又沿着他们已经走过几百次的老路走下去了。
康斯坦汀是这么想的:
“他真奇怪,这个小个子。一个天才,还是一个怪人?他能解开这个谜题吗?不可能——我看不到出路。这一切都太混乱了……没准,每个人都在撒谎……可是就算这样也没用。如果他们全都在说谎,可还是那么让人迷惑,好像他们都在说真话。关于那些刀伤的说法很古怪,我无法理解……如果他是被枪打死的,就容易理解了——毕竟,‘带枪者’这个词意味着他们得有把枪。美国是个奇妙的国家。我真得去那里看看。真是先进啊。我回到家一定得找到迪米特里厄斯·扎刚——他去过美国,有一脑子的新鲜玩意儿。不知道他现在正在做什么,要是我老婆知道了……”
他的思维已经完全走向了个人问题。
赫尔克里·波洛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
别人可能会以为他睡着了。
忽然,经过一刻钟的静默之后,他的眉毛开始慢慢地舒展开来,轻叹一声之后,他蚊子般地咕哝道:
“可是,毕竟,为什么不呢?而且如果是这样——嗯,如果这样,一切就能解释清楚了。”
他睁开了绿得像猫眼一样的眼睛,轻声说:“好啦,我想完了。你们呢?”
思绪飘到九霄云外去的两个人,开始大声地说了起来。
“我也想完了。”布克先生脸上蒙上了一层羞愧的阴影,“但是还没有得出结论。解释这个案子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朋友。”
“我也费尽心思很努力地想过了,”医生说,厚颜无耻地回想着刚才自己脑子中的色情细节,“我想了各种可能性,不过一个也不满意。”
波洛和蔼地点点头,像是在说:
“非常好。这么说就对了,你们已经给了我需要的提示。”
他坐得笔直,挺着胸脯,摸着小胡子,像演说家发表公开演讲那样说道:
“朋友们,我把脑子里的事实都检查了一遍,也考虑过旅客的证词,然后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很模糊,但我看到了某种掩盖我们已知事实的解释。这是个非常奇怪的解释,我还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为了证明其正确性,我得做几个试验。
“首先我说几点看起来对我有启发性的问题。让我先从和布克先生在这个地方一起吃午饭时,他给我讲的一句话开始说起吧。他说我们周围都是一些不同阶层、不同国籍、不同年龄段的人。这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确实是很少见的。比如,雅典-巴黎,布加勒斯特-巴黎这两节车厢几乎是空的。别忘了,还有一个旅客没出现。我认为这个人值得注意。另外,还有几个小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哈巴特太太洗漱包的位置,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哈德曼先生的侦探手法,麦奎因所说的是雷切特自己烧毁了我们发现的焦了的纸片,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的教名,以及匈牙利人护照上的油迹。”
两个人凝视着他。
“这些问题对你们有没有启发?”波洛问道。
“一点没有。”布克先生坦白道。
“医生,你呢?”
“我连你说的是什么也没弄明白。”
布克先生赶紧抓住他朋友提到的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问题,在一堆护照中分拣起来。接着,他咕哝一声,拿起了安德雷尼伯爵夫妇的护照,打开。
“这就是你说的吗,这块污渍?”
“是的,这是一块刚滴上去的油迹。你注意到它在什么地方吗?”
“在伯爵夫人姓名一栏的前端——准确地说,是她的教名。可我承认我还是没弄明白。”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块手帕上面。就像前不久我们说过的那样,三个人跟这个字母有关系:哈巴特太太、德贝纳姆小姐和女仆希尔德嘉德·施密特。现在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看这块手帕。我的朋友们,这是一块非常昂贵的手帕——一件奢侈品、手工制作、巴黎刺绣。这些旅客中,先不说姓名首字母,哪一个人有可能拥有这么一块手帕?不是哈巴特太大,她是个举止得体的女人,不喜欢在衣着上表现得很奢侈。不是德贝纳姆小姐,那个阶层的英国女人都用雅致的麻布手帕,而非昂贵的、可能要花掉两百法郎的棉纱手帕。而且肯定不是女仆。但是火车上有两个女人有可能用这种手帕。总之,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把她们的名字跟字母H联系起来,我说的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
“她的教名是娜塔丽亚。”布克先生挖苦道。
“对极了。而且她的教名,正如我刚才所说,显然具有启发性。另一个人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那么我们就会马上想到——”
“只有你!”
“好吧,是我会马上想到。她护照上的教名被一块油迹弄糊了。只是个意外,任何人都会这么说。可是,想一想那个教名。埃伦娜[英文为Elena]。假设,不是埃伦娜,而是海伦娜[英文为Helena]。大写的H可以改成大写的E,就能轻易地盖住旁边那个小小的e,再弄一块油渍掩盖这种改变。”
“海伦娜!”布克先生喊道,“想法真不错。”
“当然是个好主意!我到处寻找我这个想法的证明,不管多么微小——并且找到了。她行李箱上的一个标签有些潮湿,正好在箱子上面的首字母上。标签是用水浸湿之后,揭下来又贴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开始说服我了,”布克先生说,“但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当然——”
“啊,现在,我的朋友,你必须转变观念,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探索这个案子。凶案本来应该怎样出现在众人面前呢?别忘了,大雪打乱了凶手的原始计划。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大雪,火车就会正常行进,那么,会发生什么?”
“可以说,凶手十有八九会于今天早上在意大利边境被发现,意大利警方同样会获得很多相同的证词。麦奎因先生会说出那些恐吓信,哈德曼先生会讲他的故事,哈巴特太太会急切地说出有个男人经过她的房间,纽扣也会被发现。我想,只有两件事会有所不同。那个男人会在一点之前穿过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而列车员制服会被扔在一个厕所里。”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凶杀案原本计划得像是外面的人干的。凶手原本打算等火车零点五十八分准时到达布罗德时下车,有人可能会在过道上碰见一个奇怪的列车员,制服则被扔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样人们就能看清凶手设计的骗局。这样所有的旅客都不会有嫌疑。我的朋友,凶案原本是想以这样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但是大雪改变了一切。毫无疑问,我们已经知道凶手为什么在房间里跟受害人待这么久了,他在等火车继续往前开。但是他最终意识到火车开不了了,必须另行制订计划。现在已经知道凶手仍然还在火车上。”
“没错没错,”布克先生不耐烦地说,“这些我都明白。但是手帕从何而来?”
“我会用比较曲折迂回的方式解释给你听。首先你们得意识到那些恐吓信有些瞎蒙的性质,可能是从一本差劲的美国侦探小说里抄的,不是真的。实际上,只是给警方看的。我们必须问自己的就是:‘它们骗到雷切特没有?’表面上看是没有。他给哈德曼的指令好像指的是一个明确的‘个人’的敌人,他完全掌握了敌人的身份,前提是我们认为哈德曼的故事是真的。但是雷切特确实收到了一封风格迥异的信——内容包含阿姆斯特朗小孩的信,也就是我们在他房间发现的碎片。万一雷切特没有及早意识到,就要确保他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一直在说的那封信,凶手没打算让人发现,他首先关心的就是烧掉这封信。然而这是他计划中的第二个障碍。第一个是大雪,第二个是我们复原了那封信。
“如此小心地烧毁那封信,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火车上一定有人跟阿姆斯特朗家有密切的关系,而发现那封信,就会直接导致那个人受到怀疑 。
“现在,我们说说发现的另外两条线索。我先略过烟斗通条的问题,因为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我们说说手帕的问题。很简单,这条线索直指名字首字母为H的人,而且是那个人无意中掉落的。”
“非常对。”康斯坦汀医生说,“发现手帕掉了之后,她会立即采取措施隐瞒教名——”
“你还真是快!你这么快就得出结论了,我可还不敢允许自己这么说。”
“还有其他结论吗?”
“当然有。比方说,假如你犯了罪,并且想嫁祸于人,而且,火车上有一个人跟阿姆斯特朗家关系密切——是个女人。假如,那时候你留在那儿一块属于那个女人的手帕,她就会受到讯问,她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就会公开——就是:动机——也是与案子有牵连的证据。”
“但是在这个案子中,”医生表示反对,“清白的嫌疑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掩饰身份。”
“啊,真的吗?你是这么认为的吗?这正是警方的观点。但是我了解人性,我的朋友,面对突如其来的谋杀审讯,就算最清白无辜的人也会失去理智做出最荒唐的事情。不,不,油迹和修改过的标签不能证明安德雷尼伯爵夫人有罪——只能证明她由于某个原因而急于隐瞒身份。”
“你觉得她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什么关系?她说她从未去过美国。”
“确切地说,她的英语带有外国口音,相貌也像个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是相对于美国人而言],只是有些夸张。但是不难猜到她是谁。刚才我说过阿姆斯特朗太太母亲的名字,叫琳达·阿登,她是个非常著名的演员,尤其是作为一个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员。想想《皆大欢喜》中的阿登和罗莎琳德森林。她给自己取名字的灵感即来自于此。那个让她享誉全球的名字,‘琳达·阿登’,并非她的真名。她的本名可能是戈尔登贝格,在她身上,很有可能流淌着中欧人的血,也许掺有犹太人的血液。很多民族都漂泊去了美国。我提示你们一下,先生们,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就是埃伦娜·戈尔登贝格,琳达·阿登的小女儿,惨剧发生时她还是个孩子,后来,嫁给了在华盛顿当使馆专员的安德雷尼伯爵。”
“可是德拉戈米罗夫公主说,她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可是他的名字她却不记得了!我问你,我的朋友,可能吗?德拉戈米罗夫公主爱琳达·阿登,就像贵妇人爱伟大的演员一样。她还是这个演员其中一个女儿的教母,这么快就忘记她女儿的夫姓了吗?不可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她在撒谎。她知道埃伦娜就在火车上,还见过她。听到雷切特的真实身份时,她马上就意识到埃伦娜会受到怀疑。所以我们问到阿姆斯特朗太太的妹妹时,她立刻撒了谎——模糊了,记不得了,但是认为埃伦娜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与真相相去甚远的说法。
一个餐车服务员从另一边的门口进来,走到他们前面,对布克先生说:
“吃饭了,先生们。要送上来吗?已经做好了一会儿了。”
布克先生看看波洛,后者点点头。“一定要开饭。”
服务员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传来他按铃的声音以及大喊声:
“头等厢,开饭了,开始供应晚饭——第一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