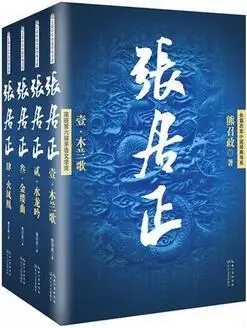直到这时为止,横贯智利的人们还没有遇到任何严重的意外。但是现在,爬山旅行难免要碰到的障碍和危险都同时来了。与自然界各种困难作斗争就要开始了。
有个重要的问题必须在出发前先解决:由哪条路可以越过安达斯山脉而离不开原定的路线呢?大家问向导。
“在这一带高低岩儿我只知道有两条路可走。”他回答。“一定是过去曼多查发现的阿里卡那条路?”巴加内尔说。
“一点不错。”
“和维腊里卡岭以南的也就叫作维腊里卡的那条路?”
“正是。”
“那么,朋友,这两条路都有一个毛病,不是过于偏北就过于偏南。”
“你能提出另一条路吗?”少校问。
“有,那就是安杜谷小道,它的位置在火山的斜坡上,南纬37度30分的地方。就是说,离我们的预定路线只差半度。这条小道是以前查密雕·得·克鲁兹探出来的,高仅2000米差一点。”
“好,这条安杜谷小路,你认得吗?”爵士问向导。
“认是认得的,爵士,这条路我也走过,我所以没有提到它,是因为它是小径,最多也只能勉强通过牧群,是山东麓的印第安畜牧人走的。”
“那么,朋友,白环什人的牛马能走的地方,我们就能走。
既然这条路仍旧在直线上,我们就走这条小路吧。”
立刻,动身的信号发出了,全队人马钻进了拉斯勒哈斯山谷,两边都是大丛的结晶石灰岩,路随着一个几乎感觉不到的斜坡逐渐升高。大约11点光景,要绕过一个小湖,这小湖是一个天然蓄水池,是附近所有小河的汇流点,风景极佳。河水汨汨地流到这里,便消失在一片恬静中。湖上是一层一层的高原,长满了林草,印第安人的牛羊群就在那里放牧。过了这里是一片南北横亘着的沼泽地,由于骡子有跨过沼泽地的本领,大家安然渡过了。午后1点,正从巴勒那堡旁边绕过。山坡已经逐渐陡起来,石头嶙嶙的,石子在骡脚下滚着,形成一种哗啦啦的碎石瀑布。快到3点钟的时候,又是许多1770年土人起义中毁掉的残壕废垒。这些遗迹充满了画意。
“真的,高山还不够把人们隔开,还要加上碉堡呀!”巴加内尔说。
从这地方起,路不但很难走,而且很险。山坡的坡度加大了,岩头的小路愈走愈窄,岸下的坑谷深得骇人。骡子谨慎地走着,鼻子贴着地,嗅着山路。人们一个一个排着前进。有时,拐了一个陡弯,“马德铃娜”不见了,旅行队就循着它从远处传来的铃声前进。也有些时候,任意曲折的山径把骡队折成平行的两行,领头的向导可以和压尾的“陪翁”谈话,其中隔着一条裂缝,宽不到20米,深达几百米以上,形成平行的两队人马中的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在这一带山地上,还有草本植物正与岩石作斗争,但是人们已经感觉到矿物界在向植物界侵略了。几块已经凝固的熔岩,呈着铁青色,耸起针状的黄色结晶,人们一看就知道离安杜谷火山不远了。岩石一层层地堆砌着,摇摇欲坠,不符合任何平衡定律,却还能互相支撑着攀附着,还不会崩倒下来。很明显地,只要有轻微的震动,这些岩石就会改变样子的,我们看到这些倾斜的尖峰,歪倒的穹窿,偏颇的圆顶,就知道这些地区的山势还没有定型。
在这种条件下,是很难辨认的。安达斯山的巨大骨架几乎不断地在摇动,因此常常改变着通行的路线,昨天认路的标识点,今天可能就不在原位置了。所以向导常常搞不清楚。停下来看看四周,辨认岩壳的形状,在那些易碎的石头上找着印第安人走过的痕迹,因为要辨别方向是毫无办法的呀!
爵士一步一步地紧跟着向导。他了解并且感到向导的烦恼随着路径的困难在增加。他不敢问他,他想:骡夫应该和骡子一样,也有识路的本领,因此还是信任骡夫好,他这种想法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整整一个钟头,向导可以说是在彷徨着,但总是渐渐进入更高的地带。最后他不得不干脆下来。那时他们正走进一条不很宽的山谷,这种山谷是印第安人称为“格伯拉达”的那些窄山峡的一种。一堵云斑石的峭壁,呈尖峰状,拦住了出口。那向导找了一阵,找不出路来,于是下了骡子,交叉着胳膊,等候着。爵士向他走过来,问:
“迷了路吗?”
“不是,爵士。”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安杜谷那条路上了吧?”
“我们还是在安杜谷那条路上。”
“你没认错吧?”
“没有认错,您看这里是印第安人烧篝火留下的灰烬,那边是羊群马群走过的痕迹。”
“那么,这条路是人家走过的呀!”
“是的,但是现在走不过去了,最后一次地震把这条路堵死了……”
“堵住骡路却堵不住人路呀!”少校说。
“啊!这要看诸位怎么办了,我尽了我的力量了。如果诸位愿意往回走,再在这带高低岩儿里面找别的路的话,我的骡子和我,都准备一齐往回走。”
“那不是要耽搁了?……”
“至少3天。”
爵士听着向导的话,一声不响。向导当然是按照合同行事。他的骡子不能再往前走了。然而,当向导建议往回走的时候,爵士回头看着他的旅伴们问:
“你们愿意不顾一切地走这条路过去吗?”
“我们愿意跟您走。”奥斯丁回答。
“甚至于抄在你的前面走,”巴加内尔补充说,“我们说来说去,究竟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爬过一条山脉,而山那边的下坡路容易得不能和这边相比!我们过了山,就可以找到引导我们过山的阿根廷的‘巴加诺’和惯于在草原上奔驰的快马。
不要迟疑,还是向前走吧。”
“好,向前走!”爵士的旅伴们都叫起来。
“你不能陪我们走了吗?”爵士转过头问那向导。
“我是赶骡子的呀!”
“那就随你的便吧。”
“我们用不着他陪,到了峭壁那边,我们就可以再找到安杜谷的小路,我保证把你们引到山脚下,不亚于这一带高低岩儿的一个最好的向导员。”巴加内尔说。
于是爵士和那向导结了帐,把他连他的“陪翁”和骡子一起都辞掉了。武器、工具和干粮由七个旅客分开背着。大家一致决定立刻再往上爬,必要时走一段夜路。在左边斜坡上有一条直上直下的小径蜿蜒着,骡子确实不能通行。困难的确很大,不过经过两小时的疲劳和周折,7个人又走到安杜谷那条路线上了。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真正叫安达斯山的部分,离那条巨大的高低岩儿的最高山脊不远了。但是,不论大路小路,都已无法辨认。最近的一次地震把这整个地区捣得天翻地覆,只有从山腰上隆起的石壳上一步一步地往山脊上爬。巴加内尔找不到可走的路,一时也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拚命爬到安达斯山的顶点,山顶的海拔高度平均都在3300~3600米之间。很侥幸,天气很好,天空晴朗,这个季节对行人有利。如果是在冬天,在5月到10月之间,这样爬就不可能了:严寒的气候,一下子就会把行人冻死;就是冻不死,也逃不过当地特有的那种飓风,这飓风名叫“腾薄拉尔”,每年被它刮落到那带高低岩儿的深坑里的也不知有多少。
爵士一行人爬了一整夜。那些几乎无法攀登的层层岩石,大家都用手扒着爬上去,那些又宽又深的缝穴,大家都跳了过去,胳膊挽着胳膊就算是绳子,用肩膀一个掮一个就算是梯子,这样冒着危险和困难的好汉就仿佛是大马戏团里的一群丑角,表演着空中飞人。这正是健壮的穆拉地和灵巧的威尔逊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这两名诚实的苏格兰人奔来跑去,到处出力,有好几次要不是他们两个那样的热诚和勇敢,那一小队旅客就过不去了。爵士不断地看着小罗伯尔,为他年纪小,性格活泼,叫人提心,怕他冒失出事。巴加内尔呢,他带着法国人特有的那种狂热,不断地前进着。至于那少校,他该动的时候才动,不多不少,恰如其分,他若无其事,不慌不忙地慢慢向上爬着。几小时来,他自己说不定还不觉得一直在往上爬呢,也许他还以为在下山呢。
早晨五点钟,根据气压表测算,他们已经达到2300米的高度了。这时他们是在二级平顶上,这是乔木地带的尽头。有几只野兽在那里跳跃,如果猎人遇到它们的话,会欣喜若狂的,说不定会发大财呢。这些矫健的野兽似乎也知道猎人喜欢打它们,所以远远见到人就跑。在那些野兽中,首先是那山区特产的骆马,它可以代替羊、牛、马之用,生活在连骡子也能不生存的地方。还有一种大耳龈鼠,是个啮齿类的小动物,温驯而胆小,长得一身好皮毛,形状又象野兔,又象野鼠,后腿特长,又类似袋鼠。看这种轻捷的小动物在树顶上象栗鼠一般跑来跑去,真是可爱。“它虽不是鸟儿,但是它已经不是四足动物了。”巴加内尔说。
然而,这些野兽还不是山上最高点的居民。在3000米高的地带,雪区的附近,还有成群美丽无比的反刍动物:一种是羊骆,披着丝绒一般的长毛,还有一种是无角的山羊,身段苗条,气宇轩昂,毛很细致,动物学家称为“未角羚”。不过这种小动物,你莫想靠近它,你连看也不容易看到它,它逃得和鸟儿展开翅膀一样,在白得眼花的雪层上无声无息地一溜就溜掉了。
在这破晓的时候,整个山区的面目完全变得虚幻不定。无数耀眼的大冰场,带点淡青色,在绝壁上耸立着,反射着黎明的曙光。这时爬山是很危险的。得先细心探测一下,摸到裂缝的时候,就不能冒险前进了。威尔逊已经跑到队伍的前面做先锋了,他用脚试探着冰面。同伴们都谨慎地踏着他的脚印子走,并且避免高声的谈话,因为声音稍微大点就会动荡空气把悬在头上七、八十丈高的大雪团震落下来。
他们已经到达灌木地带了,再爬上250多米,灌木都要让位给禾本草类和仙人掌类了。到了3300米高度的时候,连这些东西也没有了,植物都完全绝迹。旅客们只在8点钟时歇了一次,简单地吃点东西恢复恢复体力,然后又鼓起勇气冒着更大的危险继续向上爬。又要跨过刀尖一般的冰棱,又要爬过那令人看也不敢向下看的深坑。好些地方路边都插满了木头做的十字架,这说明这地方不断发生不幸的事故。午后快到2点时,一片光秃、荒凉得象沙漠一般的平地展开在险峻的峰峦中间。空气是干燥的,天空是蓝色的。在这种高度上,雨从来没有过,水蒸气只会变成雪和冰雹。零零落落的云斑石或雪花岩的峰岭就象残骸的朽骨突破白色的裹尸布,有时候,硅石或片麻石的碎块,被风吃脱了,以深厚的声响滚下去,由于空气稀薄,几乎听不见。
然而,那一小队旅客,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爵士看到同伴们都已经精疲力竭,很后悔在深山里走得这样远。小罗伯尔拼命与疲劳作斗争,但是委实不能再走了。3点钟的时候,爵士停了下来。
“要休息了,”他说,因为他看大家都不肯先提这个建议。
“休息吗?但是没有藏身之处呀!”巴加内尔说。“然而,非休息不可了,对罗伯尔来说,更有这个需要!”“我不要休息,爵士,”那勇敢的孩子回答,“我还能走……
大家不要停下来……”
“让别人背你吧,我的孩子,”巴加内尔说,“无论如何非走到东面不可。到了山那边也许会找到个把茅棚子。我要求大家再走两个钟头。”
“大家都同意吗?”爵士问。
“同意。”旅伴们一致回答。
穆拉地补上一句:
“我负责背孩子。”
大家继续向东进发。又吃力地攀登了两个钟头。大家总归是往上爬,爬,直爬到最高峰。由于空气稀薄,大家呼吸困难,这种现象叫“缺氧”。血液因为失掉平衡,从牙龈和嘴唇上渗出来,也许雪地也是渗血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高空中,雪显然是败坏空气的。空气既然稀薄,就必须加劲呼吸,才能加速血液循环,这种器官活动使人疲惫,不亚于雪面上的阳光反射。无论那群勇士的意志如何坚强,在这时候,最勇敢的人都熬不住了,高山区那种可怕的病痛——昏眩——不仅削减了他们的体力,也削减了他们的毅力,和这种疲劳作斗争是免不了要吃亏的。不一会儿,摔跤的人越来越多了,一跌倒就站不起来,只有跪着爬。
这一程攀登的时间过长,弄得大家精疲力竭,眼看都支持不下去了。那一片茫茫雪海,那冻裂体肤的寒气,那逐渐吞噬着山峰的夜影,再加上找不到过夜的地方,这一切不由得爵士胆战心惊起来。这时少校忽然以镇静的语气叫道:
“那儿有一座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