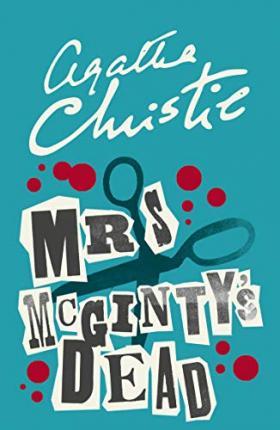客厅里的女仆为我们打开了对面那侧屋子的房门。她显得非常惶恐,语气却不失傲慢。
“想见女主人吗?”
“是的,麻烦帮忙打声招呼。”
她把我们带进一个大客厅,然后便离开了。
这间客厅的大小几乎和菲利浦家那间一模一样。客厅里的家具上铺着亮丽的印花棉布,窗户上挂着条纹图案的丝质窗帘。壁炉上方的一张肖像画吸引了我的目光——不只是因为它是大师手笔,更是因为画中人那张令人难以忘怀的脸庞。
画中的老人个子很矮,目光却极富穿透力。他戴着一顶黑色的绒帽,头缩进双肩。但老人的力量和活力跃然纸上。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牢牢地紧盯着我。
“是奥古斯塔·约翰为他画的肖像画,”塔弗纳总督察的语法不太讲究,“是个很有个性的老头儿对吧?”
“没错。”我回答说,心里却觉得这个简单的“没错”并不足以反映我的感受。
我终于了解到艾迪丝·德·哈维兰小姐所说的“房子里没了他会显得特别空旷”是什么意思了。低矮的畸形屋是画上这个奇形怪状的小矮人所造——没了这个主心骨以后,这幢屋子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了。
“那是萨金特为他的第一位太太画的像。”
我审视着两扇窗户之间的这幅画像。和萨金特的许多画作一样,这幅画也散发着刻薄的意味。画中人的脸被故意拉长,使人隐约想到马脸——这是幅典型的英国仕女画像(画家故意画得很土气,一点儿都不时髦)。画中的这位夫人漂亮,但一点儿生气也没有,和壁炉上那个满脸笑意、精力充沛的老头儿一点儿都不般配。
门开了,兰姆警长走了进来。
“先生,我找仆人们聊过了,”他说,“没问出什么来。”
塔弗纳叹了口气。
兰姆警长掏出笔记本,退到客厅一角,谦逊地坐了下来。
门又开了,阿里斯蒂德·利奥尼迪斯的第二任妻子走进房间。她周身包着一套昂贵的黑色丧服——上至脖子,下到手腕。步子懒洋洋的,像只黑色的大懒猫似的,向我们走来。她的脸蛋非常标致,棕色的头发梳成一种漂亮的发型。她的脸上抹了许多粉,还涂了口红和胭脂,不过还是看得出她一直在哭。她颈上戴着一串珠宝,两只手上分别戴着祖母绿戒指和红宝石戒指。
她显得非常害怕。
“早上好,利奥尼迪斯太太,”塔弗纳总督察故作轻松地说,“抱歉又来打扰你。”
她刻板地回答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利奥尼迪斯太太,我想你应该明白,此时有个律师在场为你出出主意也不是不可以。”
我怀疑利奥尼迪斯太太是否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但她显然没弄明白。
她只是阴郁地说:“我不喜欢盖茨基尔先生,不希望他在场。”
“利奥尼迪斯太太,你可以有自己的律师。”
“必须得请吗?我不喜欢律师。他们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就要你自己拿主意了,”塔弗纳立刻挂上笑容,“我们可以继续下去了吗?”
兰姆警长舔了舔手中的铅笔。布兰达·利奥尼迪斯则在面对着塔弗纳的沙发上坐下了。
“发现了什么线索没有?”她问。
我发现布兰达的手指一直在紧张不安地摩挲着裙边。
“我们断定你丈夫是因为伊色林中毒而死的,这点是确定无疑的了。”
“你是说他是因为那些眼药水而死的吗?”
“看来你给利奥尼迪斯先生注射的最后一针是伊色林,而不是胰岛素。”
“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和这事没有半点儿关系。总督察,我真的一点儿都不知情。”
“一定是有人故意把胰岛素换成了眼药水。”
“真是太邪恶了。”
“利奥尼迪斯太太,你说得一点儿没错。”
“你们认为这是无意的还是有意的?这不太可能是个玩笑吧?”
塔弗纳开诚布公地说:“利奥尼迪斯太太,我们完全不认为这是个玩笑。”
“肯定是哪个仆人干的。”
塔弗纳没有回应。
“肯定是的。想不出还有别的人会这么干。”
“你确定吗?利奥尼迪斯太太,好好想想。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吗?没人对他抱有敌意?没有争吵或怨恨吗?”
布兰达仍然用敌视的眼神看着塔弗纳。
“我一点儿头绪都想不出来。”她说。
“你说那天下午你去看电影了,是吗?”
“没错,我是六点半回来的——正巧是打胰岛素的时间——我——我和平时一样给他打了一针,他突然觉得很不舒服。我吓坏了,连忙冲过去找罗杰——这些我已经全告诉过你们了。是否需要我向你们多复述几遍?”她语带讥讽地问。
“利奥尼迪斯太太,我感到非常抱歉。现在能不能去找布朗先生来谈谈?”
“找劳伦斯吗?为什么要去找他?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找他谈谈。”
布兰达狐疑地看着塔弗纳总督察。
“尤斯塔斯正在阅读室里跟他学拉丁文,你想让他上这儿来吗?”
“不用——我们过去找他。”
塔弗纳飞快地退出客厅,我和警长连忙跟了上去。
“先生,你让她受惊了。”兰姆警长说。
塔弗纳嘟囔了几声,然后领着我们走上几级台阶,通过走道进入一个能俯瞰花园的大房间。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金发男子和一个皮肤微黑的十六岁男孩正坐在房间里的书桌旁。
他们抬头看着我们进门。索菲娅的弟弟尤斯塔斯茫然地看着我。劳伦斯·布朗神色惊惶地看着塔弗纳总督察。
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他这样吓得全身无力。他站起身,然后又坐了回去。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
“哦——呃——总督察,早上好。”
“早上好,”塔弗纳非常有礼貌地说,“能和你说句话吗?”
“可以,当然可以。真是太荣幸了。至少——”
尤斯塔斯站起身。
“总督察,需要我离开吗?”他的声音非常愉悦,却微微地带着一丝傲慢的意味。
“我们——我们可以稍后再学。”他的导师说。
尤斯塔斯旁若无人地漫步向门边走去,他的步态稍微有几分僵硬。通过门的时候,我和他目光相交,他把手指在脖子上一划,对我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接着便关上了门。
“布朗先生,我们开始吧,”塔弗纳说,“分析结果很明确,利奥尼迪斯先生是因为伊色林中毒而死的。”
“我——你是说——你是说利奥尼迪斯先生真是被人毒死的吗?我原本还希望——”
“他是被人毒杀的,”塔弗纳彬彬有礼地说,“有人用含有伊色林的眼药水换掉了胰岛素。”
“我不相信——太令人震惊了。”
“问题是谁有动机?”
“没人——根本没人会想去杀他!”年轻人的声音突然提得很高。
“想不想要个律师在场?”塔弗纳问。
“我没什么律师。我也不需要。我没什么要藏着掖着的——没任何事……”
“你应该知道自己所说的话会成为呈堂证供吧?”
“我是无辜的。我向你保证——我是无辜的。”
“我没有暗示任何事情。”
说到这儿时塔弗纳停顿了一下,然后转换了话题。“利奥尼迪斯太太比她丈夫小很多,难道不是吗?”
“我——我想是的——我是说,他们的确相差很多岁。”
“她有时一定会觉得非常孤独。”
劳伦斯·布朗没有答话,只是用舌头舔着干燥的嘴唇。
“有个年纪相仿的伴侣在身旁,一定会让她非常快乐吧?”
“我——才不是呢——我是说——这个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你们俩产生依赖感是件自然而然的事。”
年轻人激烈地抗议起来。
“不,不是那样的!根本没有这种事!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但根本没这种事!利奥尼迪斯太太总是对我非常好——我也对她非常敬佩——但没有更多的了——再没有更多的了!荒谬,真是太荒谬了!我不会杀任何人——更不会做偷梁换柱这种事。我很敏感,而且非常容易激动。我——我才想不出杀人的念头——分派工作的人就很理解这一点——我信仰的宗教反对杀人。他们让我去医院烧锅炉——这活儿太累了——我吃不消——于是他们又让我给人做家教。我使出浑身解数教好尤斯塔斯和约瑟芬尼——约瑟芬尼非常聪明,但有点儿难教。这里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利奥尼迪斯先生,利奥尼迪斯太太和艾迪丝·德·哈维兰小姐都是好人。现在发生了这种可怕之事……你们竟然会怀疑到我头上!”
塔弗纳总督察神情漠然地审视着他。
“我没有这样说。”他告诉布朗。
“但你是这样想的。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他们都这么想!从他们的眼光中我就看出来了。我——我不能继续跟你谈了。我感到不舒服。”
他匆匆走出阅读室。塔弗纳慢慢偏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你如何看他?”
“他被吓坏了。”
“我是问你认为他是凶手吗?”
“如果你问我的话,”兰姆警长插话进来,“我会说他没这个胆量。”
“他不会敲人的头,也不会对人开枪,”总督察附和道,“但这种罪行应该是能胜任的吧?只需要捣鼓几个药瓶就好……只是帮一个很老的老头儿相对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罢了。”
“简单实用的安乐死方法!”警长评论道,“风平浪静以后,也许还能和一个免交税继承十万英镑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已经有了差不多金额的资产,另外还有很多鸡蛋大的红宝石和蓝宝石。绝对值得干一票。”
“但这只是假设和揣度!”塔弗纳叹了口气说,“我的确设法吓唬了他,但这证明不了任何事情。即便是无罪的,他也会被吓成这个样子。事实上,我倒觉得真不是他干的。我比较怀疑那个女人——但我不知道她为何没有把胰岛素药瓶扔掉或洗干净。”说着他转身面对警长,“仆人们有没有说他们的关系怎么样?”
“客厅女仆说他们非常亲密。”
“有什么根据吗?”
“她是从利奥尼迪斯太太给他倒咖啡的时候,他看利奥尼迪斯太太的样子判断出来的。”
“这种东西不能拿到法庭上去!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没有了。”
“如果真有什么的话,仆人们肯定会看到。现在我开始相信他们真的没有私情了。”说着他看了我一眼,“回去找她谈谈,把你对她的印象告诉我。”
我态度勉强地去了,但其实我还是蛮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