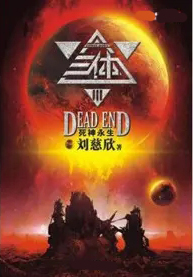我有一阵子没见到爸爸了。我发现他在忙别的案子,于是改道去找塔弗纳。
塔弗纳正好没什么事,很愿意和我出去一起喝一杯。我就破案向他表示祝贺,他接受了我的祝贺,但样子却不太高兴。
“好了,事情总算结束了,”他说,“我们成功地立了案,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个刑事案。”
“你觉得可以给他们定罪吗?”
“很难说。我们拿到的只是间接证据——谋杀案常常如此——直接证据很难到手。很大程度取决于陪审团的印象。”
“那些信能派上用处吗?”
“乍看起来,那些信非常致命。信中提到了丈夫死后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事情。信中提到‘不久以后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但你要知道,辩方律师可以对此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他们会说阿里斯蒂德已经很老了,死亡是可以预期的。信中没有白纸黑字地提到谋杀——尽管很多段落包含了这样的意味。一切都要看法官会怎么看了。如果是老卡伯利当法官的话,那他们就完了,卡伯利最痛恨这种不名誉的爱情。我想他们大概会找伊格尔斯或汉弗莱·科尔为他们辩护——汉弗莱很擅长类似的案子——但是要有辉煌的战斗经历来帮助辩护。有同情心的反战者完全不符合他的风格。重点是陪审团是否喜欢他们。陪审团历来是难以捉摸的。查尔斯,你想必也知道,他们不是那种能博得同情的类型。布兰达是个为了钱嫁给老头儿的漂亮姑娘,布朗是个神经兮兮的反战者。模式也很平常——典型得让人确定无疑他们真的干了。当然,他们也许会认定是布兰达干的,而布朗一无所知——或者说是布朗做的,而布兰达一无所知——当然也许会认定他们是串通起来干的。”
“你怎么看?”我问他。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没有任何看法。我只是把事实呈交到检察官那儿,让他们得以立案而已。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接下来就看检察官的了。查尔斯,你应该完全能了解。”
但我并不是很了解。因为塔弗纳似乎不太高兴。
三天以后,我把心里话一股脑儿地对父亲说了出来。他从没主动跟我谈过这个案子。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一些隔阂——我想我知道原因何在。必须把阻隔在我们之间的那层壁垒打破。
“我们就直说吧,”我说,“塔弗纳不满意这个结果,他觉得这个案子不一定是那两个人干的。我想你也一定这样认为。”
爸爸摇了摇脑袋。他和先前的塔弗纳一个调调。“没我们的事了。这是一个等待判决的刑事案件。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难道你和塔弗纳不觉得他们是无罪的吗?”
“那是陪审团该判断的事情。”
“别拿法律术语来应付我,”我说,“你们俩私下里怎么看?”
“查尔斯,我的看法和你的一样不管用。”
“没错,但你比我更有经验一些。”
“那我就诚实地告诉你——我真的无法对这次的案子给出判断。”
“他们可能是有罪的吗?”
“哦,当然有可能。”
“但你不确定,对吗?”
爸爸耸了耸肩。
“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
“爸爸,别戏弄我了。别的时候你不是很确信、非常确信吗?被你认准的情况不也有很多吗?”
“有时的确是这样,但不是每一次都是。”
“真希望这次你也能信心满怀!”
“我也是这么希望的。”
我们沉默下来。我脑子里出现了暮色中花园里的那两条阴影。孤独,恐惧,如鬼附身,他们一开始就很害怕。这不正是出于做贼心虚的心理吗?
我自问自答:“这并不算充足的证据。”布兰达和劳伦斯都很不自信——他们没自信避险,摆脱悲惨的命运。他们看得很清楚,知道不名誉爱情所导致的谋杀嫌疑任何时候都可能落到他们头上。
爸爸严肃而和蔼地开了口:
“查尔斯,让我们正视现实吧,”他说,“你还是认为利奥尼迪斯家族的一员是这起案件的凶手,是吗?”
“不能完全这样讲。我只是觉得——”
“你就是这么想的。你也许错了,但你真是这么想的。”
“是的。”我承认道。
“为什么?”
“因为——”我尽力思考着,试图找出这么说的原因,“因为,”——没错,就是这个——“因为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也是这样想的?这实在是很有趣,非常有趣。你是说他们互相怀疑,还是说他们实际上知道是谁干的?”
“我不是很确定,”我说,“现在我还一点儿摸不着头绪。我觉得——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说——他们都在试图对自己隐瞒真相。”
父亲点了点头。
“只有罗杰没有隐瞒真相,”我说,“罗杰真的相信是布兰达干的,一心想把布兰达送上绞架。和罗杰在一起非常舒心,因为他为人正直,胸无城府,没有半点儿私心。
“其他人却心里有愧,非常不安,敦促我让布兰达得到最好的辩护——为她提供各种便利条件——这又是为了什么?”
爸爸回答说:“因为他们不是打心眼儿里认为她是有罪的……没错,这样看才比较合理。”
接着他轻声问:
“他们在包庇谁呢?你不是已经和他们都谈过了吗?谁最有可能动手?”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案子快把我急疯了。他们都不符合你所谓的‘杀人者肖像’,但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凶手。”
“可能是索菲娅吗?”
“不会,天哪,绝对不会。”
“查尔斯,你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是的,的确有这种可能性,别跟我否认这一点。你越不承认,就说明在你的心目中这种可能性越大。在你看来,其他人有可能吗?比如说菲利浦。”
“不太可能,很难想象他会出于什么动机干出杀人的事来。”
“动机可能是稀奇古怪的,也可能是荒诞不经的。说说看,他会有什么动机?”
“他非常妒忌罗杰——一直都很妒忌。与菲利浦相比,老人给罗杰的爱更多一点儿。罗杰快破产了,老人听说后答应帮他重新站起来。假设菲利浦听说了这件事,他会怎么办呢。如果老人死了,罗杰就会因此而孤立无援、一败涂地。我知道这么说很荒唐——”
“根本不荒唐。这种事虽然不太正常,却经常会有。这是人之常情。你怎么看玛格达?”
“她非常孩子气。她——她办事不守常规。如果不是突然要把约瑟芬尼送到瑞士的话,我压根儿不会联想到她。我不禁觉得她也许害怕约瑟芬尼知道些什么,或者可能会说出什么来——”
“那约瑟芬尼被击中头部该怎么看?”
“哦,那不可能是做母亲的干的。”
“为什么不?”
“爸爸,做母亲的不会——”
“查尔斯,查尔斯,你就没看过警务新闻吗?母亲不喜欢自己的某个孩子不算是新闻了。母亲不喜欢某一个孩子,把自己的全部情感投入到其他孩子身上。这其中总会有些原因,有些关联,外人很难参透。但这种情感是存在的,而且是毫无理由,非常强烈的。”
“她把约瑟芬尼称为丑丫头。”我不情愿地承认道。
“那孩子介意吗?”
“应该不介意。”
“还有谁有可能?罗杰?”
“罗杰不可能杀他父亲,我很确信这一点。”
“那就把罗杰排除掉。那他的妻子呢——应该叫克莱门丝吧?”
“是叫克莱门丝,”我答道,“如果是她杀的,那一定是为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理由。”
我把我和克莱门丝的对话告诉了他。我告诉他,为了让罗杰离开英国,克莱门丝确实有可能给老人下毒。
“她劝罗杰悄悄离开,却被老人发现了。老人准备复兴筵席承办公司。克莱门丝的计划和希望瞬间化为泡影。她深爱着罗杰——几乎到了‘盲目崇拜’的程度。”
“你在重复艾迪丝·德·哈维兰所说的话!”
“没错。说到艾迪丝,我觉得她也有杀害老利奥尼迪斯的可能。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能说,只要有足够和适当的理由,她就会把法律置之度外。她就是那种人。”
“她也极力要求让布兰达得到最好的辩护吗?”
“是的,我想这是因为她良心上有愧。如果真是她干的,她就绝不会嫁祸在其他人身上。”
“也许是不会。只是约瑟芬尼会是她击昏的吗?”
“不会,”我缓缓地说,“我不信她会做这种事。这倒让我想起了约瑟芬尼对我说过的一些话,我一直在回想,但就是想不起来。这段话平白无故从我的记忆中溜走了。这些话正是解决案子的关键所在。如果能想起来的话——”
“别介意,总会想起来的。你是不是还想到了其他一些事或其他一些人?”
“是的,”我说,“的确想过。你对小儿麻痹症了解多少?我是指这种病症对心理的影响。”
“你是指尤斯坦斯吗?”
“是的。我越想越觉得尤斯坦斯符合作案人的肖像。他性格阴沉,古怪,憎恨他祖父。总之,他完全不是个正常的孩子。”
“如果约瑟芬尼了解到了他的什么事的话,他是唯一能冷酷无情地将她击昏的人——约瑟芬尼很可能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那孩子无所不知。她把知道的事情写在一个小本子上——”
我突然停住了。
“天哪,我真是太笨了。”我说。
“怎么了?”
“我总算知道哪里出错了。我和塔弗纳一直认为弄乱约瑟芬尼房间的人是在找那些信。我以为约瑟芬尼在拿到了那些信以后把它们藏在了水箱室里。但前一天约瑟芬尼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明确说明把信藏在水箱室的是劳伦斯本人。她看见劳伦斯鬼鬼祟祟地从水箱室里出来,然后进去翻找,找出了信。自然,她随后看了那些信。她肯定会这么干!但约瑟芬尼却把信留在了水箱室里。”
“这又怎么了?”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闯入者在约瑟芬尼房里找的肯定不是那些信。他在找别的什么东西。”
“你指的别的什么东西——”
“应该是约瑟芬尼记录‘侦察结果’的小黑本。闯入者找的就是它。我觉得他肯定没找到那个小本子,小本子应该还在约瑟芬尼手里。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支起身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约瑟芬尼的状况还会很危险,”爸爸说,“是想说这个吗?”
“没错,在去瑞士之前一直会很危险。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她妈妈想把她送到瑞士去读书。”
“她本人想去吗?”
我考虑了一下。
“应该不太想。”
“她很有可能不会去,”爸爸冷冷地说,“但你说的危险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你最好赶快过去一趟。”
“是尤斯坦斯还是约瑟芬尼?”我急切地问。
爸爸不紧不慢地说:
“我已经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我想你只是暂时没看清。我……”
格洛弗推开门。
“打扰一下,查尔斯先生,有你的电话。利奥尼迪斯小姐从斯温利给你打来了电话。她说事情很紧急。”
一个可怕的轮回。看来约瑟芬尼又遭毒手了。这次凶手不会再失手了吧……
我奔到电话旁边。
“索菲娅,我是查尔斯。”
话筒里传来索菲娅绝望的声音。“查尔斯,事还没完。凶手还在家里。”
“你是什么意思?出事了吗?是不是约瑟芬尼——”
“不是约瑟芬尼,是家里的保姆。”
“保姆?”
“是的,毒药放在约瑟芬尼的热可可里。约瑟芬尼没喝,把可可留在桌上。保姆觉得浪费太可惜。于是便喝了它。”
“可怜的保姆。她的情况一定很不好吧?”
索菲娅哽咽了。
“哦,查尔斯,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