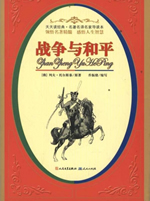上元节后第二天,刘据接到父皇要他参加次日朝会的口谕。
包桑向他转达皇上谕意的时候,他正与卜式探讨儒学提倡的“君道”与“臣道”。
卜式得知这一消息,就迫不及待地放下手中的书卷,向刘据表示祝贺:“过了年,殿下就二十四岁了,依理是该参与朝议了。”
刘据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父皇的口谕不仅让他获得在朝会上建言的机会,更表明了他、当然也包括母后在皇上心中的地位。此刻,刘据从心底感谢一任又一任太傅的传道授业。
尽管他知道母后或许早知道皇上的决定,但他还是满怀欣喜地希望与母后分享这一喜悦。
他收好书卷,又到后室痛快地沐浴、更衣之后,就登上车驾急匆匆地奔椒房殿而来。
车驾进了杜门,急急行驶。兴奋的心情使他不时撩开幔帐,欣赏着还没有散尽的节味。
春风随人意,红萼伴心开。
刘据进了椒房殿,他发现道旁的梅花都开了。粉色的、深红的、白色的,疏枝横斜,暗香浮动。春香正带着宫娥,采了一捧捧鲜花准备回去。她们看见太子,纷纷避在路旁施礼:“恭迎太子殿下。”
“母后可已起床?”
春香笑着回道:“皇后娘娘早已起来,这会儿正询问昌邑王的功课呢!”
刘据“哦”了一声,就被在殿内的刘髆瞧见了。他忙转身打拱道:“太子哥哥到了,为弟有礼了。”
那模样看上去煞是可爱,眉眼里都是李夫人的影子。卫子夫脸上充满温暖道:“髆儿虽说年幼,却懂得长幼有序。你们兄弟都流着刘氏的血,只要精诚协力,大汉江山才能永固。”
刘据和刘髆几乎不约而同道:“谨遵母后旨意。”
卫子夫知道,刘据这个时候来必是有事,遂要春香带着刘髆出去玩耍。
当殿内只剩下他们母子的时候,刘据忍不住问道:“母后真对父皇与李夫人相聚不计较么?”
卫子夫看一眼刘据,脸色就严肃起来了:“为娘虽不信仙人相通,然追思至亲是人之常情,你父皇虽贵为九五之尊,却也是有七情六欲的男子,思亲怀爱,何错之有?更何况李夫人生前,严己宽人,德范淑媛,你父皇难以释怀也在情理之中。”
刘据又道:“看母后刚才与昌邑王亲密无间的样子,倒如己出一般。”
卫子夫就有些不高兴道:“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父皇亲生。你如此胸襟,将来还怎能心怀天下?”
刘据忙道:“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为娘就不多问了。你不在博望苑中听书,来这里有何事?”
刘据的脸色这才有些轻松,忙道:“孩儿来是要告诉母后,父皇命孩儿参加后天的朝会呢!”
卫子夫并不意外,说话的语气也分外平静:“此事为娘已知道了,正要让詹事去传你呢!”
在刘据低头喝茶的时候,卫子夫眯着一双凤眼,细细打量眼前的儿子。当年的童稚小儿,如今已长成一位须眉男儿。一刹那间,泪水漫过眼角。
刘据在霍去病府邸对刘彻的冲撞,使她这些天一直悬着一颗心。现在皇上的一道谕旨,表明他已原谅了儿子。
但卫子夫在这时候依然是清醒的。这孩子不仅继承了她的宽怀雅量,更有刘彻的坚毅和倔强,他们父子之间今后难免不会再发生龃龉。她觉得只有自己才会对儿子说一些别人不便或不敢说的话。
卫子夫放下手中茶杯,目光专注地看着刘据道:“你父皇让你上朝,是为君为父的关爱,你要细细体会。”
可刘据的回答却令她很意外:“父皇十六岁时就临朝理政,孩儿年近而立,才有机会参加朝会,想来十分惭愧。”
卫子夫对儿子的回答多少有些失望,解释道:“你与父皇境况何其殊异。你父皇如今身骨健旺,雄风依旧。你作为太子,当先学为臣之道,方能渐知为君之道。”
看刘据没有再争辩,卫子夫继续道:“你在朝会上的一举一动,朝臣们都看着呢!所以,你要小心谨慎,当说则说,不当说要三思斟酌,明白么?”
“孩儿明白了!”
“明白就好!自你表兄与舅父故去后,卫氏一族势孤力单,也就只有几位跟随大司马征战的老臣仍在记挂,这一点你务必记住。”
刘据虽然没有回答卫子夫的话,但她从儿子的目光中知道,他听进去了。
“好了!你也是有儿子的人了,为娘也不想多说,你回宫后好好想想吧。春香!送太子!”
卫子夫就这样结束了与刘据的谈话。
正月十八,上元节后的第一次朝会在未央宫前殿举行。
辰时二刻,朝会正式开始。
出使匈奴的左内史咸宣首先出列陈奏,说此次参加乌师卢单于登基大典,他一路所见,匈奴部族之间人心各异,新任单于生性多疑,国势日衰。他从怀中拿出一封匈奴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给皇上的信。
“哦!呈上来。”
打开信札,刘彻的眼睛骤然睁大了,兴奋地高声道:“众位爱卿!耶律雅汗在信中声称,去年雪灾降临草原,牲畜冻死近半,匈奴国内人心不稳。匈奴新主即位后,对异姓部落大肆杀伐,而他之所部,也在征讨之列。为保全氏族,他欲杀单于降汉,请朕派兵接应。”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曾经参加过漠北战役的公孙贺、公孙敖、赵破奴等将领一时无法应对,可却把刘彻的思绪从对李夫人的悲怆追念中迅速牵引出来,唤起了他自卫青故去后一度冷却的雄心。
放下信札,刘彻环顾了一下面前的大臣们道:“如何应对匈奴之变,朕愿闻各位爱卿之计。”
话意虽不乏征询之意,可石庆却从皇上亢奋的目光中捕捉到了那种必欲为之的快意,他立即选择了赞同:“微臣以为,此乃一举剿灭匈奴的良机。倘若能杀了单于,则北海之地属汉,我疆域扩展何止万里?”
与匈奴打过多年交道的太仆公孙贺则道:“匈奴人狡黠多变,不知是不是诈降还很难说,此事还是需要谨慎从事。”
児宽选择了支持丞相:“元封元年,臣随皇上勒兵阴山,眼见匈奴大势已去,匈奴人闻汉军至而丧胆。因此微臣认为若能策动匈奴内变,不失为灭敌良机。”
赵破奴、公孙敖等人也都纷纷进言:“当年若不是骠骑将军河西受降,何来今日的武威、酒泉诸郡。左大都尉既然有意降汉,这可是河西之战后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机遇。”
这一封来自远方的信札,让他们再度看到剿灭匈奴的夙愿指日可待。
善于把握臣下情绪的刘彻很满意廷议的结果,很适时地将大臣们的谏言集中为朝廷决策。
“众位爱卿!”刘彻挥了挥手臂,正要说话,就听见刘据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来。
“父皇!孩儿有事要奏!”
刘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道:“有话尽可奏来。”
刘据向刘彻行了一礼,又提了提气,像是向刘彻奏事,又像是对大臣们的谏言发表议论,道:“众位所述皆在策应匈奴左大都尉。然在孩儿看来,此乃匈奴内部纷争,是其虎狼之性所致。我大汉劳师袭远,得不偿失;其次,我朝多年来对外用兵,以致财力拮据,府库不济,为今之计,在休养生息。孩儿恳请父皇,敛兵息戈,外结睦邻,内倡农桑,则大汉可享国万世也!”
这一番话如投石击水,顿时在大臣间引起骚动。大家都很吃惊,太子这哪里是在谈论匈奴之事,这明明是在指责大汉国策,伤害皇上那份敏感的尊严啊!而且还是这样的毫不忌讳!包括丞相和御史大夫在内的阁僚们除了呆望着太子外,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公孙贺情知刘据闯祸了,必然会招致皇上的雷霆之怒。作为卫氏宗族的至亲,他暗地为太子捏了一把汗,他悄悄挪到太子身边,拉了拉他的衣袖道:“殿下!说话还需谨慎些。”
“谨慎什么?让他说!”显然,尽管公孙贺的声音很低,但还是被刘彻听见了。
“哼!”刘彻哼声中隐含着不满,“朕风雨一生,倒不如太子明白了!”
公孙贺忙打圆场道:“太子年轻,说话不免欠思忖,请皇上原谅。”
“他还年轻么?朕登基时,比他还小八岁!”
霍光也在一旁劝道:“太子说话爽直,也是率性而为,还请皇上海涵。”
“朝会之上,可以信马由缰么?”
刘彻干脆把刘据撇在一边,面向众位大臣,话语间明显地带了怒意:“我朝自建元以来,力行新政,南夷咸服,匈奴北遁。遐迩一体,国泰民安,岂是几句狂言浪语所能抹杀的?太子肆意指责朕,是为不孝;无视为大汉捐躯的英烈,乃为不仁。朕若不是看在大司马忠贞报国,早就……”
刘彻后半句话还没说出口,就看到大臣们呼啦啦跪倒了一片。
石庆伏地而泣,那眼泪不知含了多少沧桑:“臣追随先帝与太皇太后,目睹先朝许多旧事。前车之鉴,臣望皇上三思啊!”
児宽也谏道:“丞相之言,忠心可见,请皇上三思。”
廷尉杜周却岔开了矛盾焦点,道:“教不严,师之过也。请皇上将太傅卜式问罪!”
刘据虽在公孙贺的督促下跪地垂首,可一听说要问罪于太傅,又急了,出口便道:“孩儿不过说了一些事实。父皇要治孩儿的罪,孩儿毫无怨言,只是此事与太傅无关。”
“罢了!如此冥顽,气杀朕了!”刘彻狠狠击打着公案,怒吼道,“太傅卜式,未尽师责,责令其与太子一起闭门思过。无朕旨意,不可出博望苑。”
“因杅侯何在?”
“臣在!”公孙敖答道。
“命你率一万人马,去漠北筑受降城,策应匈奴左大都尉归汉!”
“诺!”
随着刘彻声音落地,大臣们心逐渐松弛下来。
二月二惊蛰的子夜,从南山头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万物从这一天开始,将伸展希望的身姿,向这个世间展示生命的魅力。
黎明时分,下了一阵细雨,到辰时就停了。公孙敖选择在这天出发,是要借“龙抬头”的祥瑞,祈祷他此次北上顺利。
横桥十分湿润,但并不泥泞。马蹄踩在上面,听上去有些沉闷,恰似他此刻的心境。
今非昔比。往年出征,他总是追随着大司马的身影,他把大司马看作是军队的灵魂,即使处在危急关头,只要看见“卫”字大旗飘扬,他仍然能够神清气定。
如今,斯人已去,他的行旅徒添了难以言表的孤独和寂寞。
他没有文士们的丰富联想,因此这寂寞就只能是一种憋闷。
战马走到横桥中央,公孙敖一如往年习惯地回望了身后的长安,皇上在宣室殿与他说话的情景就油然地回到眼前。
皇上从来没有如此感叹朝廷将领的匮乏,他对公孙敖在这关头请缨出征给予了由衷的褒奖。当着石庆的面,皇上赏赐他金百斤,帛五十匹。
“将军年事益高,依旧慷慨出征,朕甚慰之。朕虽不忍你远途劳苦,然策应左大都尉,事关剿灭匈奴大局,朕反复思虑,惟将军担得起此任。”
皇上的赏赐和话语,让公孙敖陷入无言的惶恐,他生怕自己辜负了皇上的期望。
刘彻一只手按在他的肩头说道:“为将之要,在于静而不躁,稳而不浮,勇而不谩,藏而不露,秘而不宣。此次受降,将军应切记我为策应,不可先动,若是打草惊蛇,必然功亏一篑。须待左大都尉举事成功,我方能北去接应。”
“臣谨遵皇上旨意。”
刘彻接着道:“尽管漠南已无匈奴人,可匈奴军善于偷袭,因此将军此去,一要秘行,二要警惕匈奴骑兵偷袭。”
……
公孙敖现在想起来,皇上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无的放矢,看来,皇上对自己过去多年无功的原因知之甚深啊!
他策动马鞭,挥去如潮思绪,在登上咸阳原时,却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将军请慢行!”
他勒转马头看去,却是赵破奴和霍光从身后追来了。三人马上见礼,公孙敖问道:“二位大人怎么来了?”
霍光道:“将军乃舅父旧属,沙场宿将,此番离京又逢春秋渐高,晚辈放心不下,故赶来送行,还望将军一路平安。”
赵破奴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将军还没离开京城,皇上就又有了新的思路。”
“哦?”
“皇上念及漠南距匈奴单于庭太远,已命末将率两万骑出朔方,以接应左大都尉归汉。”
公孙敖惊叹皇上是如此的深谋远虑,更为能与赵破奴并肩作战而高兴,当他问及何时出兵时,赵破奴道:“皇上认为,在受降城竣工之后、左大都尉举事之前,末将所部一定要到达浚稽山。”
三人并马向西北而行,眼看就要走过安陵,公孙敖回身揖手道:“千里送行,总有一别,二位请回吧。本官此去,少则半年,多则年余。大司马薨后,本官所系念者,惟太子也。本官拜托两位,为大汉社稷计,请悉心保护太子。”
霍光忙向公孙敖回礼道:“请前辈放心,太子与皇上之间的纠葛晚辈略知一二。究其原因皆在太子涉世不深,易听信他人,晚辈会时刻提醒他的。”
赵破奴也有同感:“老将军所忧不无道理。如今皇上的几位皇子相继长大,据末将所知,皇上对昌邑王刘髆甚是偏爱。去年,皇上敕封诸皇子,相继命其出京就封,唯独刘髆留在京城。虽说理由是身体羸弱,却也难免不会中途生变。”
经这么一说,霍光也感到事情的严重,看来他必须进宫向皇后提个醒了。
午间的太阳驱走了料峭的寒意,望着悄然西去的队伍,无论是赵破奴还是霍光,都感受到公孙将军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的。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担心:皇上在上元节前夜的那一场人神相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而正月十八朝会上父子的冲突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这些事他们只是在心里想着,不管是不是心照不宣,可谁也没有说出口。
此时,在遥远的大宛国国都贵山城,国王毋寡和他的朝臣们正在为如何应对汉使车令而争论不休。
车令是持汉皇符节来到大宛的。他们一路上过菖蒲海,越葱岭,不仅带来了大汉的威仪,更带来了皇上远结邦交的诚意。他们一住进大宛国驿馆,就要主客(礼宾官)转奏大宛国王,说汉皇闻大宛多善马,欲以金易之。
机敏的车令拿出仿照汗血马浇铸的鎏金马,以表示汉皇对大宛马的喜爱和向往。他没有忘记大国使节的尊严和气度,在主客被金光闪闪的鎏金马耀得眼花缭乱时,他适时施加了微笑背后的压力:“不知主客是否听说我大汉浞野侯以七百骑活捉楼兰王的消息?”
主客迷茫地点了点头,他不知道面前这位膀大腰粗的使节为什么要这样说,不知道他接下来又会说些什么?
车令接下来的话锋所指,就在金与马的交易了:“我大汉带甲百万,猛将如云。北驱匈奴,南平两越,诸侯诚归,天下咸服。小小大宛国,自不在话下。然我大汉乃礼仪之邦,素不以强凌弱,以兵屈人,故遣本使前来,以金易马,还请主客向贵国大王转达我皇谕意。”
这种亦威亦利的话,主客当然听得出来。赵破奴生擒楼兰王就发生在不久前,这使他对汉使有了一种本能的敬畏,说话就不那么流畅了。
“请使君放心,本官一定上达汉皇谕意。”
离开驿馆,主客不敢有丝毫拖延,就把车令的要求禀告给相国昧蔡,他话里行间的惊恐让相国很不舒服。
“本相素闻汉使明礼仪,知进退,为何主客如此惧之?”
主客唯唯诺诺,未将那些威胁之语说出。
第二天,毋寡便召集国师、相国和将军们商讨易马之事。
昧蔡向来主张和睦相处。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时,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亲眼看见了汉使雍容大度的风采,也羡慕大汉琳琅满目的器物。从那时候起,汉皇刘彻的名字就深深嵌入他的脑海。如今,刘彻遣使到来,这该是远交睦邻的良机。
“以汉朝之强比我之弱小,汉皇大可不必这样,可直接令我国贡马。汉皇以金易马,实为向我国表达善意。而我国不缺善马,何不以我之所有,易我之所无呢?臣以为应该以盛礼接待汉使,准他们前往贰师城挑选良马。”
但昧蔡的这个谏言遭到了国师的反对。他十分鄙夷昧蔡对汉朝的态度,嘲笑他不知汉朝距离大宛之远。
“相国知道,汉朝离我大宛实在太远了,中间隔着盐泽,要穿行十分困难。如果绕道北行,则会被匈奴人阻挠;如果改行南道,就要穿越千里大漠。历来汉使都难以穿越这一险境,遑论大军到来。所以,依臣看来,不是汉朝酷爱和睦,实是对我国无能为力之故。”
从东部重镇郁城赶来赴会的亲王兴桀更是极力主张拒绝汉朝的请求:“贰师宝马,乃大宛珍宝,岂可轻易让予他人呢?”
毋寡被国师说动了,他一拍桌子下定决心道:“好!就依国师。金子和金马留下,不予贰师马,遣返汉使。”
当晚,国师就到驿馆转达了国王的意思。不过,他很快将眼神聚焦在精美的鎏金马上。那高扬的头颅,那整齐的鬃毛,那硕大的四蹄,把贰师马的雄健表现得淋漓尽致。国师为汉朝有如此能工巧匠而感到惊诧,那想据为己有的意念随着目光的流转而急剧膨胀起来。
当他伸手试图去抱鎏金马时,立即被车令拦住了。行伍出身的他给大宛国师的第一个惩罚,就是让他的胳膊如刀割一般疼痛。继之,他将鎏金马抱在怀里,严斥大宛国君臣见利忘义。
“大宛如此轻汉,本使岂可将鎏金马与你。”
“嘿嘿!大汉虽大,然远兵难解近危;大宛虽小,却可将你投入牢狱。何去何从,使君自可斟酌。”随后,他就要随从上前抢夺鎏金马。
“站住!”车令大喝一声,“国师认为这样就可以让本使屈服了么?本使左臂抱马,右臂持节,你等若敢再强行一步,本使宁可将这马摔成碎片,也不会令你等得逞。”
国师不愿再与车令周旋,大喊一声:“连人带马,与我拿下。”
不料随着他的喊声,只听“砰”的一声,车令将鎏金马摔在地上,顷刻间,一匹体格雄健的鎏金马变得面目全非。
国师颓丧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他不能理解,是什么竟能让一位臣下如此凛然不可侵犯。
当日,车令带着使团愤愤离去。临行前,他留下一句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昧蔡送车令一行出城,拱手致歉道:“使君遭此冷遇,咎在大宛,使君回到长安,万望奏明汉皇,勿轻动兵戈。本官代大宛百姓谢过使君了。”
消息传到长安,已是太初元年清明节了。
清明前夕,刘彻口谕李广利,让他陪昌邑王到茂陵为李夫人扫墓祭祀。
春雨霏霏,站在李夫人的陵冢前,李广利不知该怎么向刘髆描述他的母亲,他至今仍不能原谅妹妹生前不肯为他求官的行为。虽说死者长已矣,可死者为何就不能替生者想一想呢?
李夫人的陵冢静静矗立在茂陵,李广利的话带着湿漉漉的雨迹,在心间徘徊:“妹妹,你现在安寝在茂陵,这意味着宫车晏驾之后,将与你相伴永远。可你曾想过,你的兄弟今后如何在朝廷立足,你的儿子如何在诸子中争锋呢?”
他这些心语,在刘髆泪眼问话时,转换为对外甥的期待:“昌邑王记着,你若有一日执掌国柄,千万不要学你母亲。”
“母亲怎么了,还请舅父您告诉我。”
“唉!这怎么说呢?”李广利牵起刘髆的手,准备上车,“你母亲是个好人,就是太死心眼了。”
“哦?”刘髆直到坐上车驾,仍没有理解舅父的话。皇后不是说母亲雅操蕙质,是后宫风范么?焉何舅父如此评价母亲呢?
一路上,李广利再也没有和刘髆说起过李夫人,倒问了不少他在皇后那里的事情。刘髆对李广利说,皇后待他很好,不仅常常关心他的健康,还对他的功课问得很细。
李广利又是一片茫然。难道她不知道皇上很宠爱昌邑王么?不知这卫子夫是怎么想的,看来,世间的女子都是读不透的书啊!
但是,当车驾进了长安城时,李广利的思绪已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他打定主意,要盛赞朝廷对李夫人墓冢的呵护。他还要把这些想法告诉兄长李延年,让他最好再写一首可以与《北方有佳人》媲美的歌,以此来抓住皇上的心。
回到府上,还没有洗去一路风尘,府令就来禀告,说协律都尉有要紧事,请他过府叙话。李广利喝了一口热茶,就急忙来到李延年府中。
兄弟在前厅坐定,李延年简单地问了问扫墓的情况,便道:“皇上今天召为兄到宣室殿去了。”
“哦?”
“皇上说贤弟为大汉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怎么回事?兄长不能说得清楚些?”
李延年将汉使在大宛国的遭遇,以及在回国途中,使节在郁城被杀的经过讲述一番后道:“皇上闻之大怒,当即点名拜兄弟为贰师将军,率军讨伐大宛。”
李广利没想到,自己出城仅三五天时间,命运就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机。
“不知皇上能给予小弟多少人马?”
“为兄对兵务不懂。听公孙贺说,大宛弹丸之地,兵弱将寡,三千强弩军足以灭之。”
“三千兵马?太少了吧?皇上平定南越,发兵都在十万。”
“用兵之道,还是听皇上的。皇上说行,就一定行。”
听李延年说得如此肯定,李广利才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但他对自己却没有信心。
“依兄长看,为弟能担此重任么?”
“卫青、霍去病能行,兄弟为何不行?”
李广利无奈地摇了摇头,看来兄长弄音律可以,说起打仗来还是如隔重山啊!统兵打仗可不是谱曲吟歌,那是对将才见识的考验。李广利不得不承认,对兵法他只是略通一二,与卫青霍去病不可相提并论。
虽然统兵打仗的事情李延年说不清楚,但此次出兵对李家的利害关系他比谁都清楚。李延年在厅中踱了一圈后,话语的分量就明显加重了。
“朝廷眼下的形势你应该清楚,太子与皇上政见相左,就在前几日的朝会上,他还不赞同皇上出兵大宛。皇上将诸王都遣往封地,惟独留下髆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朝廷那么多将军,皇上唯独点名要你西征,这又说明什么?”
话说到这里,李广利豁然明白了,频频点头道:“还是兄长把一切看得明白。”
兄弟俩分手时,李延年送李广利到府门口,临上车时,他又叮嘱道:“记住!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望兄弟切勿彷徨。”
果然,第二天当刘彻在宣室殿召见李广利时,把话说得很透彻:“爱卿应该明白,夫人生前谨守朝制,从未为你们谋一官半职。就因为这个,她才让朕眷念不已。朕也考虑过对李氏族人加以封赏,然太祖高皇帝曾经誓约——非功莫侯。因此朕今日点将,这是要让你立下战功。封众人之口,望爱卿能领会朕的苦心。
刘彻指着西域全图高声道:“大宛距我朝甚远,虽使者皆言其国弱,然毕竟未知其详。故朕除发兵六千外,还从郡国集结‘恶少’四万人,归你节制。朕固然要大宛马,可朕更要的是大汉国威,朕就不信,小小的大宛国不会被朕的数万铁骑踩得粉碎!”
……
皇上的气概让李广利很受鼓舞,在咸阳西的十字路口兄弟相别之时,他向李延年和三弟李季许诺,他要向皇上献上千匹贰师马,还要捧着毋寡的头颅站在未央宫前殿。
在打马奔上征程的时候,李广利当初盘桓在心头的怯战情绪渐渐被功利的期望所取代了。
对仕途前程的兴奋,与兄弟相别时的憧憬,依旧伴着他军旅的脚步,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的梦幻,他没想到战事却进行得如此艰难。
六月,大军到达酒泉。郡守早就接到了朝廷的诏令,李广利一到,他就将所筹集的棉甲、酒食,悉数交给西征军。
出了玉门关,往前走一千六百里就到了楼兰国都。
正是大漠落日时分,看着硕大的太阳在沙海边缘一点点地沉没,茫茫戈壁一望无垠地在面前展开,余晖下的楼兰国都苍凉地站在晚风中,满目萧瑟。当夜,西征大军就在城外安营。
匆匆用过糇粮,李广利召集各路司马到中军议事。
李广利道:“大军离开长安时,皇上一再嘱咐,此次主要目的是取大宛马,因此我军沿途所过之西域各国,只要他们愿为我军供给粮草,就不必擅动兵戈。”
司马们散去后,李广利留下从事中郎,要他从军中选一曹掾进城与楼兰王阐明来意,并要他们供给粮草。
可第二天,当曹掾来到城下时,楼兰军却拒不开门,而只是将信件用吊篮吊了上去。
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从城头上投下一张用羊皮书写的信件,要曹掾转交汉军主帅。
信送到中军大帐,李广利展开一看,竟是用汉文写就——
曩者汉与楼兰,相互往来,邦交甚好。然汉使西来之势日频,多者年三五批,少者年一二批,途经鄙国,所要辎重、马匹甚多,鄙国乃沙海小国,不堪其负。今大军过境,数万之众,逾于鄙国人口,恕难应对,还乞将军明鉴。
出境第一关竟遭到阻挠,这大大出乎李广利的预料。他当即决定,由校尉李哆率一千人马攻城。
李哆率军从东门攻打,他站在高处朝城内观察,发现这虽是一座土城,却建得别具特色。城中东北角有一座烽燧,显然兼有传递情报和瞭望的功能;再看看周围的城墙,夯土中夹杂着坚硬的戈壁石,一层一层密集地垒起来。每一个城垛后面,都藏着弓箭手。
李哆传来一位君侯,要他率领强弩军,以密集的弩机和弓箭射杀守城士兵。
君侯大旗挥动,立即便有几百支箭向城头飞去。几轮过后,却没见城上守军还击,仿佛这是一座空城,只有烽燧顶端的楼兰旗帜穿了几支箭。
这时,数百步军早已按捺不住,扛着云梯朝城下冲去。可前面的士卒刚刚攀到一半,就被楼兰人煮沸的羊油烫得滚下云梯。待云梯上的士卒跌落后,守城的楼兰军又扔下火把,不一会儿,云梯就纷纷断裂。
仗一直打到中午,汉军在城下留下十几具尸体后,不得不撤到楼兰军弓箭的射程之外。
经过一个上午鏖战,汉军士卒一个个唇焦口燥,腹内空空。入口的糇粮因为缺水,黏在喉咙处就是咽不下去。
午后,李广利接到楼兰使者送来的信,他们申明并无与大汉为敌之意,实在是因为汉军人数过多,难以承受。倘若汉军不需他们供给粮草,则对汉军过境不予干涉。
楼兰王在信中还特别提醒,西行途中必经辖内白龙堆,此处常有沙暴,状如巨龙,军行其间,极易迷路。为助汉军过境,他特选向导五名并带水数百囊,助汉军通过。
李广利向李哆和从事中郎问道:“此事该如何处置?”
从事中郎道:“楼兰王所言,似无虚应之嫌。平心而论,以四万人口之国,供我数万汉军之需,确是难以承受。”
李哆也附和道:“楼兰王能派向导来,足见其诚意。我军若是在此拖延,必然贻误行程,末将以为应速速过境,实为上策。”
“如此就依大家。”
李广利当即修书一封,交与楼兰使者带回。
一天后,大军进入白龙堆沙漠。举目远眺,沙海茫茫,几十里不见一点绿。太阳更加酷热,炙烤着大地。
李广利登上一座山丘,他回看大军,弯弯曲曲地在沙梁间蹒跚,宛如一条巨龙。这时,他看见有几个黑影倒在沙谷里,便急忙唤来向导询问,原来是有人耐不了干渴,倒在沙海里了。
李广利发脾气道:“为什么不给他们水喝?”
向导在一旁解释道:“将军有所不知,进了沙海,最要命的就是缺水,若是救了他们,其他人会因为缺水而走不出去,如此,大军就完了。”
“哦,原来如此。告诉军正,令将士节制用水。”李广利朝战马狠抽一鞭,冲下山坡去了。
谢天谢地,汉军没有遭遇沙暴。走出沙海,前面有一片绿洲,士卒们才解了水荒。
李广利疲惫极了,他躺在胡杨树下,望着士卒们纷纷俯身牛饮,心头就不免生了诸多惆怅。
粗略估计了一下,大军距长安已有六千里了,但这对西征军来说,还只是个开头。若是沿途都是如此恶劣的环境,不要说打仗,只要将这几万人的命保住,就不容易了。想到这些,李广利觉得眼角有些酸涩。
这时候,从事中郎送来了一囊清水,李广利喝了一口,觉得远不及长安的甘甜。
接下来,大军所经过各国,都怀着唇亡齿寒的心理。汉军得不到粮草补给,往往要花巨大的代价攻下城池后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十月,汉军终于推进到大宛国的边境重镇——郁城。
当晚,军队在距郁城三里的叶河河谷驻扎。
眼见各路司马均已到齐,李广利让从事中郎将军情通报给大家。
“自出玉门以来,我军死伤的士卒已三成左右。由于沿途各国拒绝接济我军,眼下我军粮草仅能维持数日。”
展开地图,从事中郎继续道:“据细作来报,郁城王兴桀就是截杀汉使的元凶。他料定我皇必不肯罢休,早已严阵以待。”
李广利环顾坐在四周的司马们,接着从事中郎的话道:“本官以为,攻打郁城宜速战速决。攻下此城,不仅可以解决我军粮草困乏之危,更是打开了通往大宛国都贵山城的通道。传令下去,明晨卯时攻城,第一个破开城门者,赐爵三级;斩敌首者,赐爵一级。军正阵前督战,有退缩不前者,斩!”
凌晨卯时,星光还躲在云层深处,天空漆黑一片。李哆命所部君侯率领士卒悄悄来到城下,抬头看去,城头上除了几盏昏黄的灯外,并无巡逻的哨兵走动。
敌军似乎真睡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守城的大宛军有所警觉。可当第一批攻城的士卒刚刚登上城墙,还没有来得及站稳脚跟时,就只见夜色中寒光一闪,数十名汉军的头就滚进了护城河。接着,从城墙上射出数千支蘸了羊油的火箭,霎时一片火海,将黎明前的郁城照得鲜亮。
李哆站在城外,他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大骂兴桀奸诈。
而与此同时,从城头上传来兴桀的声音:“城下的汉军听着,速去禀告你家主帅,就说本王在城中等他来喝酒。哈哈哈!”
李哆气得脸色铁青,挥动宝剑,命令军队攻打城门。汉军的弓弩手以密集的箭雨将城楼的敌军死死压住,攻城的军队扛巨木撞击城门,半个时辰过去了,那城门仍是岿然不动。
李哆转而命令用大火焚烧,可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城门却依然丝毫未损。他们并不知道,郁城城门是用厚厚的铁板,内夹葱岭采来的石板做成,抗得住击打,耐得了焚烧。
仗打到正午,仍然毫无进展。大宛军似乎已看出汉军疲惫,不可能持久,遂采取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的战术。汉军只要攻城,必然伤亡惨重,而寒冷也在一步步地逼近汉军。
这是十月底的一个夜晚,鹅毛大雪随着西北风来到叶河两岸,将散落在河谷的汉军营帐冻成一堆堆冰锥。战衣单薄的汉军士卒吃着干涩的糇粮,吞着冻齿的白雪。为了相互取暖,往往几个士卒抱在一起,在寒夜里永远地睡去了。
后半夜,从事中郎起来查哨。他走到一顶帐篷前,看见一个值更的哨兵。他轻轻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他上前一摸,那哨兵的整个身体都僵硬了。及至沿着帐篷走了一圈,竟发现有数百士卒在寒风中冻死,这仗还能打么?
从事中郎不敢耽搁,急忙来到中军大帐,向李广利禀明情况。
这时候,天已大亮,各路司马也纷纷来报,说昨夜大雪中死伤甚众。
李广利“扑通”一下坐在地毡上,仰天长叹道:“此天亡我也。”
“为今之计,我军要速决去留。如继续这样下去,就是大宛军不来袭扰,我军也会被冻死饿死的。”从事中郎建议道。
军正也附和道:“依下官之见,眼下我军不如撤回敦煌,然后向朝廷飞报军情,请皇上定夺。”
李广利睁开疲倦的双眼,那目光十分暗淡。
“好!传令下去,即日撤军回敦煌。”说完,他懊丧地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