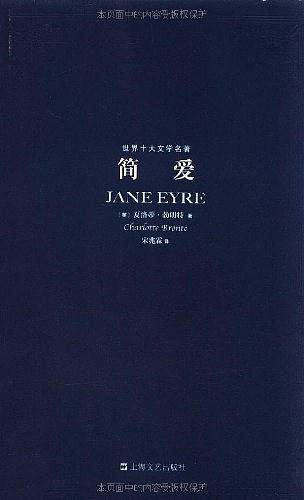李季从小黄门背上爬了起来,系好衣带,挤着淫邪的眼睛问道:“舒服吧?”
小黄门常明扭了扭屁股,坐起身来道:“又不是第一次了,何必问呢?”
“那你舒服不舒服?”
常明胆怯地点了点头。
李季嘿嘿笑了,那舌头又伸到常明口中,两个男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经过来回地折腾,两个人都有些累了,依偎在一起说话。
常明问道:“宫内外的女人那么多,公子不去找她们,却来奴才这里纠缠,图个什么?”
李季笑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再说,你的声情与女人何其相似,嘻嘻!”
常明知道,这事一旦被发现,就是死罪。因此每次过后,他都要后怕几天,见了包桑头都不敢抬。
可当他与李季在一起的时候,又能说什么呢?李氏兄弟现在是炙手可热的人物,连丞相见了都要让他三分,何况他一个小小的黄门。
这是掖庭一个十分偏僻的角落,是用来关那些有罪的宫女的,平日里很少有人来。他们就在这个阴暗之处一夜又一夜地寻求着快感。
现在,谯楼上的钟鼓已经敲过四更,再有一个时辰天就亮了。而卯时正是大臣们上朝的时节,黄门必须赶在这之前到岗。
常明内心忐忑不安,提醒道:“公子!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
“不急!再玩会。”李季说着又要来。
常明佝偻着身体,乞求道:“奴才万万不敢,黄门总管马上就要点卯了。”
“怕什么?有我呢!”
“公子,朝廷律法无情,触犯律法你我就都完了。”
“律法!哼!律法不过是一纸空文,能奈我何?要知道,我可是海西侯的兄弟!”
在李季从他的身上站起来,穿戴整齐,离开小间,沿着掖庭侧门悄悄溜出去之后,常明哭了,哭得很伤心。
他说不清这是为了自己的命运,还是为了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创伤。难道这个世界注定是如此么?李季回去了,躺在将军府里可一头睡到日色过午,有人伺候梳洗、用膳,完了就是骑马打猎,糟践百姓,而他却要拖着酸痛的身体前去应卯。
常明在心里骂着,趁黎明的朦胧,朝掖庭的点卯处艰难地走去。
看到掖庭黄门总管拿着竹简高声吆喝着,他庆幸自己没有迟到,他尽量挺直身体,不让别人看出破绽,可当每个人领了当日的差事就要散去时,他还是被身边的一位小黄门拉住了。
“常明!你怎么了,走路一拐一瘸的?”
“没有啊!我好好的。”
“没准你是偷了宫中的宝物,拿到宫外去卖,被强人打了吧?”
“就是!要不,昨日看你还清清爽爽的,怎么今天就成了这副模样?”
“老实说!作甚去了?”
“真没干什么。”他被逼到墙角,瑟缩着身体,浑身冒着冷汗,眼看都要哭了。
“不去应事,你们在吵闹什么?”掖庭黄门总管闻声赶来,大声呵斥着。
他看到缩在墙角的常明,骂道:“点卯时就见你脸色失常,不大对头,这会儿又如此模样,说,你作甚去了?”
一位小黄门上前禀告道:“公公,这小子被人把腿打瘸了。”
“哦?所为何事?”
随着黄门总管的问话,常明喊了一声“公公饶命”,就跪倒在地上了。这一跪不打紧,疼得他“哎哟”一声叫了出来。
黄门总管见此情景觉得十分奇怪,眼珠骨碌碌直转。这让常明毛骨悚然,正忐忑间,只听见总管喊了一声:“把他的裤子扒了!”
黄门们便纷纷上前,七手八脚,没费功夫,常明的裸体就暴露在晨光之下……
后宫发生如此丑闻,隐瞒下去,最终只会殃及更多的人。掖庭黄门总管不敢怠慢,匆匆地赶往未央宫去向包桑报告。
大约一个时辰后,包桑和掖庭黄门总管已拿着常明的口供出现在椒房殿。
卫子夫刚刚梳洗完毕,听说包桑求见,就有些不高兴:“一大早就来烦本宫,问问他们有何要紧之事,不能等到午间来奏么?”
“包公公不曾细说,看样子很急。”
“让他进来吧。”
可当他们出现在皇后面前时,两人却相互看着,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卫子夫问道:“你们不是有事要奏么?怎么不说话?”
“这……”包桑不知怎么说,于是用眼神示意掖庭黄门总管,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掖庭黄门总管只好大略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其间省略了许多龌龊的经过。
卫子夫没等他说完,就明白了八九分,她抬头时眼神就愠怒了:“本宫反复交代,对宫中之人要严加管束,可你们却如此纵容,做下此等禽兽不齿之事,该当何罪?说!那个该死的东西是谁?”
掖庭黄门总管急忙呈上常明的口供。卫子夫浏览了一遍,问道:“这李季是何人?”
包桑接过话道:“此人乃贰师将军胞弟。”
闻言,卫子夫倒吸一口冷气,便知此事很棘手。不过她旋即恢复了平静,问道:“此事皇上知道了么?”
包桑摇了摇头:“因为事发后宫,因此先来奏明娘娘。”
卫子夫沉吟片刻,转脸来对春香道:“你让詹事宣丞相到宫中来一趟,顺便请廷尉吴尊一同进宫。”
遣走春香,卫子夫回头对两位黄门总管加大了压力。
“败坏后宫风气,依律本宫就可以定你们死罪。不过,念在你们终日伺候皇上,本宫姑且饶了你们。既然案情牵涉到协律都尉和海西侯,情势不免复杂,何况本宫看到的也只是那小黄门的一面之词。一切还是等丞相和廷尉审理清楚后,直接禀奏皇上吧!”
这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啊!她把案子交给丞相处理,既回避了与贰师将军的冲突,又摆脱了后宫干政的嫌疑——出了椒房殿,包桑依然为卫子夫的聪明感叹不已。
公孙贺从皇后那里回来,立即把王卿、吴尊和霍光召在一起,商议李季与中人淫乱一案。他知道这既是打击李氏兄弟的良机,又是维护太子地位的必须之举——毕竟他和太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久经宦海的他却以维护贰师将军声誉的语气很巧妙地把话题切入到对案件的审理上:“现在,贰师将军正在前线与匈奴苦战。所以,此案的关键是李季的行为是不是两位兄长的纵容,老夫不希望牵涉李将军,可若是其兄长纵容犯罪,那么我们就只有如实禀奏皇上了。”
霍光当然明白丞相这番话里的意思,随即建议道:“依下官的意思,吴大人应该先将李季密捕,连夜审问,免得节外生枝。”
“霍大人所言极是。应该马上行动,以免走漏消息。”王卿也附和道。他对李广利兄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有腹诽,现在有人出来替他出气,他自然愿意顺水推舟。
而吴尊是公孙贺去年举荐到廷尉任上的,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知恩图报的机会,当即表示赞同。
公孙贺特别强调,对常明之事一定要严守秘密,不可声张。
李季是很讲究的,每次到掖庭他都要用泡着香料的温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觉得这种特殊的香味,对已经女性化的中人有着催情的魔力,这可以让他兴奋,带给他刺激。
看看亥时到了,他穿戴好宫人的服饰,就蹑手蹑脚朝掖庭狭长的复道溜去。他完全不用担心不能进去,因为常明早已为他仿制了一把侧门的钥匙。
可这一回,他错了。
他刚刚打开那扇鲜为人走的小门,就被人从身后套了布袋,扛在肩头。他想喊,嘴里却被绢帛塞着。直到被丢在廷尉大堂的时候,他才知道,常明已经招供。
吴尊命府役将口供拿给他看,他顿时就蔫了。审讯并没有多难,李季面对每一个可以令嫌犯粉身碎骨的刑具,很快就招供了。两位兄长其实早知道他的行为,只是念及去世的李夫人,因此容忍和放纵他。
第二天早朝后,公孙贺和吴尊就携着常明和李季的口供来到宣室殿。
刘彻这时候正为路博德飞马传来的一道奏章烦恼,听了公孙贺的陈奏后,把一肚子的愤懑都发泄到协律都尉身上。
“好啊!朕的赏赐益重,子弟怠惰骄恣者益多,朝廷还有规矩没有?”刘彻冷笑着,越说越生气,“将士们在前方流血,他们竟然干下如此败坏风俗的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
刘彻把常明和李季的口供掷向案头,声色俱厉地向吴尊发出口谕:“身为协律都尉,又是中人,竟不顾羞耻,朕若是姑息养奸,岂非让皇家蒙羞。速将李延年下狱审理!”
包桑从殿外匆匆进来,附耳对刘彻道:“协律都尉已在塾门等候多时,求见皇上。”
“让他去死吧。”
刘彻对吴尊的迟缓十分不满,严厉地呵斥道:“愣着干什么?还不去办!”
“诺!”
吴尊从宣室殿出来,看见李延年正忐忑不安地朝殿门口看。显然,他已得知了李季的罪行。他也许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希望皇上看在妹妹的分上,法外开恩。
“速将逆贼李延年拿下!”吴尊一声暴喝,羽林卫迅速上前将李延年扭住。
“你等大胆,竟敢侮辱协律都尉,待会见了皇上,让你们个个碎尸万段!”
吴尊讥讽的眼光掠过李延年的额头,道:“皇上恐怕不会再见你了,我的李大人,走吧。”
李延年绝望地朝宣室殿门口大声呼叫:“皇上,臣冤枉啊……”未及喊完,他的嘴就被堵上了。
“荒唐!真是荒唐!”刘彻还没有从刚才的愤怒中走出来,又被新的烦恼所缠绕。
他向公孙贺发泄着对李陵的不满:“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率兵深入敌境的,朕不仅准奏,而且还派路博德前去接应。可前不久路博德飞报说,李陵以为现正是匈奴草丰马肥的季节,战恐不利,要等明春出战。你说说,究竟是路博德畏敌,还是李陵怯战?”
其实当路博德的上书一到京城,公孙贺就先看到了。他凭借自己的战场经验判断,如果说李陵建功心切,贸然进击,还说得过去;要说怯战不进,只能是路博德的主意。
为了弄清原委,公孙贺连夜写了一封密札,六百里加急送到前线,要李陵将实情奏报朝廷。现在,一个多月过去后,已经有结果。
公孙贺从衣袖中拿出李陵送来的上书和地图道:“李陵来书,有要事禀奏皇上。”
“他还强调不宜出战么?”
“非也!”公孙贺与包桑一起,在案头铺开了李陵所绘地图,“事实上,李将军率领步军五千,沿弱水北上千里,到达浚稽山扎营。路博德率领的骑兵到达浚稽山以南的龙勒水上游,来回搜索,毫无发现,于是又回到受降城休整。此乃李陵属下陈步乐送来的沿途敌军阵势图,请皇上御览。”
“这么说,他们根本就没见面?”
“想来应该是这样。”
“路博德老迈昏庸,险些让朕委屈了李陵。”
“是非曲直,还要等到战事结束后才见分晓。”公孙贺没有急于下结论。皇上的脾气现在越来越怪,他若是把话说死,一旦形势有变,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
“李陵正当盛年,但愿他不负朕望。”
……
天时人事日相催,转眼就到了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十月。
从前方传回的战报并不乐观,匈奴人显然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因此,李广利从酒泉出发,一路上几乎没有遭遇阻击。但是,当汉军南撤时,却遭到匈奴右屠耆王大军的伏击,损失惨重。
另一路从西河出发的大军由公孙敖率领,与路博德先期到达的汉军会于诼涂山。可他们是越老越胆小,总是避着匈奴军,走走停停,瞻前顾后,虽然队伍庞大却毫无所获。
“李广利误国!路博德误国!公孙敖误国!”刘彻对着朝会上的大臣们咆哮。
公孙贺和王卿一个个低头不语,任凭皇上在那里发泄心中的怒火。
倒是霍光安慰道:“李陵乃将门之后,即使因力量悬殊不能大胜,也一定能挽回危局,不至于败给匈奴。”
司马迁也道:“臣与李陵乃莫逆之交,深知他的秉性和气节。”
散朝时,刘彻特意叮嘱公孙贺:“只要有李陵的消息,都要立即送到宫中。还有!关于李延年、李季兄弟入狱的消息,你要严密封锁消息,以免扰乱李广利的军心。”
“请皇上放心,臣深知此间利害。”公孙贺答道。
可从情感上说,他倒希望李广利节节失利,最好流亡匈奴。这样,剪除李氏家族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
皇上年纪已经大了,他唯恐中途生变,闹出一场废立风波来。那样,他就既对不起卫子夫,也对不起卫青和霍去病了。
对司马迁来说,他根本没有兴趣理会大臣们的这些明争暗斗,他关心和牵挂的是李陵的安危。
这一天黄昏,司马迁照例来到李府。他是这里的常客,与府令已经很熟悉了。因此,当他一进府门,府令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大事不好了,李将军的一位军侯从前方潜回,说是将军在浚稽山遭到单于大军的围攻,处境十分危急,夫人这会儿,正坐在厅中垂泪呢!”
司马迁心里“咯噔”一下,觉得隐隐作痛。府令后面说了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听见,而是直奔了客厅。
“情况究竟如何?请夫人告知在下?”
“唉!”夫人忍不住哭出了声音,“夫君危险啊!匈奴且鞮侯单于率三万之众将李陵围于浚稽山谷,李陵率领部下勇战数日,斩首近两千多人。匈奴不知底细,不敢轻进。不料他属下的一个校尉降了匈奴,很快汉军的处境急转直下,现时尚不知……”
“夫人不必担心,以将军智勇,必能转危为安。”
“唉!大人哪里知道,路将军竟然袖手旁观。”
“有这等事?”司马迁很吃惊,路博德是跟随霍去病多年的老将,他怎么可以这样置朝廷大局于不顾呢?
司马迁如芒在背,在客厅待不下去了,他现在最关心的是皇上对这件事情的态度。
“夫人不必担心,在下这就到丞相那儿去打探消息。”
出门时,司马迁嘱咐道:“此事先不要告诉老夫人。”
从丞相府回来,司马迁的心就更加沉重了,事情远比夫人所说要严重得多。
路博德和公孙敖报来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说李陵已经投降匈奴,余部四百多人逃回汉军大营。
深秋冷月孤零零地悬挂在院内那棵槐树梢头,周围的星辰稀稀落落地撒在天空。
司马迁再也没有心思埋头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了,他独自一人在书房前踱着步子,以致夜露湿了鞋尖而浑然不觉。他思绪纷乱,在京都与大漠间徘徊。
那是出征前的话别。也是这样一个上弦月的时光,两人喝了许多的酒。
李陵微敞衣襟,双臂撑着酒桌说,多年以来,他最讨厌的就是朝野喋喋不休地议论李广难封,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这次皇上把建功立业的机会给了他,他发誓要用匈奴人的首级为《李广列传》增添精彩一笔。
“那时候,请仁兄不要忘记写上李陵乃李广之孙,大汉骑都尉。”
夜阑相别,司马迁牵着马缰道:“愚兄在京城等待贤弟的佳音,归来之日,你我一醉方休。”
言犹在耳,可你现在何处呢?
……
匈奴人用两千具尸骨的代价,终于把李陵堵在了狭长的浚稽山谷。他们在从投降的人那里获知李陵和他的校尉韩延年没有后援时,就一面发起进攻,一面派兵喊话,要李陵和韩延年投降。
死!李陵不怕,怕的是军心动摇。
但他还是对路博德抱有幻想,心想,只要率部向南撤退,走出这条山谷,也许就可以与路博德和公孙敖在山南会师。
可这是多么惨烈的撤退,箭矢用尽了,辎重丢尽了,活着的三千将士,拆了车辐充作兵器,伍长以上的军官只剩下短刀。难道祖父当年让三千陇西子弟葬身沙漠的悲剧又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么?
不!
困境中,他拒绝军吏要他流亡匈奴的劝告,对韩延年道:“军人惧死,还称得上是壮士么?将军若有机会回到长安,当明我志……”
靠着一棵松树睡去,李陵在梦中看见了司马迁。他隐约听见太史令在呼唤他:“李陵!你还活着么?”
一个激灵,他睁开沉重的眼睛,却不见司马迁的影子。
月亮已经隐没在山后,留给山谷墨色的朦胧。他推了推身边的韩延年道:“趁着夜色,将军速速南撤,否则等到天明,只有束手就擒。”
韩延年站起来,从身边的鼓手手中拿过鼓槌,想击鼓起士,鼓却不响。借着微光一看,原来鼓面早已被匈奴的箭射穿。
李陵望了望疲惫的韩延年,脸上挤出一丝苦笑:“总共不过百骑,还用得着鼓吗?”
匈奴人很快地从灌木中惊起的飞鸟做出汉军要逃的判断,千余名骑兵围追而来,韩延年急道:“将军率部南撤,末将断后!”
“还是你先走,本官断后!”
韩延年不再说话,手持短刀冲进敌阵——他再也没有回来。
士卒一片片倒下,也将李陵的壮志撕成碎片。
“当”的一声,李陵将短刃丢在地上。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李陵放弃了最后的抵抗……
当余部四百多人在军侯的率领下退入汉军要塞时,他们的耳际仍然响着几日前李陵遣散他们的声音。
“仗打到这个分上,败局已定。本将不忍各位兄弟葬身大漠,你等可随军侯散去,日后如果能回到长安,可向皇上陈奏兵败真相。”
曹掾给每人分了二升糯米、一块冰,大家就出发了。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听到将军的消息。
军侯面对守塞的将领,放声大哭:“将军一定殉国了。”
可还没有等到要塞将领传信给酒泉太守,第二批回来的汉军就带来了李陵投降的消息……
月上中天,清凉如水,云际间传来一声孤鸿的嘶鸣。
司马迁抬头看去,多么希望从孤鸿口中落下只言片语。
那天,李陵兴冲冲地奔来,告诉他将率步军单独出击的消息,而他却把一个十分不愿提起的问题摆在了李陵的面前:“如果遭遇围困,贤弟将会怎样处置?”
李陵不假思索道:“真到了那一步,我当效法祖父,杀身成仁,绝不苟活屈节。”
“不!他一定还活着!”司马迁望着月光,在心里对自己道。
阳关相别时,李陵曾道:“家父去世早,家母孀居一生,含辛茹苦。我无法报答,却要让她牵肠挂肚。此番前去,若埋骨他乡,家母和妻儿便托仁兄照顾了。”
一个热血男儿,说到母爱,竟然泪洒尘埃,如此大孝之躯,怎会面对强敌,屈身求生呢?
司马迁怎么都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书童一觉醒来,隔着窗棂望见司马迁的背影,一下子慌了神。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太史令身边,小心问道:“大人心中有事么?”
司马迁摇了摇头。
“小人知道,大人是在牵挂李将军,可他在千里之外,大人就是着急也无济于事。现在已是寅时二刻,大人彻夜不眠,明日以疲累之身,又怎能上朝奏事呢?”
哦!都寅时了!司马迁沉吟着进入书房,眼前摊开的是正在修改中的《李广列传》,难道这是上苍的暗示么?
“李陵,我的兄弟,真到了那一步,你会如老将军那样以身殉国么?你会的!我相信我的眼光。”
司马迁打定主意,要在朝会上为李陵辩护。他朝着门外喊道:“备车!”
他记下了这个日子:天汉二年十一月初十……
塾门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李陵的投降成为官员们议论的中心。每一条消息都让司马迁的心阵阵紧缩。
“知道么?李陵投降匈奴了。”
“可惜!将门之后,就此身败名裂了。”
“不会吧!李陵从小就跟随李广将军,又长期待在侍中,深受皇恩,怎会有如此有辱家门之举呢?”
“呵呵!大人不相信吧?听说龙颜大怒,那个为李陵送信的陈步乐自杀了。”
“还有呢!昨日后半夜,廷尉府把李陵的母亲和夫人都抓了起来,发现老夫人并无丧子之哀,因此断定李陵投降无疑。”
司马迁强撑着上前,发现说话的是上大夫壶遂,就知道绝非传言了,可他还是忍不住问道:“大人也相信李陵会屈节么?”
“哦!是太史公啊!”壶遂急忙起身。虽说两人秩禄、官阶差别很大,可司马迁的才气和为人素来是受到朝野尊重的。他和司马迁来到塾门外,说话的声音就小多了。
“李陵一家俱已入狱。皇上震怒,丞相惶恐,连御史大夫都一夜未眠。此事非同小可,在下知道大人素与李陵交好,不过今日朝会说话还是小心些好。”
司马迁自是十分感激,忙打拱相谢。
尽管司马迁平日对壶遂不是很待见,可这个时候,他的一句话都会让他感到温暖。
从未央宫前殿传来包桑悠长的声音:“辰时已到,请各位大人上朝。”
司马迁定了定神,跟随丞相、御史大夫等朝殿门口走去。这平日里不知走了多少遍的熟路,今天却是如此漫长。他每朝前迈一步,都觉得膝盖分外沉重。
刘彻准时出现在朝堂,他昨夜是在钩弋宫过的。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破坏了他与钩弋夫人温存的兴致,让他一夜都陷在郁闷和烦恼中,直到丑时才昏昏睡去。
晨光中,刘彻的脸看上去有些浮肿,它虽然使得日渐爬上脸颊的皱纹浅了一些,却掩盖不了日益老去的容颜。当那阴沉的目光扫过朝堂时,大臣们都齐刷刷地垂下了头。
朝会的议题非常集中,就是怎样处置李陵投降匈奴的问题。
从丞相以下,只要是站在这个大殿里的,几乎都采取了一边倒的姿态。纷纷斥责李陵叛敌变节,投降匈奴的行为。
刘彻一直面色冰冷地听着大臣们的陈奏,当鼎沸的人声渐渐平息的时候,刘彻忽然问道:“司马迁来了么?”
司马迁没有听见皇上的叫唤,此刻在他的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幅血淋淋的画面:
李老夫人躺在血泊中,在她的身边躺着的是尸身渐冷的李陵夫人;再远一些,是被血水浸透了深衣的李陵儿女们。他们刚来到这个人世,还没有来得及品尝人间的冷暖,就成了异界的冤魂。整整百口人命啊!
“司马迁何在?”刘彻在大臣中寻找着他的影子。
这一回司马迁听到了,他走出朝列,用笏板遮住了泪水浸湿的眼睛,答道:“臣在。”
“朕记得!当初是你极言李陵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现在你还这样认为么?”刘彻冷漠的目光中带着讽刺。
司马迁对刘彻的质问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意外,声音响亮地答道:“皇上,臣现在仍然不改初衷。”
“哼!”跟在冷笑后面的是严厉的斥责,“说你是书生,果然迂腐不堪!事实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请皇上容臣详细禀奏。”司马迁向前迈了一步,好让皇上能够更清楚地听见自己的陈述,“臣观李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士之风。如此一位看重名节的将军岂能轻易屈节?倒是那些私心自用,不顾大局,只求保全妻子的人妒贤嫉能,肆意扩大李陵的罪行,实在令人痛心。”
司马迁这话一出,大殿内一阵骚动,公孙贺正待说话,却听见刘彻严厉谴责的声音:“罢了!朕何须明察,这个软骨头,既是被匈奴俘获,就该效仿他的祖父,以死殉国,孰料他竟然……”
可司马迁却并没有因为皇上震怒而有丝毫收敛,反而更加激昂地辩解道:“即便是李陵投降,也必有不得已的缘由。况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司马迁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沙哑,泪水顺着脸颊,打湿了俊美的胡须,满腔的悲愤割断了他的语序。
“他……他虽战败,然……然对敌之杀伤和摧毁足以昭示天下,即便暂时委曲求全,也是为了日后报答汉室啊!臣乞皇上开瀚海之恩!”
司马迁缓缓抬起头看着刘彻,但他没有从刘彻那里获得任何希望,等来的却是暴怒。
“吴尊何在?”
其实,从司马迁为李陵辩白时起,吴尊就在御史大夫身后窥视着这一切。
结局是在预料之中的,他明白等待司马迁的只有诏狱。可是,当刘彻点他的名字时,他还是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以致回答皇上的话都有点口吃。
“臣……臣……臣在。”
接下来,仿佛一切都陷入了死寂,只有刘彻浑重的呼吸声敲击着每个人的心。每个人在这无声的空间中,似乎心跳声都被放大了。
当刘彻用冰冷的语言打破这难耐的沉寂时,大臣们的心声被惊得戛然而止。
“将司马迁下狱,严加审理。”
“将李陵全家下狱,以儆效尤。”
司马迁的眼前洇出漫天血红。他被羽林卫押出未央宫的那一刻,仍然倔强地扭头喊道:“皇上!李陵是冤枉的。”
冬天的脚步循着节气一步不落地踏上了北海的草原。
先是刀子一样的冷风一连吼了几天,接着,大雪覆盖了枯槁的草地,冰封了湛蓝的湖水,匈奴人最难熬的漫长季节到来了。
苏武一觉醒来,发现炉子里烧的牛粪不知什么时候灭了,整个穹庐变成一座冰窖,身上似乎裹了一层冰,每一丝毛发都失去了温暖与活力。唉!平日里还可以勉强取暖的毛毯,在这样的日子里简直薄如丝绢。
苏武不再睡觉,在穹庐内来回踱步,舒展筋骨,祛除寒意。
对已在北海放牧一年的苏武来说,回大汉去,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往手上哈了一口气,苏武掀开穹庐的门,禁不住“啊”了一声。大雪在梦中已让辽阔的天空与苍茫的草原浑然一体。他惦记着羊圈里的十几只羊,本能地拿起靠在边墙的汉节,心中掠过无言的酸楚。
离开长安时,那汉节曾带给他和平的希望。可一场事变,不但将两个国家推向战争,而且也让他的回归变得越来越渺茫。
只有这汉节让他觉得必须活着,有一天回到长安去,回到皇上身边去。
苏武走出穹庐,眯着眼睛看着大雪。想必长安现在也是冰雪覆盖的深冬了吧,那时候,他和李陵都在侍中供职,每日在皇上身边参谋政事,帮助皇上整理文书。闲暇之际,两人还常常外出郊游。
那一年端阳节,他俩骑马沿着渭水一路走去。正是渭河涨水的季节,水面浩渺宽阔,他们的思绪回到了屈原年代。
苏武驻马,等后面的李陵赶上来道:“当年屈原就是沿这汉江放逐的。”
李陵笑道:“这怎么会一样呢?屈原当年是遭人迫害,又不为楚怀王所信,才被放逐的。而我们现在可是皇上身边的人,皇上惜将爱才,雄图大略,即使秦皇也不可比,此正是你我建功之时。”
苏武毕竟年长几岁,感慨道:“为兄所言在于人生的遭际。宦海沉浮,前程多变,难免你我不会遇到奸佞。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离开长安,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去。”
李陵虽然从内心对苏武的忧虑不以为然,却还是问道:“果真到了那一天,仁兄将何以处之?”
苏武勒住马头,望着从脚下远去的渭水,若有所思地说道:“家父与令祖曾是多年同僚,自为兄初晓人事,家父就不断地教诲我,君子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果真到了那一天,为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虽是郊游闲语,可这话仍让李陵十分感动,他在马上打躬作揖道:“李陵当以仁兄为楷模,恪守忠孝节义之德。”
……
现在,命运果然将苏武抛在了遥远的北海。
匈奴人的威胁他不怕,吞雪咽冰的苦他也不怕,他最难忍耐的是寂寞和孤独。他已许久没有听到乡音了,他真担心长此下去,舌尖上再也滚不出长安话中那种沉雄、粗犷的节奏。
他不敢想这些,一想心就剧烈地痉挛和疼痛。而他殷殷牵挂的还有两位好友——李陵和司马迁,他们还好么?
苏武使劲地摇了摇头,把这些痛苦驱除出自己的脑海。他出门刚刚迈开第一步,就深深陷在盈尺的积雪里,他想退回去,可羊圈里传来头羊凄凉的叫声,让他打消了退却的念头。
羊现在是他惟一的伙伴,没有它们,他会更寂寞。
羊群瑟缩着,抗御寒冷的本能使它们挤在一起,昨夜临睡前添的干草蓬乱地被踩在脚下。
苏武有些枯瘦的手抚摸着一只只羊,传递给它们一息温暖。可当他的目光停在墙角那只永远睡去的羊时,还是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昨夜的风雪又使他的伙伴少了一个。
这种日子不会再有人光顾这里,苏武俯下身体,开始清理脚下的积雪。
雪太厚,不一会儿他的额头就热气腾腾的,寒冷渐渐远去,人也有了活气。他抬眼朝远处张望,发现在苍茫的雪原上,有几个黑点在缓缓朝这儿移动。
他的眼睛顿时潮湿了,生出活过来的不尽欣慰。
那是于靬王属下的千夫长和他的亲兵。一共三个人,五匹马,马背上驮着的是何物呢?大概是冻羊肉吧!匈奴人就靠这个度过漫长的冬天的。
此刻,千夫长已经站在苏武的穹庐前,寒冷加上雪中跋涉,使他们一个个脸色青紫,嘴角干裂得没有一滴水分,只有那野性的眼睛仍被雪照得发亮。
“千夫长受累了!”苏武说着,就将他们请进了帐内。
等干牛粪冒出红红的火苗时,他把白雪倒进鼎锅,不一会儿,穹庐里就有了生机。
喝下千夫长送来的马奶酒,苏武觉得舌尖不再僵硬,话也多了不少:“感谢于靬王这样大冷的天还来关照苏武。”
于靬王是且鞮侯单于的兄弟。去年秋天,他刚刚被流放到北海不久,于靬王就率部到这里狩猎了。他毫不隐晦对单于的不满,他一直记得左骨都侯吐突狐涂的教诲,向来以汉匈和睦为己任。可且鞮侯单于哪听得进去呢?
苏武牧羊就在于靬王的领地,有一天,他到北海湖畔狩猎,就邀苏武同往。
他很惊诧,看上去文质彬彬的苏武竟射得一手好箭。一场狩猎下来,他的猎物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部属。这次邂逅使他们成了朋友,每隔一段时间,于靬王就会派人送些酒食来。但是,千夫长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刚刚复苏的感觉一下子冰凉了。
“这是在下最后一次为使君效劳了。”
“怎么,单于知道了?”
千夫长摇了摇头:“不是!于靬王已于前日暴病身亡了。”
“啊?!”
千夫长试图用滚热的马奶酒驱除心中的悲痛:“于靬王弥留之际,要在下速送些食物给使君,不想这风雪……”
苏武十分震惊,接着就按匈奴人的风俗,朝东方拜倒了。
“神圣的太阳神啊!请您保佑于靬王升天吧!”
“事已至此,使君也不必伤心。往后,使君要好自为之。”千夫长安慰道。在不经意间,他提到了一个人的名字,“使君认识李陵么?”
“李陵?”苏武眼里发出异样的光彩,“岂止认识,那是在下的兄弟。快说说,他怎么了?他到了贵国么?是作为大汉的使节迎接在下回归的么?”
这一连串的问话,让千夫长有些应接不暇,倒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更多的事情。
但这犹豫也只是一闪念,既然已是朋友了,就不该瞒他了:“他投降了。本来单于要他来劝降使君,但都被他谢绝了,在下觉得他是无颜再见使君。”
这些话苏武没有听见,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相信将门之后,大汉的骑都尉会这样不顾气节,拜倒在单于脚下。可在千夫长向他描述了浚稽山大战之后,他就不得不相信了。
“贤弟!你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难道你不顾长安的妻儿了么?”苏武暗暗叫苦。他不再说话,沉闷地喝着马奶酒,目光直直地盯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