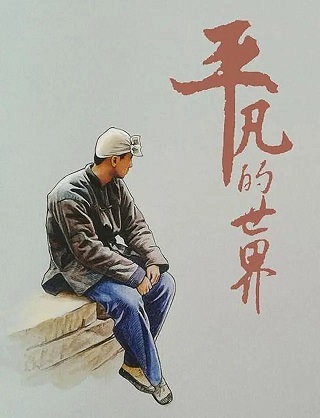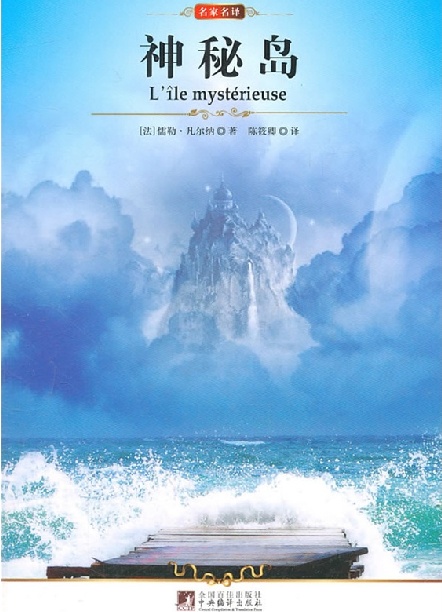三月七日,约翰内斯堡。
佩吉特到了。当然了,他惊恐万状,立即建议我们离开这里去比勒陀利亚。当我和善却坚定地告诉他我们要待在此地时,他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后悔没把自己的枪带来,并且开始兴奋地大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守卫过一座桥,在小普帝克姆之类的什么地方的一座铁路桥。
我马上打断他,吩咐他去把那台大打字机拿出来。我以为这会让他忙一阵子,因为那台打字机肯定有问题——它一直有问题——他可能需要把它送到什么地方去修一修。但是我忘了佩吉特具备总能正确地处理好所有事情的能力。
“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打开了,尤斯塔斯爵士。打字机一切正常。”
“所有的箱子……你什么意思?”
“还有那两个小箱子啊。”
“我真希望你不要总这么多管闲事,佩吉特,那两个小箱子跟你没关系,是布莱尔夫人的。”
佩吉特变得垂头丧气,他讨厌犯错。
“那么你就再把它们装好吧。”我接着说,“完事以后你可以出去走走,到处看看。约翰内斯堡明天可能就会变成一堆冒着烟的废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我想这样总能打发他一上午吧。
“等您有空时,我想跟您说点事,尤斯塔斯爵士。”
“我现在没空,”我赶紧说,“我目前一点儿空都没有。”
佩吉特退了出去。
“哦对了,”我冲他喊道,“布莱尔夫人的箱子里都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一些皮毛毯子,几件皮草,还有……还有一顶帽子,我想是的。”
“是的,”我附和道,“她在火车上买的。那种帽子——你没认出来那是帽子也没什么奇怪的,我敢说她去阿斯科特赛马会时会戴。还有什么?”
“还有几卷胶卷,一些篮子……很多篮子……”
“可以想象。”我说,“布莱尔夫人是那种不管买什么都要起码买一打的人。”
“我想就这些了,尤斯塔斯爵士。还有一些零七八碎的东西,面纱和几双手套之类的。”
“如果你不是个白痴,佩吉特,你应该一眼就看出这不可能是我的东西。”
“我以为是佩蒂格鲁小姐的。”
“啊,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你给我挑了一个可疑的人做秘书是什么意思?”
我对他讲了我被询问的事,但话一出口就立刻后悔了,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种神采,我非常熟悉的神采。我急忙转换话题,但已经太晚了,佩吉特已经做好准备和我理论了。
接着他又给我讲了一件发生在基尔默登堡号上的、毫无意义的事,无聊至极。和一卷胶卷和一个打赌玩笑有关。半夜三更,一个服务生把一卷胶卷从通风口扔进了一间客舱。我对佩吉特说我不喜欢恶作剧,而他又从头到尾把这件事讲了一遍。他真的太不会讲故事了,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弄明白。
再见到他时是午饭时间。他一脸兴奋地走进来,像只闻到猎物味道的侦探犬。我一向不喜欢侦探犬。原来是因为他看到了雷伯恩。
“什么?”我惊讶地叫了起来。
是的,他认出过马路的行人中有一个是雷伯恩,于是就跟踪了他。
“您猜我看见他碰到并跟谁讲话了?佩蒂格鲁小姐!”
“什么?”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还没完呢。我去稍微打听了一下有关她的事——”
“先等一下,雷伯恩呢?”
“他和佩蒂格鲁小姐进了一家古董店……”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佩吉特停下来,不解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说,“继续。”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但他们都没出来。最后我进去了,尤斯塔斯爵士,商店里没人!一定有另一个出口。”
我直勾勾地盯着他。
“然后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回到酒店,询问了一下佩蒂格鲁小姐的情况。”佩吉特压低声音,再次像他每次准备说出什么机密时那样喘着粗气,“尤斯塔斯爵士,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一个男人从她的房间里出来。”
我挑起眉毛。
“我还一直把她当作一位令人尊敬的淑女呢。”我嘟囔道。
佩吉特没在意,接着往下说:“我当即就上楼去搜查了她的房间,您猜我发现了什么?”
我摇摇头。
“这个!”
佩吉特拿出一个安全剃须刀和一块剃须皂。
“一个女人怎么会需要这些东西?”
我觉得佩吉特可能从没读过上流社会的女性杂志。但我读过。我不准备和他争论,但并不认同只凭一个剃须刀就质疑佩蒂格鲁小姐的性别。可怜的佩吉特远远地落后于时代,此时他如果再拿出一包香烟来当作证据,我都不会感到惊奇。不过就连佩吉特也有他的局限性。
“您不相信我的判断,尤斯塔斯爵士,那您对此怎么解释?”
他手里拿着一团东西,得意地在空中晃悠着。我看了看,恶心地说:“看着像头发。”
“就是头发,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假发。”
“是的。”我说。
“现在您相信佩蒂格鲁其实是男扮女装了吧?”
“是的,我亲爱的佩吉特,我想我信了。其实我早就怀疑她了,因为她的脚。”
“反正就是这样。现在,尤斯塔斯爵士,我想跟您说说我的私事。从您的暗示以及不断提及我在佛罗伦萨那段时间的举动,我相信您已经发现了。”
佩吉特在佛罗伦萨的秘密终于要揭晓了!
“那就说清楚吧,我亲爱的伙计,”我慈祥地说,“这样最好。”
“谢谢您,尤斯塔斯爵士。”
“是不是她丈夫?讨厌的家伙,那些丈夫们,总是在你最不想见到他们的时候出现在你面前。”
“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谁的丈夫?”
“那位女士的丈夫。”
“哪位女士?”
“上帝保佑,佩吉特,你在佛罗伦萨碰到的女士啊。肯定是和一位女士有关吧。你可别告诉我你只是抢劫了一座教堂,或是刺杀了某个你看不顺眼的意大利人。”
“我真的听不懂您在说什么,尤斯塔斯爵士,我想您是在开玩笑吧。”
“我确实是个爱开玩笑的人,特别是面对麻烦时。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现在我没有开玩笑。”
“我希望您没有认出我,因为当时我离您很远,尤斯塔斯爵士。”
“认出你?在哪里?”
“在马洛,尤斯塔斯爵士。”
“在马洛?你去马洛干什么?”
“我以为您知道——”
“我现在知道得越来越少了。你从头开始讲吧,你去了佛罗伦萨——”
“这么说您并不知道……也没有认出我来!”
“根据我的判断,你好像毫无必要地把自己暴露了——因为良知而成了一个懦夫。但是我要听听事情的全部过程才能有更好的判断。现在,深吸一口气,从头讲起。你去了佛罗伦萨——”
“我没有去佛罗伦萨,就是这样的。”
“呃,那么你去哪儿了?”
“我回家了——回马洛了。”
“见鬼,你到底为什么去马洛?”
“我想见见我太太,她身体不太好,还怀孕了——”
“你太太?我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
“是的,尤斯塔斯爵士,这正是我要告诉您的,我在这件事情上欺骗了您。”
“你结婚多久了?”
“八年多。我刚给您做秘书时才结婚六个月。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可一个住家秘书不应该有太太,所以我就隐瞒了这个事实。”
“你真要把我吓死了。”我说,“这么多年她都住在哪里?”
“大概五年前,我们在马洛的河边买了一所小房子,离米尔庄园很近。”
“上帝保佑,”我喃喃地说,“有孩子吗?”
“有四个孩子,尤斯塔斯爵士。”
我呆呆地看着他。我一直坚信佩吉特是个容不得愧疚和秘密的人,他的诚实和高尚总给我带来麻烦。不过这种秘密倒是像他会有的: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
“你跟任何人说过这些吗?”我好奇地盯着他看了好久,最后问了这么个问题。
“只和贝丁费尔德小姐说过。她去了金佰利火车站。”
我依旧盯着他,这让他有些不自在。
“尤斯塔斯爵士,您没有太生气吧?”
“我亲爱的伙计,”我说,“我不介意明确地告诉你,你把事情全搞砸了!”
我怒气冲冲地出去了。经过街角的那家古董店时,我突然一时冲动,走了进去。店主搓着手迎上来。
“您需要些什么?皮草还是古董?”
“我想要一些不寻常的东西。”我说,“为一个特殊场合,能给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吗?”
“跟我到里面的房间好吗?我们有不少特别的东西。”
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我很聪明,就跟着他走进了摇晃着的门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