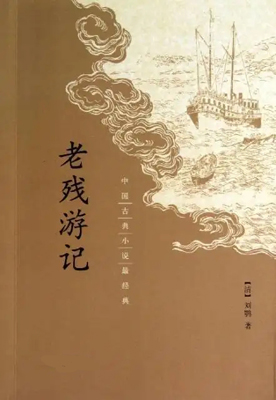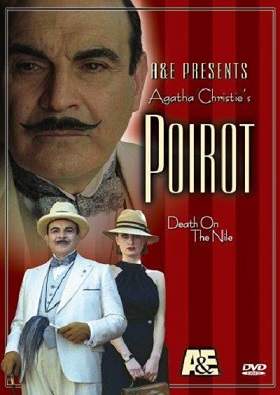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一一民谚
一
光阴似箭,腊尽春回。凤英在陈柱子饭铺面案上干活,已经半年多了。她摸清陈柱子的脾气是喜欢勤快的人以后,每天起早摸黑,拼上性命去干活。冬天腊月集时,四乡赶集的人多。陈柱子的饭铺每天要卖五六十斤面的面片,这五六十斤面全由凤英和成面块,再擀薄切成面片。几十斤重的面块放在案板上,先用压杆压,再用擀杠擀,两块面擀下来,凤英全身都是汗水了。白天再忙一天,到了夜里,浑身的骨架就像散了一样。可是凤英没有叫过苦,不管再累再苦,第二天见人总是满脸笑容。她也不是没有伤心的时候。比如说和春义就经常生气。春义冬天卖了一冬青菜,赚的钱并不多,有时一担菜要卖两三天,但他决不串小巷子叫卖。
有时候凤英劝他:“这有什么难的,你就磨炼着喊叫几声,还能小了你?”
春义不吭声。凤英说得多了,他就冷冷地说:“我嗓子有毛病,不能大声喊叫。”
凤英说:“明天我跟你一道去卖菜。我替你吆喝!”
“你去叫卖我就走。”春义吼着。
“你干吗发那么大火?”
“我见不得丟人败俗!”春义仍大声嚷着,凤英委屈地说:“我给你丢了什么人了?”
春义回答不出,气呼呼地走了。就因为这点口角,春义竟至两天不和她说话。凤英几次笑着和他搭讪,春义却冷冰冰地不理她。
凤英心里委屆,有时在夜里悄悄蒙着被子哭一场。她觉得吃好吃坏、干活轻重都无所谓。两口子每天不说一句话,真要把人别扭死。不过她毕竟能拿得起放得下。晚上不管再别扭,早上眼泪一擦就是笑容。陈柱子的板扇店门只要一下掉,顾客们像潮水似地向里边涌着,这时就又响起她银铃般的笑声。
到了春二三月,新菜没有上来,白菜萝卜之类的冬菜也都下市了,正是卖菜的淡季。春义到菜园子里贩不来菜,赚不来钱,只好歇着。不过他也自觉,凤英在店里吃饭,他自己烧饭吃,平常吃三顿饭,现在吃两顿饭。凤英看他人已经瘦下来,脸像个刀条一样窄,心里着实疼他,有时候趁陈柱子和老白不注意。狠狠心把饭铺里的馒头,偷偷拿一个塞在春义口袋里。春义却掏出来,正经地说:“给人家送回去!你这样叫人家怎么信得过?”
凤英看他那么固执,恨恨地啐着他说:
“饿死你,我也不心疼!”她说着,自己却落了眼泪。不过她还是心疼春义,她听人家说香油最养人,一口油能顶得上一斤面的营养。有一天晚上,她悄悄把灶上炒菜的香油噙了一口。装着和春义玩,吐在他的嘴里。春义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又在躺着,只好咽了下去。
两口子闹别扭,哪能逃过陈柱子的眼睛。凤英每天虽然装得若无其事,可是人后长吁,背地短叹,连老白也看出来了。她和柱子商量说:“如今青菜没下来,春义整天在家蹲着,每天半饥半饱的,得给他想个办法。”
陈柱子叹了口气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什么都对他说了,可他就是一个不出摊。可见人有几种,天生的秉性不同,凡是大灾大难,饿死的都是这号人。其实只要舍得身份,现在也有钱赚。卖不了地里菜,卖树头上的菜,洋槐花、榆钱儿都下来了。他要是会爬树,每天采几篮子在街上卖,城里人吃个新鲜,照样能变成钱。”
老白说:“这办法不行。他挑青菜还不好意思,去人家树上摘更磨不开了。本地人欺生,他干不了这个。叫我说就叫他也到咱饭铺里来,他能不会挑个水、和个面?”
陈柱子说:“我早想过了,只是乡亲邻居,好进难出。再说他这个人成天拉着脸,好像人家都欠他二斗黄豆钱没还一样,谁还敢来买面吃?这种人不适合跑堂站柜台,只会干点死活。”
老白是个心里盛不住半句话的人,早把陈柱子这些话传给凤英了。凤英听了以后,一方面感激老白,一方面却还不死心。
她对春义说:“你看咱们在柱子哥店里住,你不能学得有点眼色?
回到店里,看见有什么活就干,人家留咱在这里住,心里也高兴一点。”
春义听她说得在理,也不拗她,只是说:“我插不上手啊!”凤英笑着说:
“扫地你会不会?每天清早那一阵最忙,你就把地扫一遍,也给我们腾点工夫。”
春义说:“扫地当然可以。”
第二天早上,春义下大劲儿去帮陈柱子扫地。可是等他起来,陈柱子已经在打扫了。他走过去说:“柱子哥,叫我扫。”陈柱子说:“不用。我这用不了几下子就扫完了。你赶快准备去挑菜吧。”
凤英看他没有把扫帚抢到手,又好气又好笑。到了晚上,她悄悄地把扫帚藏在春义睡的席子下边,没有等天亮,就把春义叫起来扫地。陈柱子开始没有找到扫帚,后来看春义在扫,也就任他打扫。他情知这是凤英教给他的,心里想:“这媳妇可不是盏省油的灯。”
二
渭河岸上有几座小磨坊。这种磨坊都是在河上垒个堰坎,再开一条小渠,把水引过来,下边装个大木轮,用渠水冲动木轮,木轮上的立轴就带动石磨的下扇转动起来。这种水磨比牲口拉的旱磨功率要大好几倍。水顺时,一天能磨五六百斤粮食。所以咸阳城各家商店、饭铺,以至学校、机关很多家吃的面粉,都是由这些磨坊承包供应的。
陈柱子的饭铺用的面粉,由石桥村的范老四的磨坊供应。
陈柱子是用麦子换面。夏天天干,面粉里吃不得水,讲定一百斤小麦,换七十五斤面粉,到了冬天,面粉里含水分多,一百斤小麦要换八十一斤面粉。不过陈柱子有个要求,就是他在粮行里买好麦子,要范老四把这些麦子单淘单磨,保证供给他上好的细白面。因此陈柱子饭铺擀出的面片儿,烩在锅里,不但雪白光滑,软韧不断,放在嘴里还有嚼头。
一天,地里麦子扬花时候,范老四赶着个小毛驴来送面。陈柱子帮他扛下面袋,过了秤,捧过来水烟袋让他吸着问:“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送面,伙计呢?”
范老四说:“走了。人家卖壮丁走了。看见两千斤小麦眼红了。非去当兵不可,我留也留不住。我就说和你讲讲,麦子也快熟了,我人手少,磨倌也走了,从下月起你另找个面户吧!我也知道你老陈办事公道,可我实在帮不上忙了!”
陈柱子说:“你再雇个人嘛,一盘小打磨,顶上你种八十亩地。现在市上光麸皮就卖两角多钱一斤。叫我说,你这小磨不能不转圈。”
范老四说:“人不好雇啊,别看我这个磨坊,雇的人第一要能下力,第二要老实可靠,因为磨坊在河边野地里,成天胡捣棒棰的人不行。第三还多少会算个账,要不连个秤也不识,还是办不成事。”
陈柱子不慌不忙说:“我给你举荐个人,这三条都行。人是正派老实不过了。还会算账。保准你看得上。”
范老四问:“你们河南人?”
陈柱子说:“是啊。反正你相信我就行了。”范老四忙说:“我知道你陈掌柜说句话,掉到地下砸个坑。不过,最好能当面看看川川”
陈柱子说:“这好办。”他打算叫凤英去街上叫春义,却见店门口凤英已经领着春义回来了。
陈柱子说:“这不,就是他。”
范老四看着春义:白净面皮,细高个子,眉清目秀,细腰宽肩,人虽然单薄一些,面相却憨厚实诚。
范老四不先讲雇他当磨倌的事,拍拍他的肩膀说:“喂,小伙子,你帮我算一笔账。一百斤麦子换八十一斤面,我今天给陈掌柜送来一百六十四斤面,合多少麦子?”
春义几乎不加思索地说:“二百零二斤半。”
范老四把手一拍说:“帮肩!行。”说罢就要带春义走。陈柱子说:“范掌柜,最好先把身价讲一下。我们都是外乡人,家里都还有老有小。你起个辙儿,我们决不讨价还价。”
范老四说:“一天三顿饭,我用罐子送到磨坊里,一个月给他一百斤小麦,干得好了,我再外加。”
陈柱子回头问春义。春义红着脸,点了点头。陈柱子拍了一下桌子说:“行。那就一言为定了。外加不外加,那就看他干得怎样了。反正你老范是痛快人。”
春义临走时,陈柱子交代说:“兄弟!总算给你找着个事儿了。端人家的碗吃饭,不比在自己家里,要能吃得苦,受得气。
最重要一条,就是手续要清楚。他就是把钞票扔在地上,咱拾起来也要交还给他。另外,吃人家熟的,拿人家生的,要干就尽力干。活可能重一点,有时还要打夜作,习惯就好了。要不是日本鬼子把咱们家乡占住,咱也不会流落到这一步。你去吧,反正你还来送面,还要经常见面。”陈柱子教育着他,春义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春义和凤英只有一条被子,凤英把那条被子用麻绳捆好,让他背去。春义不肯带,他说:“带个破棉袄夜里盖上就行了。”凤英却执意让他把被子带去。柱子说:“河滩里夜风尖,你还是把被子带上。凤英在店里,怎么都好将就。”春义只好带着被子去了。
到了河岸范老四的磨坊,春义见到一渠清水,几株垂杨,附近地里豌豆花、油菜花一片姹紫金黄,麦田里送来阵阵扑鼻麦香,多少天来他胸中的痛苦和闷气都消溶在这宁静的大自然中。
麦子的香味是沁人心脾的。他熟悉这种气味,他热爱这种气味,尽管这些土地不是他自己的。
三
春义走了以后,凤英的肩头上像卸下一副重担:“他总算有个吃饭地方了!”同时她又产生了一种孤寂的感觉。一年多来,她们从家乡飘流到洛阳,又从洛阳飘流到西安,最后又来在咸阳。他们像两只失了窝的鸟一样,形影不离地比翼飞着。虽然经常闹些小气,但这些小气没有影响到他们患难与共的感情。
现在春义走了,她好像失去了自己身上的影子。人连个影子也没有,是最感到孤单的。
老白平常买些榆皮刨花泡在水里,每天梳头时,向头发上抹一些,头发显得蓬松发亮。她有时也让凤英抹一些,说让头发有点光泽。这几天凤英不抹她的刨花水了。她好像觉得不应该再抹。因为春义走了。这种下意识的“慎独”思想,也没有人教过她,只是受着良心的驱使。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有一种天然的宿命观念:那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联保处的秦喜来陈柱子的饭铺里更勤了。今天来借个火柴吸烟,明天来打盆热水洗脸。来到店里,屁股就像粘在凳子上,眼睛不住地在凤英身上转。凤英觉察到这一点,她的目光碰到秦喜的目光时,总是赶快眯一下眼睛不看他。她装着不理会,心里却暗暗提防着。
有一次,秦喜来说要找点生姜发汗。正巧陈柱子和老白都出去了。凤英说:
“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放,等他们回来你再拿吧!”
秦喜笑嘻嘻地说:“你不知道我知道,就在那个墙角一堆沙子下埋着。”他说着就要动手去扒,凤英怕他拿多了,忙说:“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扒一点。”
凤英在弯着腰扒生姜时,秦喜站在她身后。看着凤英的修长身躯,他的头发起热来。凤英转过身,拿着一小块生姜说:“你看这够不够?”她垂着眼睫毛不看他的脸。
秦喜没有吭声,他喘着气,忽然捏住她的手,用沙哑的嗓子嗫嚅着说:“你真漂亮!……”
凤英顿时觉得浑身血液往头上冲,她把手一甩说:“你干什么!”
秦喜松开手,踉跄着脚步跑了,一块生姜落在地上也忘记了拿。他跑出饭铺后,竟碰在卖水二夯的水桶上,凤英忍不住笑起来。就在她笑的时候,觉得心脏跳动得厉害,她使劲地按住胸口,好像深怕一颗心跳出来。她按着水缸沿,在水缸里照了照自己的脸,脸竟然红得像红布。她又笑了。她不敢看西墙边地下铺着的那个草铺,那里放着春义的一件棉袄。
以后秦喜不大来陈柱子的店里了。有时候从门口经过。也是匆匆而去。有一次老白喊着他说:“秦喜你近来怎么不来玩了?”
秦喜低着头说:“我有事。”
老白说:“是不是我们店拴了个老虎,你害怕?”老白说话本来是句玩笑,秦喜听起来却觉得一定是凤英向她说了那天的事。
他没有敢回答,只在嘴里咕噜了两句,赶快走了。
凤英心里清楚却不言语。她微笑着心里想:“陕西人也这么胆小!”
四
夏天时候,咸阳铁路上来了一批铁路工人,陈柱子的牛肉面铺生意更加稠起来。为了适应这些铁路职工的口味,陈柱子还加上了炒菜。陈柱子是经过世面的厨师。熘个牛肉丝,炒个鸡丁肉片像玩的一样。炒菜要比牛肉面多卖几倍钱。陈柱子盛钱的大竹竿筒,平常一天只卖半筒钱,现在每天却卖得满满一筒。
有时陈柱子还要抓出几把,放在一个小木箱里,怕票子溢出来。
晚上串柜的时候,花花绿绿的钞票从竹筒倒出来有一大筛子。凤英这时才感到一个店铺的威力。他看着陈柱子整好的一叠叠钞票,那些钞票散发出一股油腻的气味,也散发出汗水的气味。一天几十斤面,都是她和出来的,擀出来的。老白干什么?
老白不过摘摘菜、剥剥葱,有时给客人们端端饭菜。夜里,她扳着指头算着:这个饭铺的本钱有什么?也不过是一口将军帽大锅、两个炒锅、一个案板、一个水缸,剩下就是那些碗、碟、刀子等小厨具了。可是就这些东西,每天却能挣那么多钱。她自己每月才挣十元钱,占不到陈柱子一天赚的十分之一。不过她又想到陈柱子的手艺。陈柱子用抹布握着炒锅翻菜的样子,陈柱子勺子放调料的利索姿势。她想着:“人家有手艺,所以人家赚的钱多!”可是她又想:“手艺不是人学的吗?谁也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会。”
金钱是个魔鬼。它改变了人的性格,它诱发着人的能量,它粗暴地、无情地破坏着人和人的淳朴关系。
凤英好像又长了一颗心。她干活更卖力了。特别是对陈柱子,不但给他打水洗脸盛饭,每天上午还要给他沏一杯茶。
有一天她问陈柱子:“大哥,为什么把空锅放在火上,等着冒烟才放油?”
陈柱子说:“热锅凉油炒出来的肉嫩。”说了以后,他又赶快说:“肉有几种肉,油有几种油,里脊和臀尖不一样炒法,草头和后腿又是不同炒法,花生油和菜子油不一样用法,豆油和芝麻油也不一样用法。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凤英看柱子不肯细说,也就不敢再多问。原来陈柱子有个规矩,就是“能舍钱一千,不教一招鲜”。他学来这把手艺不容易,又深知在市场竞争上“同行是冤家”,所以对外人,不管再亲再近,总要留着一手。
凤英用嘴问不来的本领,却用眼看来了。每逢陈柱子在菜案上切肉下料,她总用心瞅着,陈柱子怎么样炒菜烧鱼,她也留心看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时间久了,她也把炒菜的程序路数记得八八九九,特别是做牛肉面这些容易做的面食,她已经领悟得烂熟了。
有一次,她去石桥磨坊看春义。正巧碰上两个农民在离磨坊不远的地方,刨一棵老皂角树,她就问:“你们怎么把这棵皂角树刨了?”
一个农民说:“这是棵公皂角树,多年不挂皂角了,想把它刨掉做几张案板卖。”
凤英灵机一动,她知道皂角木案板最好,坚实有韧性又光滑。就问:“你们自己做案板吗?”那个农民说:“实不瞒你说,我们爷儿俩就是鲁班爷门下的木匠。”凤英看了又看这棵皂角树,有五六把粗,主干有一人多高,就说:“要是给我合一张四尺半长、三尺宽的大案板要多少钱?”
那个老木匠说:“你不是春义的屋里人吗?我们和春义都熟。你随便给,自己的皂角树,也不费两个工。”凤英看他们说话诚实,就叫着:“大爷,你还是说个价。我不能亏你。”老木匠想了想说:“你给十块钱吧!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价。”
凤英听他说只要十块钱,比市上的大案板几乎便宜一半。
马上从袜子筒里拿出十块钱递给老木匠说:“大爷,那就算回事了。案板做好,就放在春义的磨坊里,我改日来取。”
老木匠连忙点着头说:“一定,一定。”
她到了磨坊里,春义正在蹬着大木箩箩面,凤英笑着说:
“来,让我替你蹬一会。”
她蹬着大箩对春义说了说刚才订了一张皂角木案板的事。
春义说:“那个老木匠叫范清水,是专门做木锨头、犁底卖的。没有错。”他接着又问:“咱买这么大案板干啥用?”
凤英笑着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两个月以后,范老四赶着大车进城拉麦子,春义怕做成的新案板在磨坊里丢了,就放在车上拉到了城里。
到了陈柱子店门口,春义把案板往里边搬时,老白说:“春义,你买这么好一块床板啊!”春义正待要说话,凤英急忙跑过去装着帮他抬床板,悄悄向他摆摆手,又扭回头笑着对老白说:“我叫他买的床板,睡在地上有点潮,他能想得起来?”
春义听凤英把面案板说成床板,也不知道原因,不敢再说话了。陈柱子在灶上烩面,也瞟了一眼。见这个板有一寸多厚。四尺半长,做得严实合缝,刮得起明发亮,心里早清楚了。他暗暗吃了一惊。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但没有料到这一天来的这么快。
夜里,陈柱子收拾好碗筷锅灶封上火,往小茶盅里倒了一两白干,照例用食指在酒里蘸了一下弹在地上,表示每天对财神的敬意。然后慢慢放在嘴边呷起来。
老白披着个棉袄,坐在被窝里没有睡。她说:“凤英买了那么好一块床板,两个人都抬不动,真舍得。”
陈柱子慢条斯理地说:“看起来你跟我出来跑了半辈子,你连凤英一半都赶不上。那不是床板,是准备开饭铺的案板。”
老白这时才恍然大悟。她说:“怪不得凤英遮遮藏藏的。她能开起饭铺?”
“她怕钱咬手?”
老白气愤地说:“想不到这个长眼睫毛存了外心了。太没良心了!要不是咱收留她,两口子说不定早倒在哪条大路边了!
如今才硬了翅膀,就想飞啦!”
陈柱子呷了一口酒说:“这事情你也不用动那么大的气。跳行立店,这些都是我当年玩剩下的把戏。‘房檐滴水照样行’,谁也不傻。现在咱一天能进七八十块,她当然能算这个账。人只要看到钱会赚钱,你就是用八根大套绳,也捆不住她。”
老白揉着眼说:“她会不会马上就去开个饭铺?”
陈柱子说:“眼下她还未必能唱这本戏。不过她真要这样干,可苦了咱了!”
“为什么?”
“她比你年轻,比你漂亮!”陈柱子说着吹熄了灯。
里间屋灯熄了。外间地铺上春义和凤英还没有睡。
凤英悄悄地对着春义耳朵说:“我的憨大哥,你怎么今天把案板拉回来了?一块案板能压塌你磨坊的地皮?”
春义说:“我怕在磨坊里被人偷跑了!”
凤英:“小声点!……”
春义又问:“你到底买这块大案板干什么?”
凤英压低着声音说:“我也准备开饭铺哩!告诉你,菜刀、炒锅我都买好了。”
春义忙说:“啊唷!这样不好吧,柱子哥该伤心了。他现在生意忙,正需要人手,咱就给他出几年力,算得了什么。”
凤英娇嗔着说:“我给他出的力够大了。这一年我当牛当马,累得衣裳能拧下来汗水。一个月才赚他十块钱。可他呢,一天就赚七八十元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不想再给他背这包袱了。钱兴他赚,也兴咱赚。八仙过海,各显各的本领。”
话虽这么说,春义总觉得这样作太不仁义。他正色说:“凤英,你要在这里扎根吗?咱们还不是混两年,等黄河水下去了,还要回家吗!你要真的这样做,你自己干,我可不干。我觉得这样做对不起人。”
凤英笑着,暗暗地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说:“死心眼!……”
夜里,凤英几次醒来,她用手摸着身子下的案板,她深怕把案板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