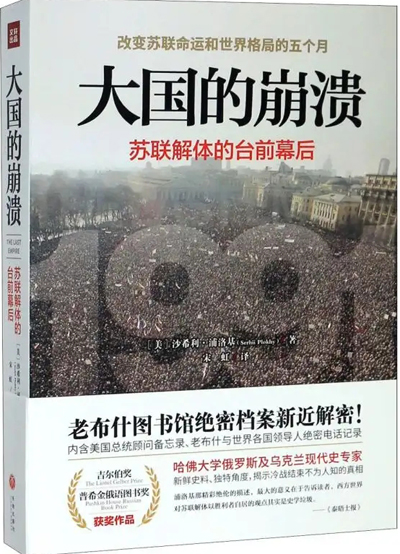好难好难,
吃饭没盐。
吃水没井,
割麦没镰。……
——黄泛区民歌
一
自从天亮参军跟随部队走后,李麦就留在黄泛区。宋敏和几个有病的老弱同志没有走。他们化装成老百姓,一直坚持在这茫茫无际的水荡子里。
宋敏和李麦住在一起。两个人相依为命,就像亲母女一样共同生活着。几年来,她们搬了多次家。在这里搭个草庵,在那里搭个窝棚。后来她们就住进离泥土店不远一个土地庙里。黄河水虽然年年改换河道,渐渐地,她们也摸出了它的规律:“紧水冲沙,慢水冲淤。”每年河道走慢水的地
方,总会留下一片肥沃的淤泥土地。她们就在这块淤地上种庄稼,搭草庵。待到冬天时候,她们就回到高岗上的土地庙里。
部队离开时,徐中玉因为发疟疾也没有走。他和几个老弱病号留在赤杨岗的沙岗上。离李麦住的地方只五六里地远。这些年来,徐中玉几个人主要靠捕鱼为业,到了秋天大水过后,这里的黄河鲤鱼遍地都是。一个个水洼子里,挤满了红尾巴鲤鱼。他们不用网打,不用笊捞,跳到水里一捉就是一大筐,然后把鱼挑到周家口去卖。
这里距离周家口比较近。他们挑一担鱼到周家口,两天能打个来回。初开始,他们没有经验,鱼挑到周家口市上,大多数都死了,卖不上价钱。后来他们发现在路上只要换两次水,不断地摇晃着鱼筐,到周家口市上大多数鱼都还活着。几年来,他们就是这样从周家口换来些日用必需品,艰苦地生活着。
李麦和宋敏住在泥土店,有时候徐中玉给他们送来些食盐、火柴,再从她们这里背走些粮食。有时候因为大水下来了,把他们两家隔在河两岸,李麦她们就只好吃淡饭过日子。
在水荡里过日子是苦寂的,每天只看到日出日落,鸟去鸟还。她们不知道初一,也不知道十五。有时候哪一天过年也不知道。在这个环境里,李麦慢慢学会了唱歌。她唱的歌都是她自己编的。比如到了没有盐吃的时候,她就扯起嗓子唱着:
“好难好难,吃饭没盐。吃水没井,割麦投镰。……”
她唱歌的声音是忧郁的,但脸上表情却是快乐的。她的歌子总带点解嘲味道。有时候她和宋敏吃几天白水煮豇豆,实在熬不下去,她又唱起来了。她唱着:
“桑木弓,牛皮弦,弹一斤花,两毛钱。拿上钱,买汤元,桂花馅儿鲜,豆沙馅儿甜。老娘不吃你这赖汤元,有钱去称二斤盐。……”
不知道为什么,宋敏特别爱听这些俚俗的民歌,每一首都使她增加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每一句都好像又把她重新放在儿时的摇篮里。
大约是这个苍茫无际的荒野芦荡太寂寞了,人们对一股烟、一点火都感到亲切。她们需要抒发自己的胸臆,需要歌声的抚慰,在这个满是荒榛的大自然怀抱中,人们又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李麦似乎也年轻多了。她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的智慧光芒又点燃了起来,她那张小巧的嘴里,不断地流泻出像珠玉一般的语言和歌声,使人感到新鲜、痛快、惬意。
她们吃着豇豆麦粥,漫天的柳絮在她们跟前飞舞。李麦叹息着,忽然用筷子敲着碗唱起来:
城里菠菜靠南墙,
乡里老娘不得尝,……
她不假思索地唱着。有时候一口气能编几十句。这些朴素的山歌俚句像小河流水一样,滔滔不绝地向外流淌着。宋敏总是笑得流出眼泪来。
有时,李麦还唱些情歌:
哥哥挑担一百三,
磨烂肩头磨烂衫。
磨烂衣衫妹会补,
磨烂肩头妹心酸。
每逢唱这些情歌时,她的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好像有说不出的惆怅。
“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多歌儿?”宋敏有时问。
李麦说:“有的是我自己编的,有的是小时候学的,有时候狼腿拉到狗腿上,都互相串了。你想,我推过十几年磨,又推过十几年盐,不会唱个歌不闷死了。”她问:“你就没有听过这些山歌?”
宋敏说:“没有。”
“你就没有个奶奶教过你?”
宋敏苦笑着说:“我奶奶整天躺在床上抽鸦片,烟瘾过足了,就打麻将牌,她哪里有工夫教我们唱歌。我们家是个地主家庭。我几个叔和我爹整天吵架闹事,翻箱倒柜。从我记事,俺家不隔三天,没有不吵架的,一个大院子里,四五桌麻将牌天天打着,就像个赌博场。”
“你妈哩?”李麦问。
“我亲妈在我十四岁那年就死了。”宋敏说着低下头,“她不识字,没有文化,我爹在城里又娶了个姨太太,是南阳简师的学生,从此就不理我妈,他们打过几次架,把穿衣镜都砸了。就是那一年,我妈气疯了。每天披头散发在大街上乱跑,手里拿着一根小棍,见个人就对人家说:‘我识字!我也识字!我会写字。’说罢就在地上乱画。其实画的什么也不是。后来病越来越重,就死了!……”宋敏说着眼圈红了:“我们那个家就不像个家,哪像你们,爹像爹,娘像娘。我恨死了我那个家,我就是因为这个才参加了革命。”
二
去年秋天,海骡子汉奸队里两个人来赤杨岗这一带搜粮食,被徐中玉等人打死在西沟苇川里。从此以后,汉奸队不敢进苇川了。这却惊动了驻周家口的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听说黄泛区有了共产党,就从周家口调出一个小队,在黄泛区通住周家口的李桥地方,安了个据点。
鬼子把据点安在原沙河大堤上,周围架了铁丝网。他们把附近的芦苇烧了个干净。每天设岗放哨,切断了黄泛区通往东南的大道。去年腊月,有两个老百姓到周口卖鱼,走至李桥北边堤下,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从此,这条路再没有人敢走。徐中玉等人也不能去周家口了。他们每天从苇川里望着大堤上那个碉堡,好像眼中扎了根钉子。
今年收罢麦子时候,徐中玉绕道去了一趟开封。回来时,他拐到泥土店,兴奋地对宋敏说:
“部队快回来了!咱们的部队快回来了!听说要在咱们这里建立豫皖苏八分区,还要建立县政府。……”
一听说大部队要回来,李麦和宋敏都高兴得想要跳起来。宋敏大喊着:“苦日子熬到头了!苦日子熬到头了!”她一会儿抱住李麦,一会儿拉住徐中玉,后来一个人在岗子上唱起歌来。她唱着: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这歌声是那么悲壮,那么雄健,她好像要把这五六年的苦水一下子倾倒出来,把这么多年胸中郁积的块垒喷吐出来。徐中玉看着她那高兴的样子,感叹地对李麦说:
“小宋可真高兴啊!”
这天中午,李麦留下徐中玉吃饭,她煮了几条鱼,烙了几张饼,徐中玉还带来半瓶酒。他们用芦苇杆插在瓶子里,轮流顺着喝着。宋敏没有喝惯酒,竟然喝得满脸绯红,醉眼朦胧,嘴里还喊着:“我一点也没有醉。你是大婶,你是老徐!”她指着他们说着,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吃罢饭,徐中玉要走,他说:
“小宋,你不去送送我?”
“还用送啊!下苇川一直往南走。”宋敏说着又换了口气说:“好,我去送你!”她站了起来,却走不成路了,身子东摇西晃像扭秧歌一样。
“好玩极了!好玩极了!就像驾云一样。”
李麦说:“还说你没有醉?脚下边变成三条路了。到路上风一吹,才走不成路呢。叫我看,哪里也别去了。”
徐中玉看她走不了路,扶着她说:“小宋,你别送我了,明天我再来看你。”
宋敏要强地说:“我没有醉,我去送你!……老徐……不,徐老师,……我应该叫你老师。那一天,你亲了我一下!……我……”
徐中玉听她说出这种话来,脸一下红到耳朵后边,他连忙说着:
“你休息吧!你休息吧!”把她交给了李麦,自己匆匆走了。
三
夜里,芦苇里的青蛙叫声停止了。夜色像墨一样浓,一阵微风吹来,苇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宋敏一觉醒来,已经是后半夜了。她觉得有些兴奋,同时又觉得有点儿惆怅。她今年二十四岁。在农村,算是年龄很大的姑娘了。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她在这个水窝里已经蹲了整整五年。岁月,时光,都在手指头上流逝了,这些天来她特别想念大部队,那里有她的真正的“家”,那里有她亲爱的同志和姐妹。那是一个快乐和有朝气的集体。
她又想起了徐中玉,她想起他那两只忧郁而胆怯的眼睛,……干吗总像老夫子一样?说话嗫嗫嚅嚅的,难道就因为当过自己一学期老师吗?……我喜欢他吗?我不喜欢他。我要是喜欢他,我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可是每一次单独在一起时,他的嗓子就沙哑起来,像伤了风。唉!不去想它了。大部队马上就要回来了。那里小伙子多的是!”
她仍然睡不着觉,翻了个身,故意把睡在她身边的李麦弄醒。
“大婶!你说人一定得结婚吗?一辈子不结婚行不行?”她附在李麦耳朵跟前问。
李麦醒了。她迷迷糊糊地说:“好好的人,为啥不结婚?”
宋敏说:“一个人也可以过一辈子呀r’
李麦说:“老天爷把人分成男人、女人,就是叫结婚的。”
宋敏吃吃地笑起来。她说:
“你回答得倒简单!”
李麦也笑了。她说:“这本来就很请楚嘛。”她问:“宋敏,我看老徐和你说话时,温首腆颜的,他是不是对你有点意思?”
宋敏笑了。她没有回答,却问:“大婶,我昨天喝醉酒,是不是说了什么话?”
“你没有说什么。”
“我说了,好像他红着脸跑开了……”她思索着,停了一会儿,又说:“大婶,我不喜欢他。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窝囊,说话细声细气的……”
李麦说:“男人们也不能都像猛张飞!你喜欢什么样的人?”
“我喜欢有点男子汉的气魄。”
“老徐也是高高大大,站到那里像模像样哩。”李麦故意说着。
宋敏摇摇头。过了一会,她侧过身对李麦说:“大婶,有一次我们两个在苇塘边洗衣服,他忽然抱住我的头亲了我一下。我还不懂啊,我推了他一下,他就跌倒苇塘里边了,最后还是我把他拉了出来。从那以后,他看见我就像老鼠见猫一样,”她说着,吃吃笑起来,又说:“大婶,我那时真不懂啊,我又不是存心推他。”
李麦也笑着说:“怪不得,有一段时间我看他来到我们这里,很不自然。宋敏,这件事以后别再向别人说了。这种事儿,要给人留点面子。再说老徐都二十七八了,要不是抗日打仗,还不早结婚了。……”
宋敏摇晃着李麦说:“大婶,别说了……”
夜深了。月光透过房角上的空洞,照射进茅屋里。宋敏已经安详地睡了,发出了均匀的呼吸。李麦却睡不着觉,她在想念着儿子天亮。五六年来,在芦苇荡里东藏西躲,她没有做过一次看见儿子的梦,听人说心宽的人不会做梦,难道自己是心宽的人吗?她又有点害怕作梦。因为按农村圆梦的说法,梦里的事情都是和真事相反的。比如说梦里看见人死了,恰恰是人活了,看见一副白木料棺材,说是要发财,因为棺材和银子一样颜色。据说最不好的梦是在墙头上骑马,在井里行船。李麦不想做这些梦,她既不愿看到满脸是血的死人,也不愿意看到代表银子的棺材。她只希望天亮平平安安。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平安即是福啊!”
下午,她曾问过徐中玉:
“部队要回来,我们家天亮也会回来吧?”徐中玉回答说:“原则上是地方干部都回地方。他们是四师,四师的人大部要回来。”
李麦不好意思再深问了。几年来她和宋敏一块生活,使她懂得了许多道理,她知道了一个八路军战士不应该有太多的“家庭观念”,那么她这个八路军战士的妈妈,也不应该只想到自己的儿子。想到这里她默默地说着:“谁家的儿子都有娘,谁家的儿子都不是柴禾棒,随他吧!……”
四
黄昏时分,秦云飞和天亮等才回到红柳集。红柳集被黄河水冲走了一半,另外半条街还有一些房屋。到了营部门口,只见几个衣服褴褛的人,并排坐在一棵倒在地上的老柳树上。
一个黑脸汉子向他们走过来。他一张污黑的脸,满脸胡子。张大嘴笑着,露出一排白牙。
他怯生生地说:“你是老秦吧?”
秦云飞审视着他忙问:“你是?……”
“徐中玉。原来咱们在一个大队。”
“你是老徐?”秦云飞一把把他抱住了。徐中玉一边笑着,一边抽出手擦着眼泪说:“听说咱们……部队回来了,我们在苇川晕找了几天了。……”
宋敏这时跑过来喊着:“秦政委!”她紧紧握住秦云飞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泰云飞看她穿着一身像鸡子啄过一样的破军装,脚上穿着自己打的草鞋,脸晒黑了,颧骨凸起来,只有那一双眼睛,还认得出是当年那个唱歌的小文工团员。
他有些凄然。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笑着说:“小宋,你变成大姑娘了。不简单,在水窝里坚持了五六年。”
宋敏笑着说:“人都快泡成酸菜了!”她说着,流下两行热泪。
李麦瞪着眼睛,看着每一个战士的脸,她要寻找自己的儿子。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战士急促地走过来。
“妈!”
李麦听着这个声音,浑身哆嗦起来。眼前这个战上,她却不敢相认。她说:
“你是?……”
那个战士把帽子拿掉说:“妈,我是天亮,你认不出来了?”
李麦重重拍了他一巴掌,说:“你个赖种!你怎么变成了方脸了?声音也变了?……”说着,她用布衫大襟擦着眼泪。天亮把她从柳树上扶下来,笑着说:
“妈,你还没有变,还是那样儿。”
李麦说:“唉,人都扭成麻花了!……”
五
晚饭时,李麦看到伙房有不少白面,就提出要给大家擀一顿面条吃。
秦云飞说:“算了吧,天也晚了,想吃面条明天再说。”李麦却执意要擀,她说:“不费事,一会儿就擀好了。”徐中玉说:“大婶,没有吃饭的,还有十几个人哪,都是小伙子。”李麦笑着说:“你就是三十个人,我也不在乎啊。我看了,现成的一块大案板,擀起来容易。常言说:‘起脚饺子落脚面’,回到老家了,还能不吃顿面条。”
宋敏知道李麦的脾气,她要想干的事儿,一定得把它干成。她喊着说:“你们别管了,我帮大婶擀面条。”
两个人到了伙房,李麦先把菜板刷了刷,没有找到大的和面盆子,就在案板上和起面来。她一口气和了三大剂面,布衫已经被汗水湿透贴在身上了。面和好后,天亮偷偷跑进来说:“妈,我来擀吧!我会擀面。”李麦说:“你们擀的面条我见过,粗得像顶门杠子!你别管,你出去!”
天亮向宋敏摇了摇头,出去了。李麦随手把门关上。宋敏说:“大婶,叫我擀吧,我先擀一剂。”李麦说:“你们谁也不用管,我一个人包到底!”她拿起擀面枝,搬过来一大块面剂,“哐通!哐通!”地擀了起来。
她先把面块轧开,把它擀成椭圆形,然后再由圆变方,由方变圆。在她的手中,擀面杖就像一架奇妙的机器,面块在案板上翻卷旋转,压延跌摸,不一会工夫,一大块面剂就变成了又薄又匀,笸箩般大的大圆皮摊在案板上……。
李麦向面上撒了点干面粉,又用擀面枝把它整整齐齐叠起来。她顺手拿过一把切面刀,在盆沿上“蹭”了两下,然后就飞快地切起面来。
一阵“格登格登”的均匀响声,转眼间,一排像银丝的面条已经放在案板上。……
煮好了面,每个人盛了一大碗,蹲在地上吃了起来。大概是因为跑了一天,肚子都有些饿了;另外,李麦做的面条确实好吃,谁也顾不得说话,只听见“呼噜噜,呼噜噜”的声音。
宋敏给李麦盛一碗面条端了过来。李麦在休息乘凉,她没有马上吃。今天晚上她心里高兴,熨贴而又有些凄然。她听着那“呼噜噜呼噜噜”的声音,简直像一曲音乐,一首诗歌。几十年前,她在给那推盐的同行们做饭时,享受过这种慰藉,那是她毕生经历过的最快乐的场面。现在她又回到这个热闹的集体中了。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她拿不出一个鸡蛋来慰劳他们,因为这里没有鸡子了。所有的家畜都没有了。可是她能用汗水、用劳动来献出她一片热爱的心意。
六
第二天,秦云飞和徐中玉等人研究,准备拔掉日本鬼子的李桥这个据点。
秦云飞告诉大家说:“现在敌人把一大部分力量集中在东南亚战场上,中原这一带敌人处于守势。据了解,开封驻的还不到五百个日本兵。李桥是通往周家口、蚌埠的咽喉要道。鬼子设在李桥的这个据点非常讨厌,等于把咱们的门户封住了。所以必须把它拿掉。”
徐中玉介绍情况说:“这个小队叫渡边小队,只有十几个人。有一挺重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还有一匹马,那个小队长每隔两天骑马去周家口一次,其余时间很少出来。”
秦云飞说:“咱们再把情况详细摸一摸。既然打,就要打得漂亮一些,这是咱们回到黄泛区的第一仗。”
为了弄清楚敌人的活动规律,由李麦每天到李桥附近观察情况。她扮一个农村老太太,每天到河边挖芦根,捡野菜,敌人的岗哨也不大注意她。经过半个月的了解侦察,弄清楚了这个小队一共只十三个人,每天早上上一次操,下午五点钟以后,总有几个日本鬼子在院子里练练单杠。中午时候,大约经常有七八个日本兵要下河洗澡。不过白天黑夜,碉堡附近总有一个站岗的,晚上在碉堡里边,白天就在桥头。
李麦每天把这些情况汇报给秦云飞。秦云飞带领着几个战士,伏在芦苇里观察了两天,最后,决定就在中午时分,趁那些日本鬼子去洗澡的时候,进行包围袭击。
计划决定以后,宋敏等几个女同志也要求参加这次战斗。秦云飞让她们全都转移到附近苇川里,因为红柳集目标太大,说不定敌人会窜到这里来。宋敏只好跟着李麦钻到小李庄的苇林里。
这天中午,天气闷热得像盖上盖子的蒸笼。鬼子们吃罢午饭后,相互喊叫了一阵,有七八个鬼子顺着桥头走向河滩。他们一个个脱得赤条精光,跳在河里洗起澡来。
秦云飞看到机会来了,就布置天亮带领一个排,从桥北边绕向碉堡,先收拾那个站岗的鬼子,然后直扑他们的宿舍。他亲自带领两个排,伏在大堤下,只要枪声一响,就到河里捉那几个洗澡的日本鬼子。
天亮带着十几个战士,刚刚爬上桥北的沙岗,就被那个站岗的日本鬼子发现了。他嚎叫着,向沙岗这边开了一枪。天亮看到已经暴露目标,就和战士们伏在沙岗下还击。那个站岗的日本鬼子被打死在桥头上了。宿舍里几个日本鬼子却不见动静。天亮等人一直向敌人宿舍扑去。宿舍门关着,天亮一脚踢开,向里边投了一颗手榴弹,里边仍不见动静。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战士发现四个日本鬼子,正从一个后窗户向外爬着。有两个已经爬出来跑到大堤下,另外两个正在向外跳。
天亮和战士们立即向窗口开枪射击,有一个日本鬼子被打死了,两个被活捉了,宿舍里的一个,从大门走出来举手投降。
在河里洗澡的几个日本鬼子听到枪响后,一个个拼命向东岸游着,准备逃走。因为枪声响得早,秦云飞等人还没有赶到。幸好这时天亮等人已经占领了桥头碉堡,他们从桥上向东岸射击,有两个鬼子被打死在水里,其余的四散游开。这时秦云飞等已经赶到,战士们纷纷跳下水去,把五个赤着身子的鬼子全捉住了。
在清点敌人的尸体和俘虏时,发现只有十二个人,另外一名日本鬼子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秦云飞命令大家赶快搜索,可是找遍了附近的苇林草丛,都没有发现一点足迹。
大家正在着急,忽然看见李麦和宋敏等几个女同志,从南边苇林边押着光着身子的日本鬼子走了过来。
原来宋敏等到小李庄以后,心里老记挂着这边的战斗,她们想看看怎样战斗,就让李麦把她们带到下游河边,装作在那里洗衣服。她们听到枪响,一个个正朝桥上张望,忽然看到河里钻出一个人来。他们还当是自己的战士,喊着问:“打开了没有?”
那人却不吭声,掉头又往下边泅着。李麦眼尖,她看着这个人上嘴唇上留着小胡子,游水的姿势也不像本地人的游法。就大喊着:
“老日!”
李麦这一声喊,几个妇女一齐跳下水去追赶那个日本鬼子。她们一齐大喊着:“截住他!截住他!’那个日本鬼子吓迷了,被她们捉上岸来。
她们把这个日本鬼子押送来后,经过询问,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渡边小队长。宋敏笑着埋怨说:
“把我们送到远远的地方,作战计划也不让我们知道,好像多神秘一样,结果还是我们捉住了个当官的!”
秦云飞说:“这一次给你们记一大功。我向你们检讨,以后再有任务,一定请你们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