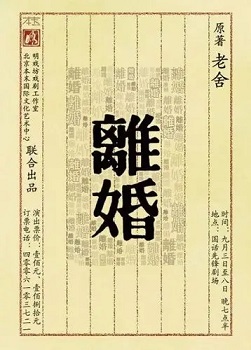小东西似乎被吓坏了。他看见宝琛说要去请郎中,就冲着他的背影喊:“宝琛,你要快点跑,没命地跑!”听见小东西这么喊,夫人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她过了一会儿睁开眼睛,摸了摸他的头对他说:“孩子,宝琛不是你能叫的,你该叫他爷爷。”随后她又对老虎说:“你带他出去玩吧,别吓着他。”可小东西不肯走。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什么事来,他趴在夫人的枕头边,凑近她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话,夫人就笑了起来。
“你猜这孩子刚才跟我说什么?”夫人对喜鹊说。“什么话让夫人这么高兴?”“还高兴呢!”夫人笑道,“他问我会不会死。”随后她又转脸对小东西说:“死不死,我说了不算,呆会儿你问郎中吧。”过了一会儿,又道:“这郎中说了也不能算,得问菩萨。”“什么是死呢?”小东西问她。“就像一个东西,突然没了。”夫人说。“可是,可是可是,它去哪里了呢?”“像烟一样,风一吹,没影儿了。”“每个人都会死吗?”“会的。”夫人想了想,答道,“你公公活着的时候,常爱说一句话,他说,人生如寄。这话是说呀,这人活着,就像是一件东西寄放在世上,到了时候,就有人来把它取走了。”“谁把它取走了呢?”“当然是阎王老爷了。”这时喜鹊就过来将小东西从床边拉开,对老虎说:“你领他出去玩儿吧,别在这儿尽说些不吉利的话。”老虎带着小东西刚从夫人房里出来,就看见宝琛领着唐六师呼哧呼哧地跑了进来。这唐六师进了门,就问宝琛:“老夫人刚才吐的血在哪里?你先领我去看看。”宝琛就带他去了厅堂。那摊血迹已经让喜鹊在上面撒了一层草木灰。唐六师问:“那血是红的,还是黑的?”宝琛说:“是红的,和庙上新漆的门一个颜色。”唐六师点点头,又俯身闻了闻,摇了摇头,咂了咂嘴,连说了两声“不大好”。这才去夫人房中诊病。夫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七八天。郎中配的药方一连换了三次,还是不见效,等到老虎和小东西进屋去看她的时候,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来了。家里整天都弥漫着一股药香味。村里的人都来探病,连夫人在梅城的亲眷都来了。喜鹊和宝琛也是眉头紧锁,成天摇头叹息。有一次,老虎听见他爹对喜鹊说:“夫人要真的走了,我们爷儿俩在普济就呆不住了。”这么一说,就触动了喜鹊的心事,她就咬着手绢哭了起来。老虎听他爹这么说,就知道夫人恐怕快不行了。这天深夜,老虎在睡梦中,忽然被人推醒了。他睁开眼,看见喜鹊正一脸慌乱地坐在他床边:“快穿衣服。”喜鹊催促道,然后背过身去,浑身上下直打哆嗦。“怎么啦?”老虎揉了揉眼睛,问她。喜鹊说:“快去请你干爹来瞧瞧,夫人又吐血了,吐了一大碗,脸都变黑了。”“我爹呢?”“他不是去梅城了吗?”喜鹊道。说完,她就咚咚地跑下楼去了。老虎记起来了,他爹今天下午去梅城替夫人看寿板去了。孟婆婆说,要做寿材,她家门前的那棵大杏树是现成的,宝琛想了想,说:“还是去梅城,看一副好的来。”小东西睡得正香,他正犹豫要不要把小东西叫醒了跟他一块去,喜鹊又在楼下催他了。老虎下了楼,来到院外。繁星满天,月亮已经偏西,看时辰,已是后半夜的光景了。他穿过弄堂朝后村走的时候,村里的狗一个跟着一个都叫了起来。唐六师的家在后村的桑园边上。他家世代为医,传到他手上,已经是第六代了,他一连娶了三个老婆,还是没能生出半个儿子来。宝琛曾托夫人登门说情,让唐六师收老虎做义子,传他医术。唐六师碍不过夫人的情面,就勉强答应说:“请贵府管家把那孩子带来,让我先帮他看看相。”那是前年的正月十五,宝琛穿戴整齐,提着漆盒礼品,喜滋滋带着老虎登门拜师。那郎中一看见他们父子俩,就笑呵呵地说:“歪头,你让令郎认我做干爹,是笑话我生不出儿子来吧。”宝琛赶忙说:“这是哪儿的话,这是两全其美的,两全其美,这个那个,唐家绝学后继无人,犬子也可以日后有样手艺,在世上有碗饭吃。”那郎中说要替老虎看相,却连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只用眼角的余光朝他轻轻一扫,就摇了摇头,道:“令郎这副材料,让他去跟大金牙学杀猪还差不多。”一句话把宝琛说得笑也不是,急也不是。过了一会儿,那郎中又说:“我倒不是在说笑,你看他眉眼粗大,骨骼英武,让他学医,只怕是大材小用,若从武行出身,将来必有大的造化,做个一两任府尹不成问题。”明摆着是推托,可宝琛居然还信以为真。带着儿子乐呵呵地回去了。他说这唐六师给人看病有下错药的时候,可给人看相却是丝毫不差。打那以后,老虎觉得,因这唐六师“府尹”的预言,父亲连跟他说话的语气都跟平常不一样了。老虎来到唐六师的门前,敲了门,半天,屋里才亮起灯来。这唐六师果然有几分仙气,他也不管来人是谁,就在屋里干咳了两声,送出一句话来,“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老虎一边往回走,就忽然有点担心,他也不问问谁来找他看病,就让我先回,万一走错了人家怎么办?他正犹豫着要不要回去跟他叮嘱一声,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孙姑娘家门前的池塘边上。黑夜中,他听见那扇院门吱嘎一声就开了。老虎吃了一惊。他知道孙姑娘家住着一个从外乡来的弹棉花的人,可这个时候,他出来做什么呢。隔着树丛他看见一前一后两个人影从院里出来。他听见一个女人娇滴滴的声音在说:“你还真是属猪的?”那男的说:“我是光绪元年生的。”“你可不许骗我。”那女的说。“心肝,你自己算算不就知道了?我骗你干吗?”说完,那男的就一把将她拖过来,搂住她腰就亲起嘴来。难道是她?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这么说,他们俩早就认识,这个弹棉花的人果然有些来历,只是他们说的话,什么属猪不属猪的,听上去让人如坠五里雾中。老虎的心里怦怦直跳,他想起几天前在孙姑娘屋里看见的那个绿头巾和竹篦。果然是她。他听见,那个女人把男人推开说:“我底下又潮了。”那男的只是嘿嘿地笑。他们又低声地说了几句什么话。那男的转身进屋,随后,门就关上了。老虎看见她正经过池塘朝他这边走过来,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吓得一时手足无措,只得硬起头皮急急地往前走。那个女的显然是已经发现了他,因为他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越走越快。到后来,她就跑了起来。老虎走到孟婆婆家旁边的弄堂口,那个女的已经追上他。那女人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上。老虎的周身一阵冰凉,站在那儿,手和脚都不会动了。那女人将脸凑在他的脖子里,低低说:“老虎,这么晚了,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她的声音像雾一样,细细柔柔,丝丝缕缕。老虎说:“请郎中给夫人瞧病。”她紧紧地搂着他,热气喷到他的脸上,可她的手指却是凉凉的。“刚才,我们俩说的话,你可都听见了?”她问道,声音像叹息,又像呻吟,她的声音太轻了,如果老虎不屏住呼吸,根本就听不清她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