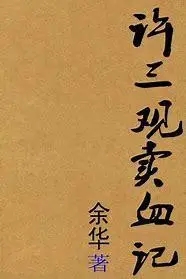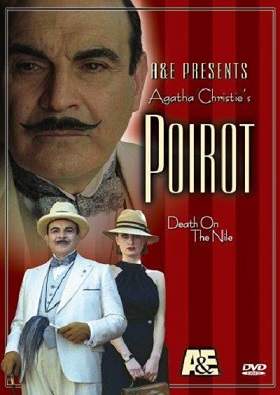这天晚上,秀米从阁楼上给她找出一本《李义山集》,这本书是她父亲旧藏中为数不多的元刻本之一,书页间密密麻麻布满了蝇头小楷:眉批、夹批以及随意写下的字句。不过,对于现在的喜鹊来说,李商隐的诗作显然还是太难了。一会儿萼绿华来,一会儿杜兰香去,大部分篇什不知所云。溽暑来临,喜鹊闲来卧于竹榻之上,随意翻看,尽挑一些雨啊、雪啊的句子来读,像什么“红楼隔雨相望冷”,什么“雪岭未归天外使”,什么“一春梦雨常飘瓦”,虽然不明白这老头说了些什么,可用来杀暑消夏到也正好。
一天深夜,屋外豪雨滂沱。喜鹊在翻看这本诗集的时候,发现一首《无题》诗中有“金蟾啮锁烧香入”一句,不知为何,陆家老爷在“金蟾”下圈了两个圆点。蟾,大概就是癞蛤蟆吧,他干吗要把这两个字圈起来呢?再一看,书页的边上有如下批注:金蝉。凡女人虽节妇烈女未有不能入者。张季元何人?看到这里,喜鹊不禁吓了一跳。本来李商隐原诗,喜鹊不明大概,什么叫“金蟾啮锁烧香入”?再一看老夫子批注“凡女人虽节妇烈女未有不能入者”,似乎是老夫子对原诗的注释,虽然荒唐无稽,但与“金蝉”、“张季元”连在一起,到也并非无因。按照喜鹊的记忆,张季元是在陆家老爷发疯出走之后才来到普济的,那么,他是从何得知这个人的呢?难道说他们原来就认识?另外,“金蝉”又是何物?“金蝉”二字虽由“金蟾”而来,但喜鹊一想到小东西带到坟墓里的那只知了,还有几年前那位神秘的访客所赠之物,不由得背脊一阵发凉。此时,屋外电闪雷鸣,屋内一灯如豆,暗影憧憧。难道陆家老爷的发疯和张季元有什么瓜葛?喜鹊不敢再想下去了,似乎觉得那个老头子就在她的身后。她把书合上,再也无心多看它一眼,一个人呆呆地缩在桌子边发抖。等到雨小了一点,她就赶紧抱了书,一溜烟地跑到后院找秀米去了。秀米还没有睡。她正坐于桌前,呆呆地看着瓦釜发愣。喜鹊一直用它来腌泡菜,秀米从狱中回来后,将它洗净了,拿到阁楼上去了。她的脸上绿绿的,眼神样子看上去有些异样。喜鹊将诗集翻到《无题》这一页,指给她看。秀米拿过去心不在焉地朝它瞭了一眼,就将书合上,随手丢在了一边。眼中冷冷的颇有怨怼之意。她的目光仍在盯着那只瓦釜。她用手指轻轻地弹敲着瓦釜,并贴耳上去细听。那声音在寂寞的雨夜,一圈一圈地漾开去,犹如寺庙的钟声。她一遍遍地弹着瓦釜,眼泪流了下来,将脸上厚厚的白粉弄得一团狼藉。随后,她又抬起头,像个孩子似的朝喜鹊吐舌一笑。在这一刻,喜鹊觉得她又变回到原来的秀米了。这些年,喜鹊往丁先生家去得少了。不过,四时八节之中,喜鹊也偶尔去探望一下,先生爱吃的鸡蛋都按月挑大的送去,从未短少过一枚。丁树则自然地无话可说。师母倒是动不动就到家中来喊她。每次,她都是踮着小脚,风风火火地赶来,一张口,就是“快快,你先生快要不行了”。每一次,喜鹊过去看他,都看见先生好端端地在床上哼着戏文呢。不过,到了今年十一月,丁先生真的是不行了。照例是师母亲自来报信,她只说了一句,那个死鬼,……就哭起来了。丁树则仰卧在竹床上,肚子胀得像个鼓一样,屋子里挤满了人。六师郎中、花二娘、孟婆婆,还有两个从外地赶来的亲眷,都侍立在床侧,一言不发,等着丁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听师母说,先生自从入伏之后,就没有像模像样地拉过一次屎。六师郎中开出的药方,用芦根加荷叶、大黄煎了汤,一连服了七八天总不见效。丁先生一会儿急喘,一会儿蹬腿,眼睛半睁半闭,从中午一直折腾到天黑。最后连师母都看不过去了,就流着眼泪,俯下身体对先生喊道:“树则,你就走了吧。这样硬挺着,又有什么用呢。你走在我前头,好歹有个人替你送终,我要是死了,身边连个张罗的人都没有了。”她这一喊,先生果是乖乖地一动不动了。不过,他还是抬起那只瘦骨嶙峋的手,抖抖地在床单上重重地拍了三下。他这一拍,把屋里的人都拍得面面相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是师母了解他,揭开床单,从铺下取出一张毛边纸来,打开它,孟婆婆拿过去一看,道:“原来是丁先生自己写的墓志。”花二娘笑道:“多亏丁先生周到,这普济能写墓志的,除了丁先生外,再无别的人了。”唐六师似笑非笑接口道:“写墓志的人倒有的是,不过,依我看,丁先生是不放心让别人代笔罢了,他替人写墓志铭写了一辈子,到了自己的这一天也就不假手外人了。”大伙儿只管议论,师母却早已趴在先生的身上哭了起来。六师过去替他号了脉,半晌才说道:“凉了。”〔丁树则自撰墓志铭。其铭文是陈伯玉的《堂弟孜墓志铭》一字不漏的抄袭。铭曰:君幼孤,天资雄植,英秀独茂。性严简而尚倜傥之奇,爱廉贞而不拘介独之操。始通诗礼,略观史传,即怀轨物之标,希旷代之业。故言不宿诺,行不苟从。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闺门穆穆如也,乡党恂恂如也。至乃雄以济义,勇以存仁,贞以立事,毅以守节,独断于心,每若由己。实为时辈所高,而莫敢与伦也。〕丁树则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寿终内寝,丧事多少也就有了喜事的氛围。师母虽然哭得死去活来,但言语之间总离不开一个“钱”字。普济的乡绅出钱替他置办了寿材,树碑立墓,延请和尚颂经、道士招魂。恰巧徽州来的戏班子路过,好事者也就请他们来村中唱戏,一连三天。麻衣相士、风水先生也闻风而来,左邻右舍也都出钱出物,丧事办得既热闹又体面,光酒席就摆了三十余桌。孟婆婆对喜鹊说,你可是正式拜过师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弟子之礼可含糊不得。师母闻说,立即夺过话头,补了一句:“按理那秀米也是正式拜过师的。”花二娘答道:“她一个哑巴,你与她计较个什么。”于是,喜鹊跟着孟婆婆和花二娘,更是整日在丁家帮忙,从天亮到天黑。这天傍晚,喜鹊从丁家忙了一整天,正想回家看看,出门时,看到丁家屋外的树阴下,摆着一张破圆桌,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正在那边吃吃喝喝。这些都是乞丐,循着酒香来的,上不得正席。丁家就在屋外摆上桌子,搁上米饭和简单的菜肴供他们吃喝。那群乞丐又喊又叫,都在你争我拉,还有一个孩子,跳到桌上,抓起盆中的米饭就往嘴里塞。在这群人中,有一个人身穿麻衣,头戴一顶破草帽,怀里掖着一只木棍,只是静坐不动,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喜鹊觉得奇怪,就多看了那人两眼。当她回到家中,在灶下生火时,忽然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她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就起身熄了火,又折回丁家而去,想去探个究竟,可到了丁家门前,发现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到了出殡的这一天,那个神秘的乞丐再次出现了。这人蜷缩在邻舍的房檐下,背靠着山墙,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馒头。帽檐压得很低,抱着一只打狗棍,一双手又瘦又黑。不过,喜鹊看不到那人的眼睛。这个人一定在哪儿见过。当时,喜鹊手里托着一只簸箕正在和孟婆婆给送殡的人发丧花,那些小花是纸做的,有白、黄两种。她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还是理不出任何头绪。她决定上前看个究竟。奇怪的是,她刚往前走了几步,那个乞丐也顺着墙角往后退。喜鹊加快了步子,那个人也随之调整了步伐,一边往村外走,一边扭过头来看她。这说明,那个乞丐不仅认识自己,而且担心被喜鹊认出来。她一直追到村外,看见那个人走上了通往梅城的官道,这才停了下来,两手按着腰眼直喘气。过后好多天,喜鹊一直心事重重的,心里老想着这个乞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