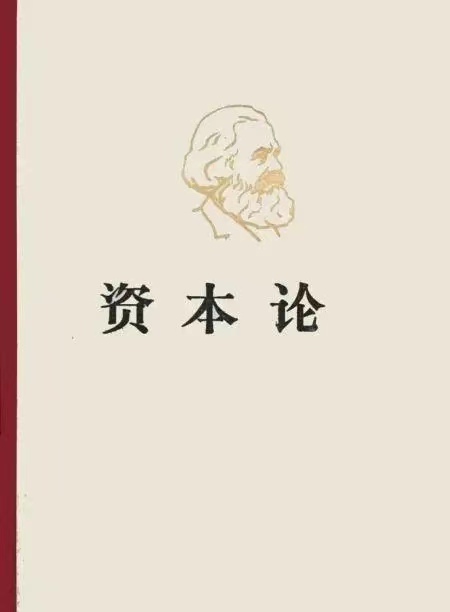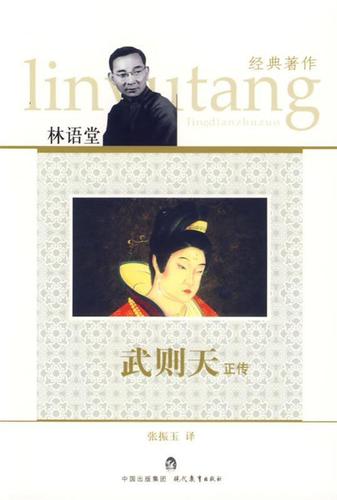1
六月末的一天,谭功达在酣睡中被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惊醒。这似乎是一个恶作剧的糟糕开始:他把手伸到帐子外面,在黑暗中摸索着抓起电话,却听见一个小女孩在电话里唱歌。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谭功达很快意识到,可能是电话串了线,因为伴随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一个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向他问道:
“怎么样,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那时候妈妈没有土地,全部的生活都在两只手上……嗯,你说话呀!”
谭功达昏睡未醒,太阳穴一阵剧烈的胀痛,愣了半天,一时竟没有听清电话是谁打来的。
“什么情况怎么样?你是谁?”
可对方立刻就发起火来,在话筒中叫道:“你他娘的这个县长是怎么当的?她去为地主缝一件羊皮长袄,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怪不得省里一连批转了三封要你辞职滚蛋的匿名信,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迷迷瞪瞪的!”
谭功达终于在那讨厌的歌声中,辨认出了聂凤至的声音。他翻身从床上爬起来,拉了一下灯绳,恍忽中看见墙上的挂钟已指向凌晨三点十分。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打电话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对方根本不容他多想,追问道:
“你现在在哪里?喂,你现在在哪里?你怎么不说话?经过了多少苦难的岁月,妈妈才看到今天的好光景,我问你,你现在在干什么?!”
“睡觉啊!”谭功达似乎没听懂他的话,嗫嚅道:“我在睡觉。”
“睡觉?你说什么?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你在睡觉?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有心思睡大觉!”
“出什么事了?聂书记?”
又是一阵咔咔的咳嗽声。聂凤至似乎要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咳出来似的,谭功达只得静静地等着他呼呼的喘息声平静下来。过了好一阵,对方清了清喉咙,正要说话,话筒里突然一片静默。小女孩的歌声也嘎然而止,谭功达徒劳地冲着话筒,喂喂喂地叫了半天,对方已没有了任何声息。或许是电话线被大风刮断了。
屋外大雨如注,狂风大作,又急又密的雨点嗖嗖地泼向窗户玻璃。水从窗缝中渗进来,把桌子上的一本《列宁选集》都浸湿了。院子的门被风撞地砰砰直响,他不时可以听到瓦片被风刮到地上而发出的碎裂声。谭功达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电话机出神。
聂凤至是出了名的好脾气,谭功达从未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他在凌晨三点多钟给自己打来电话,这还是第一次。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谭功达撩起帐子,胡乱地擦了擦身上的汗珠,心脏仍在突突地狂跳。他竭力地回想着聂凤至在电话中跟他说过的每一个字,可嗡嗡叫着的蚊子和那该死的
歌词,搅得他大脑一片空白。电话断了线,外面的雨又下得这么大,虽然心里七上八下,他知道现在除了等待天亮之外,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
他重新在床上躺下,随手抓过一张旧报纸来,心烦意乱地看了起来。在这张五月十二号出版的报纸上,他读到了如下新闻:
中国政府致电卡斯特罗,坚决支持古巴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事业
首都各界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盛大集会
中国与老挝建立外交关系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二十六届世界
乒乓球锦标赛上,庄则栋,邱钟惠分获男女单打冠军
清华大学举行建校五十周年校庆
国务院召开坚决纠正“五风”,坚决贯彻农业“十二条”座谈会
……
当谭功达想弄清纠正哪“五风”,贯彻哪“十二条”时,沉重的睡意再次向他袭来。他使劲地睁开眼睛。不,不,不能睡着!可他还是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谭功达一觉醒来,太阳已经照到了他的床头。他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就夹着公文包,趟着齐踝深的积水,去县里上班。田里的秧苗浸没在水中,池塘的水都漫到岸上来了。几个打着赤膊的年轻人,手里提着渔网,正在秧田里捉鱼。当他经过西津渡桥的时候,看见整座桥面都淹没在浑浊的洪水中,只露出了一截桥栏的铁桩。街道上也都积满了雨水。被大风吹折的树木横卧在街道上,一群人推着一辆熄了火的汽车,向前缓缓蠕动。供销社的柜台也泡在水里,两名女售货员高挽着裤腿,正用瓷碗往外舀水。看着她们的小腿在阳光下白得发青,谭功达心里不禁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他走到县委大院的门口,已经九点多了,他看见门卫老常手里拿着一根通煤炉的铁条,正在疏通堵塞的阴沟。
“天漏了!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他笑着对谭功达说:“谭县长,怎么您没下乡去啊?”
谭功达没心思跟他搭讪,只是啊啊了两声,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拎着凉鞋,歪歪扭扭地踩着院中一溜红砖,像跳舞似的上楼去了。办公楼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看不到一个人。就连平常在楼道里打扫卫生的两个清洁女工也不见了踪影。他顺着楼梯走到三楼,见办公室的门锁着,就意识到姚秘书没来上班。假如她临时外出,门通常是虚掩着的。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很快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张姚佩佩留给他的便条:
我在县
医院。
她去县医院干什么?莫非是她生了什么病?谭功达疑虑重重地走到电话机前,给白庭禹、钱大钧、杨福妹逐一打了电话。和他心中不详的预感一样,电话没人接听。糟了!谭功达快步冲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对正在楼下捅阴沟的老常叫道:“老常,你上来一趟。”
不一会儿,他看见老常手里仍抓着那根铁条,两只手上沾满了污泥,出现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人呢?人都到哪儿去了?”他问到。
“人,什么人?”老常茫然不解地反问他。
“这办公楼里怎么一个人都看不见?”
老常吃惊地望着他,眉毛都拧到一块了,半天才说:“不是下乡抢险去了吗?”
“抢险?抢什么险?”糟糕!谭功达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普济的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垮了。那个江水倒灌,这个冲走了两个村子,那个那个省里地委都派人来了。谭县长,你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吗?”
“你是说普济大坝决了堤?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不,前天。”老常道。
“死人没有?”
“怎么没死人?昨天小王从乡下回来说,就他运回来的重伤号,死在县医院的,就有两个。”
“出了这么大的事,他们怎么不打电话通知我呢?”
老常的目光变得躲躲闪闪的,“县长,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你有烟吗?”谭功达忽然对他道。
“谭县长,你知道,这个,我是不抽烟的。”
谭功达又问他被洪水冲走的是哪两个村庄。老常说,这个他不太清楚。
谭功达问他省地领导都是谁来了,老常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不太清楚。要是没什么事,我先下去了。”
谭功达赶到梅城县医院的时候,已快到中午了。门外的空地上乱七八糟地停着四五辆驴车和平板车,地上的积水尚未完全退尽,让人一踩,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大夫正忙着把一个裹着纱布的伤号从平板车上抬下来。大门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他发疯地扯着自己胸前的衣服,号啕大哭。他的几个亲属表情木然地看着他,也不去劝。一旁的墙根下,摆着一个蒲包,上面躺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尸体,脸都已经发了黑。
医院的走廊里也是满地泥水。为了防止打滑,地上铺了干稻草,有一个护士手里端着一只簸箕,正朝地上撒炉渣,走廊两侧的木椅上横七竖八地挤满了伤号和家属。谭功达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护士手里举着一只盐水瓶,推着一辆担架车,已经到了近前。
“让开。”那护士头也不抬,向他命令道。
谭功达问她,院长室在哪儿,那护士突然两眼一瞪,怒道:“我叫你让开!”
谭功达一侧身,那辆担架车就贴着他的肚子过去了,把他的中山装纽扣崩飞了一颗。
谭功达一点都不生她气。这个护士的眼睛又深又亮,像秋天芦苇覆盖的深潭。只是不知她摘了口罩是个啥样子?在这紧急的关头,他的心里居然还有如此肮脏的欲念!王八蛋,王八蛋,你是个王八蛋!不过,他很快找到了院长室,一个大夫在门边的池子里洗手,谭功达站在门口,等他洗完了手,这才问他:“你们领导在不在?”
“我就是领导。”那人把口罩往下一拉,露出一张长满胡子的三角脸来,“你有什么事?”
“我要找你们院长。”谭功达记得他们院长姓彭,去年春天,他因肾炎在这住院的时候,是院长亲自主刀替他做的手术。
“院长带着医疗队下去了,我是这儿的副院长。”白大褂双手插在口袋里,“您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找几个人,我们来开个短会?我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
“开会?您是说开会?您有什么资格召集我们开会?”那人上上下下地把谭功达打量了半天,摇摇头,冷笑道:“哼!开会?神经病!我那边还有个大手术,你一边呆着去。”
说着,用那只带着塑胶手套的手把他一推,谭功达冷不防差点被他推了一跟头。那大夫径自朝手术室走去,一边走一边回头道:“你以为你是谁呀?有病。”
谭功达受了这一阵窝囊气,怔在那儿。县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作风是该好好整治整治了。等到这件事过去之后,要在常委会上专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好讨论讨论!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到医院来开个现场会,这个同志要做深刻检查。他沿着走廊,一直走到住院部的小楼前,脑子里晕乎乎的,突然听见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多种经营办公室的小汤。
她正蹲在地上,用一把汤匙,往一个满脸裹着纱布的病人嘴里喂水呢。这是他在这里遇见的第一个熟人,就像看到亲人似的,略微有些激动。谭功达挨着她蹲了下来,问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汤碧云笑了笑道:“别提了,简直是一锅粥!我已经两天两夜没好好睡过觉了。”
谭功达又问她知不知道这次大坝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汤碧云抬起胳膊,擦了擦鼻尖上的汗,说:“还好。”谭功达又问她“还好”是什么意思,汤碧云说:“送到县
医院来的病人,只死了三个,一个老人,两个孩子,还有一个人刚送来,听说正在手术室急救,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谭功达问起大坝那边的情况如何,汤碧云忽然抬头看了他一眼,咯咯地笑了起来:“您是县长,怎么这些事情倒反过来要来问我?你是刚从月亮上下来的吗?”
不过,她还是絮絮叨叨地说:“普济是个高地,没什么损失。兴隆,常旺两乡受灾比较严重。听那边回来的人说,目前已经找到了六七具尸体,失踪人员还没有统计清楚。送到这里来的,都是重伤员,轻伤都就地安排在普济、夏庄的卫生院里。地委的医疗队今天早上已经赶到了。天气太热,昨晚这里的大夫们议论说,弄不好会有大的传染病发生,要是那样的话,事情就糟糕了……”
这该死的沼气!谭功达不禁红了脸:“听说,听说姚秘书也在这儿,怎么没见她?”
“她呀,您快别提了!”一提起姚佩佩,汤碧云就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俗话说,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她昨天晚上才从家里赶过来,浑身上下淋了个落汤鸡,我们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去央求护士找衣服给她换。七手八脚总算把她伺候停当了,就让她帮着去抬伤员,没想到这个人丢人现眼,一见到那人嘴里吐出血来,就把担架一扔,自己先晕了过去。把那伤员重重地摔在地上,嗷嗷地乱叫。大夫们还得先腾出手来救她,您说她这不是添乱吗?”
谭功达也笑了起来:“她人呢?”
“在住院部的104房间,躺在那儿吊盐水呢。我刚才还去看过她,早没事了。”
谭功达来到住院部,104病房的门开着。里边躺着几个待产的孕妇,家属们坐在床上聊天。谭功达伸着脖子朝里边张望了半天,才在北窗的墙边找到了姚佩佩。她正躺在床上照镜子呢。一看到谭功达,姚佩佩的脸上就露出吃惊的神色,随后她就笑了起来:
“怎么搞的?你怎么把自己弄得像个叫花子似的?”
她这一说,早已引得同病室的那些孕妇都把目光投向他。谭功达手里拎着一双凉鞋,打着赤脚,裤腿卷过了膝盖,大热天还穿着中山装,敞着怀。
“你怎么样?头还晕吗?”他在姚佩佩床头的一张小圆凳上坐了下来。
姚佩佩没有吱声,她紧蹙着眉头,嘴唇有些发干,过了半天,才叹了一口气,侧过身来看着他,轻声道:“我倒还好,你呢?你可怎么办呀?”
他知道姚佩佩话里的复杂意思,心头一热,喉咙就有点堵得难受。姚佩佩问他有没有吃午饭,谭功达摇了摇头。她指了指床头柜上的一个饭盒,说她姑妈刚给她送了点桂圆粥来,问他要不要吃。谭功达说,他没有一点胃口,只是想在这里静一静,一会儿就要走的。
姚佩佩说,大约是在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第一个接到高麻子打来的报警电话。她发了疯似的到处找他,可整幢楼都找遍了,就是不见他人影,她不断地给他家打电话,一直打到天黑,也没人接,这个时候,她才无奈地想起来,应该向白庭禹汇报。白庭禹一听大坝决了堤,当即就兴奋得不行。白庭禹让她通知所有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下班的一个不许下班;已经回家的也要在20分钟之内召回,全体人员赶到四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姚佩佩大着胆子没去开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守着那台电话机:
“我想着,万一你要是听到一点风声,说不定就会打电话来的。”姚佩佩道:“这两天,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去了外地?出了这么大的事,你都不在现场,接下去怎么办?”
“我哪儿也没去,”谭功达叹了口气道:“这些天我没在家住,一直在郊外的红旗养猪场。”
“你到养猪场去干什么?”
“都是那该死的沼气!”谭功达道:“星期三刚上班,沼气攻关小组的阿龙来找我,说他们试验了一年的沼气池已经可以产气点火了。问我要不要去现场看看。我们刚刚赶到那里,就下起雨来。”
“沼气成功了吗?”
“点了几次火,都没成功。后来阿龙说,雨下得太大,也许密封池进了水。在大雨的间歇,他带我去了二号池边看了看,阿龙还朝池子里丢了一根火柴,谁知道“嘭”的一声,差点没把池子炸塌,还溅了我们一脸猪粪。”
“怪不得你身上一股臭味!”
“当天晚上,阿龙就让我在他们那儿打个地铺,住一宿,等第二天雨停了,再试一次,谁知这雨越下越大,没完没了。”
“那你眼下打算怎么办?”佩佩问他。
“我这就到普济水库那边跑一趟。”
姚佩佩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钱匣子来,把里面的钱和粮票都翻出来,递给他:
“你这会儿去那边,不就成了峨眉山上的猴子了么?”
“猴子?什么猴子?”
姚佩佩冷笑了一声,接着又说:“峨眉山上的猴子下来了,要去抢夺胜利果实……人家总指挥、副总指挥正忙得不亦乐乎,你这时跑去插一脚,哪里能讨到个好脸色?只是自取其辱。要我说,干脆你哪儿也别去。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个觉是正经。这么一闹腾,别的事我不知道,好歹,你这个县长恐怕是做不成了。”
她见谭功达木呆呆地坐在那儿发愣,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再说,你怎么去呢?小王又不在。”
“我在马路边随便拦个什么车就行了。”
谭功达来到
医院外,瞅见一辆运伤员的驴车,停在马路对面。一个黝黑的中年汉子头戴一顶破草帽,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正在给毛驴喂桑叶。谭功达朝他走过去,问他能不能捎他去普济。
“不行不行!”赶车的说:“给我多少钱都不行!一天跑两趟县城,我的这头驴都累得快吐血了,不要说你,呆会我自己回去,都舍不得坐。”
谭功达没再说什么。等到毛驴吃完了桑叶,那汉子晃了晃手里的柳条,赶着毛驴,一路摇摇晃晃地走了。在烈日炎炎的煤渣公路上,谭功达差不多站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拦下一辆车来。有一辆装煤的车倒是停了,可司机嘴里叼着卷烟,跳下车来就是一顿臭骂,连推带搡,差一点没把谭功达撵到路边的排水沟里。
谭功达气得双手在裤腰带上乱摸了一气。他是在摸枪。这是他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每当他遇到难以忍受的耻辱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去腰上摸枪。
他听着淙淙流淌的渠水,脑子里悲哀地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属于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远方钢蓝色的群山,看了看那条蜿蜒起伏的煤渣公路,四周的旷野一片岑寂。
他把手里拎着的那双塑料凉鞋穿在脚上,返身朝县城的方向走。可他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个世界在顷刻之间似乎突然变得与自己无关了,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黄昏的时候,他终于来到了梅城汽车站的售票窗口。里面有两个女售票员,正盘腿坐在床上打扑克牌。谭功达把脑袋伸进去,问她们有没有去普济的班车,那个年轻的姑娘立刻瞪了他一眼,道:
“最后一班车半个小时前已经走了。”
说完,她从床上跳下来,“啪”的一声就把那扇小门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