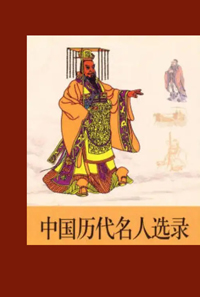5
这天傍晚,白小娴端着塑料盆,从浴一室出来,一边梳着头,一边回宿舍。刚走到琴房边,忽见团长满头大汗地朝她跑来了。
“找了你半天,原来去洗澡了。”团长喘着气,对她说。
“你有什么事?”白小娴冷冷地道,仍旧梳着头,不仅没有停下来,反而走得更快了。
小娴还在为去年他无故开除舞蹈教师的事生气。团长只得跟着她往前走,侧着身子,对她笑道:“白书记刚刚来过一个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哪个白书记?”
“就是你叔叔。”矮胖、敦实的团长一路追着她,“让你马上去他家一趟。”
舞蹈教师王大进刚从鹤壁调来梅城工作,还没待满一个星期,谭功达一个电话,他就给不明不白地开除了。他是连夜离开梅城的,走前没有跟白小娴告别。第二天,白小娴四处找不到王大进,就去问团长要人。团长当然不能说是谭功达的授意,只得支支吾吾地拿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来搪塞她。他的闪烁其辞加重了白小娴的疑虑。凭着直觉,她认为这其中一定藏有某种不可告人的一荒薄N瞬槊魇虑榈恼嫦啵碧煜挛纾仔℃稻筒淮嵌穑簧硪蝗俗狭饲巴妆诘某ね酒怠
她把鹤壁所有的机关单位都找了个遍,最后还真的在地区舞蹈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了王大进。当时,王大进正在宿舍楼的过道里生煤球炉子。他那黄脸婆的妻子,还有四个小孩,全都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筒子楼里。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其中的一张还缺了一条腿,直接搁在一堆码放整齐的蜂窝煤上。
当着老婆的面,王大进一脸尴尬。他一个劲儿地朝白小娴挤眼睛,丢眼色,假模假式地问她是哪里人,来找谁,白小娴死死地咬住嘴唇,脸色煞白。她不是不想回答他,而是根本忘了说话。可王大进的老婆有着一双天生的火眼金睛,已经看出了其中的名堂。她在屋里摔锅摔碗,为接下来歇斯底里的疯狂发作做铺垫。王大进赶忙丢下生了一半的火炉,回去想稳住她。白小娴就听见那女人尖一叫道:
“你和这婊子要是没什么勾当,人家怎么会好端端地把你开除?你他娘的狗改不了吃屎,走到哪里都惹一身腥!”
屋里的几个小孩一起放声大哭。煤炉里的浓烟不断地冒出来,在楼道里起了一层黄雾。白小娴看见邻居的门开了,一个大胖子穿着一件汗背心,拿着一手扑克牌,咳嗽着把脑袋伸出来叫道:“王大进,你狗日的赶紧把炉子弄一弄,我们都给你呛死了!”
白小娴从鹤壁回来之后,人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成天懵懵懂懂。跟人说话眼珠子都不爱转一下,看到什么就怔怔的发呆。嘴里喃喃自语,可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团长也慌了手脚,一连三次请他吃饭,白小娴都未予理会。
白小娴骑着自行车,往叔叔家赶。天已经黑下来了。虽说前天已是高秋,可是天气依旧闷热。街上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游手好闲的男人们摇着扇子、打着赤膊,坐在小板凳上,高声地说话。有的人家甚至把床都支在外面。白小娴想起很久没有去过叔叔家了,就在一个小摊前买了一些水果。
白庭禹家的门开着,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门前的一排铸铁围栏。他听见屋里隐隐有人在说话,可进了屋,只见到婶子一个人。她刚刚洗完澡,正抬着胳膊往胳肢窝里抹花露水呢。婶婶说,她知道小娴要来,已经给她盛了一碗绿豆汤,在窗台上搁着呢,还没凉透。随后,又就将桌上一片早切好的西瓜递给她:
“先吃瓜吧。”
小娴咬了一大口西瓜,嘟嘟囔囔的道:“我叔呢?他这么急喊我来也不知有什么事?”她一说话,红红的西瓜水就从嘴角流了出来,只得用手接着。
“在屋里和人谈事呢。”婶子努了努嘴,笑道:“咱们先说会儿话”。
白小娴见叔叔书房的门关着,里边的说话声忽高忽低,可什么也听不清。婶婶问了问她在文工团的情况,又问了问家里的事,随后就从桌上抓过一把乱绒线来让小娴给绷着。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把香烟盒一揉一成一个小球,绕起线团来。她在绕绒线的时候,膀子上的肉就跟着松松垮垮乱颤起来。小娴不由得想起,叔叔第一次带婶子从东北回家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婶子头上还扎着羊角辫子,可现在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已经老成这个样子!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变成这个样子,心里就有些黯然神伤……
不多一会工夫,叔叔的房门打开了。风一吹,屋子里的烟雾就一团一团的涌了出来。等到烟雾散尽了之后,她看见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大高个儿,穿着短袖衬衫,头发梳得油光,发型看上去有点像毛主席。手里托着一只大烟斗。
他一出门,就拿眼睛朝小娴身上看,随后笑道:“你就是白小娴同志吧?”随后向她伸出手来。可小娴的手里正绷着绒线呢,那人只得把手半路缩了回去,抓了抓头皮。小娴朝他笑了笑,心里道:这么热的天,这人头上竟然还抹着油,难道他就不怕痒吗?
白庭禹紧接着也跟了出来,指着那人向小娴介绍说:“这是钱县长!”
那人托着烟斗,莞尔一笑:“钱大钧,钱大钧。”他回过头去对白庭禹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
白庭禹道:“我怎么记得你是见过她的?”
“嗨!那是在舞台上,又化了妆……”那个名叫钱大钧的人在叔叔耳边嘀咕了句什么,白庭禹忽然哈哈大笑。小娴猜到他们大概是在议论自己,微微红了脸。钱大钧又嫂子长嫂子短的跟婶婶搭讪了几句话,这才告辞离去。白庭禹也不远送,只是冲他摆了摆手。
他转过身来看了白小娴一眼,就问了问她最近在团里的情况,又问到家里的事。奇怪的是,他的客套竟然和婶子一字不差,就好像预先商量过似的。半天,才对小娴道:“小娴,你到我屋里来一下。”
白小娴进了屋,刚坐下不一会儿,就见嫂子手里拿着一只
苹果走了进来,她一边削着苹果皮,一边对丈夫说:“你们说你们的,别管我。”
“小娴哪,今年已经满二十了吧。”白庭禹靠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双手按压着两边的太阳穴一。
“什么呀!二十四了。”小娴笑道。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啊,要正确认识事物的本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得来它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改造功夫。稍一不慎哪,就会落入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况且,啊,事物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由量变到质变,在一定条件下产生飞跃。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呢,啊,也可以变成好事,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来都……”
“老白呀,你有什么话就跟孩子直说吧,这么绕来绕去的,把我都给绕糊涂了。”婶婶笑着打断了他的话,把削好的苹果递给白小娴。白小娴刚吃了两片西瓜,肚子里撑得慌,就将苹果放在茶几上的果盘里。
“比方说,啊,”白庭禹道,“我们当初劝你和谭功达谈恋爱,啊,就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事实表明,这个谭功达伪装得很巧妙!隐藏得很深!啊,骗过了广大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在梅城,他是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头号阶级敌人!别的且不论,他四十多岁了,还不成家,为什么?啊,就是为了以谈恋爱为名,不断玩弄我们无知女青年的感情,你和他交往多年,对于这一点应该最有发言权了。”
白小娴听叔叔说到“党内头号阶级敌人”这几个字,本能地吃了一惊。后又听叔叔说玩弄感情那一番话,心里就想,自己大概也被他列入了无知女青年行列,心里就有些不开心。
她对白庭禹道:“谭县长出了什么事?”
“他已经不是什么县长了。”白庭禹脸上的笑容突然收敛,变得严肃起来:“他是个大叛徒!大流氓!大野心家!我们找你来,啊,就是为了重新核实前年春天发生的那件事。”
“什么事?”白小娴警觉地看着她的叔叔,似乎已经模模糊糊的意识到叔叔叫她来的用意。
“傻闺女!就是为了谭功达强奸你的那件事呀!”婶婶笑着对她说,“那天晚上,都快半夜了,你一个人满脸是血,跑到我家来敲门,雪还在下着……你想起来没有?”
白小娴点点头,急忙道:“那天晚上他是抱了我一下。我以为他要强奸我,可你们劝了我一个晚上,说那不叫强奸。”
“那就是强奸!”白庭禹斩钉截铁的说,“那不叫强奸,还有什么事可以算强奸呢?”
白小娴的脸一下就红到耳根,申辩道:“您亲口说的,那不叫强奸,那叫操之过急。您还说男一女之间搂搂一抱抱是感情必要的润一滑剂,是革命同志之间一种十分常见的革命行为,为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所必需的前奏曲,您还说,即便是在马克思和他夫人燕妮之间也免不了会发生这样的事,您又说……”
“好了好了,”白庭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了,然后冷笑道:“小娴哪,你的记忆力还是很不错的嘛!的确,我承认说过这些话。可我当时并不了解太多的情况,事情被弄颠倒了,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可我们共一产一党人认识到错误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改正错误。我们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把颠倒了的事情重新颠倒过来。”
“不管您怎么说,反正我不认为那是强奸”,白小娴交叉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嘴里嘟囔道:“他这个人,只是性子有点急。”
“什么叫强奸?强奸就是以性交为目的,违背妇女意志而采取的暴力行动。请问,他当时有没有违背你的意志?再请问,他有没有采取暴力行动?你的嘴都被他咬破了,”白庭禹气得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可你,还要为他辩护!”
婶子一看两人谈僵了,就赶紧插话说,“小娴,他玩弄你纯洁的感情,最后一脚踢开了你,你难道就不恨他吗?”
“恨他?我为什么要恨他?”白小娴赌气似的说,“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
“你这孩子,好不知轻重!明明是他欺骗了你,怎么还要感激他呢?”婶子问。
“要不是谭县长当机立断,将那个狗屁王大进从文工团里开除,我早就落到了那个流氓手里了……”
“谁是王大进?”白庭禹转过身来,不解的望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