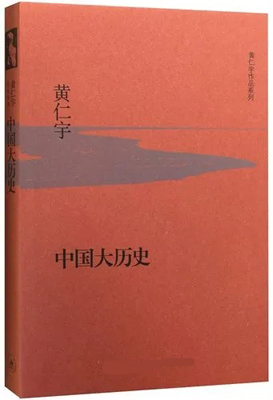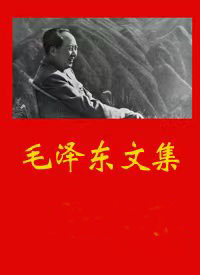木兰与八岁大的妹妹,还有珊瑚姐,在轿车里蓝色硬棉垫子上盘腿坐着,生平头一次尝到北京轿车的颠簸的滋味,也同时分明感觉到在这个茫茫世界上正在冒险赶路。
不久,木兰、莫愁、珊瑚姐开始与车夫攀谈起来。车夫为人和气,告诉她们义和团的情形,义和团的所作所为,还有哪些事是义和团不做的事,他跟义和团怎样闲谈,谈些什么,以及天津的战争,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大阿哥,以及这段路前面会有什么状况等。
由北京北城进入南城,她们看见好多烧毁的房子残留的废墟瓦砾。这时顺着城墙往西,在那荒凉废弃的地区,看见一群人站在一块空地上,中间是义和团的一个神坛,盖着红布,锡镴蜡扦儿上面有红蜡烛。几个中国人跪在坛前接受审问,因为有二毛子的嫌疑。
车夫指出几个义和团的少女与妇人给她们看,这些人都穿着红小褂儿、红裤子,红裤腿下面露出缠裹的小脚儿,头发梳成宽辫子,盘在头顶上。男的义和团员也是穿红褂子,有的胸膛上只是红前襟,女团员腰上围着宽带子,显得勇武精神。车夫告诉她们这些女义和团员叫作“红灯照”和“黑灯照”。白天她们拿一把红扇子,扇子股儿也油成红的,夜里就打着红灯笼。“红灯照”都是少女,“黑灯照”则是寡妇。不裹小脚儿的是招募来的船娘。她们的首领,称作“圣母”,原来也是运粮河上的一个船娘,但曾坐着黄绫轿由巡抚请进巡抚衙门。那些少女有些会打拳,但大部分不会。她们有法术。她们必须要学念咒语。一段短期练习之后,她们若是要上天的话,一摇动红扇子就可以飞上天去。她们至少总会爬墙,因为车夫曾经看见她们站在人家屋顶上。
车夫看见过他们作法没有?
不错,他看见好多次了。他们先设神坛,点上蜡烛,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忽而神态有异,口中说的是法术语言。这时就是神仙附体了,两眼发直,瞪得又圆又大。接着挥舞大刀,往自己肚皮上猛砍,但是皮肉不受伤。
来附体的神仙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这些小说神话,如今木兰听来,竟变成了眼前的真实故事。
天还没黑,他们早已过了西便门,出了城,来到荒郊野外。
旅途的前三天还算是轻松容易的,没发生什么事,只是天太热,车又颠簸得厉害。人人都抱怨腿疼。每天赶早出发,早饭前就赶出十里地,有时二十里地,清早与午后下半天赶的路最多,中午,人和骡子都要长久地歇息一段。体仁和冯舅爷常下去跟着车走一里地,因为腿弯曲得太难过。第四天过了之后,身子对车的颠簸似乎已经习惯。
体仁最不安静,换了好几次车;有时要跟母亲坐,有时要跟丫鬟坐。母亲宠着他,也就任凭他,不加管束。银屏比他大三岁,每逢他跟银屏在一块儿,他就很快乐;他喜欢瞎扯,跟锦儿开玩笑。锦儿受不了的时候,就到姚太太车上去,帮着照顾小孩子。
在第四天,也就是离开了涿州两天,在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正往东南走,一切事情似乎都不顺。谣言满天飞,说八国联军已经进了北京城,乱军和拳徒正往南撤退。另一个谣言说总督裕和将军已经自尽,甘军正往南撤退。
在拳徒与军队之间时有战斗发生,因为拳徒只有刀枪交战,吃亏不小。一听见枪炮声,拳徒就四散奔逃。拳徒究竟是什么性质,老百姓和政府军队也弄不清楚。在军队之中,一半人说应当剿灭拳徒,一半说不。拳徒因为烧教堂,杀万人痛恨的洋人,所以深得民心。朝廷在春天曾下令收编拳徒;现在又让军队剿灭拳徒;新近朝廷似乎又宠信他们,并采取他们的排外政策。
兵和拳徒往下溃散的渐多,抢劫也就日渐增多。路上逃难的百姓人潮汹涌,步行的,坐轿车的,坐手推车的,骑驴的,骑马的,样样儿都有。农夫有的挑着两个筐,一头放几个小猪儿,一头放着个婴儿。姚家的车远在这些散兵游勇之前,所以一路上还算平安无事。女人们开始安心,体仁也慢慢安顿下来。姚大爷吩咐尽量赶路前进,能少歇息就少歇息,指望在乱兵赶上之前能到德州。他已经把端王爷发的护照撕碎,因为它根本像废纸一样,毫无用处;并且,遇见拳徒或是官兵,反倒会引起麻烦。
那天下午日落之前,他们到了任丘,因为中午打尖只歇息了一小会儿。住了店之后,姚大爷问店家城里可有官兵。听说天津镶黄旗第六营的徐管带(营长)正驻扎在此维持治安,才放了心。此地的天主教堂一个月前才遭烧毁,不过徐管带(营长)进城之后,逮住了几十个“大师兄”砍了头,余众逃往乡下去了。
一个旅客带着家眷,两个妇人,三个孩子,也是逃难而来,比他们到得晚一点儿,带来了使人心神不安的消息。那天早晨他离开保定府,一直往南向任丘逃,因为听说徐管带(营长)能在任丘保境安民的缘故。
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富有的官宦之家正往保定府走。这家一个女人戴着一只金镯子。一队散兵游勇渐渐行近,看见那只金镯子就要,那个女人给得不痛快,拖延了一会儿,一个兵就把她的胳膊砍了下来,拿下镯子逃跑了。另有一股官兵来了,听说这件事,好像看见那只镯子在前面几个兵的手里,追上去把那几个兵枪杀了。前面那几个兵当中逃走了几个,藏身在路旁高粱地里。在抢他们的那几个兵经过之时,又把他们开枪打倒。
一只金镯子就要了七八条人命。
那几个同路人低声说路上发生的这件事,姚大爷一个人听了默不作声。他叫家里人吃晚饭之后立刻睡觉,孩子丫鬟一概不可出屋去。他们只有一个屋子,要睡十二个人,因为全家不肯分店去住。那一家来了之后,弄得情形更糟。那间屋子只有一个炕,才十五尺宽,所以丫鬟必须睡在地上。别人在有急需之时,姚大爷并不是死咬定自己的权利不肯放松的。所以他答应后来的那家的两个女人睡在他家的小房间里,而他、冯舅爷、罗东,跟那一批旅客之中的男人,则都睡在外间,外间是厨房客厅餐厅一屋三用的。
在里间,孩子们安然入睡,罗东也鼾声大作,而姚大爷则不感觉困倦,也不想睡。他心中估量明天若起个大早儿出发,日头西落以前会赶到河间府的。
暂时,一切总算平静。炉台子上一盏小油灯,灯火荧荧,美丽而安稳。他拿出烟袋,心中沉思。这是好久以来他难得享受的宁静的夜晚了。后来他回想到这天晚上,觉得真是像幸福的天堂一样,自己的亲人在另一间屋子里安睡,而自己抽着一袋烟,一盏油灯在炉台子上燃烧着晃动。
时将半夜,觉得听见太太在睡梦中惊呼一声,然后屋里有骚动声。他在炉台子上端起油灯,往那边门里一望。姚太太身旁是小孩子,她已经坐起来,正轻拍木兰的脸,捋顺她的头发。
姚太太问:“这么大深夜你干什么呢?还没睡呀?”
丈夫说:“我觉得听见你在梦里喊叫了一声。”
“是吗?吓了我一大跳。我梦见木兰在老远的一个山谷里叫我。我一打哆嗦,就惊醒了。还好,幸而只是个梦。”于是看了看木兰,又向身边儿看了看别的孩子。
姚大爷说:“只是个梦就好了。睡吧。”
于是走出屋去。
不多一会儿,来了一阵暴雨,雨声淅沥,使姚大爷感到困倦,不知不觉睡着了。
七月二十五早晨,姚大爷被屋子里的声音吵醒,看见大部分人都已起身,已经洗过脸。车夫正在门前,说雨后天气凉爽。天上有云彩,看样子要整天阴天。到河间府只有六十里地,走起来是不难的。因为骡子若不拉太重,一天走一百里很容易。若走长途,拉着车,可以走六十里,顶多走七十里。有一头骡子踩到沟里,差一点儿跪下翻了车,一条前腿似乎扭了一下。所以今天车自然要走慢一点儿。
大概八点钟光景才出发。姚太太叫青霞到她的车上,好抱着孩子。木兰的轿车上的骡子有点儿一拐一拐的。
走了约莫十五里地之后,那头骡子越发显得焦躁不安,常常停下来,直喘气,肚子两侧时时鼓胀收缩。骡子的身子像马,头脑像驴,力量之大像马,脾气之倔犟也像驴。车夫说那骡子出了毛病,若不慢走,恐怕要没命。他说:
“骡子比君子。一生病,就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这头骡子早晨只用鼻子闻了闻草料,嚼了一点儿。空着肚子怎么赶路?还不是跟人一样?”
走了三个钟头才走了二十里地,到了新中驿。大概一点半,大家才下车,饿了,去打尖。新中驿是个老驿站,给官家传递公文,人马是在这里换班儿的。官方紧急的公文,从河间府到京城一百里地,十二小时是可以送到的。附近有个马房,有三四匹马拴在旁边的树上。
因为他们打算在河间府换几头骡子,再走其余的那段路程,现在这个骡子的车夫决定从那几匹马之中找一匹代用,至少先帮着赶完这一天的路程。他认得驿站上的人,事情当然好商量。
午饭之后,大家在凉亭之下歇息,木兰、莫愁、体仁三个人闲荡到树林之下去看马。体仁走得离一匹马太近了,那马开始乱踢,吓得木兰拉着莫愁边跑边叫。这些驿马都是身强力大的,姚大爷向那边儿急叫体仁回去。
姚大爷脾气急躁。姚太太又已经告诉过他昨天晚上的梦。在梦里只记得她在山谷里走,一条宽大的溪水在山谷中间流,另一边儿是一带树林子。她那时拉着莫愁的手。她觉得听见木兰叫她。她忽然想到木兰并没在她身边儿,似乎好几天没见到她了。最初,木兰的声音似乎来自树顶上;在她转身进入阴森森的树林时,发现好多小径都阻塞不通,正不知如何是好,又听见木兰喊叫,声音清楚可闻,但是软弱无力,似乎是从溪流对面传来。声音是:“我在这儿哪!我在这儿哪!”母亲一转身,看见孩子的身影儿,正在溪水对面的草地上摘花儿。她既看不见船,又看不见桥,心中不由得纳闷儿,孩子是怎么样过去的呢?她把莫愁留在岸上,自己在清浅的激流中涉水过去。忽然一股洪流冒起,使她脚下悬了空。一惊醒来,原来正躺在旅店里的炕上。
这个梦让人听了,都心里忐忑不安,但是她说完之后,谁也没有说什么。
那头瘸腿的骡子就暂时留在驿站上,车夫回来时再带回去。大概三点钟的时候,他们又起程出发,新借来的那匹马拉珊瑚跟木兰姊妹俩坐的那辆车。那匹马老是冲到前头去,车夫不知道它的脾气习惯,很不容易控制它。
将近五点,离河间城只有十二三里地了。他们看见在左方远处,有军队横越田野而来。姚大爷说他要到前面车上坐坐,但那走了多年的古道比平地低三四尺,到宽广的平地以前,根本没法子错车,而且在他们前后百码之遥的地方也有别的难民。
忽然听到一声枪响。附近的田地都是由一丈来高的高粱形成的青纱帐。这时他们正在低洼的地方,看不见兵究竟在何处,只是听见说话声越来越近。又听见几声枪响。他们既不能转车倒退,又不知道往何处走,这时听见似乎兵是自前后两路而至。他们到了平地,有七八个逃兵在十字路口儿跑过去,还看见有成队的兵离他们左边五十码远。所有的车都停住了,姚夫人向珊瑚喊,教把她们姐妹俩送到她的车上。
珊瑚裹着小脚儿,从马车上下来,不是件容易事,不过她照吩咐办了。她下到地上,向莫愁伸出胳膊,把她抱下来。她把莫愁抱到姚太太车上,打算回来再抱木兰。这一停就阻断了十字路口车辆的交通,挡住了后面的难民,后面的车夫又骂又喊,吵作一团。
这时,又听见枪声,有几个兵骑着马,在他们正前面疾驰而过。驿马吃了一惊,开始向前飞跑,木兰的车就随着一群兵马疾驰而去。
在一阵混乱之中,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群兵似乎只是急于逃命,并不太存心想抢劫。姚家,受阻于前面来往越来越多的人马,后面又有车拥挤上来,真正是夹在了中间,这时骡马散乱奔驰。混杂嚣乱,尘土飞扬,简直伸手不见五指。珊瑚正匆匆忙忙爬到姚夫人的车上,几个骑马的官兵在她身旁飞驰而过。她刚一定神,一想木兰还犹自一个人儿在那辆车上。她尖声喊叫:“木兰!”木兰的母亲不假思索,立刻就要往车下跳。但是在眨眼之间,所有的车都动起来。她能看见的只是人、车、马蹄,在她前面乱作一团,她自己的车也随同着向前冲下去。骡马一旦放开腿跑,你再喊叫指挥它们,那就如同向火车头喧叫一样无效了。前面有十几辆车,她一心指望其中有一辆拉的是木兰。这时姚大爷几乎还不知道木兰是一个人儿在车上。因为官兵没停下来抢,他还满以为灾难已经过去了。
几辆车正向前奔驰之时,姚大爷一心想赶紧离开官兵,越快越远越好,然后再查看一下有什么损失没有,心里还以为全家正往一个方向走呢。木兰的母亲简直想要身分两处:一是到前面去认一下木兰的车跟那个车夫;一是慢下来察看一下后面的车辆。可是实际上,她却一筹莫展。路只能容单向行车。她几次想跳下车来,幸亏珊瑚拉住了她。
她着急过了七八分钟后,骡子渐渐慢了下来。举目四望,也看不见官兵的踪影了。离开了那个十字路口至少已经有二里地。一辆车栽到路旁的壕沟中,摔下来的那个妇人几乎被后来的车轧过去。另有一辆车驶来,一个客人认识那个人,就跳下车,但是那辆车却停在路当中。当然姚家的车也被挡住了。冯舅爷就各处跑去打听。姚太太简直急疯了。珊瑚跟青霞一直哭。姚太太指着那在前面还在走而且渐渐消失了踪影的几辆车,喊说木兰的车也许在当中,他们必须追上去,不能停在那儿不动。
她喊说:“木兰一个人儿在车上呢!”
父亲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当时也来不及问为什么木兰是一个人在车上。他抓住了一匹马,从车上解下来,纵身上去,飞驰过人群,追向前面的难民。但是只是一路空追,徒劳无功。
丫鬟这时都下车来问,听了这个消息,脸吓得惨白,说不出一句话来。珊瑚简直真从车里滚下来了。为什么在过去十五分钟内那辆车里只有三个女人两个孩子,谁也说不清楚。母亲把莫愁紧紧地抱在怀里,青霞抱着小孩子。莫愁最初怕得说不出话来,现在开始哭。别的难民挤过来看看又过去了。有人站住看由车上掉下来的女人。那个女人仿佛是因为她的骡子腿上中了子弹,要从翻了的车上解开套把它松开,可不是容易的事。也有人停下来,听说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与大人失散的事。有人显得伤心,有人无动于衷地走过去。体仁说他曾看见木兰车上那匹驿马随着官兵往右方跑去,不过看得不太清楚。若当真如此,木兰已然离开了他们走的那条路,大概是随着一群官兵跑去了。但是车上还有车夫呢?他会把车赶向河间府,也许会追上他们,在路上也许会碰见的。
大家正在心绪纷纷,不知如何是好,看见木兰的车夫手中拿着鞭子从后面跑来,一边跑一边喊。大家一看有车夫没有车,不由得脸色变了。
“孩子没出事吧?”
“谁知道?我们叫官兵一冲,驿马受了惊,怎么也勒不住它了……”
“她现在在哪儿?”
“她跑到哪儿去了?”
“你怎么把车丢了呢?”
车夫之茫无头绪,正跟问他话的人一样。他的车是被兵马冲到右方去,然后走上右边的一条路,离开了官兵;等他看见离开了人群,下车想把马拉住。马力气太大,他拉不住缰绳,马就向前跑去了。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那就是木兰还在车里。还有,那辆车并没往河间府去,因为车夫最后看见车转弯儿消失在青纱帐里时,车是向北方回去的。他相信那匹驿马还会自己认路奔回新中驿。他出于一片老实忠厚的心肠,才跑来告诉木兰的父母的。
大家无可奈何,等了几个钟头之后,姚大爷骑着马回来了。每辆车他都看过,绕着弯儿察看过,甚至直到跑近看见了河间府的城墙,才放弃了追寻。
姚大爷觉得车夫的想法蛮有道理,那匹马会寻路返回新中驿的。
太阳快落了。姚大爷要坐着他那辆车回到新中驿,车夫去找他的车和马,父亲去找自己的女儿。别的人只得继续奔向河间府,因为河间府的城门快关闭了。车夫告诉他们在河间府城内要住的那家旅店的名字,他们就在那家旅店等消息。
木兰的母亲整夜没睡,只是暗自流泪。黎明,她叫罗东跟她哥哥起床到北门去找木兰。
第二天早晨约莫九点钟,姚大爷回来了。马和车已经回去了,但是没有孩子。他曾经折回去,在十字路口儿一带去寻找,什么也没找到。
这个消息真像晴天劈雷。木兰是丢了,还有什么疑问?母亲号啕大哭:“木兰,我的孩子呀,你不应当这么离开我呀!你不应当去找你妹妹目莲呀!你现在若离开我,我这日子还有什么过头儿哇!我还要这条老命干什么?”
珊瑚劝道:“妈,一切都是天意,万事顺逆好坏,人不能预知。您不要太伤心,免得有伤身体。这条旅途往前还远呢。这些人的命都要靠着您呢。您若没灾没病的,我们孩子们的担子也就减轻了。木兰是不是丢了,也还不能太一定;我们还要接着往各处去找她。这都是我的不好。我千不该万不该把她一个人儿留在车上!”
姚太太勉强抑制住悲伤,回答说:“这不能赖你,是我命不好,才招出这个乱子。我不应该叫你去把她们俩抱过来。可是谁会知道发生这种意外呢?若是木兰出了什么差错儿,让人拐跑了,让人卖了的话……”说着又哭作一团儿。
姚大爷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木兰是他最心爱的孩子,若是真的丢了,他可伤透了心。他一听到“拐跑”这两个字,立刻走开,就像个受伤的兽一样。
锦儿,原本静悄悄地倚着墙站着,忽然大哭起来。她今年十四岁,差不多跟木兰一起长大的。她教给木兰一切游戏,唱摇篮曲,从小就跟木兰在一块儿玩,木兰待她就像亲姐姐一样。刚才一提到“拐跑”两个字,她立刻想到自己的命运,想到自己父母的杳无消息。她倒在床上,哭个没完。看见她哭,体仁跟莫愁也哭起来,于是屋里哭喊吵闹,乱到极点。青霞走近,把锦儿拉起来说:
“太太刚忍住哭,你又大号起来,招得少爷跟莫愁也哭,快别哭了。”
锦儿坐起来,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还用手揉哭得通红的眼睛。银屏向来不喜欢锦儿,看见就褒贬她说:“从今天早晨她就一直一个人坐着。莫愁也没梳头,也没洗脸,后来我帮她穿好衣裳的。她们俩那么好,当然她很难过了。”
锦儿走出屋去,好像受了委屈似的,一边走一边说:“我哭我的。我爱哭与你什么相干?我喜欢木兰小姐又不干你的事!”
银屏怒冲冲地说:“我们同是伺候太太、少爷、小姐的,谁也管不着谁。”
姚太太喊道:“你们造反了!”
珊瑚连忙跑到另一间屋子去。她说:“现在是闹事的时候吗?难道现在还不够吗?”
锦儿一边哭泣一边说:“我也不想要哭,我是想起木兰小姐来。太太一提到拐卖,我又想到我自个儿。哎呀!妈呀,你若活着,我也不致这么受人家欺负哇!”
珊瑚安慰锦儿说:“当然我们大家都难过,当然是会哭的,你也是情不由己呀。”
锦儿恶狠狠地说:“若是体仁少爷丢了,你看她哭不哭?”
银屏原来在外面听着呢,现在迈步进来。珊瑚转身把她推了出去,叫两个人谁也不许再开口。
现在父母陷于想象中的恐怖,想到像木兰那么年轻、那么漂亮的姑娘丢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种恐怖简直比死还可怕。心中的狐疑不定,心中驱之不去的恐惧,无法猜测她现在的情形,还有能在河间府城里或别的地方会找得到她,这难得实现的希望,这一切一切,使他们的头脑麻木瘫痪了。
那天早晨,姚太太不再说别的,只是说:“不管死活,我总要找到她。”她简直变成了呆子,心里只有一件事,对别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中午,摆上饭菜之后,她呆呆地走到桌子那儿。她吃东西,但是不知道自己是吃饭。还有,锦儿正在安静地吃饭,忽然把饭碗放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离开了桌子。
姚太太这种异乎寻常的沉静,真使珊瑚害怕。她说:“妈,您得多歇息歇息。您昨天晚上没有睡觉。现在各处去找也得找上好几天。咱们自己也得保重才是。”姚太太像机器一样,就由珊瑚引到床边儿去,半句话也没说。
河间府城有五千居民,这片地方坐落在一带低洼地的中央,周围有一条大河的支流向东北流向天津。东边三十里以外就是沧州,正在运粮河的岸上。往南四十里地就是德州,正在这块三角地带的顶尖儿上,往北几乎距离沧州河间一样远,往河间府要走旱路,往沧州走运粮河。
他们寻找木兰只得在客店、城门、通往城镇的路上贴寻人告白。告诉人家他们旅店的地址,悬赏寻人。赏钱是二百两银子。女人要停留在店里,父亲、冯舅爷、仆人罗东,以及赶车的,带着赏钱,要到全城及四乡去寻找。木兰的母亲则变得坚强有力,默默地满街满巷徘徊寻找,还往河里看,不分昼夜地寻找,寻找她的骨肉。
但是河间府挤满了难民和走失的孩子,并不止木兰一个走失的。有几次是来虚报消息的。木兰的母亲甚至于到西门外河边去看一个姑娘的死尸。
姚大爷骑着马到四乡去找,别的人往东走到沙河桥,往西走到肃宁县。
但是找不到木兰的踪影。
这个孩子也许已经落到贩卖童奴的贼匪手里。这种情形有八九成。木兰总会值一百两银子,虽然谁也不敢这么说。冯舅爷一天回来说,人贩子都在运粮河上跟那些船娘做生意。锦儿本来就是被人拐卖的,她说在河上贩卖人口是真的,并且说当年那船娘待她很好。那些年,运粮河是由北京到南方的交通要道。青帮霸占着运粮河,他们有一套完善的组织。在津浦铁路修建之后,运粮河失去了生意,青帮才加入了红帮,在长江上称为青帮,后来在上海法租界还统领着盗贼、鸦片烟贩子、妓院。他们是以拐卖、绑架、抢劫出名的,不过他们也慷慨行善。他们的首脑人物充当工部局的顾问,领导水灾旱灾赈济,每逢他们的生日,官方高级人员还亲身前往拜寿。这一组织是个自卫、互助、合作的秘密团体,对低级失业的大众保障其生活,大家公平分享,彼此之间十分慷慨大方,共同遵守荣誉义气的门规,这种组织实际上源于一千年前的秘密会社。稗官野史上的英雄就是他们崇拜的神,还有忠贞的战将,劫富济贫的侠盗,群众仰慕的好汉都是。
义和团本也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是白莲教的一支。明亡之后,他们是要推翻大清的。但是历史环境却使他们变成扶清灭洋的一股力量,引起了国际间的大事。
姚家既然深信木兰是被拐卖了,于是搜寻几天得不到结果之后,就决定往运粮河上去找。冯舅爷自请往东到沧州,只有一日的行程,顺着运粮河往下去,在市镇上、渡口上,都停下来寻找线索,大家则继续赶路,约好在德州等他。
只有两件事,似乎显得有一线希望。第三天,姚太太找来一个算命的瞎子,向他问丢了个孩子的事。她把木兰的生辰年月按天干地支说明。算命的说木兰的八字有福气,有双星照命,所以十岁时该有磨难,但因命好,自会逢凶化吉。并且,她运交得早,虽然不为高官显宦的夫人,一辈子也不愁吃不愁喝的。问他这个孩子是否可以找得回来,他则深不可测地说:“有贵人相助。”总之,因为木兰的八字太好,所以卦金他索要大洋一元,姚夫人则给了他两元。
这样,姚夫人心情好了许多,她到城隍庙去烧香。说也怪,两个杯筊,在神前扔了三次,都是大吉。
那天晚上,做母亲的做了一个梦,跟以前梦见的一样。她分明听见木兰叫:“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于是又看见女儿在溪流的对面草地上摘花儿,跟木兰在一起的是另外一个女孩子,她不认识,以前没见过。母亲叫木兰过来。木兰在那边儿喊:“您到我这儿来啊!我们的家在这儿。您在的那边儿不对呀。”母亲想找一个渡船,或是找个桥,但是没有。于是似乎觉得自己在水面上安然行走,往下,往下,再往下,顺流而下得好快,这时已经忘记了女儿。她经过了城镇、村庄、山顶的佛塔,正漂近一座桥时,看见一个老翁在桥上疲惫而行,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丈夫。她还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搀扶着丈夫,而那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木兰。她在河上向他们呼叫,但是他们好像没听见,还是照旧一直往前走。她两眼盯着她不放松,不料自己碰到桥柱子上,不能在水上漂了,往下一沉,就醒了。
第二天早晨,她把梦告诉了丈夫,两个人都大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