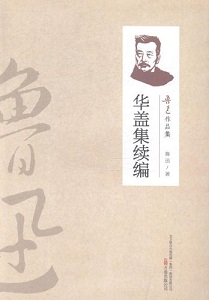莺莺遭人刺杀的消息,北平各报一律不许刊登。好多中国报这时都停刊了。一个傀儡报,叫作《新民报》,在六月份曾遭封闭,如今又复活出现。在天津意租界发行的天主教《益世报》,有人私运到北平,售价甚高,但是卖报的若被发现,即遭逮捕。傀儡报纸上只发表日本的同盟社的稿子,或东京来的电文,社论也是有关“亚洲新秩序”的文字。北平是与外界隔绝了。家里有钱的人才有无线电收音机,用户急切于收听到南京的消息。
警察对凶手的线索一无所得。但是怀瑜既惊怕又恼怒,眼睛死盯在姚家的王府花园。
第二天,一群警察到姚家花园,仔细打听居住的每个人,把人名字记了下来。家里的人是冯子安、冯太太、阿非、经亚、博雅,冯氏夫妇和宝芬的父母都是老人。幸亏立夫、环儿、陈三的名字早已不在。警察确定家中只有那几个人之后,看了看房子,没有骚扰,客客气气走了。
阿非已经听到莺莺的被刺,对陈三和环儿与此事有关,半疑半信,但是幸而他们已经走了。他也怀疑警察来搜查会与刺杀案有关系,也相信十之八九是由牛怀瑜派来的。后来他听说警察也到过黛云家,黛云的母亲说她女儿在天津,没有回来。
在这种情形之下,阿非认为他自己和花园这个家,是有危险了:第一是怀瑜又回到北平,第二是他在禁烟局任职期间已经树敌不少,而且会被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的官员。他邀请宝芬的美国朋友董娜秀小姐来住在花园里,立了个合同,把静宜园转卖给她,告诉她在门上插上美国旗。他知道董娜秀小姐为人正派,绝不会占便宜。而那个合同不过是个形式,若有什么麻烦时,警察也容易找理由应付交差。至少有一个白种人住在里面,日本兵、日本浪人,也有几分顾忌。
警察来调查时,册子上漏了曼娘和阿瑄。因为卢沟桥事变刚发生之后,曼娘怕日本人抢到城内,已经决定搬到乡下去住。她以为姚家的别墅靠近玉泉山,很不错,可是曼娘的媳妇坚持她娘家在京北,更为安全,因为离北平更远。曼娘的母亲孙老太太,已经在去年冬天去世,所以阿瑄便和曼娘、他太太、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搬到他老丈人家的村子去住。
那村子离火车站有三里远,他们是坐火车去的,那是在北平陷落之前三天,一路没有什么困难。阿瑄他太太娘家姓朱,那村子叫朱家庄,是一个集镇,坐落在山区,全村人都姓朱。曼娘全家一到,是村子里一件大事。曼娘和她儿媳妇穿的朴素衣裳,在乡下人看来,简直是奢侈华丽的上等衣裳。乡下女人都凑在一处,来看王府花园的小姐太太。
他们住的房子是阿瑄的老丈人的姐姐的。这栋房子是用土坯盖的,虽简陋,不过因为四周有围墙,很与别家不同,因此很显眼,前面是个空院子,院里是打麦场。墙的下一截是用山上的圆石头砌起来的。
乡下老太太把自己的屋子腾给侄女住,自己搬到后面屋里去,再三说招待他们太简慢。因为没有别的屋子给曼娘住,阿瑄说他可以睡在外面客厅里,让他母亲和他媳妇、孩子睡一个炕。
在北平城被围困的那些日子里,在乡间倒是蛮愉快。村子靠近山丘,平静无事。在傍晚天气凉爽下来,阿瑄和他那时髦的妻子、他的孩子,一同漫步,走到附近的一条小溪旁,走近火车道,看见满车的日本兵往北开往长城上的南口。乡村里还没出什么差错。
又过了五天,日本兵开始在乡间经过,大都顺着铁路走。他们开始看见农夫带着家人逃难,还带着猪、鸡,以及别的家畜,有的是从靠铁路太近的地方逃往别处,有的是从北平郊外逃来的。这些只是华北乡间大动乱的最初征兆,而将来遭受蹂躏最厉害的地方,会使人畜一扫而空,甚至一棵树也不留下。逃难的妇女向村中的妇女低声说受污辱的经过。一个做丈夫的从日本兵手里抢夺他的妻子,他的头被日本兵拿棍子痛击。男人告诉他们村子里住着日本兵,鸡猪都宰杀吃了,门窗都打烂了,木器家具都拿去做柴烧。因为在华北木柴缺乏,每一有兵灾,第一件事就是木制的东西遭受破坏。
现在,说来也怪,朱家庄竟能免于灾难。因为朱家庄和火车道之间有一条小溪,村子在山坡上,经过的日本兵走不到。传闻南口附近有猛烈的战事,但是距离太远,连炮声也听不见,只看见远处有数千之众的日本军队沿着铁路走过,配有坦克车。夜里有时可以看见远处有大火,他们知道那是烧的农人的家具、织布机、门框。可是朱家庄虽然在日本兵的眼界之内,却能安睡无惊。
现在又有大批难民从北方源源不断而来。他们说全村子都烧毁了,几百妇女逃到矿穴里去避难,藏在里头,一连几天没有东西吃。成群的土匪,也在乡间时时出没。
一天,因为看不见日本兵的踪影,阿瑄冒险渡过小溪,走到一个荒凉的小村子里。村子里已经荒废无人,因为正在日本兵行经的路径上。他在死气沉沉的村子里走,处处都是曾经遭受抢劫蹂躏的样子。在墙上有一张日本军队的布告,中文还不错:
大日本皇军布告第一号
本司令官将下列命令告知汝中国民众:我军为实现大日本帝国之使命,只求在远东建立和平,增加中国民众之幸福,但求中日合作,共存共荣。此外,别无所求。此次,虽本军为中国军队之荒谬无理之态度所激动,但本司令官仍一再容忍,深盼情形不致恶化,并能早日获得解决。但中国军队尚未自知错误,停止挑衅。中国军队之行动,不仅污辱大日本帝国之光荣,并危害东亚之和平,陷人民于千载不复之灾难。因此之故,本皇军仰体天心,俯顺民意,对残忍不义愚蠢顽梗之匪徒,决予严惩。但对本皇军毫无敌意之善良百姓,皆视为本军之亲友,绝不加害,且为彼等谋永久之幸福。希望居民慎勿惊扰,明辨是非,深体本军之诚意,各安本业,静待福祉之来临。凡乘时局未定,造谣滋事,或帮助匪徒者,决予严惩不贷。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香月清司
---昭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阿瑄看的是商店一旁的一个布告,商店的货架子上空无一物,地上满是碎玻璃,桌子翻在地上,半毁的木门框横躺在门槛上。
看了这一个布告,几天之后,阿瑄对从北方逃来的难民口中所听来的事情就更明白了。下面是某弟兄二人告诉他的:
他们村里有人在日本军队的布告里的“大”字右上角添上了一点儿,成了“犬”字,于是成了“狗日本皇军”,其他所有“大”字都改了“犬”。后来有四五十个日本兵从那村子里经过。有一个兵让日本军官过去看。那个军官把村长传来。村长跪在地上说他不知道是谁写的,说他以后留心就是,并且说愿在布告前跪一天来赎罪。日本军官一定要他找出改字的那个人,村长说实在不知道。
那个军官喝道:“起来!去给我找!我给你十分钟。”
没到十分钟,日本兵在村中各处泼煤油,把全村房子都烧起来。居民想逃命,但是全村都被日本兵包围,谁逃跑就射杀。全村都烧毁了,人都死在火里。那兄弟二人藏在破砖瓦下,藏了一天一夜,后来才跑出来。
现在他们又看见成群的伤兵从南口回来,据说有两万五千日本兵集中起来猛冲南口,真是血流成河,尸骨堆山。显然军队铁路已经无法全部运输,因为还要运军火、重炮、补给品。
情形越来越可怕。疲惫不堪的小股的日本兵,开始在邻近的路上回来。有的直接穿过村庄,女人开始害怕。普天下的战争都是一样,但是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态度,或者说日本人的性生活这个题目,尚待专家研究。
阿瑄很焦虑,坚持要逃离日本兵经过的路线再远一点。听说几里地之外,有一个村子,隐避在幽深的山谷里。一天,他自己去看,好安排睡觉的地方。他出了一个高价钱,一家人愿意让他们去住。
黄昏时节他赶回来,遇见同村住的一群人,哭喊着说日本兵已经进了村子。父亲背着祖父,丈夫背着受伤的女人,说出惨绝人寰的遭遇。
阿瑄问:“我们家的人在哪儿?”
大家说:“谁知道?各人只能自己逃命。”
阿瑄一直奔向自己的住处。日本兵已经走了,冷落的街上只看见几只狗悄悄地走动。
他进入自己的家。在外间屋里,一个桌子翻在地上。他进入卧室,他太太赤裸裸躺在炕上,肚子上有刺刀伤痕,已经断气。他脊梁骨不由得发麻。孩子四仰八叉倒在地上。他赶紧去抱,只是一堆血肉,两个对角线的伤口,显示当时划得很熟练,在脖子和两肩之间交叉。阿瑄把儿子抱在怀里,抬起头来看看妻子那赤裸裸还在流血的肉体,自己也忘了怎么回事,手一松抱着的孩子就软软地掉在地上。他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觉得自己堕入了地狱,要千年万代受苦受难。并不是感觉到自己此次得免于难,而是自己正陷在紧紧的魔掌之中,而自己完全无力挣扎对抗。他并没有哭。他浑身的循环系统似乎都颠倒过来,唾沫向外流,眼泪和汗向里流,两眼出奇地发干,汗毛倒竖,好像外面泡着冷水。
后面屋里有呻吟之声,把他从神志恍惚中惊醒。
他冲入后屋,看见母亲曼娘的身体用绳子吊在窗子附近,衣裳脱了一部分。他吓得闭上眼。
又一个呻吟声,使他毛骨悚然。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说:“把她的身子解下来,好好儿盖上。”
他睁开眼睛,往床的方向一看,从那个黑暗而遮着布的角落里发出说话的声音,似乎一个人在移动。
阿瑄走近床铺,发现她太太的老伯母软弱无力地正想抓一块席子。
阿瑄问:“您受伤了没有?”
那声音又说,软弱无力:“把她放下来。”他又看曼娘那可怕的姿势。她那一生从来没有被男人的眼睛看见过的身子,现在挂在那儿,一半赤身露体。
阿瑄把视线一转,鼓起勇气,迈步向前,首先把母亲的裤子提起系好,再把母亲放下来。现在一摸到母亲还温暖的身体,他才能哭出来,好像才又回到人间。他看见母亲的脸,人虽已死,脸还是平静而美丽。他接触到母亲柔软下垂的胳膊,就是从婴儿时抚摩他,抱着他,把他拉扯大的胳膊。从他灵魂的深处,泪如涌泉奔流出来,那无法抑制的眼泪。
他也不知道他坐在曼娘身旁抚尸而哭了多久。等他的眼泪流干了的时候,才又想起了那位老伯母,站起来向她走去。
那声音说:“点上个灯。”
阿瑄很急躁地找火柴。他又走到他太太和孩子的尸体所在的那间屋子,忽然恐惧起来,跑到院子去,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又想起来自己正在找火柴,于是走进厨房,拿起一个盆子,走回那黑暗的屋子。一迈步进屋,眼泪又涌出来——曼娘虽死,尸体仍然使他触动不已。
他划了一根火柴,把小油灯点着。灯一亮,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形状。火柴,灯,他的手,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是灯?什么是火焰?什么是人的手?什么是他手指头的骨节?他在半精神错乱中,渐渐恢复了知觉。不错,他是在那间屋子里。他的妻子死了,还有他的孩子、他母亲。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个老伯母在那屋子里,离北平有很多里路。他明白了那可怕的现实,他心里清楚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身一人了。他心里忽然有一阵子冲动,想把这栋房子一把火点着,自己与家人同归于尽。但是床那边儿的声音又说话了。
“给我一点儿水喝。”
他的精神又回到了这个现实世界。他走到厨房去,端了一碗水来,走近老伯母,把灯端得离床近一点儿。他看见老伯母的头有擦伤。他把老伯母轻轻扶起来,递给她那碗水。
阿瑄说:“您往后躺,我洗一洗您的伤。”
他又去端了一盆水来,拿了一块手绢儿,蘸了水,把老伯母鬓角儿上的血洗下去。老太太直喊疼,可是他看出来只是表皮受伤。
他说:“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哭着说:“真丢脸,我都五十多岁了。为什么他们不杀了我呢?”
阿瑄说:“这也不算什么丢脸。”
“不要告诉村子里的人。”
“村子里都没有人了。”
“他们呢?”
“都逃跑了。全村都空了。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伯母提起精神来说:
“东洋鬼子来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是怎么来的。他们闯进院子来,你太太正和孩子在前面院子里玩儿。一个凶神般的日本兵走进来,你太太就拉着孩子跑,那个日本兵在后面追。她把门闩上,可是那个日本兵把门撞开。曼娘和我跑到后面这间屋子来。我们听见喊叫声,随后听见铁东西呛啷一声,孩子的哭声就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听见你太太尖声喊叫。我爬到床底下去,你母亲上了吊。日本兵进来,把我从床底下拉出来。他大发脾气,打我,把我放在床上,我就昏过去了。我苏醒过来之后,房子里什么声音也听不见。我看见你母亲的尸体在那边儿挂着。你看,女人死了之后,他还戏弄她。你太太和孩子也都死了吗?”
阿瑄没说话,点了点头。他不敢进他太太所在的那间屋子去。他只是坐着,注视母亲躺在地上的尸体。说也奇怪,每一次他一看母亲,他就有了勇气。曼娘并没有可怜的表情,只是死了,在儿子眼中和以前一样美。最后,他终于鼓起全身的勇气,走到前面屋里去,把孩子摆在母亲的身旁,找东西遮盖起来。
老伯母说:“你想吃东西吗?”
他说:“不,我吃不下去。”
“到橱子那儿把右边儿抽屉里一根人参拿出来,给我熬点汤喝。我没有力气。”
他照吩咐去做。他要把那人参,切,煮,做汤,这使他平静下来,使他稳定下来,但并非因此就忘了当时自己的处境。自己的骨肉都死了,都在地上躺着,他却安安静静地做人参汤。他觉得什么都奇怪,什么细小的事情都不应当像那种样子。他看火焰乱闪,不觉陷入沉思。慢慢地,静静地,他心里构成了一个新的决定。
回去,他又看了看母亲的尸体,他对母亲说出声来:“妈,我要替您报仇。我要杀!杀!杀!”
他现在对死已然毫无恐惧,并且自己也再没有什么忧虑。若与今天早晨心中的紧张不安比起来,他现在突然觉得轻松了。他现在准备随时遇见一个日本人,随时准备死。他毫无牵挂,毫无恐惧了。
他走到外面去,向四周邻居的房子看了看。不见一个活东西,只是处处是死尸,但是他不再感觉恐惧。他再往远处去,听见受惊的脚步奔跑声,还有活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有活力的人,正在一个鬼世界漫步。他走到黑屋子里去,大声咳嗽。
真正是万籁无声,他自己有一点儿紧张。
他喊叫:“我是中国人。这儿有人吗?”没人回答。
他又向黑黝黝空洞洞的地方,重新问了一遍:“不要害怕。鬼子走了。”
有脚步移动窸窣作响的声音,他仅仅能看见两个人形向前移动。
一个女人的声音问:“你是谁?”
“我姓曾,北平来的。我家的三口人都死了。”
一个女人去点灯。
他问:“你怎么活命了?”
“我们婆媳两个人藏在厨房炉灶后面一个角落。”
他告诉她俩说:“明天早晨你们最好到山里去找亲戚朋友。日本鬼子也许还会来。”说完,回到自己屋里去,那天夜里他就睡在母亲的身旁。
第二天早晨,他帮着伯母和另外那两个女人搬往山里,然后又回来,回到自己死去的骨肉身旁。在村子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找了把铁锹,在后院子里把死尸埋葬,直到黑夜才完工。
他觉得饿了,走进厨房去,自己做了一顿简单的饭吃,又出来,在母亲、妻子、孩子的坟头儿上坐着。
第二天早晨,他不忍心离开他们,又多待了两天——他仍然是村庄群鬼中唯一的活人。
第三天早晨,他按礼俗向坟墓哭别而去。
他两个小手指头上各戴一个戒指,一个是他母亲的,一个是他妻子的;又在衣袋里带了三绺头发,他母亲的,妻子的,孩子的。
他一路走向游击队的大本营,去参加打游击。加入之后,他总是在前线作战,而从未受过伤。他的性命好像是疯魔了一样。他的同志都奇怪为什么他打起仗来那么勇敢,打得那么狠。他没有告诉他们是因为母亲、妻子、孩子的阴灵保佑,增加了他的勇气。别人不知道他是孤身一人了,但是他并不孤单。
在北平,家中得不到曼娘的消息。自从警察来搜查和美国小姐迁入后,表面上一切倒安静无事。阿非和宝芬则打算离开北平,因为情形很清楚,只要牛怀瑜和亲日的官僚想以他曾充任国民政府的官吏为理由而来逮捕他,他是随时都会被捕的。经亚和暗香也决定逃出怀瑜的手心,才感觉较为安全。
这些个人的情形姑且不表。北平现在是一个真正沦陷的城市了,和自由中国完全隔绝,一切陷入混乱、非法、流血的气氛之中。
日本人并没有公开接收市政府,但是一群傀儡政客则急于成立一个地方维持会,好帮助日本维持地方秩序,和日本合作。亚洲文化协会转眼兴起,提倡学习日本话。学校的教科书要改编。过去几年鸦片烟馆本来已经减少,如今又兴隆起来。好多日本商人开始进入北平。大部分日本女人有的穿西装,有的穿旗袍。穿旗袍的原因是因为旗袍是满洲旗人的衣裳,穿旗袍就是“和满洲国团结一致”,是表示爱国。不过可以注意的是,自从通州伪军张庆余率军杀光三百日本人之后,日本女人才有穿旗袍的时尚,以前却没有。在中国人看来,北平在各方面都是个亡国的城市。老安福系的政客王克敏,当年西原借款计划下中国段祺瑞政府的财政主持人,现在又和他的同僚在积极筹设傀儡政权。
阿非和经亚讨论准备携眷到上海去。博雅吸毒的毛病已完全戒除,决定和太太仍住在北平不动。冯舅爷和他太太都上了年纪,还有宝芬的父母认为他们自己无须离开,他们愿和董娜秀小姐一同看守王府花园。
这时,上海的保卫战已经爆发,但是外国轮船仍然在津沪之间定期航行。阿非他们一旦上了船,离开了天津,个人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他们知道若是坐火车离开北平,一定要受检查,不过头等火车的乘客,遇到的骚扰会少一些。最容易遭受严密盘查,甚至被逮捕的,是学生和二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像军人的那些人。商人通常是容易通行的。经亚将近五十,应当是平安无事。阿非在四十以下,他特别小心,改作商人模样,戴上旧式眼镜,拿着旱烟袋,胡子故意不剃,尽量显得岁数大。他们还要带着药铺和古玩店商业上来往的书信账簿等东西。
暗香扮作商人妇,自然很容易通过。宝芬看来时髦又年轻,但是和阔气的商人乘头等车,有丈夫同行,还带着孩子,也还可以。再者董娜秀那位美国小姐也愿和他们一同旅行一段,送他们到天津平安上船。因为知道有美国女人在场,容易提醒日本人在举止行动上,要像个“文明”国家的人。
所以在八月半,他们向古老的北平告别。他们过哈德门大街时,又看见那熟悉的店铺,阿非和宝芬在压抑的情绪之下,紧握着彼此的手。过东单牌楼时,阿非告诉司机往西转,走东长安街,以便再看一眼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董娜秀小姐用英文说幸而北平的皇宫仍然无恙,她觉得北平还是北平,没有什么变化。
那天一大早,他们到了火车站。车八点半开。火车站前成群的人,男女老幼,转来转去,中间有洋车、汽车、马车,上面高高地装着行李。
进火车站时,旅客必须接受身体搜查,不论年龄、性别,在外面的人要等候很久,通过身体检查之后,再在月台上打开箱子、旅行袋。阿非这一批人,没遇到什么困难就进入了头等车的中间。那时已经十点钟,车还没有要开的样子。
阿非等得不耐烦,下车到月台上走一走,告诉宝芬和暗香好好看着孩子,不许下车。他看见别的旅客还正受搜查,行李也在检查当中。
一个警察对轮到检查的旅客说:“打开箱子!”然后又低声说:“不相宜的书跟东西不要带。”两三个一组的日本宪兵拿着枪,枪上上着刺刀,只是在一旁看着。
再往前走到三等车箱,看见乘客站成排,在上车之前,正逐个儿遭受搜查。他们已经自己解开衣裳的扣子。一个女学生没有解开她的上衣,因为她以为衣裳上没有口袋。
一个日本宪兵走过来,指着那个女学生,和一个中国翻译官说了几句话。
一个五十岁的中国商人,站在女学生旁边,向女学生说:“这种年头,最好随和一点。”
那个女学生开始解开上衣,脸上很羞愧,在衣服里面贴边有几个字。
日本宪兵指着那几个字问是什么。
女生回答说:“是学校洗衣裳的号码。”
幸而中国翻译官,他显然是沈阳人,特别帮助她,替她翻译得很好,那日本宪兵才走开。
十一点半,火车才开。火车每站都停,甚至在离开北平城之前,也遇站就停。有两次,日本兵由中国警察陪同,上车再度检查行李,头等车则草草了事。
离开北平之后,他们看见一队日本飞机,有十架,也许十二架,在头上往西北飞去。大战还在南口和别的地方进行,日本忙着运送军用补给品,所以火车每站都停。后来看见往西开的列车通过,车上装着大炮、军火、几车厢的马,车过后,掉在地上一些草料。铁路沿线曾发生激烈战斗,小镇都遭炮火之灾,极为凄惨。处处日本兵成群,蹲在地上,秩序散乱。一路中国村子的房顶子上飘着日本国旗。树木砍倒在路边,显然是为了日本军队的防御之用,但是倘若防御不周密,也似乎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埋伏偷袭的绝好机会。
下午七点半钟,他们才到天津,这段途程竟走了八个钟头,若是在太平年间,两个半钟头就够了。
通过天津火车站是最不容易的事。
卫兵警告他们说:“过桥,走中间,不要忙!”
由美国小姐相陪,他们出火车站毫无困难。他们正说运气好平安通过之时,几个卫兵近前来说:“到左面去排队。”他们看见人们三三两两慢慢走过去。四五个日本兵站在左边儿,把旅客一个一个挑出来再仔细盘问。商人,学生,男,女,穷,富,身份似乎无所谓,只是随便挑。那些被挑到的人必须散开,站在外面去。
轮到他们的时候,日本兵忽然揪到经亚十七岁的儿子,把他拉出去。美国小姐董娜秀从中干涉,向日本人说话,但是日本人只是望望她,叫经亚的儿子站在一边。暗香不由得颤抖起来。他父亲递给儿子一个小衣箱,里头有商业信件等东西。日本兵看见了,并不拦阻。
家里人正焦急地等着他回来时,他却和另外一些人被赶到附近的一个办公处去。他父亲曾经告诫过他,不要怕,不要慌,小心回答问题。他知道有的立即放回,有的留上两三天,有当过兵证据的就枪毙了。凡是经过盘问之后就匆匆忙忙走开的,还会被叫回去再盘问。
经亚的儿子很仔细,他提着手提箱,很有耐性地站着等轮到自己去回话,一点儿提心吊胆的样子也没有。等轮到他时,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去,里头有三个日本兵,各坐在一张桌子旁,脸上表情非常严肃。下面是问的一串问题:
“你反对日本吗?”
“你是国民党吗?”
“你是蓝衣社的吗?”
“你是共产党吗?”
“你是英美派吗?”
“你念过三民主义吗?”
“你崇拜孙中山吗?”
“你拥护蒋介石吗?”
“你对满洲国怎么个态度?”
“你觉得日中满应当合作吗?”
“中国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对吗?”
“你什么时候生的?你有几个姐妹?她们多大年岁?叫什么名字?上什么学校?”
这些问题很机械地一个一个地问,答案被很认真地记下来。日本军官自己非常严肃,绝不许自己流露一点笑容。在那种情形下,仿佛谁都应当用个“是”字答前几个问题。
“你带的是什么东西?”
经亚的儿子打开箱子请检查。在仔细看了大概有半点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让他从一个门出去。
他知道已经获得释放了,慢慢走下楼梯,来到外面的空地,看见家里人正很焦急地在入口等着他,一见他出来,好不欢喜。暗香拉住他,好像他死而复生一样。
他们到英租界,住在一个外国饭店里。在三天以后才有船。董娜秀一定要陪他们,直到他们平安登上了驳船,把他们送往停在塘沽的英国轮船才肯走。宝芬告诉她说他们已经安全无事,催她回去,对她这份患难之中的深厚友谊,表示衷心的感谢。
董娜秀是在他们开船的前一天动身返回北平,因为她担心她不在家时王府花园的人会有麻烦。阿非和经亚两家坐了五天的船才到上海,因为每处都停。一进黄浦江就发现一个日本舰队正停在港口,炮轰上海市区,火光闪动,浓烟蔽天。
轮船在公共租界靠岸。他们住进一家饭店,打电报给木兰和莫愁,说他们已经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