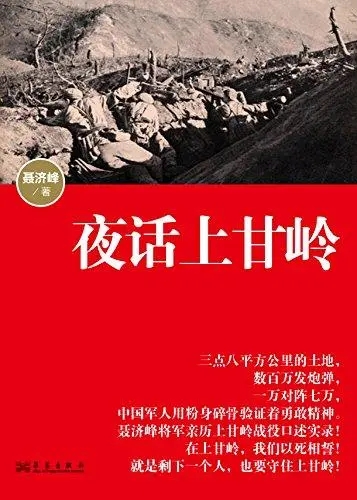铜壶漏尽,铁马摇曳。伍次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来到北京几年,那些惊险而又带着神秘色彩的变故,在脑海里不停地闪过。他一会儿兴奋,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感到欣慰,一会儿又情不自禁地叹息流泪。他想得最多的,是龙儿这个怪学生,那令人生疑的身份,那不同凡响的气质,那凡事都要问个究竟的脾气,那嫉恶如仇却又藏而不露的深沉,和与他年龄不符合的个性,这一切都是一个难猜难解的谜。还有那个以仆女身份出现的婉娘,更是令人费解。她忽而低眉顺眼,忽而自信高傲,忽而似含深情,忽而又拒人千里,尤其是她那风姿卓约的倩影,顾盼有神的眼睛,总是在伍次友的面前晃来晃去。有时,似乎走到近前了,可以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和机智而又爽直的话语,看到她那似笑含嗔的脸庞,但是,立刻又不见了,只剩下眼前这长夜难眠的孤苦……朦胧之中,伍次友似乎听见有人在喊自己——啊!是柱儿,他喊什么呢?
“二爷,二爷你听见了吗?快起来开门吧,索大人和龙少爷来了!”
“啊!”伍次友一惊,这才明白。原来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连忙揉着眼睛坐了起来,看看窗外,已是日上三竿,听听声音索额图和龙儿,也已经来到房门口,便一跃而起,打开了房门。面前站的,果然是半个多月来自己日思夜想的龙儿。
康熙笑嘻嘻地跨进门来,作了一个长揖:“龙儿久不见先生,着实惦记着呢!”说着便想下拜。伍次友急忙拦住,扳着双肩端详着,笑道:“一天一个模样儿,你倒出脱得越发精神了!”回头看时,索额图、魏东亭也前微笑着站在一旁;还有个长随的人手里提着一个礼盒子,跟在魏东亭后边;婉娘则握着手帕在一旁垂手侍立。大家都见过了礼才走进屋里。
“听婉娘说,先生这几日清恙在身,不知可好些了?”索额图满面堆笑,一边吩咐人打开礼盒,取出礼品放在桌上,一边说:“家母听说后把我好训了一场,说是请了个这么好的先生,除了惊吓没给人家半点好处,还不赶快瞧瞧去——说起来也很怪,这些天来我们家里老出事儿,竞没有顾着来看望先生,实在有愧得很哪!”
“索大人国事家事烦忙,还不断地派人送东西来。大人如此费心,又何必呢!”伍次友说着便起身来到桌边,瞧那些礼物:一柄镂花嵌珠的玉如意,一枝用红绫桑皮纸包着的老山参,几瓶陈酿老酒和一方石砚。
伍次友对其它的礼物,只是瞟了一眼,这方石砚,他却拿起来仔细端详,爱不释手:“索大人和龙儿深知我心。还请二位代我谢过太夫人。晚生不过是稍有不适,却劳太夫人如此惦记,反倒觉得惶恐不安了。”
魏东亭趁机上来看座,顺口向伍次友说:“先生,熊赐履大人让我带信问候你。他今日有公务,不能来了。”
“哎呀呀,这是怎么说呢?都这样客气。熊大人人品学问,我也是十分敬仰的啊!”
康熙原来以为,熊赐履尊儒重道,而伍次友却讲实用杂学,二人不一致。想不到伍次友却这样称赞熊赐履,便接口说道:“可惜呀!熊大人不过是个道学先生!”
“哎——龙儿,你这话说得不全对。熊大人只是过于老诚了些。听说去年平西王吴三桂进京,熊大人和他讲了大半天的道德经,这就有点迂腐了。像吴三桂、鳌拜这样的人,秉的是大地乖戾之气,行的是人间邪恶之道,和这样的人谈什么仁义道德,因果报应。不是对牛弹琴吗?哈……”
看伍次友今日精神振奋,眉飞色舞,几天来因为不见龙儿而生出的猜疑和郁闷一扫而空,魏东亭也十分高兴。笑着说:
“如果先生现在跟皇上参赞朝政,说出这些话来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呢!”伍次友笑道:“到哪山唱哪山歌,若让我参赞朝政,我就不能听任鳌拜势压朝野,吴三桂拥兵自重。如果听任这两匹野马胡作非为下去,一旦合槽作乱,局面就不好收拾了。现在一个在云南养精蓄锐,虎视耽耽,一个在北京网罗党羽,专横暴戾,应该趁早定下拿掉他们的方略。——咳!说这些做什么,布衣论朝政,隔靴搔痒,白白地惹人耻笑!”
鳌拜和吴三桂常有书信往来,康熙是早就知道的,倒没多想他二人“合槽”的事。现在听到伍次友的一番议论,内心也不禁焦急万分。但又不能让伍次友看出,只得强装笑脸,打趣道:“先生是布衣,龙儿便是布衣的学生呢!我们闲说三国,原不必替古人耽忧,不过先生既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问,他们会不会合槽呢?依先生之见,该怎样制定对付他们的方略?”
伍次友看一眼索额图,笑道:“索大人,你是朝廷重臣,你看他们会不会合槽?”
“暂时不会。”索额图想到吴三桂拥有庞大的军队并和耿精忠、尚可喜二藩声气相投,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沉吟道,“不过时间长了就很难说。姓吴的翻云覆雨,不是个好东西!”
伍次友接着说:“对。索大人所言极是。此人先叛前明,再叛李自成,脑后还会有第三块反骨。如今,当务之急,就是不能让他们合槽,采取一个一个拿掉的办法。”
康熙着急地问:“依先生看,怎样才能使他们合不起来呢?”
“自古攘外必先安内,鳌拜把持朝政,窥测神器,一日不除,皇帝便无一日之安宁。而欲除鳌拜,则必须稳住吴三桂,不令他心生疑惧,更不让他干拢除奸大计。好在,当今皇上还算聪明,没有急急忙忙地动三藩。但是,如果再进一步,给吴三桂一点甜头,比如说,既然把他的儿子招了驸马,索性再加封个官爵,让他们父子宽宽心,定定神。等这边除鳌拜、清君侧、朝政走上正路之时,再专心致志地去对付吴三桂他们,那就是另一局面了……咳,我今个是怎么了,当着索大人、魏大人的面,这样没完没了地议论朝政干什么?”
龙儿,来来来,咱们还是讲书吧。康熙的心里觉得好笑:“还讲什么书啊,我想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他向索额图递了一眼色,索额图会意,“啊,先生刚刚康复,不宜太劳神。太夫人吩咐,龙儿的功课过几天再上不迟,好在来日方长。”
伍次友是个爽一快人,见他们执意要走,也不强留:“既是索大人如此说,晚生恭敬不如从命。请拜候太夫人安好。”
魏东亭赶前一步,掀起门帘,送康熙等人出去,又转身拦住伍次友:“先生留步,东亭代先生送客好了。”
来到前院,康熙低问魏东亭:“小魏子,给吴六一的密诏可曾送到。”
“皇上放心,一切均已安排妥当,吴六一让我代奏圣上,”他决不负圣上眷顾之恩。”
此刻,吴六一坐在九门提督府衙门的签押房里,屏绝了弁从官佐,他要独自好好想想,他拿着小魏子方才送来的“圣上密旨”反复阅读,虽早已背得一字不漏,但仍舍不得收起来,还在那里一字一句地咀嚼。他佩服这个谕旨写得好,——不是文字好,而是意思精深周密。他相信这必定是受了能人的指点。现在自己已再无回旋的余地了,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不能不小心一些。因为鳌拜那边也常派班布尔善、济世一干人来打点。顶头上司泰必图又是鳌拜一党。这是自己一生的关键一步,万万不能走错!
“来啊!”吴六一忽然唤道,一个长随毕恭毕敬地进来,干净利落地打了个千儿,后退半步垂手听差。“去,请何先生来!”
那差人去后不到一袋烟工夫,便听何先生在门外头笑道:“东翁昨夜的双陆打输了,今儿还想着找回来呀,”说着便挑帘进来。吴六一忙笑着起身让座道:“志铭,铁丐正要同你共下一盘大围棋,咱们可不能输了。”
“是啊,这盘棋还得你我共下才成,”何志铭狡黠地眨着双眼说道。
何志铭五短身材,两只小眼黑豆一般嵌在脸上,一说话便滴溜溜乱转,一脸的精悍之气。在吴六一邀聘的清客中,他是最得用的一位,从吴六一当参将时起就跟随着。两个人几次一起死里逃生。故虽有宾主之分,实在比家人还来得亲近。
这一“围棋”笑语,在他们二人身上还有一段掌故。何志铭下得一手好围棋,那吴六一却是臭棋。他们二人联手,曾与金陵国手王守泰师徒对奔,竟把对方杀得中盘推枰认输。这会儿提到“双杀棋”,何志铭呵呵大笑:“好,好!照上次的杀法儿,保管取胜!但不知敌手是何人?”
“辅政首席大臣鳌拜!”吴六一暗哑着嗓子,身于往前一倾道,“怎么样,不至于不过瘾吧?”
何志铭正笑得开怀,闻得此语嘎然止住,撩了撩袍子坐下:“东翁,你与他下了快二十年的棋了,难道是今日才开始的么?”
“是的。但若说今日之举,于围棋言,算得上中盘胜负生死劫,于象脚!是杀将!”吴六一脸上横肉一颤一颤,眼中凶光逼射。何志铭虽与他多年相交,也觉不寒而栗。沉默了一阵子,何志铭忽然抬起头,一双黑豆眼闪烁有光:“明白了,怎么个杀法儿?”
“圣上要我做他的杀手铜,”吴六一道,“这是绝大的一盘棋,你可要帮我走好了。咱们不能输给人家!”何志铭兴奋地将身子一挺道:“怎么会呢!”
“走好了,红顶子是有你的。”吴六一在椅子上将身子向后一仰,舒展一下身子说道:“走不好,那咱们就一块儿‘顶子红’了!”说完,眼睛望着棚板不言语了。何志铭一边思索一边说道:“前几日都察御史弹劾巡防衙门玩忽职守,那个缺只怕要出。这像是鳌中堂开出的盘子。您今日此语既出,那准是有信儿了。”
“姓鳌的这会儿把金山搬来我也不能从他!”他本来就与鳌拜不睦,魏东亭又当着查伊璜的面几次暗示:救查伊璜出狱的七个折子都是被鳌拜驳回的,万岁爷作不了主。弄得吴六一更加憎恶这位辅政大臣。
“说到金山是没有的。这里倒有一件东西请将军过目。”何志铭说着,弯腰从靴筒里抽出一张纸来递上。吴六一接过一看,知是十万两一张的龙头银票。看着吴六一怀疑的目光,何志铭忙道,“这是晚生的一个同窗,在泰必图属下,于昨晚奉命送来的。”
“用的什么名义?”吴六一上下打量着何志铭。
“名义?”何志铭大笑,“为了祝贺将军少公子百日汤饼会。他怕将军未必肯收,就叫我瞧着办。我想着他们发的黑心财也够多的了,既然取不丧廉,也就笑纳了。”
“好!有你的,拿了来使也很好!”吴六一满意他说道。又问,“他还说些甚么?”
“他还说,鳌中堂要荐你做兵部侍郎!”
“兵部侍郎?哈哈哈哈……”吴六一仰天大笑,“十万银子加一个二品官,要换一龙百虎和一乞丐还有你何先生的头……”吴六一背起手,来回踱了两步,“何先生,我也给你瞧一样东西。——事情一发动,我立刻就能委你作兵部侍郎!”说着从怀中抽出密诏给何志铭看。
何志铭接过诏旨,反复地审视了上面的朱砂玉玺“体元主人”,一字一句啃着诏书上面的几句话,忽地击案跃起道:“军门,有这个在,事情就好办了。”
“所以我请你来,”吴六一冷静了下来,“议议怎么个着手法。”
何志铭踌蹰一下,取出火楣子点着了旱烟,半躺在椅子上,眯缝了眼苦苦思索,二人足有半顿饭工夫没说话。良久,何志铭轻叹一声,坐直了身子,从那黑豆眼里发出绿幽幽的微光,“唉!虽然狠了一些,有伤阴骘,但也只有如此了。”
“请道其详!”吴六一坐正了,他不抽烟,手里两只硕一大的钢球唰唰地转个不停。
“在军门帐下,我料鳌拜必定另做了手脚。这十万银子,明知无用,不过用它来买大人轻慢之心而已。”
“说的透!他要做大事,如今便许个王爷也只一句话,明知道我不买帐,才来这一套。”
“军门所见极是!”何志铭笑道,“您就是买帐,将来他做了皇帝,也要把你列在清君侧的名单里。”说着话锋一转,“可虑的,倒是将军帐下的李、黄二参将,还有张副将、刘守备,这十几个人素来……”
“你不必说了,”吴六一道,“我心里有数。我即日就把他们都打发到福建办差,叫他们作不成耗!”
“那不成!”何志铭道,“鳌拜是何等样人?班布尔善更不可欺!如今时机未到,您先就这么摆一布,他们能不猜疑?倒让他们有了防备……
“他奶奶的!”吴六一咬牙道:“到时候全都扣起来!”
“不成!我们在这局棋中是杀手铜,主角是姓魏的他们。万一扣押不尽,或又被别的救了,铁丐死——你我可就真要‘顶子红’了!”
“那,依你呢?”
“杀!”何志铭黑豆眼一闪,“死人是作不得乱的——自今而始,帐下军官全部到衙应差,将两廊厢房腾出来给他们住。这是一!”他伸出两个指头,“二、密布几名心腹校尉,许以高爵、酬以重金,弓上弦、刀贴身,随时应变。”吴六一听得出神,不住点头。何志铭又伸出第三指头道,“待事一发,颁圣上密旨,下令将这十几个人一鼓擒斩!敲山震虎,余下的就不敢发难了!”
“这——”
何志铭突然扬声大笑:“军门枉自称了”铁丐’!做这事岂能心软!早年您杀人如麻,如今莫非回心向善了?”
“那好!”吴六一咬牙道:“就这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