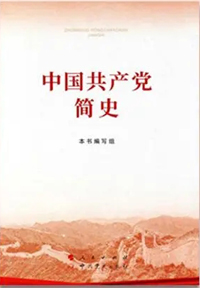“堂堂塌!堂堂塌!”今日天气清和,在下唱一个道情儿给诸位贵官解闷何如?唱道:
尽风流,老乞翁。托钵盂,朝市中。人人笑我真无用。
远离富贵钻营苦,闲看乾坤造化工。兴来长啸山河动。
虽不是,相如病渴;有些儿,尉迟装疯。
在下姓百名炼生,鸿都人氏。这个“鸿都”,却不是“南昌故郡,洪都新府”的那个“洪都”,到是“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神致魂魄,”的那个“鸿都”。究竟属哪一省哪一府,连我也不知道,大约不过是北京、上海等处便是。少不读书,长不成器,只好以乞丐为生。非但乞衣乞食,并且遇着高人贤士,乞他几句言语,我觉得比衣食还要紧些。适才所唱这首道情,原是套的郑板桥先生的腔调。我手中这鱼鼓简板也是历古相传,听得老年人说道,这是汉朝一个钟离祖师传下来的。只是这“堂堂塌”三声,就有规劝世人的意思在内,更没有甚么工、尺、上、一、四、合、凡等字。
嗳!“堂堂塌!堂堂塌!”你到了堂堂的时候,须要防他塌,他就不塌了;你不防他塌,也就是一定要塌的了。这回书,因老残游历高丽、日本等处,看见一个堂堂箕子遗封,三千年文明国度,不过数十年间,就倒塌到这步田地,能不令人痛哭也么哥!在下与老残五十年形影相随,每逢那万里飞霜、千山落木的时节,对着这一灯如豆、四壁虫吟,老残便说:在下便写,不知不觉已成了《老残游记》六十卷书。其前二十卷,已蒙天津《日日新闻》社主人列入报章,颇蒙海内贤士大夫异常称许。后四十卷因被老残随手包药,遗失了数卷,久欲补缀出来再为请教,又被这“懒”字一个字耽阁了许多的时候。目下不妨就把今年的事情叙说一番,却也是俺叫化子的本等。
却说老残于乙已年冬月在北京前门外蝶园中住了三个月,这蝶……(编者按:这中间遗失稿笺一张,约四百字左右)也安闲无事,一日正在家中坐着,来了两位,一个叫东阁子、一个叫西园公,说道:“近日朝廷整顿新政,大有可观了。满街都换了巡警兵,到了十二点钟以后,没有灯笼就不许走路,并且这些巡警兵都是从巡警学堂里出来的,人人都有规矩。我这几天在街上行走,留意看那些巡兵,有站岗的,有巡行的,从没有一个跑到人家铺面里去坐着的。不像以前的巡兵,遇着小户人家的妇女,还要同人家胡说乱道,人家不依,他还要拿棍子打人家。不是到这家店里要茶吃,便是到那家要烟吃,坐在板凳上跷着一只脚唱二簧调、西帮子。这些毛病近来一洗都空了。”
东阁子说道:“不但没有毛病,并且和气的很。前日大风,我从百顺胡同福顺家出来,回粉坊琉璃街。刚走到大街上,灯笼被风吹歪了。我没有知道,哪知灯笼一歪,蜡烛火就燎到灯笼泡子上,那纸灯笼便呼呼的着起来了。我觉得不好,低头一看,那灯笼已烧去了半边,没法,只好把它扔了。走了几步,就遇见了一个巡警兵上来,说道:‘现在规矩,过了十二点钟,不点灯笼就不许走路。此刻已有一点多钟,您没有灯笼,可就犯规了。’我对他说、‘我本是有灯的,被风吹烧着了,要再买一个,左近又没有灯笼铺,况且夜已深了,就有灯笼铺,已睡觉了,我有甚么法子呢?’那巡兵道:‘您往哪里去?’我说:‘回粉坊琉璃街去。’巡兵道:‘路还远呢,我不能送您去。前边不远,有东洋车子,我送您去雇一辆车坐国去罢。’我说:‘很好很好。’他便好好价拿手灯照着我,送到东洋车子眼前,看着坐上车,还摘了帽子呵呵腰才去,真正有礼。我中国官人总是横声恶气,从没有这么有礼过,我还是头一遭儿见识呢!”老残道:“巡警为近来治国第一要务,果能如此,我中囗前途大有可望了。”
西园公道:“不然。你瞧着罢,不到三个月,这些巡警都要变样子的。我囗一件事给你们听,昨日我到城里去会一个朋友,听那朋友说道:‘前日晚间,有一个巡警局委员在大街上撒尿,巡警兵看见,前来抓住说:“嘿!大街上不许撤尿,你犯规了。”那委员从从容容的撒完了尿,大声嚷道:“你不认得我吗?我是老爷,你怎样敢来拉我?”那巡兵道:“我不管老爷不老爷,你只要犯规,就得同我到巡警局去。”那委员更怒,骂道:“瞎眼的王八旦!我是巡警局的老爷,你都不知道!”那巡兵道:“大人传令时候,只说有犯规的便扯了去,没有说是巡警局老爷就可以犯规。您无论怎样,总得同我去。”那委员气极,举手便打,那巡警兵亦怒道:“你这位老爷怎么这们不讲理!我是办的公事,奉公守法的,你怎样开口便骂,举手便打?你若再无礼,我手中有棍子,我可就对不起你了。”那委员怒狠狠的道:“好东西,走走走!我到局子里揍你个王八旦去!”便同到局子里,便要坐堂打这个巡兵。他同事中有一人上来劝道:“不可!不可!他是蠢人,不认得老兄,原谅他初次罢。”那委员怒不可遏,一定要坐堂打他。内中有一个明白的同事说道:“万万不可乱动,此种巡兵在外国倒还应该赏呢。老兄若是打了他或革了他,在京中人看着原是理当的,若被项宫保知道,恐怕老兄这差使就不稳当了。”那委员怒道:“项城便怎样?他难道不怕大军机么?我不是没来历的人,我怕他做甚么?”那一个同事道:“老兄是指日飞升的人,何苦同一小兵呕气呢?”那一个明白事的,便出来对那拉委员来的巡警兵道:“你办事不错,有人撒尿,理当拉来。以后裁判,便是我们本局的事了。你去罢。”那兵垂着手,并一并脚,直直腰去了。’老兄试想一想,如此等事,京城将来层见迭出,怕那巡警不松懈么?况天水侍郎由下位骤升堂官,其患得患失的心必更甚于常人。初疑认真办事可以讨好,所以认真办事,到后来阅历渐多,知道认真办事不但不能讨好,还要讨不好;倒不如认真逢迎的讨好还靠得住些,自然走到认真逢迎的一条路上去了。你们看是不是呢?”
老残叹道:“此吾中国之所以日弱也!中国有四长,皆甲于全球:廿三行省全在温带,是天时第一;山川之孕蓄,田原之腴厚,各省皆然,是地理第一;野人之勤劳耐苦,君子之聪明颖异,是人质第一;文、周、孔、孟之书,圣祖、世宗之训,是政教第一;理应执全球的牛耳才是。然而国日以削,民日以困,骎骎然将至于危者,其故安在?风俗为之也。外国人无论贤愚,总以不犯法为荣;中国人无论贤愚,总以犯法为荣。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所以犯法的,大概只三种人,都是有所倚仗,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倚官犯法;一种倚众犯法;一种倚无赖犯法。倚官犯法的,并不是做了官就敢犯,他既做了官,必定怕丢官,到不敢犯法的。是他那些官亲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这三样人里头,又以官家亲信的家丁犯法尤甚,那两样稍微差点,你想,前日巡警局那个撒尿的委员,不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这都在倚官犯法部里。第二种就是倚众犯法。如当年科岁考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一定要有些人特意犯法的。第二便是今日各学堂的学生,你看那一省学堂里没有闹过事。究竟为了甚么大事么?不过觉得他们人势众了,可以任意妄为,随便找个题目暴动暴动,觉得有趣,其实落了单的时候,比老鼠还不中用。第三便是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屡次打戏园子等情,都老爷不敢过问,这都在倚众犯法部里。第三种便是倚无赖犯法,地方土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人,他就仗着屁股结实。今日犯法,捉到官里去打了板子。明日再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官也无可如何了。这叫做倚无赖犯法。大概天下的坏人无有越过这三种的。”
西园子道:“您这话我不佩服。倘若说这三种里有坏人则可,若要说天下坏人没有越过这三种的,未免太偏了。请教:强盗、盐枭等类也在这三种里吗?”老残道:“自然不在那里头。强盗似乎倚无赖犯法,盐枭似乎倚众犯法,其实皆不是的。”西园子道:“既是这么说,难道强盗、盐枭比这三种人还要好点吗?”老残道:“以人品论,是要好点。何以故呢?强盗虽然犯法,大半为饥寒所迫,虽做了强盗,常有怕人的心思。若有人说强盗时,他听了总要心惊胆怕的,可见天良未昧。若以上三种人犯了法,还要自鸣得意,觉得我做得到,别人做不到。闻说上海南洋公学闹学之后,有一个学生在名片上居然刻着‘南洋公学退学生’,竟当做一条官衔,必以为天下荣誉没有比这再好的。你想是不是天良丧尽呢?有一日,我在张家花园吃茶,听见隔座一个人对他朋友说:‘去年某学堂奴才提调不好,被我骂了一顿,退学去了。今年又在某处监督,被我骂了一顿。这些奴才好不好,都是要骂的,常骂几回,这些监督、教习等人就知道他们做奴才的应该怎样做法呢。可恨我那次要众人退学,众人不肯。这些人都是奴性,所以我不愿与之同居,我竟一人退学了。’”老残对西园子道:“您听一听这种议论,尚有一分廉耻吗?我所以说强盗人品还在他们之上,其要紧的关键,就在一个以犯法为非,一个以犯法为得意。以犯法为非,尚可救药;以犯法为得意,便不可救了。
我再加一个譬语,让您容易明白。女子以从一而终为贵,若经过两三个丈夫,人都瞧不起他,这是一定的道理罢?”西园子道:“那个自然。”老残道:“阁下的如夫人,我知道是某某小班子里的,阁下费了二千金付出来的。他在班子里时很红,计算他从十五岁打头客起,至十九岁年底出来,四、五年间所经过的男人,恐怕不止一百罢?”西园子道:“那个自然。”老残道:“阁下何以还肯要他呢?譬如有某甲之妻,随意与别家男子一住两三宿,并爱招别家男子来家随意居住,常常骂本夫某甲不知做奴才的规矩;倘若此人愿意携带二千金来嫁阁下,阁下要不要呢?”西园子道:“自然不要。不但我不要,恐怕天下也没人敢要。”老残道:“然则阁下早已知道有心犯法的人品,实在不及那不得已而后犯法的多矣。妇人以失节为重,妓女失节,人犹娶之,为其失节出于不得已也。某甲之妻失节,人不敢要,为其以能失节为荣也。强盗、盐枭之犯法,皆出于饥寒所迫,若有贤长官,皆可化为良民,故人品实出于前三种有心犯法者之上。二公以为何如?”东阁、西园同声说是。
东阁子道:“可是近日补哥出去游玩了没有?”老残道:“没有地方去呢。阁下是熟读《北里志》、《南部烟花记》这两部书,近来是进步呢,是退化呢?”东阁子道:“大有进步。此时卫生局已开了捐,分头二三等。南北小班子俱是头等。自从上捐之后,各家都明目张胆的挂起灯笼来。头等上写着某某清吟小班,二等的写某某茶室,三等的写三等某某下处。那二三等是何景象,我却不晓得,那头等却是清爽得多了。以前混混子随便可以占据屋子坐着不走,他来时回他没有屋子,还是不依,往往的把好客央告得让出屋子来给他们。此时虽然照旧坐了屋子尽是不走,若来的时候回他没屋子,他却不敢发膘了。今日清闲无事,何妨出去溜达溜达。”老残说:“好啊!自从庚子之后,北地胭脂我竟囗曾寓目,也是缺典,今日同行甚佳。”
说着便站起身来,同出了大门,过大街,行不多远,就到石头胡同口了。进了石头胡同,望北慢慢地走着,刚到穿心店口,只见对面来了一挂车子,车里坐了一个美人,眉目如画,面上的光彩颇觉动人。老残向东阁子道:“这个人就不错,您知道他叫甚么?”东阁子说:“很面熟,只是叫不出名字来。”看着那车子已进穿心店去,三人不知不觉的也就随着车子进了穿心店。东阁子嚷道:“车子里坐的是谁?”那美人答道:“是我。你不是小明子么?怎么连我也看不出来哪?”东阁子道:“我还是不明白,请你报一报名罢。”车中美人道:“我叫小蓉。”东阁子道:“你在谁家?”小蓉道:“荣泉班。”说着,那车子走得快,人走得慢,己渐渐相离得远了。
看官,你道这小蓉为甚么管东阁子叫小明子呢?岂不轻慢得很吗?其实不然,因为这北京是天子脚下,富贵的大半是旗人。那旗人的性情,最恶嫌人称某老爷的,所以这些班子里揣摩风气,凡人进来,请问贵姓后,立刻就要请问行几的。初次见面,可以称某大爷,某二爷,汉人称姓,旗人称名。你看《红楼梦》上,薛蟠是汉军,称薛大爷,贾琏、贾环就称琏二爷、环三爷了,就是这个体例。在《红楼梦》的时候,琏二爷始终称琏二爷,环三爷始终称环三爷。北京风俗,初见一二面时称琏二爷、环三爷,若到第三面时,再称琏二爷、环三爷,客人就要发膘闹脾气,送官、封门等类的辞头汨汨的冒出口来的,必定要先称他二爷、三爷才罢。此之谓普通亲热。若特别的亲热呢,便应该叫小琏子、小环子。汉人呢,姓张的、姓李的,由张二爷、李三爷渐渐的熬到小张子、小李子为度。这个道理不但北方如此。南方自然以苏、杭为文物声明之地,苏、杭人胡子白了,听人叫他一声“度少牙”,还喜欢的了不得呢。可见这是南北的同情了。东阁子人本俊利,加之他的朋友都是漂亮不过的人,或当着极红的乌布;或是大学堂的学生;或是庚子年的道员,方引见去到省;或是汇兑庄的大老板。因为有这班朋友,所以备班子见了他,无不恭敬亲热,也无人不认识他,才修出这“小明子”三个字的徽号,在旁人看着,比得头等宝星还荣耀些呢。
闲话少讲,却说三人慢慢地走到了荣泉班门口,随步进去,只听门房里的人“嗥”的叫了一声,也不知他叫的是甚么。老残便问,东阁子答道:“他是喊的‘瞧厅’两个字,原是叫里面人招呼屋子的意思。”三人进了大门,过了一道板壁腰门,上子穿堂的台阶,已见有个人把穿堂东边的房门帘子打起,口称:“请老爷们这里屈坐屈坐。”三人进房坐下,看墙上囗囗,知是素云的屋子。那伙计还在门口立着,东阁子道:“都叫来见见!”那伙计便大声嚷道:“都见见咧!都见见咧!”只见一个个花丢丢、粉郁郁的,都来走到屋门口一站,伙计便在旁边报名。报名后立一秒钟的时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去了。一共来了六七个人,虽无甚美的,却也无甚丑的。伙计报道:“都来齐了。”东阁子道:“知道了,我们坐一坐。”老残诧异,问道:“为何不见小蓉?”东阁子道:“红脚色例不见客,少停自会来的。”
约有五六分钟工夫,只见房门帘子开处,有个美人进来,不方不圆的个脸儿,打着长长的前刘海,是上海的时装,穿了一件竹青摹本缎的皮袄,模样也无甚出众处,只是一双眼睛透出个伶俐的样子来。进门便笑,向东阁子道:“小明子呀,你怎么连我也不认得了呀!你怎么好几个月不来,公事很忙吗?”东阁子道:“我在街上,你在车子里一幌……(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