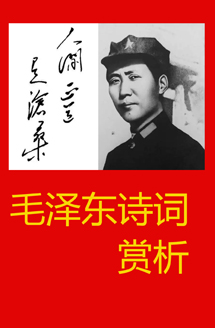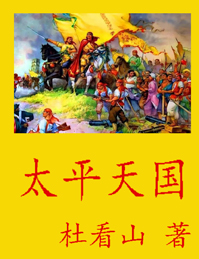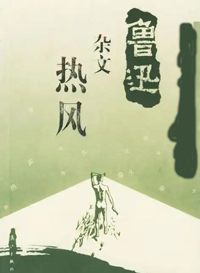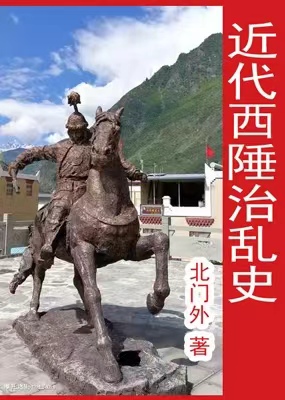二十一 大迁徙:盘庚迁都
伊尹之后,商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平淡无味的时期。史书里又是沉闷地记录历代商王的流水账,并没有很多故事,我在这里简明扼要提一下。
太甲在位时间共计十二年,他应该是个不错的君主,因此被尊为“太宗”。商代不像后世那么注意虚名,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尊号或谥号,只有特别杰出的帝王才有,因此能被称为“宗”的人是很少的。太甲之后一直到盘庚,其间的帝王分别是沃丁、太庚(《竹书纪年》称为小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祖乙、外壬、河亶甲、祖辛、祖丁、沃甲(《竹书纪年》称为开甲)、南庚、阳甲,共计十四位帝王。我们看商代帝王的名字很有意思,都包含有十天干的一个字,而且是最后一个字。这种命名法,在夏代就出现了,比如夏帝中有胤甲、孔甲等,但并不普遍,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命名。
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代帝王以“天干”为名字,其实对应的是他的生日。古代以天干地支纪年纪日,生日这天对应的天干是什么,就拿来当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这样还不够,遇到同样“甲”日出生的,如何区别呢?因此前面还要加一字来区分。譬如都是“甲”日出生的,有太甲、小甲、河亶甲、沃甲、阳甲等,尽管我们读起来很乏味,但毕竟有些许差别了。
从太甲到阳甲,商帝国并非一帆风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
第一,商帝国曾经几度中衰。
据《史记》载,到了商帝国第八任帝王雍己时,商帝国对诸侯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诸侯开始不来朝见。然而第九任帝王太戊重振雄风,恢复了帝国的威严。到了第十二位帝王河亶甲时,商帝国又一次衰弱,一直到第十四位帝王祖乙,又扭转局面,实现中兴。然而到了阳甲时,商帝国又一次衰败。
尽管史料含糊其辞,但我们大致对商帝国的历史有了个笼统的印象:几起几落,两度中兴。两位中兴之君分别是太戊与祖乙,他们也是商帝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两位帝王。我在前面说过,商代谥法制度刚刚兴起,但并不是每个帝王都有谥号,只有少数极其出色的帝王才有谥号。除了被尊为“太宗”的太甲之外,还有一位帝王被尊为“中宗”。中宗究竟是谁呢?
依《史记》的说法,中宗是第九任商王太戊,而后来出土的《竹书纪年》则明确地记录了第十四任商王祖乙才是中宗。究竟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法证明谁是谁非,直到殷墟甲骨文的出土,才彻底解开谜团。在一片刻有文字的龟甲上,写有“中宗祖乙牛吉”六字,在商代古文物前,真相浮出水面,祖乙才是真正的中宗!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是错的,《竹书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竹书纪年》在古史研究中具有其他书籍所不可企及的价值。
尽管在太戊与祖乙时有过两次短暂的中兴,但商帝国总体上在走下坡路,其中的原因在于内部争权逐利加剧。商帝国在继承人制度上,没有定法,经常弟弟继承哥哥的帝位,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又为争夺权力而大打出手,造成政治上的频频动荡。
第二,商帝国频繁迁都。
据《史记》所述,商最初的都城是亳,中丁时迁到隞,河亶甲时迁到相,祖乙时迁到邢。《竹书纪年》的说法与《史记》有不同之处,称中丁时迁到嚣,河亶甲时迁到相,祖乙时迁到庇,南庚时迁到奄。
依《史记》,商帝国迁都三次;依《竹书纪年》,迁都四次。后来盘庚把首都迁到殷,在《尚书》中的《盘庚上》中,曾提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就是说,盘庚之前,商帝国已经建过五个都城了,初都亳,后来迁都四次,总计是五都。由是对比,又足以印证《竹书纪年》的记录较《史记》更为精确。
如此频繁的迁都,在中国历史上诸王朝中并不多见,一方面这可能跟政局多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跟自然灾害的威胁有关。
盘庚是商帝国的第十九位王,也是商代非常重要的一位君主。他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把商都城迁到殷,这是商帝国最后一次迁都,一直到商灭亡为止,共计二百七十三年,结束了商代频繁迁都的历史。第二,他实现了商帝国又一次复兴。第三,他留下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也就是《尚书》中的《盘庚》三篇(有的版本合并为一篇),这是研究商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据《史记》述,这份文献是盘庚去世后,大家为纪念他迁都之功而追记的,可视为盘庚的思想记录。
在盘庚之前,商帝国已经迁都四次,迁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令民众苦不堪言。当盘庚决心第五次迁都时,可以想象会招到多大的反对,那么他为什么执意要迁都呢?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缺乏足够的资料去分析。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极少数的资料里去寻找蛛丝马迹。
首先我们看看盘庚登基时的历史背景。
《史记》中写道:“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从中丁开始,商帝国便频频陷入权力斗争,尽管其间祖乙曾有过短暂的中兴,但总体上内部政治混乱,派系斗争激烈,也失去了诸侯国的支持。盘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登上帝位,可以说,摆在他面前的,是先王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我们可以推测,刚刚上台的盘庚,地位并非安如泰山,一则要面对国内野心家的挑战,二则诸侯离心离德,这些诸侯曾是帝国的屏藩,保护中央政权免遭蛮族入侵。当诸侯拒绝效忠朝廷时,商王室不得不亲自组织军队抵御蛮族,中央政权表面上是天下至尊,实则孱弱。
还是回到原始文献《盘庚》三篇,看看盘庚本人是怎么回答迁都的问题的。
《盘庚》第一篇说到迁都的理由是:“重我民,无尽刘。”意思就是说,为了重视民众的生命,免得遭遇灭顶之灾。在第二篇中又说道:“殷降大虐。”就是说商帝国遭遇到巨大的灾难。
到底是什么灾难呢?史料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人认为是水灾,毕竟黄河一直以来水患频频,首都遭到洪水的威胁,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如果是水灾,那么对于都城奄的百姓来说,应该是司空见惯,不可能到盘庚时才有水灾啊。那会是某种极厉害的传染病吗?显然不可能,如果有这种传染病存在,不用盘庚下命令,大家早就逃得远远的了。最可能出现的灾难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蛮族的威胁,特别是来自西部蛮族的威胁。
我们来看一则史料。
《今本竹书纪年》里记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古本竹书纪年》则记为:“和甲西征,得一丹山。”和甲就是阳甲,他是盘庚的哥哥,也是前一任商王。我们对照《史记》中的记载:“帝阳甲之时,殷衰。”也就是说,商帝国在衰败之时,阳甲仍然发动了一场西征,讨伐丹山戎,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西部的戎人势力正在不断地增强,对商帝国的威胁越来越大。
明白了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盘庚所面临的困境:西部蛮族的势力正迅猛扩张;原本拱卫中央的诸侯不再听从调遣;国内政局混乱,已经“比九世乱”(《史记》语)。我想这时盘庚实际能控制的,可能只有帝国首都及其附近的一小块地盘而已。我们不知道盘庚执政初期,西部蛮族有没有发动大举进攻,但是商帝国已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却是事实。
此时盘庚的最佳选择,当然是把帝国首都迁移到东部,以避开西部蛮族的兵锋。但是倘若盘庚迁都仅仅只是退避,又谈何伟大呢?他的策略只是以退为进,先建立起一个稳固而牢靠的大后方,然后才能重振商帝国的雄风。我们从《盘庚》第一篇中可以看到这位新帝王的志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zhǐ,平定)绥四方。”
盘庚迁都的背后,是怀抱着伟大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复兴先王的伟大事业,安定四方。所谓安定四方,就是消除帝国内部的纷争,重新得到诸侯的支持,降伏蛮族部落,这是三位一体的事业。
然而盘庚始料不及的是,迁都计划遭到民众的广泛抵制。
这是可以理解的,盘庚迁都之前,商帝国的都城奄使用年限是很短的。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南庚三年,商朝都城由庇迁到奄,三年后,南庚去世。接下来的帝王阳甲在位时间仅仅四年便去世,盘庚继位,盘庚十四年迁都于殷。如此算下来,奄城作为首都的时间只有二十一年,年限很短。
大家想想,当年从庇迁都到奄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民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初修建奄都的那些人,多数应该尚在人世,又要面临新一轮的迁都,新一轮的筑城,这不是折腾人吗?
此时民众的沮丧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这对盘庚可是一个艰难的挑战。
不错,作为帝王,他有权发布命令,强迫民众迁都,然而这是有政治风险的。商帝国权力斗争的传统由来已久,觊觎王位者大有人在,若是他失却民心,可能会诱发政变的严重后果。怎么办呢?盘庚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迁都计划,又得说服民众,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
可是盘庚不愧是一名伟大的领袖,他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当时可没有电视广播这些东西,就算贴上布告,大家也未必看得懂,那个时代识字的人恐怕是稀有动物。他用了一个土办法,把王室亲戚、贵族们叫来,要他们上街向民众宣传迁都的必要性。可问题是,这些皇亲国戚中也有很多人不愿意迁都,叫他们出去宣传,他们会不会阳奉阴违呢?
盘庚对他们强调说:“你们不能把我规劝民众的话隐匿不讲。”
确实有一部分官员不仅没有向民众传达政府的政策,反而煽风点火,企图以民众的不满来阻止盘庚迁都。对此,盘庚愤怒了,他严厉地警告说:
“要是不把我的善言传达给百姓,那你们是自种祸根,干出祸害奸宄之事,是自取灭亡。若是诱导百姓做恶事,就得承担后果,到时你们追悔也来不及了。你们看看小民,他们还知道听从规劝的话,唯恐祸从口出,何况我还掌握着你们的生杀大权。你们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而擅自用无稽之谈蛊惑民众?如果爆发了动乱,就会像大火燎原一样,连靠近都不行,怎么扑得灭呢?倘若如此,是你们咎由自取,不是我的过错。”
最后,盘庚告诫道:“你们要把我说的话相互传达,自今往后,做好本职工作,尽到自己的职责,不要信口雌黄。否则的话,惩罚就会降落到你们头上,后悔也没用了。”
从这些话里面,可以看出反对迁都力量的强大,更可看出盘庚坚定不移的信念与铁的手腕。在盘庚的严厉警告下,原本阳奉阴违的官员不敢不认真执行命令,不然说不定哪天脑袋就搬家了。
他们向民众宣传什么内容呢?
主要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迁都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利益,免受巨大灾难的威胁。第二,占卜的结果显示旧都不适合居住,得迁新都。这里之所以要强调占卜的结果,是因为商代乃是最为迷信的时代,什么事都得占卜。第三,援引商代迁都的历史,说明这是顺应天命。第四,只有迁都才能重振先王的伟大事业,才能安定四方。
在政府执着不懈的耐心劝导之下,多数民众最后还是服从盘庚的命令,陆续渡过黄河迁往新都殷城。
仍然有顽固者,拒绝迁徙。
看来还得盘庚亲自出马才行,他把反对者邀请到王宫。这些百姓平常估计也难得见帝王一面,进到王宫之内,大家都毕恭毕敬。盘庚以极其诚恳而又不失严厉的语气对他们说:
“如今殷商面临深重的危机,先王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安心住在他们所建造的宫室里,而是只考虑百姓的福利,迁徙到更合适的地方。我现在所做的,正是先王们当年做的事。我是要保护你们,让你们生活更加安定,而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要惩罚你们。我呼吁你们都搬迁到新的都城里,这是为了你们,只要努力,一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我要求你们迁徙,是为了安邦定国。但你们却不能体恤我的苦心,不愿意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你们为什么不说出来,看能不能打动我的心呢?你们是自寻苦恼,这就好比乘船,你们把东西都搬上船了,却迟迟不渡河,岂不是要让这些东西发臭发烂吗?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们上了船,却不愿聚精会神,那么船就会被打翻而沉没。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延误时日,只知闷声生气,这样又有什么用呢?你们没有长远的打算,也不想去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们只顾现在,根本不考虑将来,这样还能指望上天救助你们吗?”
最后,盘庚说道:
“今天,我已经把自己不可动摇的决心告诉你们,你们要体恤我的良苦用心,君臣之间不要因疏远而产生隔阂。你们应该同心同德跟随我,不要受流言蜚语的干扰,在内心要有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至于那些为非作歹、放肆无礼、奸邪狡诈之人,我要视他们罪行的大小,施予劓刑乃至死刑,让他们断子绝孙,不让他们的后代在新的都城繁衍生长。到新的都城去吧,到那里开始新的生活。我现在就要带着你们迁徙,在那里将建立永久的家园。”
盘庚的这些话,先礼后刑、先恩后威。你想想,这些小民们进了王宫,原本就被帝王家的气势压矮了半截,现在盘庚大帝又这番苦口婆心外加大棒,大家还能说“不”吗?得了,看来不搬也得搬了。
在一片反对声中,迁都工作终于勉强完成了。对盘庚政府来说,这是一次大考验,倘若没有广泛的动员工作,迁都有可能酿成一起巨大的灾难。只要商朝的都城出现动荡,各种政治力量就会卷入这场旋涡之中,搞不好可能造成帝国的垮台。但是盘庚像一个老舵手一样,以巧妙而高超的手腕,化解了危机,让帝国之舟得以平稳靠岸。
盘庚迁都,并不是整个新都城全部建好才迁居,而是边迁边建,这显然与人手不够有关系。从这点来看,证实了我的猜测,盘庚时代,帝王的权力仅限于都城一带,否则盘庚完全可以动员全国力量先筑好城、修好宫殿后再搬迁。事实上,盘庚迁到殷地时,这里的基础设施仍很薄弱。据《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早在夏朝帝芒时代,商部落就曾迁居于此,因此在这里有一定的基础。不过作为新的都城,殷都需要建造更多的房子以供居住,这是很大的工程,也十分艰巨。
可以料想,许多人内心还是满怀怨恨的,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盘庚不敢松懈,他还要继续宣传鼓动,因此他把民众召集在一起,又发表了一番重要讲话:
“你们不要懈怠,要全力以赴完成伟大的使命。现在,我敞开心胸,把自己的志向告诉你们,我的百姓。我不会惩罚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人,当然,你们也不要怒气冲冲地联合起来诽谤我。”
“我的先王为了开拓事业,曾经迁徙到山上,以消除灾难,振兴国家。如今我的百姓流离失所,没有一个永久的居住地。你们也许会责备我说,为什么要扰动万千民众来迁都呢?我必须明确地回答你们,这是因为上帝要重振我高祖的事业,恢复我家族的荣光。我抱着笃敬之心,顺天承命,要把这个新的都城建成永久的
居住地。我年轻,经验也不足,并不是我不听众人的意见,迁都这件事,是经过占卜的,我不敢违背占卜的结果,这是天命,我们理应将其发扬光大。”
“各位方伯、大臣、百官执事,你们可能还有若干不满藏在心里,但你们要以恭敬之心为百姓着想,在这件事情上我要考察你们。对于那些贪财之人,我绝不会任用;对那些能为生民谋利、为民众谋求安居乐业的人,将赢得我的尊敬与提拔。今天我已经把心里话都告知你们了,希望你们不要置若罔闻。不要总想着发财致富,利民厚生才是伟大的功业,对民众要施行德政,这一点要永远铭记在心。”
从盘庚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雄心壮志。迁都对他来说,是重振商帝国雄风的第一步。他曾多次强调,这次迁都乃是一劳永逸,这里将成为永久的居住地。事实也是如此,一直到殷商灭亡,帝国之都再也没有变更过。这说明盘庚的眼光远大,择都的选址确实非常理想,以此终结了商帝国频繁迁都的历史。这也使得政府有了更大的精力放在治理国家上,解决各种危机与隐患。
根据《史记》的说法,盘庚迁都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继太戊与祖丁之后,盘庚实现了商帝国的第三次中兴,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各路诸侯又纷纷来朝。
盘庚在迁都之后,究竟做了哪些事,史料残缺。然而,商都东迁到殷,确实是商代的一大重要事件。正是因为政治中心稳固下来了,才有了商代后期灿烂的文明。
殷都位于河南安阳市的小屯村,中国历史上有众多都城,殷都是考古发现中确认证实的最古老的一座都城。殷墟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殷商的器物文明也浮出水面。在此之前,甚至有学者怀疑商朝是否真实存在过?殷墟的发现,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在这里发现了商代大规模宫殿宗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上面所刻的文字有四千多个,现今能辨认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
出土的殷墟青铜器可谓是商代器物文明之代表作,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后来称为“后母戊鼎”),重800多公斤,几近一吨,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梁漱溟先生称中国之文明乃是早熟之文明,岂虚言哉?当世界多数地区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之时,殷商就已经步入高度文明的阶段。尽管殷墟出土的文物并不出自盘庚时代,但若没有盘庚一劳永逸之迁都,创造稳固之政治基地,岂能有商后期之灿烂文化?故而盘庚实有再造殷商之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