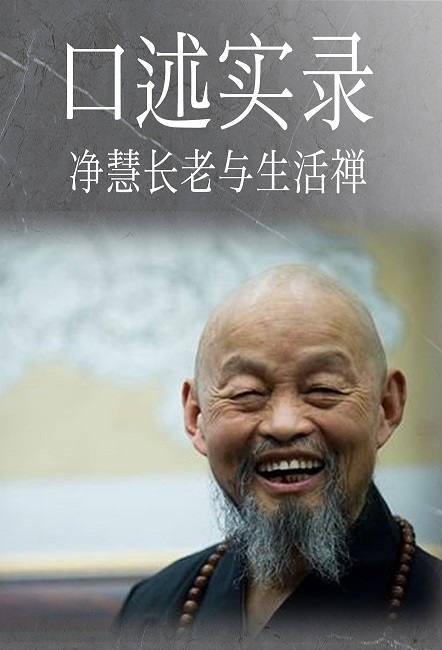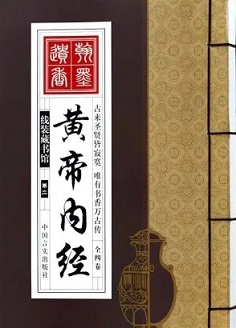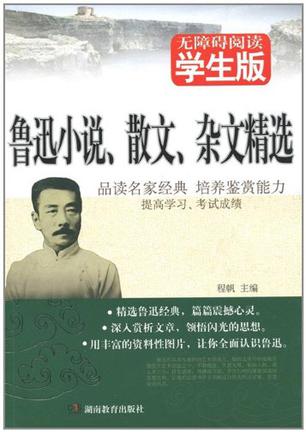三十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姬发东征,把纣王拉下马,为民除害,固然可拍手称快,但除害之后呢?是从殷商遗老中选立新帝,或者是取而代之?以诸侯的身份挑战帝王,这叫以下犯上,既已冒犯,就要一犯到底,推倒旧秩序,建起新秩序。
一个崭新的王朝破茧而出。
这便是周王朝。
纣王死后第二天,姬发正式称王。
这一天,在故殷商王宫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登基仪式。姬发乘坐一辆马车,拉车的是他弟弟叔振铎,周公旦手持大钺、毕公手持小钺分别站在他的两旁,大钺、小钺便是权力的象征。臣僚散宜生、太颠、闳夭等人手执宝剑,站在马车两旁,保护姬发的安全。
到祭祀上天的时候,主持仪式的卜者口中念念有词地说道:“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显闻于天皇上帝。”这是解释革命的合法性,宣布纣王的罪状。这时姬发向上天磕了两个响头,恭敬地接受天命:“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说完后又磕了两个响头。
这样,姬发成为周王朝的第一任天子,称为周武王。武王把父亲姬昌尊为周文王,姬昌虽然生前未称王,但周王朝的基业,实是由他奠定,他也是周王国的真正缔造者。文王的父亲季历被尊为王季,祖父古公亶父被尊为周太王。后世把周文王、周武王并列为最伟大的英雄,同尊为“圣人”。
有两个政治名词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维新。这两个词,与周王朝都有关系。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tuàn)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当然,这个意义,与现在我们说的是有区别的。古代把成汤推翻夏桀、周武王推翻商纣称为革命,乃是仁政推翻暴政,仁君推翻暴君,上应天理,下合民心。可以说,汤、武革命,乃是文明进步之体现。维新一词,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一个老诸侯,但其使命却是崭新的。
现在,周武王的革命成功了,接下来就是要做“维新”的事业。
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摆在周武王面前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殷商部众。
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周武王想听听诸臣的意见。他首先询问姜太公:“要如何处置战俘呢?”
姜太公是兵法家,又是谋略家,当然颇有雷霆手段,他回答道:“臣听说爱一个人,连他房屋上的乌鸦也爱;恨一个人,也不会喜欢他身边的东西。大王与商纣有深仇大恨,对他手下的那帮人,应该斩尽杀绝,您看怎么样?”
周武王摇摇头,答了两个字:“不可。”然后他又询问召公奭(shì)同样的问题。
召公奭回答说:“把有罪的人杀掉,把无罪的人释放,怎么样?”
周武王还是摇摇头,不认同召公的意见。
下面要看看周公旦怎么回答,因为在所有弟弟中,周武王是最欣赏周公旦,他的意见会不会跟自己相同呢?
周公旦回答说:“战争都已经结束,不如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耕作自己的田地。不论他是旧政府的臣民还是新政府的臣民,只要有仁义德行就能得到器重。如果百姓有什么过错,我作为政府的首辅,责任就由我一人承担吧。”
这一番话,让周武王大为赞赏,叹道:“你所说的话真是博大精深,可平天下矣。自古以来,士人君子之所以受到推崇,正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仁义道德。”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经常改朝换代,城头变幻大王旗,而每次政权交替之际,总是伴随着血腥的残杀。但是这种大规模屠戮,在商取代夏、周取代商时却没有发生。中国早期文化传统中,“仁义”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这也使得华夏文明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
这种仁义的观念有其产生的土壤,在夏、商、周三代,所有的天子,不过是邦联制的首领,中央帝国对诸侯国并没有绝对的权力,甚至在军事上也没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光凭恃武力者,难以服人,必须要辅以道德仁义,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是受到了诸侯们的权力制衡,有制衡的权力,自然不能为所欲为。而秦一统天下后,君王再也不受制于诸侯们的权力制衡,不受制衡的制度下,要帝王克己奉公当圣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周朝之后,帝王家再无圣人。
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接下来便是如何处置殷商王族。
在这方面,新兴王朝体现出罕见的宽宏大量。
除了纣王及其几个妃子外,殷室王族并未遭到大规模清洗。纣王死后,他的儿子禄父不仅未遭处决,还继续统治殷城,他也被称为武庚,只不过不再是帝国之王,而降格为普通的诸侯。当然,监视是必要的。周武王把两个弟弟——管叔姬鲜、蔡叔姬度——留在殷地,表面上是辅佐禄父,实际上则是殷地的实际统治者。
纣王的庶兄微子原本已经逃得远远的,周武王攻克殷都后,他担心族人的安危,遂返回殷城。微子手持祭器,脱了上衣,把自己绑起来,左手牵着一只羊,右手拿着一束茅草,跪着走路,前去见武王。这什么意思呢?羊与茅都是祭祀时用的东西,表示我把家族的命运交给你了。周武王当即把微子释放,官复原职,确有大政治家的胸襟与风范。
以前装疯又被纣王囚禁的箕子,也得以重获自由。
箕子与比干都是纣王的叔父,德高望重,学识渊博。如今新朝草创,能马上得天下之人,未必能马下治天下。周武王求贤若渴,亲自登门拜访,向箕子讨教治国之道。箕子做了长篇回答,后来被整理成文,收入《尚书》,这就是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在古代极受重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哲学、政治、卜筮等。在政治上,箕子推崇仁政与宽容,倡导王道,这些见解对周王朝的政策有一定的影响。
可是箕子毕竟是殷商遗臣,不愿意当周的臣民,也不想居住在殷这个伤心之城。虽然这时他已经很老了,可是仍然怀揣着一个梦想。他带着一帮殷商旧民,朝着东北方向而去,最后到了朝鲜。箕子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政权,史称“箕子朝鲜”,把中原先进文明传播到了这里,这也是朝鲜历史上的第一个政权。周武王把箕子的朝鲜国列为“不臣之国”,不必向周王朝称臣,表达对箕子的敬重。尽管如此,箕子也没有把自己的小国与周王国平起平坐。数年后,他前往周都朝见周武王,这也是对周武王宽宏大量的感谢。
除了善待前朝遗老之外,周武王也没有忽视殷民们的利益。以前被纣王拘捕的百姓,都被释放。纣王在鹿台库藏的大量钱财,在钜桥囤积的大量粮食,都分发给百姓,因为这些本来就是从百姓那儿搜刮来的。
武王还表彰了殷商几个已经去世的贤臣,他下令为名臣比干修建一座高大的坟墓,以示尊崇。另一位贤臣商容也得到褒扬。周武王在他家门前立了一块华表,以表彰其高尚的品德。这样做,无疑使殷民觉得光荣,脸上有光。
应该说,在处理殷商遗留问题上,周武王的做法是明智而谨慎的。正因为如此,避免了许多潜在的冲突,维护了前朝贵族与殷民的利益和面子。光凭这点来看,周武王便堪称伟大。因为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中,没有任何一个君王能像周武王一样善待前朝的王室,并给予他们相当多的特权与自主权。
此时周武王的感受一定颇似于当年的商汤,帝国建立起来了,但这只是开始,远非终点。当年周与八百诸侯能团结一心,乃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当敌人不复存在时,关系便悄然发生变化,当初的盟友,随时都可能成为新的敌人。任重道远啊,当权者能不慎乎?武王西归后,总是闷闷不乐,有时独自一人登上山丘,遥望殷邑的方向,默不作声。到了晚上,又时常难以入睡,秉烛沉思。
一天,姬旦见哥哥的寝室仍烛光摇曳,便入室问道:“为什么不睡觉呢?”
武王看了弟弟一眼,若有所思地答道:“我告诉你吧,我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纣王即位时,我还没有出生呢,从那时起,上天就抛弃殷商,到现在大概有六十年了。在这六十年里,殷商朝廷之上,奸臣当道,正人君子却遭放逐。正是因为上天不眷顾殷人,我们才能推翻他们成就今天的事业。想当年殷商建朝时,任用的贤人有三百六十人;可是后来,商王弃贤人不用,因此走向灭亡。现在我还没有完成天命,要做的事情还太多,哪有时间睡呢?”
谁说国君容易当呢?地位越尊崇,责任就越大。
姬旦听了哥哥这一番话后,非常佩服。这时武王又说道:“我要继续完成上天交给的使命,夜以继日地艰苦奋斗,以安定西土(即周的领地),把周所奉行的道义发扬光大。”
说实话,周武王是够勤政的,怪不得后世儒家人物都要对他竖起大拇指。既然要把德政进行到底,就必须做出表态:裁军!
要知道武王推翻商纣,武功盖世,现在他怎么要放弃“武力”呢?在他看来,“武”的含义,就是由“止”、“戈”两个字构成的,原来武力只是制止战争的手段。在伐纣之役中,武王的嫡系军队多达四万八千人,这当然不是常备军,而是为战争而征召的,如今殷商已灭亡,也不可能养着这么多军队。于是放战马于华山之南,放牛于桃林之野,把召集起来的临时军队解散,把干戈兵器藏入库中。
这是昭告天下:战争结束了,和平年代到来了。
从季历到文王再到武王,周的成长就是军事扩张的过程,如今天下初定,当务之急乃是休养生息。事实上,周武王并不过多忧虑军事问题,因为在伐纣之前,天下就有八百诸侯归附周,殷商灭亡后,周王室受到的外在威胁并不大。
他考虑的是另一个问题:迁都。
自古公亶父迁到岐下后,周有过两次迁都。第一次是西伯姬昌迁都于丰邑;第二次是武王迁都于镐京。但武王显然对镐京的地理位置不太满意,他要物色一块更适合的土地。为此,他考察了从三涂山到太行山一带的地形,确定了一块理想之地,位于洛水与伊水之间。周武王开始在此地筑城,这就是后来的洛邑,又称为雒(luò)邑。他甚至把象征国家权力的九鼎从殷邑迁往洛邑,可是迁都计划并没有实现,因为在灭商后六年(周武王十七年),这位新王朝的缔造者便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四岁。
周武王缔造的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王朝,尽管人们对它的兴趣远不及汉朝或唐朝。它是古代最长命的王朝,而且中国古代之核心思想,均奠基于周代,特别是东周时代(春秋战国),更是古代思想文化之登峰造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流派,皆创于此期,自秦以降到清,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学术可以媲美于周代,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谓的“早熟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