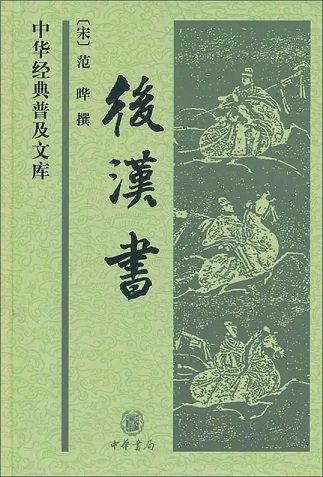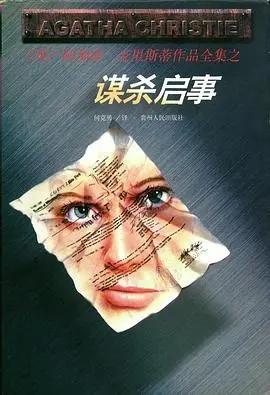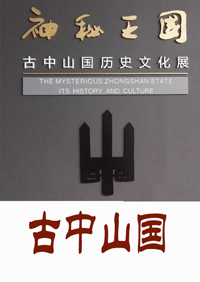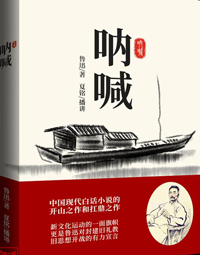六 齐国文姜乱伦杀夫事件始末
前几篇主要讲了郑庄公姬寤生,以及卫国(石碏)、晋国(祁奚)的事情,接下来把镜头摇向地处黄海之滨的齐国。
西周建立后,对姬姓宗室子弟大行分封,天下诸侯半数姓姬,而且都封到了肥地。比如周武王弟姬旦(即周公)封在鲁国、弟姬鲜封在管国、弟姬度封在蔡国、弟姬封封在卫国,周武王子姬虞封在晋国,即使是姬姓旁支召公姬奭也封在燕国。
姬姓之外也有许多分封,但无论是楚之熊氏、秦之嬴氏,都封在当时远离中原文明的边荒地区,算不上是肥封。在外姓诸侯国中,唯一自西周创建以来就算得上大国的,只有齐国。
说起齐国的首位君主,可以说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就是直钩钓来周文王,辅佐周武王灭商得天下的太公姜子牙!
姜子牙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用多介绍,可以说有多少人知道诸葛亮,就会有多少人知道姜子牙。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诸葛亮的千秋盛名,一部《封神演义》也成就了姜子牙的万古不朽之名。
如果说诸葛亮是蜀汉建立的第一功臣,姜子牙就算得上是姬周灭商的第一功臣,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这一点都没有太大的争议。套用现在的政治语言,姜子牙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在西周王朝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事业进程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基于此,武王灭商后,把姜子牙封在齐国,史称“齐太公”。这位齐太公将自己丰富的政治智慧运用到齐国的政权建设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从姜子牙到春秋初期,传了十三代齐侯,齐国几乎没有闹过太大的动静,但情况到了齐僖公姜禄甫(也称“齐釐公”)发生了变化。姜禄甫即位于公元前730年,卒于公元前698年。在姜禄甫统治时期,他经常跟着春秋小霸姬寤生在江湖上来回蹚,也混出了一些知名度。郑庄公姬寤生“春秋小霸”的盛名在外,实际上与姬寤生同时代的还有一个春秋小霸,就是齐僖公姜禄甫。
姜禄甫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后世记住他,不是因为他的所谓春秋霸业,而是他那几个成为“人中龙凤”的儿女。这几位活宝把本来好端端的春秋历史搞得乌烟瘴气,一地鸡毛,其荒唐、荒谬程度比周郑交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姜禄甫生有一个儿子,就是日后继承君位的齐襄公姜诸儿,以及两个女儿:宣姜、文姜。宣姜的故事特别精彩,先嫁给卫国太子姬伋子,但被在位的卫宣公姬晋看中,强行抢过儿媳妇,立为夫人。一千三百多年后的唐玄宗李隆基强抢儿媳妇杨玉环做情人,其实不过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因循故事而已。
宣姜抛弃丈夫,转投公公怀抱,后来又嫁给了宣公的儿子姬顽,生下一堆女儿,已经让人惊掉了下巴,但她的妹妹文姜的乱伦“事业”比她更上一层楼,“事迹”也更为惊人。宣姜乱伦只是在外姓父子,而文姜乱伦则是和自己的亲哥哥姜诸儿!
姜禄甫真是前世修来的好福分,两个宝贝女儿在嫁为人妇后,大搞乱伦八卦。说来奇怪,但凡是姜氏诸侯国的宗女嫁到国外后,几乎都闹出过大动静。除了武姜没有乱伦及私通外,其他诸姜几乎都有,比如宣姜和卫宣公父子、文姜和兄长齐襄公、哀姜和丈夫的兄长庆父、齐姜与晋献公父子。
关于哀姜的精彩故事,会在《春秋名女篇》中进行讲述,现在先讲一讲文姜的风流韵事。
我们都知道文姜后来嫁给了鲁桓公姬允,成为鲁国国母。实际上文姜在姬允之前,是许过婆家的,只是后来被准夫婿退了货,这才转了二手,去了鲁国。
文姜的准女婿名叫姬忽,姬忽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但姬忽的父亲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大人物,就是前几篇的主人公——郑庄公姬寤生。姜禄甫之所以要把女儿嫁给郑国公子,应该是他看到郑国国势如日中天,而姬忽将来会继承郑国君之位,所以想把女儿嫁给姬忽,提前在郑国内部插个钉子。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姬忽决定放弃这门亲事,理由是郑是小国,齐是大国,他高攀不上,这就是著名成语“齐大非偶”的由来。以当时齐郑两国的国力来看,郑国绝不逊于齐国,姬忽说齐强于郑不过是个借口。
推测一下,姬忽悔婚,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已经风闻到了文姜和其兄姜诸儿之间的“闺房秘事”。被扣了绿帽子的姬忽不想娶进这个扫把星,一怒之下放弃了文姜。
郑国退掉了婚事,总要给女儿寻个婆家,姜禄甫把主意打到了邻居鲁国的头上,鲁国君主就是鲁桓公姬允。这位鲁国第十五位君主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本是鲁隐公姬息姑的弟弟,为了夺得君位,与公子翚合谋,一刀做掉姬息姑后,姬允大模大样地继位。
文姜色艺双绝,却被退货,而姬允对文姜却非常中意,你不要,我要。公元前709年,姬允亲自跑到齐国,和姜禄甫在嬴(今山东莱芜附近)碰头,商量迎娶文姜过门事宜。
文姜和兄长姜诸儿暗中保持情人关系,作为父亲,姜禄甫应该是知道的,但家丑不可外扬,与其让齐公室蒙羞,成为天下人的笑柄,不如趁早拆散这对野鸳鸯。齐鲁双方达成协议后,公子翚以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代表姬允去临淄迎娶文姜。
按当时礼制,国公的同生姐妹出嫁外国,应该由该国上大夫陪送,如果是国君之女,则由下大夫陪送。而文姜出嫁鲁国,却是由姜禄甫亲自陪送的,此举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姜禄甫和姬允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能肯定的是,姜禄甫不会把儿女乱伦的事情告诉女婿,否则老脸往哪儿搁?
从历史记载来看,姬允是非常疼爱文姜的,夫妇二人和敬有礼,举案齐眉,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婚后的第四年(前706)九月,鲁公夫妇的第一个儿子来到人间。因为儿子和自己的出生日期相同,所以姬允给儿子起名为姬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鲁庄公。
如果生活能这样平淡而幸福地过下去,对文姜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她和兄长之间的那段感情太不正常,从姜诸儿那里,她能得到肉体与灵魂的双重快感,但她不会感受到夫妇和敬的快乐。这段感情一直处在地下,会对文姜的性格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进而变得压抑,甚至发生扭曲。
自嫁到鲁国后,文姜就和兄长很少有机会接近了,时间会冲淡曾经的海誓山盟,文姜也应该断了对兄长的非分之想。但当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十二月二日,父亲姜禄甫去世、兄长诸儿即齐侯位的消息传到曲阜时,文姜仿佛感觉到了冥冥之中,她和兄长之间又将要发生什么。
爱情就像鸦片烟,一旦上瘾,根本拔不出来,文姜就是如此。她和兄长之间的“爱情”故事,经历了十多年的沉寂,文姜对乱伦的欲望不但没有转淡,反而越来越强烈。恪守妇道十年,对文姜来说只是火山爆发前可怕的寂静。
鲁桓公十五年(前697),姬允和自己的大舅哥姜诸儿在艾(今山东莱芜东)举行齐鲁领袖级会谈,商谈的议题是如何平定许国之乱。史料并没有记载文姜是否跟着丈夫去见兄长,从后来鲁大夫申需的劝谏来看,文姜应该没有出行。但姜诸儿不会忘记这个和自己曾经有过一段不伦之恋的妹妹,与姬允的谈话中,姜诸儿有可能会向姬允询问妹妹的近况。
姜诸儿想妹妹想得眼都绿了,但礼法森严,春秋时规定“男女之别,国之大节”,姜诸儿也不敢轻易逾制。思念是一种无解毒药,越想越难受,简直如百爪挠心。如何能让姬允带着妹妹来见自己,这是摆在姜诸儿面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是姜诸儿的刻意安排,在他即位后的第三年(前696),姜诸儿准备迎娶周庄王姬佗(周桓王姬林的长子)的妹妹做夫人。然后,姜诸儿以此事为借口,请鲁公姬允来齐国替他主婚。
如果是国家公事,姬允可以不带夫人前来,但这是个人私事,又是姬允的大舅哥结婚,于情于理都应该带上文姜。但从鲁国大臣强烈反对文姜赴齐的态度上来看,姬允本人似乎并不想带文姜去齐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大夫申反对的理由非常明确:“女人嫁夫,男子娶妻,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不再有私相往来,这是礼法的规定。如果国君执意带夫人前去,必生祸乱。”细测申的话,估计申已经知道文姜和姜诸儿之间的精彩故事,就差直接把话挑明了。
姬允不是傻子,申的话中话,他当然听得出来,但姬允最终还是带文姜去见姜诸儿。个中原因,《左传》没有交代,《公羊传》和《穀梁传》对此事却有一些记载。从其中的蛛丝马迹不难看出,姬允此行,基本上可以认定是被文姜“绑架”过去的。
如果按传统惯例,姬允偕夫人出行,应该写成“公与夫人姜氏如齐”,文姜的地位应该低于丈夫。而《公羊传》、《穀梁传》均记载为“公、夫人姜氏遂如齐。”把文姜放在此句记载的主体地位,与姬允并列,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个“遂”字用得很巧妙,“遂”的字面意思是“终于能”,姬允以鲁公身份去见齐侯很正常,用不着做什么努力,这只是说明特别想见姜诸儿的正是文姜本人。
《穀梁传·桓公十八年》还有这么一句话:“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意思是文姜处事霸道,对鲁公傲慢无礼。《穀梁传注疏》也记载“夫人骄伉”,说明姬允已经失去了对文姜的控制。文姜在私下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强迫老公带她去齐国,姬允应该是反对过,但没有成功。
姬允想必已经知道了文姜和姜诸儿那些拎不上桌面的风流故事,他明知道此行去见姜诸儿,难保文姜不会旧情复发,再和姜诸儿乱搞一腿。但来自文姜的压力又让姬允感到窝火,同时又无可奈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什么事情都不要发生,好去好回。
姬允与姜诸儿会面的地点在泺(今山东济南西北),虽然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完全可以推想出,当姜诸儿和文姜见面的时候,二人的心中会激荡出怎样的浪花。这就好比妻子带上丈夫去见旧情人,妻子当着丈夫的面对旧情人投怀送抱,把一顶绿帽子扣在丈夫的脑袋上。丈夫成了电灯泡,燃烧自己,照亮情敌,这是多么让人尴尬和愤怒的事情。
当姬允意识到此行带文姜是个巨大的错误时,错误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应了那句老话,“该来的,迟早会来”,躲是躲不掉的。有一次,文姜外出,虽然理由千奇百怪,但姬允知道她是去干什么的。果然兄妹二人一见面,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立刻宽衣解带,红绡帐中成了好事。
对于一个已婚男人来说,野男人和自己的老婆通奸,是件极伤尊严的事情,没有哪个正常的男人愿意戴绿帽子。姬允对文姜本来抱有希望的,他希望文姜能悬崖勒马,戒掉“毒”瘾,好好跟他过日子。
文姜带着双重满足回到姬允的驻地时,已经忍无可忍的姬允,对着坐在铜镜前自我欣赏的文姜大发雷霆,咆哮之声震动屋瓦。维系夫妻感情的最重要纽带,就是忠诚,特别是在男权社会里高端女人对感情的背叛,必然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直接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
虽然姬允得国不正,但他对文姜的感情确实是非常真挚的,当年姬允接纳在江湖上几乎无人问津的文姜,从某种角度讲,是在拯救文姜。不过文姜从来没有这么认为,她甚至认为是姬允破坏了自己和兄长的甜蜜爱情。如果让文姜自己选择的话,她一定会选择留在齐国,与兄长长相厮守。
正是出于这种心态,文姜对姬允毫无好感,更多的是憎恶。在文姜的潜意识中,兄长才是她的丈夫,此生最可托付的人,姬允不过是个同床的路人。姬允冲着文姜发脾气,不但不能改变文姜的执迷不悟,反而激化了文姜对他的这种憎恶之情。对姬允怀恨在心的文姜在丈夫那里挨了骂,转身就去找她的姘头姜诸儿,把自己受的“委屈”全都倒了出来。
历史上还有一个相似的例子,就是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和自己的姑妈刘英媚之间的乱伦故事,刘子业为了长久霸占姑妈,毒死了姑父何迈。但刘英媚深爱自己的丈夫,对自己和侄子的乱伦深以为耻,只不过畏于强权,不敢反抗而已。
相比之下,文姜的行为尤为恶劣,这是一出红杏出墙被揭穿后,对受害者反攻倒算的人伦闹剧。为了捍卫她所谓的爱情,她不惜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酿出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变局。
话题再回到姜诸儿身上。老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文姜再怎么折腾,如果没有姜诸儿的配合,事情也不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姜诸儿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堂弟公孙无知钩心斗角,最终导致齐国大乱,二公子争位,齐国差点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以姜诸儿的地位,什么样的女人他得不到?偏偏喜欢自己的同胞妹妹。以姜诸儿的本意,如果不是封建礼教所束缚,他都敢立文姜为夫人,这种事情他绝对能做得出来。
和文姜一样,姜诸儿对姬允也有一种莫名的憎恶,他始终把姬允当成自己不共戴天的情敌。正是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推动下,再加上文姜的哭诉,让姜诸儿咬牙决定:做掉姬允,然后和文姜做一对长久的露水夫妻。
姜诸儿明知道杀掉姬允会引发不可预知的外交麻烦,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原因应该有二:
一、他深爱着自己的妹妹,不能容忍妹妹受“欺负”,虽然明明他勾搭人妻在前。
二、自持齐国实力强大,杀掉姬允,鲁国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
特别是第二点,是姜诸儿敢于下黑手的主要原因,自古强权即真理,有了枪杆子,即使所有人骂自己,又能改变什么?郑庄公姬寤生与天子交恶,甚至箭伤天子,依然不影响郑国的小霸事业。
自古杀人有罪,但强者无罪,出于这种考虑,姜诸儿理直气壮地干起了这票杀人买卖。其实这个故事的情节很老套:淫妇不喜欢自己的丈夫,和姘头密谋,杀死丈夫。
我们都知道名著《水浒传》中有西门庆和潘金莲谋杀武大郎的精彩故事,施耐庵以他的如花妙笔,把这段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是《水浒》最经典的桥段之一。对比一下,不难发现,西门庆、潘金莲谋杀武大郎,几乎就是全盘照抄姜诸儿、文姜做掉姬允的情节。唯一不同的是,在这两场情杀案中,文姜主动出手谋杀亲夫,而潘金莲则是被动地谋杀亲夫。潘金莲淫则淫矣,但未必毒辣,文姜则是“五毒俱全”。
西门庆很狡猾,他虽然策划谋杀,却是唆使潘金莲给武大郎灌下毒药,而姜诸儿干脆亲自披挂上阵,置亲夫姬允于死地。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94年四月十日,姜诸儿打着国宴的幌子,请姬允赴宴。
当时没有“鸿门宴”一说,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姬允此次赴宴,肯定与文姜乱伦一事有关系。不过姬允虽然想到了文姜会把自己发脾气的事情捅给姜诸儿,但他不相信姜诸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自己下毒手。
姬允对姜诸儿和文姜的性格都不是很了解,这对“奸夫淫妇”为了他们所谓的爱情,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而且姬允也忘记了当年自己是如何杀兄夺位的,他自己做事心狠手辣,却希望别人发善心,岂非荒唐。
这场“鸿门宴”的结局没有任何意外,姜诸儿先是用甜言蜜语打消姬允的戒防心理,然后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把姬允忽悠得找不着北。等姬允醉得不省人事时,姜诸儿给守候在旁边的大力士彭生递了个眼色。彭生心领神会,把如同一摊烂泥的姬允抱进了鲁国公的专用马车,在车上,彭生“拉杀”了姬允,就是折断肋骨,姬允惨叫吐血而亡。
奸夫姜诸儿一直在不远处等待着彭生的好消息,而淫妇应该不在现场,但以她对姬允的刻骨仇恨,当她得知姬允的死讯时,可以想象得到她的庆祝方式是何等的夸张。
姬允的死,也就意味着姜诸儿可以和文姜长相厮守了,但来自鲁国强大的外交压力,也迫使姜诸儿不得不做出一些虚假的姿态,以缓解鲁国的愤怒。打手彭生为主人办完了事,还没来得及数赏钱,就被姜诸儿杀掉了。
杀彭生,是鲁国对齐国提出的唯一要求。鲁人知道桓公之死,是姜诸儿的杰作,但慑于齐国强大的实力,鲁国不敢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只好退而求其次,杀彭生泄愤。
鲁国突遭这种弥天大祸,而天下皆知桓公的死因,如果不对齐国施加一点压力,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混迹?这就是鲁人所说的“无所归咎,恶于诸侯”。
姜诸儿远比西门庆幸运,因为他是大国之君,鲁人奈何他不得。西门庆虽然在阳谷县势力大,但奈何武松是个愣头青,一刀就把他宰了。而文姜之所以没有落得潘金莲身首异处的下场,原因有二,一是她背后站着齐侯姜诸儿,二是因为她是新任鲁公姬同(即鲁庄公)的亲生母亲。
特别是第二个原因,虽然姬同痛恨自己的母亲,断绝了母子关系,但在文姜回到鲁国办事期间,姬同并没有加害母亲。估计是文姜受不了儿子的冷眼,在鲁庄公元年的三月,文姜裹着金银细软,乘车狼狈逃回齐国。
如果唯心一些讲,鲁桓公姬允的被杀,不过是在为当年他杀害隐公还冥债,也算得上“死有余辜”,但鲁国世系自桓公以下,皆是姬允的子孙。所以鲁国史家对文姜杀害桓公一案耿耿于怀,极力将文姜描绘成一个万恶不赦的淫妇。
《左传·庄公二年》记载文姜在榚(今山东长清西)幽会时,用了一个特别刺眼的“奸”字。《左传》作为一部正史,书中却记载了大量社会上流人物的八卦故事,如婚外恋、养小三、兄妹乱伦、公媳乱伦,甚至还有祖母和孙子的乱伦。
作为最有名的春秋八婆之一,文姜的“精彩故事”让后人惊叹,《左传》自然不肯放过这个绝好的题材。何况文姜和鲁国有世仇,自然会极尽丑化之能事。文姜和姜诸儿的每次幽会,《左传》都会记录在案。
从鲁桓公被杀,到姜诸儿后来在齐国内乱中被杀,前后相隔八年。在这八年中,《左传》共记录文姜和姜诸儿幽会五次,每次记载都笔带辛辣,极力挖苦。这一次记载文姜邀请姜诸儿共赴宴会,共享二人甜蜜世界,下一次记载文姜窜到齐国军队中见齐侯通奸。
历史是男人写的,特别是封建礼教极为森严的春秋时期,文姜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当时人共同遵守的行为约束,她在史书被抹黑也就不足为怪。“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文姜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是她自找的,不值得同情。
路是自己走的,坑是自己跳的,怨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