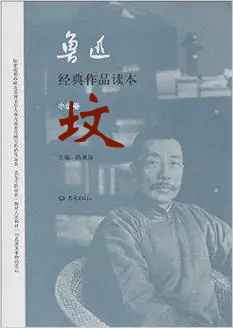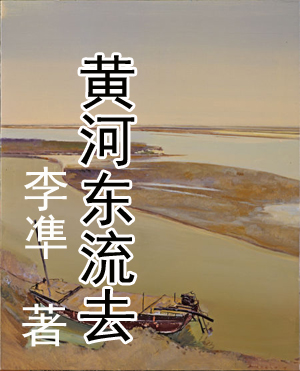五〇 《诗经》的魅力(下)
《诗经》中多以民风诗为主,反映孝道的作品不多。但其中有一篇,论艺术感染力,论给人们带来的心灵震撼,论催人泪下的程度,在诗三百中都是首屈一指的,就是《诗经·小雅·蓼莪》。
全诗如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罍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谷,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谷,我独不卒!
《蓼莪》有一点特殊之处在于,虽然这首诗是孝子感念父母养育之恩,但该诗的立意主旨,却是控诉统治者的残暴。通过此诗来展现一个孝子浓浓的思亲之情,所以后世作注者多把此诗归入讽刺诗,比如《毛诗》就说《蓼莪》“刺幽王也”。
故事的情节并不复杂,《蓼莪》讲的是一个农家孩子被官府征兵入伍,不得不离开父母,去异地服役。后来从家乡传来噩耗,父母已经亡故,士兵站在河边,看着随风摇荡的芦苇,哭诉着对父母的思念,以及未能在二老面前尽孝的自责。这首诗行文流畅,感情真挚,感人肺腑,非大手笔不能出此。
《蓼莪》没有用太多的情景铺垫,就直接切入思念父母的正题。前两段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生我劳瘁”。我们会联想到一个场景:白发苍苍的父母,腰弯背驼,在烟熏火燎之间品尝着生活的艰辛。
孩子长大后,会因为各种原因抱怨父母。我们总认为向父母索取是天经地义的,但我们很容易忽略父母把我们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是何等的不易。有句话说得好:“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等孩子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后,会更深刻地体谅父母的辛苦。
第三段是讲对父母离世的彻入骨髓的痛,“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接下来紧跟一句:“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看着让人心酸,父母都不在了,无依无靠的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
经过前面的铺垫,诗人的感情越来越饱满,情绪越来越激动,高潮即将到来。
第五段是《蓼莪》最精彩的段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这一段并没有用直白的感情抒发,而是客观描述士兵还在襁褓的时候,父母抱着他的场景,可谓字字深情,情感表达反而更加强烈。
如果换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生下我,母亲抚养我,你们爱我养我,抚养我长大,教我做人,出门抱我。”天下的父母之爱是相通的,不论古今中外。除了一些不幸的婴儿,大多数人都被母亲柔软温暖的身体抱过,能嗅到母亲身上那股深沉而博大的母爱。
当士兵流着眼泪讲完他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时,突然情绪失控,仰天哭喊“我想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可他们现在在哪里!苍天可恨!”虽然后面还有两段,但感情已经基本平复,算是给这首感情饱满真挚的孝亲诗实现了软着陆。
历代诗评家对《蓼莪》的评价极高,其中以清晚期的诗评家方润玉的评价最有代表性,方润玉在《诗经原始》卷十一中,称《蓼莪》是“千古孝思绝作,尽人能识”。甚至可以这么说,《蓼莪》在历代孝亲诗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三国演义》在通俗小说中的地位,当得起开山鼻祖。
一向提倡孝道的孔子对此诗极为推崇,说“于《蓼莪》见孝子之思养也”。自此之后,“蓼莪”也成为孝子的别称,后世许多诗人都在自己的诗篇中用到了“蓼莪”一词,比如在曹植的五言诗名篇《灵芝篇》中就写道:“蓼莪谁所兴。念之令人老。退咏南风诗。洒泪满袆抱。”唐人牟融在《邵公母》中也饱含深情地歌颂母爱的伟大,“伤心独有黄堂客,几度临风咏蓼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著名孝子故事集《二十四孝》中,也有“蓼莪”孝子的一席之地,就是著名的“王裒闻雷泣墓”,排在《二十四孝》最后一位。
王裒是魏晋人,其父王仪是司马昭属下司马,因事被司马昭杀害。王裒痛恨司马昭,终生不为晋臣,在父亲墓前筑庐教书。每天早晨和傍晚,王裒都要给父亲扫墓,跪在墓前痛哭流涕,泪水淹湿了墓前的树木,树为之枯死。
后来母亲病故,因为母亲惧怕雷声,每次天空打雷,王裒都来到墓前对着天空大喊:“有儿在此,阿母莫惊。”因为思念父母过度,王裒每次读到《诗经·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的时候,总会情绪失控,失声痛哭。学生们担心老师的身体,以后读书时就把《蓼莪》删掉了,以免刺激到老师。
王裒的孝思是天生的,并非刻意做作,以至于连性命都不要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家族成员纷纷逃到江南避难,王裒不忍抛弃父亲墓舍,号啕不去。后来乱兵闯到墓前,王裒动了逃跑的心思,但最后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遂为贼所害”。
除了《蓼莪》,《诗经》中还有一篇悲恋父母的孝亲诗,就是《国风·唐风·鸨羽》。《鸨羽》和《蓼莪》的结构形式大体相同,都是孝子在边疆服兵役,而且起句皆借物言志。士兵看到天上飞翔的鸨鸟,联想到自己的父母在家无依无靠,泪如雨下,悲愤地痛斥统治者的贪婪残暴:“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情义真挚,同样感人至深,只不过《鸨羽》没有过多地铺开讲述孝子之思,从艺术感染力上比《蓼莪》弱了许多。
说完了《小雅》,我们接着讲《风》。
关于《风》与《雅》、《颂》在歌颂形式上的区别,宋人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认为“风土之音曰风”,而《雅》是朝廷音,《颂》是宗庙之音,换言之,《风》是属于民间的。
《风》的正式名称其实是《国风》,顾名思义,“国”就是周朝分封的诸侯,按朱熹的解释,“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泳歌,各言其情者也。”这个解释和郑樵是相近的。
《国风》共分为十五个部分,即十五国之歌风,为《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一百六十首诗。
还要讲两个问题,一是作为西周和春秋前期的重要国家,《国风》中为何没有鲁风和宋风。其实鲁国和宋国并非没有作品入选《诗经》,而是都放在了《颂》的部分里,鲁歌称为《鲁颂》、宋歌称为《商颂》。
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宋国是商殷子姓后裔,受周朝礼待,可以用天子礼乐。鲁国是周公姬旦之后,王国维说鲁国“亲则同姓,尊则王朝”,所以鲁国和宋国的地位较高,得以进入《颂》,与《周颂》并列。这就相当于司马迁著《史记》,把项羽放进了本纪,把孔子放进了世家,以显示他们与众不同的历史地位。
第二个问题,《国风》为何没有楚风和晋风,而楚晋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实际上《唐风》就是《晋风》,因为晋国的开国始祖姬叔虞本来封在唐国,后改名为晋。
关于楚风,实际上就是《周南》和《召南》二篇,“二南”文学覆盖的范围大致在长江流域和汉水流域,和楚国的统治区域基本重叠,近人胡适就坚持这个观点。“二南”在《诗经》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排在各篇之首,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关雎》就是《周南》第一篇。
《国风》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四诗中最高的。《小雅》虽然尽可能地接了地气,但毕竟是用士大夫的眼光往下看,有时难免带有一丝清高,更注重于写作技巧。
《国风》是民歌合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方面生活形态,真实、纯朴、质朴,没有过于精细的雕琢,更注重原生态的释放。《国风》堪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百科全书,大致可以分为感情生活类、社会劳动类、讽刺官府类、歌颂英雄类。
感情生活类,这类在《国风》中的比重最大,相关诗章有《桃夭》(女子出嫁)、《汝坟》(思念远方的丈夫)、《女曰鸡鸣》(夫妻的和谐生活)、《野有死麋》(男女幽会)、《绿衣》(悼念亡妻)、《木瓜》(恋人互赠礼物)、《狡童》(恋人之间产生小矛盾)、《风雨》(夫妻久别重逢),等等。
我们都知道,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也维系着人类生存繁衍的重大使命,甚至有人说没有爱情的诗篇是灰暗的。打开这些情诗篇,扑面而来是的一股带有远古质朴气息的真实,虽然相隔两千多年,依然感觉那么的亲切。
《小雅》中有几篇爱情诗,但从影响力上讲,《国风》的爱情诗更胜一筹,有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关雎》就不用多介绍了,小学生都能张口即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面讲讲几首知名度不如《关雎》,但艺术魅力同样精彩的爱情诗篇。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日惭疏远,特别是婚姻,“七年之痒”,几乎成了夫妻谈虎色变的名词。其实婚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婚姻的不自信,只要双方相敬如宾,忠于对方,就不会出现什么危机。婚姻危机,往往都来自背叛。说到夫妻和睦,我们会想到东汉梁鸿和妻子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其实要说文学作品第一例反映夫妻生活和谐的,当属《诗经·郑风·女曰鸡鸣》。
与其说《女曰鸡鸣》是首诗,不如说它是一副动态的家庭生活组画,语言生动,画面感很强。《女曰鸡鸣》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对夫妻一天的幸福生活,恩爱礼敬,让后人羡叹不已。全诗如下:
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的开头其实是夫妻刚睡醒的一段有趣对话,看到丈夫还在呼呼大睡,妻子摇醒了丈夫,然后指着窗外说道:“该起床了,鸡都打鸣了。”丈夫似乎还没有睡醒,揉着惺忪的双眼,反驳妻子:“你胡说什么呀,没看到天上的启明星灿烂吗?再让我睡一会儿。”妻子很可爱,她在床上做了一个射箭的动作,然后撒起娇来:“早点起来吧,一会我们到外面打几只野鸭子,改善一下伙食。”
看来丈夫已经答应了妻子的请求,妻子依偎在丈夫怀里,用轻柔的声音告诉丈夫:“等你把野味打来后,我下厨做菜,再给你准备一壶好酒。我愿意和你共品美味,共享幸福人生。我弹琴,你鼓瑟,歌唱美好的生活,就这样我们一起牵着对方的手慢慢老去。”
这对夫妻家境并非大富大贵,丈夫的职业应该是以打猎为生,生活质量并不高,但幸福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更重要。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副场景:丈夫哼着小曲,拎着野鸭回家,妻子轻轻扑打丈夫衣服上的灰尘,然后把野味拿到厨房,丈夫在旁边打下手。夫妻有说有笑,什么叫幸福,这就是幸福。
讲完《郑风·鸡鸣》,再来讲一下《齐风·鸡鸣》。二者的结构基本相同,都是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夫妻在床上的对话,但《女曰鸡鸣》洋溢着夫妻恩爱的幸福,《齐风·鸡鸣》重在讽刺贪吃好睡的丈夫,有很强的视觉笑果。
根据《毛诗·鸡鸣诂训传》的解释,这个好吃懒惰的家伙是齐哀公姜不辰,也有观点认为此诗是讽刺齐襄公姜诸儿的。《鸡鸣》和《女曰鸡鸣》中的女主人公,都非常善良贤惠,天要亮了,妻子有责任催促丈夫起床,去忙营生。
所不同的是,《女曰鸡鸣》中的丈夫知道男人肩上的责任,很顺从地起床去打猎,而《鸡鸣》中的丈夫,不但不听妻子的话,反而胡搅蛮缠,和妻子打嘴仗,场面非常有趣。
还是妻子先推醒沉睡的丈夫,说:“没听到鸡在打鸣吗?大臣们都来了,你该起床上朝了。”同样遭到了丈夫的反驳,不过这位丈夫也许天生就是一个搞笑派,他的回答足以让人喷饭,把妻子气得差点背过气去。
“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你听错了,哪有什么鸡打鸣的声音,明明是一群苍蝇在嗡嗡乱叫。丈夫慵懒地回答完,然后翻过身去,又想继续睡觉。妻子有些不高兴了,苍蝇的叫声怎么能和鸡鸣一样,一定是丈夫不想起床。她告诉丈夫天色已经大亮,结果丈夫又无厘头地回了一句:“你看错了,那不是天亮,那是月亮的余光。”
第三段是丈夫的“反击”,他似乎不满妻子对他的催促,反而想让妻子再陪他多睡一会儿。“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丈夫说苍蝇的嗡嗡声非常悦耳,可以起到催眠作用,夫妻二人同入好梦。
面对这个懒丈夫,妻子被彻底激怒了。虽然诗中没有动作描写,但可以想象一下:妻子满面怒气,一把掀开被子,或者干脆一脚把丈夫踢下床。然后妻子做河东狮吼状:“还睡个屁!大臣们等不到你,都下朝回家了!你再这样懒散,会招人骂的,不知内情的还以为我是个狐狸猜,老娘可不想替你背这个黑锅!”
关于《鸡鸣》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历来争议很大。有人认为这对夫妻不是国公与妃,只是普通士人家庭,还有观点认为这对夫妻是一对偷情的野鸳鸯。其实这对夫妻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国君也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也和普通人一样,该懒的照样懒,该坏的照样坏。
《诗经》能被历代儒家奉为国学经典,不是没有道理的。《诗经》不仅是一部质量优上的文学作品,还是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百态的史料集,更重要的是拓宽了华夏先民的文学创作思路,对后世的文学、美术、音乐,乃至政治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才是《诗经》留给后人最大的价值所在。
说到《诗经》对中国美术史的影响,就不得不提及一首极为著名的诗篇,就是特别受文艺青年追捧的《诗经·秦风·蒹葭》。《蒹葭》是诗经中最富有“小资情调”的一首诗,意境之朦胧、视觉之丰富、感情之幽深,历代诗中无出其右者。有观点认为,《蒹葭》是中国朦胧诗的鼻祖,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对于《蒹葭》的解读,《毛诗》认为这是讽刺秦襄公嬴开不用贤人的,实在有些牵强。西汉的道学先生们从来不用爱情的视角来审读《诗经》,动辄讽刺这个国主,讽刺那个夫人,现代人看历史的角度与古人是有所区别的,我们更愿意从人性的角度来解读历史,对《蒹葭》同样如此。
《蒹葭》基本上被现代人看作一首让人动情的爱情诗篇,其实这也不难理解。这首诗的第一句就让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不由自主地被带入一幅动态的水墨画中,随之悲,随之喜。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翻译过来,就是:“一个初冬的清晨,长满芦苇的河边,白露点点滴滴在芦苇的叶上,晨风轻拂,芦苇摇荡,河水轻轻地流淌。有一个男人站在岸边,透着河上泛起的轻薄雾气,痴情地望着对岸,他似乎发现了一个长发飘散、素衣轻盈的女子,漂在清澈的河水上,在雾气朦胧之中,看不真切。”
这已经不是一首诗了,这是一位画者在宣纸上尽情泼洒着墨香,几笔连下,遂成千古巨制,让人爱不释手。近人王国维对这首诗推崇备至,他在《人间词话·卷上》中说过:“《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以《蒹葭》笔下之美,当之无愧。
北宋词人晏殊那首著名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就是借用了《蒹葭》的意境,但按王国维的说法,《蝶恋花》意气悲壮,不如《蒹葭》洒落轻盈。
其实,要说意境与《蒹葭》最为相似的,并不是晏殊的《蝶恋花》,而是三国第一才子曹植那篇感动千古的《洛神赋》。《洛神赋》之所以能打动人,大致有两点,一是曹植对甄洛割舍不下的感情,二是赋中缥缈朦胧的情景描写,读之仿佛置身于仙境中。河水中升腾的雾气,影衬着一位美丽女人的忧伤,打湿了诗人的心扉,也感动了读者。
虽然《蒹葭》是诗,《洛神赋》是赋,但二者的精神内核是相同的,充满了彷徨和忧伤,而且主场景都发生在河边。从曹植悲剧性的人生来推测,《蒹葭》的诗人也应该是一位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只能写诗以歌志。“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他们个人的不幸,恰恰成就了后世读者们的幸运。